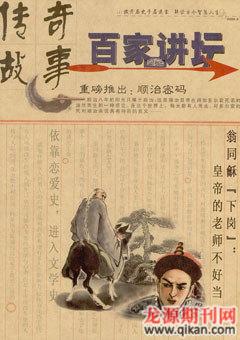戴铎:野百合为何没有春天?
王克强
雍正三年(1725年)初春的一天,晨曦微露,川陕总督衙门笼罩在一片静谧中。突然,马蹄声急,一群全副武装的御前侍卫,策马疾驰而来。为首一人,着二品锦鸡补服,手托圣旨,眼露凶光,将总督衙门门前守卫吓得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到内院禀报。
川陕总督年羹尧,在睡眼惺忪之中闻得“圣旨到”,顿时吓得汗毛直竖。因为近来雍正皇帝的一系列举动,让他频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先是严词斥责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接着更换了他属下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后又将他的爱将——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年羹尧知道,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迟早会向自己落下来,可没想到的是,竟然落得这么快!
穿戴整齐赶出去,听到的却是:“戴铎接旨!”年羹尧惊魂甫定,即命人火速把军中参议戴铎唤来!
戴铎是谁?雍正为何特旨委派钦差到年羹尧军中来提拿他?这一切的一切,还得从多年前说起。
康熙后期,从小喜欢耍心眼的戴铎,就主动投靠到了皇四子胤稹麾下。
戴铎的如意算盘是:为皇四子谋划“争储”大计,继而成为四爷倚重的心腹。一旦大功告成,奴以主贵,飞黄腾达。
那么,戴铎的政治预判来自于怎样的现实呢?原来,自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胤扔再度被废后,康熙的众多皇子就开始围绕储君之位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争夺,这场争夺持续了十多年,大量朝臣士子、文人清客蜂拥参与,都企图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较量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康熙五十二年,戴铎迫不及待地给四爷献上了“争储”秘策。他在信中说,自古以来,平庸父子容易相处,英明父子频生龃龉;弟兄寥落就相安无事,兄弟众多则纷争四起。为什么呢?原来,如果父子都很英明,那么一旦儿子不能显露自己的才华,就会被父亲鄙弃。可过分露才又会引发父亲的猜忌。而弟兄太多,各有所长,又会引发继承权之争。因此,四爷一定要做到“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笑到最后。
毫无疑问,这封秘信分析得入情入理,很有践行的价值。可是戴铎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绞尽脑汁想出的计策,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恩宠和实利,反而为以后的暴尸荒野埋下了祸根。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戴铎空有恭身事王之心、政治投机之能,却无识人心机之才。
胤祺并非毫无主见的庸主,在他的心中早就拟好了“争储”的全盘计划。一切工作正围绕该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此时此刻,他最怕的就是被他人窥破心机,以致功亏一篑。现如今,戴铎不仅窥破了,而且通过书面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留这种人在身边,岂不是引狼入室,坏己大事?
于是,胤稹立即回信,信中说,你说的虽然是金玉之言,但对我来说却并不起什么作用。你难道没看见我平日里的所作所为?我如果有争储之心,怎么会以“破尘居士”自称?怎么会终日与僧人共论佛法?怎么会致力于“鳊诗集、赏烟霞”?何况当皇帝是“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怀希图之心乎”?你如果为我着想,今后还是少说这样的话,做人要慎重些!
接到四爷的来信后,戴铎有没有品出其中的玄机呢?以他的小聪明,应该有所领悟。但是,对权力的憧憬还是让他丧失了理智。他竟然召集好友秘议“唤醒主子”的良方。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传到胤稹耳里,立即引起了胤稹的警觉与恼怒。他意识到,在争储的关键时刻,戴铎的盲动一定会节外生枝,破坏他多年经营的“持重无争”形象,导致全局被动。为了树立这一形象,胤祺努力了许多年。弟兄们之所以不到皇阿玛那儿去说老四的坏话,还不就是因为老四从来没有“以对手的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如今,这个不识相的戴铎非要彰显出四爷的进取心,这不是添乱吗?
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胤稹不等戴铎的第二条秘计出笼,就先下手为强,略施小计,将这个多嘴好事的人打发到千里之外的福建,下放锻炼去了。
那么,被“发配”到南方去的戴铎,有没有反思一下自己“蒙尘”的原因,徐图大计呢?还是没有。他的富贵情结让他的“羡权”之心不死,他还想为主子谋划,妄想抢下“助主争储”的头功。
自康熙五十五年到康熙五十七年,短短的三年间,戴铎竟然给他的主子写了十多封信,信中的内容全部都是倾诉水土不服之苦、缠绵病榻之痛,强烈请求回京效力。
胤稹当然不会让他得逞,对于这种有忠心却无大智的蠢才,胤稹自有一套拿捏的方法。其一就是万万不可留在身边,以免其自作聪明,道破天机·其二便是诱之以利,不能把他逼急,因为戴铎一旦绝望,就会狗急跳墙,同样会破坏争储大事。因此,他一方面千方百计阻止戴铎返京,另一方面又封官许愿。他在回信中说:“接你来信甚不喜欢。为何说这般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愿乎?”戴铎接到来信,读到督抚二字,顿时心花怒放,他似乎看到封疆大吏的顶戴花翎正在向自己飘来。想到这里,戴铎即使有千般怨言,也不敢在人前吐露,只能继续滞留南方,耐心等待主子所许诺的提拔机会。
可是,他似乎仍然没有看出主子“嫌他多嘴”的心思,对权势的渴望,使戴铎欲罢不能,仍然在谋划争储大计。于是,此后的两封信,一下子勾起了胤祺由“厌之”转向“杀之”的态度变化。
康熙五十六年,想当官想得发疯的戴铎,竟要求四爷把他安排成“台湾道”。还说什么一旦争储失败,奴才就可以在海上接应主子,拥四爷退守台湾。胤稹阅信大怒。以他的雄心壮志岂会愿意步郑成功的后尘!更何况,这封书信的内容一旦泄露,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俨然老四有割据之念,康熙皇帝岂能饶他!因此,胤稹在回信中将戴铎骂了个狗血喷头:“我以国士待你。而你之言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旁人一看便知,如此严厉的口吻,犹如屠刀上的寒光,直逼远在福建的戴铎之脖颈。
可戴铎偏偏忽视了这道可怕的寒光,他力挺四王爷成瘾,竟至于不分场合,不看观众,终于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康熙五十七年,大学士李光地告病假回福建调养。在一次与闽中官员的闲聊中,李光地信口说了一句:“目下诸王,八王最贤!”戴铎听了,很不以为然。竟大声说:“八王柔懦无为,不及四王聪明天纵,才德兼全,恩威并济,大有作为!”李光地听后,不置一词,微笑颔首。散席后,戴铎自以为得计,立即修书一封,一心想听四爷的表扬。
胤稹阅信后差点气晕过去。因为谁都知道戴铎是他的“藩邸旧人”,既然戴铎敢这么说,必定是秉承了主子的意愿,这无疑是泄露了他的争储之心。更何况李光地是康熙身边的红人,万一这个李学究回京跟皇父一讲,胤稹此前的一切努力、一切付出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胤稹一方面手忙脚乱地布置挽救措施,同时回信大骂:“你在外身居小任,怎敢如此大胆。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从此,找机会杀掉戴铎的意念,已经在胤稹心中扎下了根。
平心而论,戴铎对政治风向的揣摩、分析和判断是相当准确、迅捷的,其文才也是出众的,可他却被权力欲冲昏了头脑:炫耀聪明、轻狂示人、妄言无忌、恃主而骄——这一类传统知识分子最普遍的陋习终于把他送上了绝路。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皇帝突然病故,一向隐忍的胤稹终于捷足先登,成为雍正皇帝。
雍正人承大统之后,当然不会忘记屡次给他添乱的戴铎。为了防止戴铎泄露旧时机密,雍正索性把他派往年羹尧军中任职。年羹尧也是他的“藩邸旧人”,让他们互相监督,互相攻讦,正是雍正精心设计的一箭双雕的名局。
果然,年羹尧不久就弹劾戴铎,说他故意私藏皇帝秘折,时常炫耀,好像官员的升迁,全都离不开戴某的操纵,并以此来要挟同僚。同时,戴铎也检举年羹尧让全军唯其命是从,有不臣之心。
雍正期盼的正是这种局面。他可以轻松找到借口,将熟知他起家内情的老部下逐一铲除。当然事有轻重缓急,他决心先拿无足轻重的文人开刀,以解当年掣肘之恨。
雍正三年,皇帝下旨,说戴铎“行止妄乱,钻营不堪,暗入党羽,捏遣无影之谈,惑众听,坏朕名声,怨望讥议,非止一鳊”。于是,戴铎身陷囹圄,被严刑拷问“谤君之罪”。戴铎当然不服,他在公堂上历数自己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并声称“日月可鉴”。雍正怕他那张乌鸦嘴再胡说八道,赶紧将戴铎的罪名坐实为“贪污”。就这样,戴铎一下子又从“政治犯”蜕变成“经济犯”,罪名转换的速度之快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
戴铎的倔劲也上来了,对贪污罪名照样死不认账,他为自己辩解说:“在任时确有几十万钱粮不清,奴才始终不避嫌疑,为主子出力,及闻主子龙飞九五,奴才即向巡抚蔡梃说:‘恐怕西边十四爷和总督年羹尧有事,当以死自誓。倒借给其钱粮,冀用其力,此奴才之愚忠也!”戴铎死到临头还在表忠心,可雍正非要灭口,那么按照《大清律》,这些自作主张花在士兵身上的几十万钱粮,就足够让戴铎身首异处了。
这一年,尚未到秋后问斩之期,因为怕戴铎在狱中妄言,清廷秘密行刑。
行刑之日,戴铎痴痴地凝视着狱窗外土墙上的小花出神,小花像他一样,很平凡,也很顽强,不娇艳,也不精致,却能抢先体会到春天的气息。而他呢?顽强地忙碌了一生,人生的春天何在呢?想到这里,戴铎的面颊上涌现出两行浊泪……
编辑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