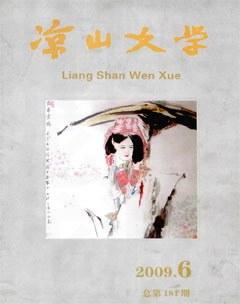吉狄兆林散文四题
牛
牛以它天生的勤劳、善良、坚韧、踏实等优秀品质,常常被赞美,被当成道德楷模,古往今来,不知玉成过多少书斋里的文人雅士的华丽词章。或许由于我经常跟活生生的牛打交道,或许由于我无论怎么努力学习也改变不了山野粗人的本性,我的笔却至今没有为它说过一句好话。曾经有张清华先生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年诗歌》,选用了我的两首诗,一首是写羊的,叫《看见一只羊打败一只羊》,说的是,羊打羊的架,也会让我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又心疼;另一首是写牛的,叫《面对一朵花的牛》,基本上就是跟牛开的玩笑,说它面对一朵花,大不了会想:吃得就吃,吃不得就不吃。那还是在我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写的。一般情况下。如果面对的是一头母牛,我会希望它尽其所能保持身体健康,保证按时怀孕,让它的主人家,比如我家,财富得到稳定增长;如果面对的是一头公牛,我会羡慕它像一个王,妻妾无数,儿孙满山,而且从来不需要负什么责,并由衷祝愿它,寿比南山;如果面对的是一头不公不母的耕牛,我会代表全人类,感谢它为人类的吃饭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并对它付出的惨重代价,真诚地表示道歉;如果面对的是一头小牛,我会勉励它,努力吃草,争取早日成为一头有用的牛。同时,不管面对的是公牛、母牛还是不公不母的耕牛,我都会习惯性地估计一番:如果它意外死亡或者被人因为某种需要而杀掉,能有多少斤肉,皮值几个钱——第一,因为我和大多数彝族人一样,比较喜欢吃牛肉;第二,因为家庭负担重,许多年来,我不得不工作之余再做点小买卖,于是跟矮郎街上见啥贩啥的小窜窜甚至会理城里的二老板们都混得很熟。总之,我从来不会像死去许多年后汉语世界里至今常常被提起的鲁迅先生那样,想做牛。而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算它的表现跟平常时间没啥两样,“笨得屙牛屎”的牛,那是怎么看都不顺眼,把鞭子抽在它身上,我根本不会要求自己先找到理由。几年前,我甚至曾经亲自结束过一头牛的命。事情的起因是,我的岳父大人去世,按照彝族传统的规定,作为女婿,我必须为此献上一头牛。结果是,由于随我奔丧的族人都是些年轻人,都没有杀牛的经验,我不得不亲自出手,把它杀掉。具体经过记忆犹新,趁今日心情不好不坏,略显夸张地,整理如下:
牛们的眼睛,鼓鼓的,看上去有点吓人。让人难免要这样想:假如它们想到了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与其任人宰割,不如团结一致,下定决心,铤而走险,拼个你死我活,凭着它们强健的体魄,谁能有效地把局面控制?奉命抓牛的两个小伙子,于是装腔作势,大声地警告它们:老实点,老实点,要不然老子对你们不客气。虽然很高兴他们尊重老辈子,让我站在一边做旁观者,但是他们的这一声“不客气”还是轻轻地刺痛了我的心。看看惊慌失措的牛们,看看身边日子过得都不怎么样的族人,点起一杆特别适合我这样的低收入小学教师抽的叶子烟,我在想:很久很久以前,那些大裤赤脚的祖先大约曾经对虎豹豺狼或者别的谁谁不客气过(至今仍有不少以此为素材的传奇故事在流传),如今的我们,种地的可能被村社干部不客气,打工的可能被老板不客气,拼命学习汉语文考成了教师或者公务员的也还是可能被领导不客气……不知不觉,我的烟抽完了,他们却还没把牛抓住。我觉得有必要给他们鼓鼓劲,于是告诉了他们,忘了出处,也不知是真是假的一点有关牛的知识:恰恰是那看上去有点吓人的眼睛把它们自己给害了,由于它的结构有问题,把见到的东西都放大了太多倍,比如人,在它们看来就是自己根本对付不了的庞然大物。不一会儿,我选定的牛,终于被抓住,并套上了绳索。是一头不再年轻却也还能生儿育女的黄母牛,一身的黄毛,干净、清爽,使它风韵犹存。它还在挣扎。紧挨着它的是它同父异母的两个兄弟,从小就都被割去了睾丸,早就成了两头安分守纪的好耕牛,明白了人要的不是它们以后,就开始低头吃草,离它稍远些的是已经有些苍老的姐姐和因为有孕在身而得以置身事外的妹妹,还有它前年生的女儿和去年生的儿子,它们好像有话要说,却又全都默默无语。“可怜的牛。”我差一点儿这样说。但没有。因为我考虑到,这种猫哭老鼠的把戏,毫无意义——无论表现得如何富有爱心,也都无法掩盖我将要用它的一条命去岳父大人的葬礼上争点面子的事实真相。
我记得,那虽然是条母牛,它的气力也不小。或许仅仅因为反感那栓在它头上的绳索,而不是感觉到了,山正青,草正绿,水也一如既往地清凉甘甜,可这一切,从今往后,它将再也看不见,吃不到,喝不着了……可它一会儿窜到路上边,一会儿窜到路下边,还是把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折腾得连声叫苦。我只好微笑着安慰他们:“将就着它一点吧,这一去它就回不来了,而我们是都还要回来的”。没想到,我的话还没说完,在一条小溪旁,一个地势很险要的地方,它却干脆就趴在地上,随便怎么拉,怎么推,怎么劝说,就是不走了。小伙子们跟我开起了玩笑,说这完全是我故意泄密造成的,要我做思想工作,请它站起来。我当然无能为力。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提高一点他们的积极性,我还是摸了摸牛头,对着它已经不那么吓人的眼睛,一本正经地说:“曾经因为勤劳勇敢而大名鼎鼎的吉狄家族的面子今天就全靠你去撑一撑了,好不好?”它当然一声不吭,面无表情。我只好提议大家就地休息休息,等它考虑考虑再说。然后,我也开始变得面无表情——尽管从小就知道,牛羊猪鸡等,都是上天赐予人类的食物,对它们的死,没必要感到愧疚,面对着具体的善良、软弱得无法形容却突然没有了明天的这一头风韵犹存的黄母牛,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过。我确实很想,从得益于诗歌的滋润而避免了漆黑一团的内心深处拿出一些带着心血的文字,说出它的沉默。
我还记得,当我们终于到达时,在一阵哔哔啵啵的烟花爆竹声中,它却仿佛被什么力量左右着似的,不再乱来,一步一步,走得那么从容不迫,使我不得不怀疑,我们头上那因为被各种飞行器不断糟蹋而不再显得神秘的天空中,是不是真的还住着我们的神。带着说不清是感激,还是敬畏的心情,我认认真真看了它一眼。随后,又听见它,放出了响亮的一声:“哞……”不知是在告诉我岳父已经上了天堂的灵魂,他最漂亮的三女儿家的礼数到了,还是在向这里的同类咨询,这是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那么多两条腿的家伙聚在一起又哭又闹。最后,在它散乱茫然的目光中,用主家提供的一把斧头的背,在它的两只角中间,稍微有点凹,毛也有点乱的部位,就那么一下,就躺下了。这让我多多少少感到有些意外,至今仍在猜想,是不是它的魂魄之前就已被生前曾经身为毕摩的岳父接走只留下了煮来吃、炒了吃或者边烧边吃,不管怎么吃,都很好吃的一身肉。
石榴花妹妹
五月之夜,一场小雨温柔地拍打着古老而又年轻的日木会理充满生机的大地,悄悄鼓励
它,用无私而伟大的母爱,抱紧了包括石榴树在内的它的正在做梦的好孩子们。雨停了。轻轻的风里,喜悦漫过石榴树身体的各个部位,使它们非常冲动,纷纷从内心深处,拿出了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告诉世界,一株有梦的石榴树,可以有多美。常常希望自己能够“比人民政府还沉得住气”(引自诗歌《携八百里凉山今夜我将梦见谁》)的彝族诗人吉狄兆林我,于次日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下,从乡下到县城的一路上,一再目睹这植物的冲动,灵魂被牵引,完全不顾自己已经四十二岁高龄——就算不是一国之主,不是一省之主,不是一县之主……至少也已经是一家之主,表情应该老谋深算,举止应该庄重严肃,说话应该掷地有声——轻浮如一只石榴花间轻轻舞动的蜻蜓,随手写下了这么一个花哨的题目。而且不仅不因此感到羞愧,反而认为很光荣。而且居然说,人世间,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都是轻浮的
扑面而来的五月的风是轻浮的。随风而动的云是轻浮的。从云里爬出又爬进的太阳是轻浮的。绕着太阳转的地球是轻浮的。绕着地球转的月亮是轻浮的。大地上奔跑的马,唱歌的牛,咩咩叫的羊,摇头晃脑的猪,甩着尾巴的狗,一只脚站着的鸡,一点辣子没得吃也要一直舔着唇的蛇,从来无盐吃却浮肿着一张小脸的青蛙……比赛着轻浮……最轻浮的。也许是蜻蜓:它们,巨大而突出的双眼占了头的大部分,视界可接近360度,整个头看上去就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想”的;它们,喜欢并且能够,在空中,完成交配;它们,生产下一代这么严肃的工作也一点不正经,被人类称为“蜻蜓点水”。
——我的意思是:许多时候,人,作为宇宙问一粒微尘,装模作样的“稳如泰山”,其实多么滑稽!讲给一只刚刚脱离母体的蜻蜓的幼虫听,它也会觉得非常可笑…它正在一心一意努力长出翅膀,为的就是能够早日轻轻地飘浮在爱的气息日益浓厚的蓝天下,尽情地展现生命本身的美,享受生命本身的快乐。
当人到中年的我,放胆向蜻蜓学习,“想”都不想,轻浮地漫步在钟鼓楼、科甲巷、元天街、石榴广场……一种受惠于石榴花,石榴花一样美丽如火的“花”的大面积存在,不仅愉悦了我的身心,而且滋润了我的灵魂。她们可能姓张,姓李,姓王,也可能姓沙马、杰克和时乍……我在心里轻轻地把她们命名为了“石榴花妹妹”。我觉得,因为她们的存在,这里的阳光多了许多明媚;因为她们的存在,这里的空气少了许多浮躁;因为她们的存在,这里的男人勤劳致富——比如经营因为得天独厚而品质优良,越来越多的人:本县人和外县人,本省人和外省人,本国人和外国人,“用”了都说好的“会理石榴”——的路上,一般不至于“穷得只剩下了钱”,连自己的灵魂也养不活,一脸油汗,一肚子屎,一条道走到黑。
随机抽取其中的一位,就叫她王美丽。虽然我们之间目前为止什么关系也没有,但我愿意,久久地站在这里,行注目礼,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还希望,明天的这个时候,在这里,再一次沐浴因她而更加明媚的阳光,呼吸因她而更加清新的空气。
脚下是古老而又年轻的日木会理,心中是美丽如火的石榴花妹妹,尽管两鬓早已出现了白发,我依然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重新诞生。
感谢诗歌
许多年前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可怜的樵夫,艰难地扛着一根大树干,呻吟着,走回他那破旧不堪的茅屋。由于过度疲劳,终于,他走不动了。他丢下树干,苦思苦想起他的苦境:常常没有面包,从来无暇歇息,为了养活一家人、供应军粮、偿还债务,他不得不终日劳作。这是多么不幸的生活!他呼唤死神。死神即刻来到了他身边,问:“你需要什么?”樵夫却回答:“我想要你帮忙把这树干放回到我的肩上。”
长期生活在会理县小黑箐乡火草尔村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地干着教书这样一份没出息的工作,工作之余,还得回家主持伺候十几亩日益贫瘠的土地,曾经有朋友误会我是有意的,是在学嵇康(魏晋名士。朋友山涛推荐其为尚书吏部郎,他却因此写下绝交书。三十九岁被司马昭杀害)。我无言以对。嵇康那种彻底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的人生主张,确实也曾让我痴迷一时。但我深知,我不是那块料。奔跑在大西南崇山峻岭间的我的祖先并没留给我拒绝名誉、地位和金钱的基因。我只是不想低三下四地获得。我把自己的这种状态,归纳成了一个词:潜伏。只是潜伏的日子,一不小心,已经许多年。
许多年来,作为一个体弱多病的女人的丈夫、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的父亲和一大群曾经因为拿不到工钱差点饿死在回家路上可还是要一次又一次地出去打工的侄儿侄女的苏日苏莫,面对的情况虽然远不如那可怜的樵夫的境遇那么糟糕,说实话,也好不了多少。所以,难免也会有走不动的时候。我呼唤的是诗神。
——因为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吉狄马加、倮伍拉且和胥勋和先生的引领下我就已经和她建立了联系。
——我请她帮忙放回到我的肩上的,有时候就真的也是一根树干(需要用它把家里的火塘烧得旺旺的);更多的时候,当然是看不见摸不着却沉甸甸的使命。
——就这样,我成了一个诗人。所以,我说——
诗歌是一种力量。
感谢她,在我一次次陷入困境时撑起我的腰,让我从未失去人格和尊严。
感谢她,陪我一直活在自己生命里,活得越来越快乐和体面。
故乡昭觉冬天的太阳
鼠年冬月的一天,曾经在从彝族自治州凉山的现任首府西昌到会理的中巴车上巧遇一个在昭觉做服装生意的会理人。他坐在我旁边,大声武气而且没完没了地与朋友通话。说的尽是钱。我有点反感。我很想问问他,钱多为什么不自己买辆车?在这样一个公共场所不顾别人的感受,那么大声地说话,是因为手机有毛病,还是因为朋友的耳朵有问题?但我没有。我听见他提到了昭党。出于对昭觉,这个在我的心理建设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心灵深处我一直把它认定为故乡的地方的与日俱增的思念,我迅速谅解了他,敬了他一支烟,并热情得有些过分地替他点燃,与他攀谈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当天早上刚从昭觉出来,过几天还要回去。我仿佛闻到了残留在他身上的故乡昭觉冬天的太阳的味道。那太阳,说来就来的一场雨雪之后终于地拨开云雾再一次深情地普照万物的太阳,因为来之不易,毫无疑问,比西昌、会理这样一些气候相对好些的地方的太阳,更可爱,更使人感恩。我的心回到了昭觉,回到了十八九岁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同着一瓶荞麦酒盘腿坐在故乡昭觉冬天的太阳下的快乐时光。我没喝酒,却好像已经醉了,在连他姓啥名谁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唐突地邀请他下车后共饮一杯。他很老练地,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只说他不喜欢喝酒,一般只在朋友劝得实在难以拒绝的时候喝上那么一点。我开始没心没肺没完没了地说话。我说,昭觉人一般都有点酒量。我就是在昭觉把酒学会的。因为在昭觉,特别是冬天的昭觉,那
个冷,不是一般的冷。穿行在不知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把它弄来的光胴胴憨戳戳地站在街道两旁的梧桐树之间,我曾经稍嫌夸张地说,昭觉的冬天,鬼都冷得出病来。我的办法就是喝酒。他说,他是一年多前才去的,他去的时候街道边已经没有那样的梧桐树。我说,昭觉人特别重朋友。我在昭觉就结识了到死也忘不了的许多好朋友。其中的董晓帆为朋友不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还花费了大量的人民币,以至于收入可观却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点积蓄也没有;罗耀君更厉害,为朋友,花掉的是自己的事业和前途;陈玉红是个敢爱敢恨敢想敢说的美女,动不动就请朋友们吃饺子;柳雪琼偏瘦,也许跟一直亲姐姐一样坚持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不少的钱照顾来自贫困家庭的穷学生——我不无关系;洪东兵虽然有肝炎,和大家一起吃饭、喝酒都需要自带碗筷,挺麻烦,但每次聚会为了让朋友们高兴总会有精彩的表现;熊英很漂亮,比我小几个月,虽然过早地结了婚,锅碗瓢盆间仍然坚持用燃烧着真情的诗歌给朋友们带来温暖和感动。尽管后来我们都先后离开了昭觉,可我们建立在与感觉共有的缘分基础上的友谊早就已经深入骨髓。所以,过去我曾经说,现在我仍然说,朋友就是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太阳。他说,那地方的人确实耿直,买东西一般不会讨价还价。我说,我是为了跳出农门,找一碗轻松些的饭吃,十七岁那年怀揣一份当时设在昭觉的凉山民族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去的昭觉,在那里呆了当时觉得太漫长现在觉得其实很短暂的四年。他说,那块地方上,现在好像是一所中学。我说,离开昭觉二十年来,虽然相距三百来公里其实也不算远,但我一直只在梦里回到过昭觉。原因是,有时候有时间却没心情,有时候有心情却又没时间。比如这次,到了西昌,很想很想顺便就过去,却没了时间。不过,我已经和一个同样从昭觉出来的现在在西吕经商的朋友约定,下个月一起回去看一看二十年后的昭觉变成了啥模样,晒一晒久违了的可爱得难以形容的故乡昭觉冬天的太阳。他说,那地方虽说是个县城,但还不如我们会理的鹿厂镇闹热,唯一的好,就是房租比较便宜。尽管他的本意中也许并不含轻视的成分,而且说的很可能也是事实,我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说,我那西昌朋友做的也是服装生意,西昌肯定比鹿厂和会理闹热,要不要请他看在咱们都和昭觉有点缘的份上,帮你联系一下?他说,西昌的房租太贵,他暂时还承受不了。我说,昭觉是咱们彝族自治州凉山的老首府,晓得不?他听出了我的不舒服,却不知道为什么,扭头看窗外,不再言语。
腊月二十六,时隔二十年后云雾缭绕中再一次走在昭觉大街上,就像在做梦。我很想联系上几个目前在昭觉工作的同学,到母校的大操场上,燃起一堆火,围着火喝点酒,就着酒再唱点八十年代的老歌,或者即兴随意地说唱上几句。我甚至想好了我的开场白:没有太阳的时候,火就是太阳,朋友就是太阳。我还估计到,总是容易感情冲动的自己有可能会哭。我对自己说,想哭,你就哭去吧。可是,从西昌陪我一起回昭觉的那个朋友反对得很坚决,他知道我的胃和肝都因为喝酒有了毛病,如果再狂饮,就可能会危及生命。像个淘气的孩子似的,我说,早知如此我应该自己一个人来。其实我的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我知道他是放下生意不说还把跟他一起住的病中的妈妈托付给妹妹坚持陪我到昭觉来的。我知道。我得到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切。我知道,面对这份天大的福,唯一能做的是,永远地记住,并默默地把同样的关切蘸满心血给他。谁也不再说话,饿着肚子,我们绕着城走了一圈。参观了现在成了昭觉民族中学的我的母校凉山民族师范学校的遗址,在曾经给我留下无数美好回忆的大操场和过街天桥上我留了影。看了罗耀君、柳雪琼、陈玉红和熊英工作过的昭觉毛纺厂的遗址。拍下了盐业公司已经被拆掉一大半即将消失的、董晓帆曾经用来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友情盛宴的那间砖木结构的小屋。简单却惬意的晚餐后,似乎知情知意的亲爱的昭觉的天,仿佛为了勾起我们的更多回忆,黄昏中,下起了毛毛雨。我们在雨中,漫步来到城东的昭觉大桥。站在虽然上了年纪,但是看上去却一点也不显老的昭觉大桥上,面对着欲断还流的昭觉河,我忍不住用我的所地土语,牛哞般唱起歌来。唱的是我自编的曾在电话里给朋友唱过,然后又一句一句翻译成汉语讲给他听过的彝语歌。大意是,人世间越来越美好,妈妈的儿子却越来越衰老……唱过歌,我忍不住给家在昭觉的曾经在这桥下的河滩上与我,还有另一个和我一样来自会理的比我高一级的同学,一起跟一大群其实也没什么深仇大恨的人打架的比我矮一级的蒋勇打了个电话。我把早就告诉过他的那个高年级同学几年前的死再一次对他讲述了一遍。杀死我们那同学的凶手,是酒。最后,蒋勇遗憾地说他人在西昌,要告诉我其他几位在昭觉的同学的电话号码。望望身边一言不发、神情严肃地向北注视着传说中曾有双舌神羊出没其间的身影模糊的木佛山的朋友,我说,算了,这次就不打扰他们了。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朋友说,走吧,再不走,要感冒了。我说,要得。我们回到城里,住进了我们离开昭觉时还没有出世的年轻的宽敞明亮的恒泰大酒店。作出不喝酒的保证,取得朋友的同意后,通过昭觉县委宣传部的阿克鸠射,约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过对一些敏感的问题有自己难得的思考和追问的散文集《昭觉的冬天》的吉布鹰升到酒店的茶楼上清谈。见了面才知道,他也是同学,比我矮两级。我们谈的内容主要是毒品的肆虐和艾滋病的蔓延对古老的彝民族构成的威胁。热情接待朋友惯了的吉布鹰升老是觉得这样的清谈难以表达心意,一再提议去吃一点烧烤喝一点酒,并告诉我,我的同班同学陈东坡、苏天浩、杨兴慧、马海公布等都在城里。虽然很想见见二十年不见的这些兄弟姐妹,和他们手拉着手,告诉他们飘游浪荡二十年的酸甜苦辣,和他们紧紧地拥抱,感受他们身上长期沐浴昭觉的阳光呼吸昭觉的空气饮用昭觉的水得以形成的高寒山区人特有的热诚和坚强,但我知道。跟大家见了面却不能开怀畅饮,将会比不见面更难受。我频频向鹰升兄弟举起茶杯。我们喝的是价廉物美且正合心意的苦荞茶。
故乡昭觉冬天静静的这一夜,无论身体还是心灵都得到了一次完全彻底的休息。早上起来,我对朋友,同时也对自己感叹道,活着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呵!拉开厚厚的窗帘,打开窗户,没想到,外面在下雪,远处的山野,近处的屋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白。我想起了年纪轻轻就选择了自杀的优秀诗人海子的诗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燃起一支粗黑的雪茄烟,我确信,虽然没交上官运和财运,但是吉狄兆林我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人,我的幸福从昨天,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吃过早餐,纷纷扬扬的小雪中,我和我的朋友又随意走了走,走着走着,我听见我的很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朋友发出了他平时很
少发出的惊喜的声音。他说的是:“看呵,太阳!”抬起头来,我差一点儿落泪。
我又看见了太阳,故乡昭觉冬天的太阳。
朋友对我说,这太阳是为你出的。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明白,我的朋友这是在鼓励我尽量把文章写像样一点。因为,来之前,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他,离开昭觉二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写昭觉却始终没写,这一次,一定要写一写,题目就叫《故乡昭觉冬天的太阳》,在来的路上,我们还就这个题目展开过讨论,只是过了解放沟后,由于天的脸色越来越黑,谁都没有再提起。我微笑着说,这是天意。我的朋友使劲点了点头,很认真的样子。这当然是在开玩笑。我再愚蠢也不会愚蠢到跟古来那些所谓真龙天子的“万岁”声中人不人鬼不鬼地死去的可怜虫似的,拿天意之类屁话糊弄别人,最后糊弄自己。我从来就知道,我是大凉山上的一棵小草:不需要有花的香,不需要有树的高,不需要被朋友或者能够成为朋友只是暂时还无缘相识的人之外的人知道;我吮吸着大地母亲的乳汁,享受着太阳父亲的温暖,远去的河流带走的是我对远方朋友日复一日的思念和祝福;春天里我绿了,是我自己要绿的,而不是让风给吹绿的;夏天里我长大了,有了寂寞和烦恼,但是我对生活仍然充满了信心;秋天里我成熟了,学会了冷静地思考,从容地表达;冬天里,某个再也不能推迟的日子,我将死去,不自豪也不悲哀地死去。
朋友的大哥就在昭觉做生意,他要去看看。我们约定下午一起回西昌。我独自来到我以为能够看到更多来自山上的父老乡亲的农贸市场。因为下雪,除了两边摆摊的商贩,来往的人很少。我的目光停留在了一群卖柴人身上。他们中大多数是妇女,只有一老一少两个男性。少年略带忧郁的眼神,让我想起自己跟他一般大时也常常从山上背东西走很远的路到城里去卖,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我突然非常想喝酒。我对自己说,少少地喝一点,应该没事。我走过去,先请他们抽烟。他们以为我是来买柴的。我赶紧告诉他们,我不买柴,我只想和他们一起喝点酒。老者坐在自己的柴堆上,轻轻地朝我笑了笑。这轻轻的一笑,让我深深地相信,虽然他的皮肤确实比较黑,虽然他很穷以至于不得不冒着雪背点柴来卖,但他的心,一定是明亮的,他的人格和尊严,是从来没有丢失的。“生命因为唯一而珍贵,生命因为顽强而精彩”——我这样想着,到小商店里买来两瓶酒,开了一瓶,放在地上,把没开的一瓶双手递给老者,一边劝一边就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我说,这一瓶请莫苏带回家去慢慢喝,那一瓶我们现在喝。说着。请老者先喝了一小口之后,自己也美美的干了一大口。感觉非常好。我把酒瓶传给少年,但我的心里非常希望他还没学会喝酒。如我所愿,少年礼貌地接住,说他还不会喝,把酒瓶传给了一位小声地说了声“让我们也来一口吧”的中年妇女。一瓶酒快喝完的时候,来了个买柴的女人,看样子,是个生活在城里的彝族女人。她问少年的那堆柴要多少钱。少年说。二十五块。她只给二十。少年有些羞涩,不知该怎么说。旁边有个卖柴的妇女替他说,二十二块吧。可那女人坚持只给二十。少年说,好吧。那女人又说,要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少年又说,好吧。目送背柴的兄弟跟在那个因为有钱而显得有些傲慢的女人身后渐行渐远,我站起来跟他们道了再见,来到出口处,想见见当年经常一起玩的住在这一段的一对双胞胎兄弟。问了五个人,终于问到了他们现在的家。不过大双几年前就已经死于吸毒,小双也因为吸毒被送去劳教还没回来。在由政府免费提供的他们的小小的家里,只住着他们的靠每月一百余元“低保”维持着生活的年迈而孤独的父亲。由于自己经济也并不宽裕,我只拿了一百元给老人,让他在即将到来的汉民族特别重视的春节随意买点什么。老人很激动。老人的激动让我很不安。不安的我,尽管知道没用,还是拿出随身带着的笔记本,撕下一页,留下了手机号码。我再一次差一点儿落泪。
告别老人,沿着一条熟悉的小路,我又来到了当年我和我的同学们经常去散步的母校背后的小海子。那个被称为小海子的池塘里已经没有水,变成了地,不知里面种了些什么。难免使人产生那么一丝“沧海桑田”之感。好在周围的民居,基本上由原来低矮的瓦板房变成了砖木结构的漂亮瓦房,又让我眼前一亮。蹲着抽完一支雪茄,又抽了一支。我想慢慢穿过这片给了我好心情的漂亮瓦房,回到街上,与我的朋友会合。哼着一支一直比较喜爱的叫做《让我看到天堂》的曲子,我却停在了其中一家的门口。因为我看见那门上用汉字写着这样一句话:“这里是尔古阿罗的家”。我的心一下子非常激动。我认定,这是一个小太阳般健康的、快乐的、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爱的、信心十足的彝族男孩写的。我想把门敲开,看看我的认定对还是不对。再一想,又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事情肯定就是这样的。我对自己说,二十年后再回来验证吧。我掏出笔记本很快写下了题为《昭觉之歌》的没什么艺术含量但感情绝对真实的一首小诗:“灿烂的阳光下/轻轻的风来啦/带着幸福来啦/带着安康来啦//美丽的月光里/轻轻的风走啦/带着我的爱走啦/带着我的祝福走啦//这里是昭觉/这里是我的家/尔古阿罗的家/健康的尔古阿罗的家/快乐的尔古阿罗的家。”在我的泪眼中,一个健康快乐的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爱的信心十足的新型彝人迅速拔地而起,浑身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我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