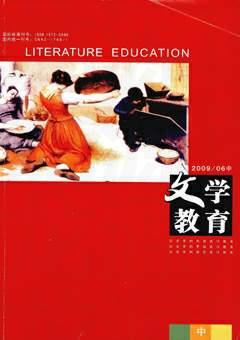刘震云新写实小说中的社会人生
李 雯
[摘要]诗性消解是刘震云《单位》和《一地鸡毛》为代表的新写实系列小说的最外在特征。而诗性消解的根本原因是主体的隐匿。知识分子是主体中的主体,主体的隐匿是知识分子身份危机的表征。这样,边缘化与市民化了的知识分子便还原为凡俗的人。刘震云的小说生动地表现了人的日常沉沦这一事实。这种沉沦不仅存在于高度官僚化的“办公室”,而且还存在于灰色的日常生活中。如此一来,就使刘震云的小说具有了浓郁的存在主义色彩。
[关键词]诗性消解;主体的隐匿;人的沉沦
以新写实主义创作著称的青年作家刘震云称得上是当代文坛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之所以为人瞩目,是因为他一反旧有的创作模式,突破了文坛上的一些浮华奢糜,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沉闷气氛,而是另辟蹊径,由看似寻常的凡人琐事发掘出深刻的社会意义,给当代文坛注入了一股活力。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被评论界公认为新写实的代表,下面就《单位》、《一地鸡毛》谈谈刘震云新写实小说中的社会人生。
一、诗性消解及其原因
刘震云在谈到他的小说《塔铺》时曾说过:“《塔铺》是我的早期作品,里面还有些温情。这不能说明别的,主要说明我对故乡还停留在浅层认识上。到了《新兵连》、《头人》认识就加深一些。”[1]这里的温情,实质上就是诗意。刘震云在《塔铺》等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套用了理想主义的传统叙事模式,因为在这一传统模式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便是这种诗意盎然的一幅幅图景。但是刘震云的转向是迅速而及时的。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文化的进一步的凡俗化与庸俗化,使得生活中的诗性消解殆尽,生活无诗成了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在这场否定性结构性大潮中刘震云也不例外,他的对诸如《塔铺》中的温情主义的清算自然就来得十分彻底了。《新兵连》直指人性的丑陋和卑琐,而《单位》和《一地鸡毛》则将这种丑陋、卑琐和现实的荒谬放大到极点。如果说,《新兵连》里尚有李上进的向指导员开黑枪,“老肥”自杀的激情的话,那么到了《单位》和《一地鸡毛》生活的平淡和琐碎,连这样的一丝激情都不复存在了,生活除了鸡毛蒜皮、婆婆妈妈、俗而又俗的尴尬和无奈便别无所有了。
诗性消解的根本原因是主体的隐匿。主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不是指人的自然状态,而是指非自然的社会存在物,是“大写的人”。因此,主体的隐匿,就是“大写的人”被凡俗的人所取代,英雄被消解成了平民,理想回到了世俗。众所周知,主体性、主体意识、人道主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中是何等光辉的字眼。“人”的发现,“大写的人”,构成新时期初期文学的重要主题。无论是“班主任”还是“犯人”李铜钟;无论是陆文婷,还是青年知识分子“研究生”[2],他们都有着崇高的英雄气质。然而“85新潮”(20世纪)之后,“大写的人”颓然倒地,这正预示着主体的隐匿,而主体的隐匿,则标志着我们时代的神性之光无可挽回地黯然失色。
一切不要急,耐心就能等到共产主义。倒是使人不耐心的,是些馊豆腐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3]
是的,“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于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小林夫妇是如何一步步放弃作为启蒙者的优越感而日益沉沦为卑微可怜猥琐的凡俗市民的。这里体现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危机。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就是一个“遭威胁”的身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一直处在政治权力话语的压抑下,但经济上相对尚可优越。但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变得相对贫困化,他们的付出与所得不成比例。经济地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于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成了一个沦为底层平民的身份,但知识分子又具有内在矛盾性和分裂的人格。这主要是与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文化因素的多重作用有关。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因素中一直是作为“读书人”的身份而受到潜在的承认和尊崇;而在主导文化因素中亦有虚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新崛起的文化因素中,而是倍受歧视,而中国文化的实质是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文化的核心是实用理性。“读书人”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为这“读书人”可以变成“官”;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是因为这有知识的人才对官有用;而受到歧视则是因为知识分子既无权又无钱。这就造成了知识潜在的有用和实际的无用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造成知识分子自我幻想中的高高在上和实际生活中的穷酸潦倒的状况。这样,清高与穷酸,有价值与无价值,重视与轻视都集于一身,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在新写实小说,特别是刘震云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我们通读《单位》和《一地鸡毛》时,在“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的貌似肯定的声音里,仍包含着多种声音,既有隐含作者愤懑的不甘心的叹息,也有社会话语的迫人就范。在此我们看到了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隐匿和市民化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行为。那么,放弃启蒙身份的知识分子在融入民间之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二、灰色的日常生活及其杀伤力
如果说《单位》写了“单位”这种权力密集型官僚网络,在对人的异化和使其迅速沉沦于非人状态的游戏规则的话,那么《一地鸡毛》则将这一规则推广到底层人琐碎的日常生活领域,看看这一无所不在的权力游戏规则是如何运作和发挥作用的。灰色是一种无生气、无特点的颜色,这就是我们在刘震云《新兵连》以后的作品里再也看不到《塔铺》里那些“红”、“金黄”等诸种生动颜色的原因,也可以说刘震云此后的作品里,极少用有颜色的词汇,这是一种无色彩的生活,所以从情绪上看,这一颜色只能是灰色。
灰色的日常生活是从馊豆腐开始的。注定了它的凡俗与卑琐。因而刘震云的作品都没有戏剧化的故事情节,没有高潮,它的平淡流水账式的日常记录,成了一个个俗得不能再俗,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事件的“堆砌”。但刘震云的高明之处也许正在于,透过这些一件件俗事的“堆砌”,使我们视而不见,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有了“意义”,它所引发的我们心灵的“震惊”也许并不亚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它使我们看清了日常生活的杀伤力,它是如何令人一步一步地步入沉沦,异化为“非我”的。
小林与妻子两个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有过远大的志向、宏伟的理想,有过一番事业心,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
而这正是日常生活游戏规则的伎俩。你想调动就得送礼找关系,然而你的礼都送不进去,说明你仍然未将生活的这套游戏规则弄娴熟。你还得学着点混。“小李白”是一个混得“较好”的榜样,他从一个写诗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卖板鸭的个体户,每天大把大把的金钱进手,的确令小林开了眼界。但是“小李白”的这一天壤之别的变化,既突兀又合情理,因为“小李白”看透了人生,正像他说的:
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
这个反问不仅是针对小林的,也是针对我们的。“我们”难道不都是在“混”吗?然而反过来想,“小李白”由机关到公司,由公司到个体,他虽然摆脱了体制化的桎梏,但他却逃不出另一个专制,即金钱。金钱淹没了“小李白”的灵气、才气、志向。那么“小李白”还是“小李白”吗?
小林不能潇洒说明了小林内心深处仍存有一丝渴望拯救的幻想,因而他注定要在尴尬的处境中挣扎。老婆坐上了班车是沾了厂长小姨的光,女儿入托是跟人陪读,尽管小林心里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
但是事情的龌龊在于:老婆哭后,小林安慰一番,第二天孩子照样得去给人家当陪读。在好的幼儿园当陪读,也比在差的幼儿园胡混强啊!就像蹭人家小姨子的班车,也比挤公共汽车强一样。当天夜里,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眼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
“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但他的声音不大,怕把老婆弄醒。
巨大的辛酸和无奈,由反讽的手法写出,就显得充满了喜剧色彩。令人忍俊不禁,但分明又苦从中来,笑过之后只想哭了。
小林沉沦的道路也许是痛苦的。他的挣扎与无可奈何,表现在由一开始的给人送礼到最终的收别人的礼,由一开始的不安到最终的坦然,是他内心矛盾的巨大反映。本来举手之劳的事,他却收了查水表的瘸腿老头的微波炉。当吃着微波炉烤的鸡,喝着啤酒,小林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其实世界上的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6]按“道理”办事,就是顺从社会的权力游戏规则,完全泯灭自我个性特征,成为非人。小说的结尾,小林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鸦鸦无边无际人群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
这个梦,实际上表现了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性和荒谬虚无的人生。如蚂蚁一般的人群难道不是也如“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一样毫无价值和意义吗?老师的死讯尽管让小林难受了一天,但大白菜冲淡了小林的忏悔感。“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至此,小林完成了自己的沉沦与异化。“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7]
刘震云的小说为我们充分展示了广阔的社会时空,展示了纷繁的社会百态,真诚的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他的创作始终贯串一条主线那就是抗议物资对于精神、权力对于尊严的威胁与摧残,特别是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对其生存状态的不满与反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刘震云的新写实小说所展现的社会人生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生,一个习以为常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活世界,从而使其小说蒙上了浓郁的存在主义色彩,具有了区别于现实主义理性化特征的现代性的哲学文化深度。
参考文献:
[1]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J].文艺争鸣,1992,(1).
[2]分别出自:刘心武《班主任》、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谌容《人到中年》,张承志《北方的河》.
[3]刘震云:《单位》,《刘震云自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4]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官人》,《刘震云自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3).
[6][7]刘震云:《一地鸡毛》,《刘震云自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李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