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诞子礼俗描写
刘燕歌
亘古至今,对家族兴旺的期盼,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读《诗经》时,便可以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企盼心理,如“干禄百福,子孙千亿”(《大雅·假乐》)、“克襁克祀,以弗无子”(《大雅·生民》)等,都是希求子孙昌盛、瓜瓞绵绵的祈祝之词。古代隆重热闹的诞子礼俗便是这一文化心理的重要体现。
诞子庆贺之风在唐朝始盛,有洗儿礼、满月礼等项目,史书中多有记载,现今研究成果也颇丰富。综观之,已有研究多取自正史、笔记资料,这些史料的记载大多较为概括,只点明主要仪式,或是以仪式为背景叙述一些宫廷轶闻趣事,到底礼俗活动的细节如何,则语焉不详。但在题材丰富的《全唐诗》中有十余首诗作,则较详细地描绘了当时诞子庆贺的情景,为我们了解古人生活细节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民俗资料。本文通过对相关诗歌作品的钩稽分析,意在使唐代诞子礼俗的画面与唐人生活世界的细节更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并结合出土文献资料对所涉习俗略加考释,希冀可以在已有的借助典籍与笔记所进行的研究之外,起到弥补罅隙的作用。
唐代文人遇添丁之喜,常欣然命笔,遂留下了多篇为皇室或官宦之家诞子之喜而写的酬贺之作,表达了对婴孩的怜爱、誉美、期许之情,亦展现了唐代诞子礼俗的丰富内容。这些作品的描写至少为我们展示了诞子礼俗中的如下几项细节:
一、洗浴。
唐代有三日洗儿礼,主要是为婴儿洗浴,史料中记载颇详,诗歌中也有生动描写。皇室子女降生,除洗浴外,还要赏赐洗儿钱。
日高殿里有香烟,万岁声长动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王建:(《宫词》)
从诗歌来看,洗儿钱主要是赏赐给执行洗浴仪式的宫女们的。洗儿钱具体包括的内容,诗中并未详写,我们从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六“洗儿金钱”条可略窥其大端。据文中引韩偓《金銮密记》可知,唐昭宗时,洗儿钱即有“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即银片)坐子、金银铤子(即锭子)”等名目,宋代此风更奢,“自金币之外,洗儿钱果,动以数十合,极其珍巧”,具体有“金银、犀象(犀角、象牙)、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及铸金银为花果”(《容斋随笔》四笔卷六)等,由此可知唐宋时洗儿钱一般包括三类:以金银制作的精巧华贵花果、以金银制作的珍奇日用器物装饰品、金银钱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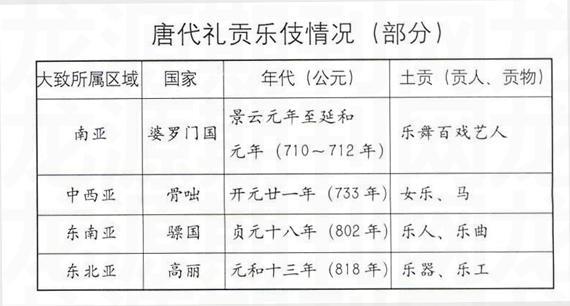
一般官宦之家诞子后只有洗浴习俗,未见提及洗儿钱。白居易诗歌描写了唐代官宦之家在洗儿礼中为婴孩洗浴的情景,其诗云:
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凤雏。还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满月即成珠。(白居易:《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诗见示,因以二绝句和之》)
玉茅珠颗小男儿,罗荐兰汤浴罢时。苤蔬春来盈女手,梧桐老去长孙枝。(白居易:《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诗中以“玉芽”(形容嫩笋)、“珠颗”(据南朝梁-任叻《述异记》卷上载:“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谓之珠儿。”)的比喻使沐浴于香水中的婴儿可爱的娇态尽现眼前。洗浴时要用以兰草制成的芳香之水(即诗中之“香水”、“兰汤”)。以植物的芳香之水沐浴是古代一种普遍的习俗,为人所熟知的是古人五月五日以兰汤沐浴之习尚,宋代陈敬《陈氏香谱》即云:“五月五日以兰汤沐浴。”相传有驱病祛邪之奇效。

白诗的描写发人联想:呱呱在抱的婴儿也许还未睁开眼睛,便被放入芳香充溢的温水中,柔滑娇嫩的肌肤接受轻轻的爱抚,在一片祝福声中,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洗礼。
二、裹襁褓、围绣襦。
嘉客会初筵,宜时魄再圆。众皆含笑戏,谁不点颐怜。绣被花堪摘,罗绷(绷即襁褓)色欲妍。将雏有旧曲,还入武城弦。(严维:《咏孩子》)
玉女贵妃生,娶规始发声。金盆浴未了,绷子绣初成。翡翠雕芳缛,真珠帖小缨。何时学健步,半取落花轻。(张谔:《三日岐王宅》)
沐浴完后,一般用襁褓将婴儿裹起来。从诗中“绣被花堪摘,罗绷色欲妍”的细腻描绘可以看出,小儿的褓被做工极讲究,上有手工刺绣成的鲜艳夺目的花朵。除裹襁褓外,还要戴“襦”,相当于现今系于小儿颈下之围嘴。在白居易《阿崔》诗中有“香绷小绣襦”之句,杜甫《别李义》诗也有“忆昔初见时,小襦绣芳荪”的描写,可见这种小襦也是刺绣精美、颜色鲜丽的。在小儿衣物方面准备得如此精致,大概是希望孩子在人生的起始便光彩照人。
三、剃胎发、以酥点肤。
白居易《阿崔》诗中描写爱子阿崔初生时的情景日:
兰入前春梦,桑悬昨日弧。里闾多庆贺,亲戚共欢娱。腻剃新胎发,香绷小绣襦。玉茅开手爪,酥颗点肌肤。弓冶将传汝,琴书勿坠吾。未能知寿天,何暇虑贤愚。乳气初离壳,啼声渐变雏。何时能反哺,供养白头乌?
白居易58岁得子阿崔,其喜悦、感慨、爱怜之情在诗中尽情流露。《唐宋诗醇》卷二五评此诗日:“写小儿初生,端详入细。一结喜极,不觉虑其将来;软语心酸,逼真老人情景。此种自让香山独步。”诗歌不但情真意切,而且还描写了婴孩初生的几种礼俗。“腻剃新胎发”一句展示了为小儿剃掉柔软粘腻之胎发的情景,但略去了细节。南宋吴泳《鹤林集》卷三九收有《公主剃胎发祝寿文》,可以使我们看到古代剃胎发礼俗较详细的情景:
伏以青炜熙和,绛河烂明,宝婺炳秀,蕊宫毓精。帝子降兮琼圃,天孙下兮玉京。如葬吐英,如兰茁芽。菀春柳其方荑,粲裱桃其始华。南薰入弦,月良日吉。夏簟清安,夜衣芬苾。宝刀具,瑶席张。涤犀钱兮泛璇果,进鞶悦兮沐兰汤。云鬓兮削青,螓首兮凝绿。阿保抱持,傅姆延祝。宜君宜王兮万斯年,宜兄宜弟兮百其禄。更祈罩讦,共燕戬谷。
文中展示了剃发用具的准备,以及洒钱果、兰汤沐浴、剃发、祝祷的全过程,是古代少见的对于剃胎发习俗的描写,可与白诗合而观之,以补其缺略。
其次,白诗中有“玉芽开手爪,酥颗点肌肤”一句。前句容易理解,指小儿的小手张开,如玉芽般的嫩笋,光滑娇嫩。后句则莫知所名。据孟晖《酥花入座颇欺梅))一文考释,“酥”乃是一种乳油状的食品,唐代宫廷中有将酥点成花朵状作为食品装饰的作法,王建诗中即有“一样金盘五千面,红酥点出牡丹花”(《宫词一百首》)的描写,红酥是在原本白色的酥乳中加上红色染成的。唐人也称化妆为“点妆”,当与点酥手法有类似之处。笔者推测,白诗中“酥颗点肌肤”一句,很有可能是指用红酥在婴儿面部肌肤上点出形状。有两则材料或可有助于这一推测。一为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一种民间习俗:“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厌疾。”另一则是在河南考古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考证文物年代为1l世纪晚期到12世纪初)中,有一些据考证是家供之物或儿童玩具的襁褓俑,婴儿身着红色襁褓,额间、眉顶、眼侧常有红色圆点或月牙形花钿点缀(望野:《河南中部以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文物》2006年第2期)。唐人以酥点婴儿肌肤及后代在婴儿面部装饰以红色花钿的习惯可能与南朝民间禳疾法有一脉相承之处。
四、乞名、汤饼宴。
婴儿初生,要由受人尊敬的长者为孩子取名,称“乞名”。白居易诗中就有“嘉名称道保,乞姓号崔儿”(《和微之道保生三日》)的记述。白居易又有《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一诗:“新年逢吉日,满月乞名时。桂燎熏花果,兰汤洗玉肌。”由寺可知,也有将乞名、沐浴一起放在婴儿满月时进行的情况。
此外,婴儿初生之喜宴有食汤饼之俗。刘禹锡《送张盥赴举》诗云:
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
作者在诗中回忆了曩时躬逢张盥初生之盛宴,宾客成集食汤饼的情景。乞名、宴客习俗在已有研究中涉猎颇多,此处略言之,不复赘述。
除对婴儿初生礼俗的描写外,唐诗中对满月、生日、啐日(满一周岁)情景也有表现。沈俭期《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诗描写了“咏歌麟趾合,箫管凤雏来”的歌吹宴乐场景;包何《相里使君第七男生日》在“今日悬弧宴乐酣”的喜庆气氛中以“荀氏八龙”、“桓山四凤”高赞使君家中的凤雏麟子。也有的诗歌不涉礼俗,注重描写婴儿的姿容情态。如孟郊《子庆诗》以“小小豫章甲,纤纤玉树姿。人来唯仰乳,母抱未知慈”来描写婴儿的不凡之貌与娇痴吮乳之态;白居易《金銮子啐日》中写幼女“生来始周岁,学坐未能言”的娇弱柔软之态等,都是唐诗中描写婴幼儿的佳作。
唐诗中的诞子礼俗描写充满温情,流溢出抱子弄孙的愉悦,从一个侧面将笔触深入到唐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现代生活中,诸如洗浴、剃胎发等习俗仍然保留着,唐诗的描写使现时人得以将古今之生活空间连通起来,为生活史、礼仪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