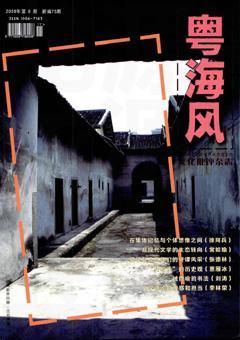“反智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表现
曹学聪
“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译为“反智主义”,该名词因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2)一书而走红,此书出版后影响甚大,两年后即获新闻大奖——普利策奖,继而在美国掀起了霍夫斯塔特热。按余英时的解释,“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余氏认为“反智论”有两种情况:一是“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即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即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如余英时所言,两者实则无本质区别。[1]无论是霍夫斯塔特还是余英时所谈及的“反智主义”,都是将之纳入到复杂的文化范畴里,从而涉及政治、历史、思想、社会等各个层面。本文旨从文学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反智主义的表现作一梳理,并简单分析其产生的缘由。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述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反智论”的书写。具体来说在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等各个形态上有不同的表现。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乡土”无疑是一个不能遗忘的母题。从20年代肇始于鲁迅的“乡土文学”,到沈从文那一系列悠长而又隽永的“田园牧歌”,再到80年代赢得广大读者的汪曾祺那独特且极富“民间性”的写作,尽管他们书写的角度各异,但不可否认,“乡村”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作为题材和表现对象的重要性,几乎要超过城市。如果说鲁迅的“乡土文学”是在于批判国民性,那沈从文的“田园牧歌”则着力于远离现代城市文明的喧嚣,建造不曾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着“人性”。沈从文对现代性的反思、质疑是通过在乡村与城市、自然与文明的二元比照中显现的。正如他所说:“请你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段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应在作品里。”[2]在这种城乡的对比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对启蒙运动的反思甚至对历史进化论也不信任。这是审美现代性层面上的“反智主义”,从《绅士的太太》中对上流社会堕落的鄙视,到《薄寒》里对都市文明的否定,再到《有学问的人》、《八骏图》中对知识分子虚伪、卑琐心理的揶揄,都明显表露出这种反智论调。
汪曾祺曾坦言受到过鲁迅、废名的影响。[3]但在表现乡土民俗方面,其创作风格主要得益于沈从文,作为沈的学生,无论是在为人抑或为文等方面都受其师很大影响。汪曾祺在创作中,重点将乡土风情纳入到审美创造中,从而远离政治背景,淡化时代环境,沈从文的语言、意境、心态等等无不在汪曾祺身上再现。但更重要的是,沈从文远离城市文明、回归乡土民间的“反智”倾向也流淌在汪曾祺的笔尖,“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自然会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保持一些传统品德,对于建设精神文明,是有好处的”。[4]虽然汪曾祺没有明确指出反对精英文化,也没有像沈从文那样明确地批判现代文明,但其对民间文化的肯定与褒扬,并用对“乡土”写作的执著追求在实践上与“反智”论调有契合之处。在现代生活中,“人”已被工具理性异化,不再自由。汪曾祺在创作中把追求生命自由的笔端伸向了民间,在那里他看到了现代都市中难觅的“和谐”,这里“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纯朴,不受任何的清规戒律的束缚,正所谓‘饥来便食,困来便眠”。就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这个桃花源中诸多的人物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其情感表露非常直接而且质朴,他们虽然都是凡夫俗子,却没有任何奸猾、恶意,众多的人物之间的朴素自然的爱意组成了洋溢着生之快乐的生存空间”。[5]
分析汪曾祺的回归民间写作的原因,可以看出汪曾祺一直都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及“再使风俗淳”的重要性,汪曾祺对民俗文学有着特殊的偏爱,甚至说过“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6]这样不无偏激的话。在喧嚣异质的现代都市文明里,在日益紧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专制控制下,汪曾祺在前现代的淳朴乡村找到了渴求已久的自由生命、完美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真实的人性;在自己魂系的乡土中构建着理想的世外桃源。
在现代中国,“民间”、“大众”,作为特定的能指概念,其政治意义远甚于社会学内涵,与今天在商业运作下的“大众文化”也有着不同的含义。早在“五四”时期,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口号就已喊遍中国,知识分子已有明显的反智论迹象,陈独秀就认为“只有做工的最有用最贵重。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7]1919年在《平民教育》上有一篇文章《教育的错误》谈及:“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这一种无用的人纵然受了教育,在社会上依然无用……再翻回头来,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的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的分子。”[8]30年代,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并控制的左翼作家们,号召到底层去、到民间去、与大众结合,认为应该用大众口语作为创作的语言,并且认为真正的道德与智慧来自底层民众。当时的文艺大众化使得文艺走向了宣传、鼓吹,从而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的功利色彩。40年代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毛泽东认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 脚上有牛屎, 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9]文艺作为政治文化语境下的产物,“知识分子”与“智性”本身已经全然遭到否定。这个层面上的“反智”,究其根源在于中国知识分子潜意识当中浸染的儒家民本思想在俄国“民粹”思想的影响下,再加上本身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从而在强硬的政治意识形态面前容易丧失自己,逐渐从精英滑向底层,由批判转为颂扬。
同以审美现代性批判启蒙现代性的纯文学和在政治意识形态下书写的严肃文学一样,通俗文学也有着“反智论”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注重德性,回归纯朴自然的本性。这一点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突出表现。不少论者都曾提及,金庸凡十五部作品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从早期的陈家洛、袁承志,到郭靖、杨过,再到狄云、石破天,可以看出金庸认为“知识”有碍真正的“侠”的塑造,所以金庸让他的主人公们一个个在远离正统教育的地方成长,蒙古大漠之郭靖、流浪市井之杨过、海外极地之张无忌,闭塞乡村之狄云、石破天……正因为他们是没有受到“正统知识”污染的璞玉,故而他们的人格较之那些所谓的中原“侠义之士”才更健全更理想。
倪匡评价《连城诀》是一部“坏书”,“写尽了天下各色人等的‘坏”。[10]的确,金庸对世俗文化中的虚伪、贪婪、卑鄙、阴谋、残忍作了彻底的暴露,这一切对刚从乡下走出来的不谙世事、无知无识的狄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个无知胜有知的极端例子,《侠客行》中的狗杂种不仅没有知识、毫无欲求,甚至连自己的姓名家世都没有,但金庸偏偏就让目不识丁的他破解了几十年来两位岛主和中原无数“武学专家”都不能参透的至上武学。看似意外,实在情理之中,金庸在“后记”中解释到:“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民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因此强调‘无着、‘无住、‘无作、‘无愿。邪见固然不可有,正见亦不可有。”[11]金庸对“智性”及“知识分子”的价值的否定,来自于对禅宗和道家精神的领会。禅机所谓“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要真正悟会要义,须不为“所知障”才行。道家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唯有“绝巧弃利”,“绝圣弃智”,道德方能臻于理想完美。
通俗文学由于其通俗性与大众化,受市场取向的影响,适应大众的消遣娱乐需要,从而在内容上多浅显明白,反精英立场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了,当然易于在大众中流行。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肯定大众艺术具有民主性的一面,并认为大众文化可以增进人们的民主意识,进而能影响社会变革。本雅明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反对精英文化,肯定大众艺术的。“反智”倾向显而易见。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从“五四”伊始直到新时期,在文学的三种形态上均有不同程度及性质的“反智主义”表现。中国的“反智主义”作为话语资源直接来源是霍氏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而深层根源是来自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中以禅宗及道家尤为明显。如果对“反智主义”稍加追究,即会发现,对“知识”或“知识分子”的反对并非来自其对面平民或大众,而是精英知识分子自身制造的一种质疑、批判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是知识分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代之言说的一种态度。作为审美现代性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反智论,对在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异化的今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当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渐失,迎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屈身仰视底层民众来贬斥自身及自身拥有的“智性”,这种带民粹思想的“反智论”破坏性很强。由此看来,对“反智论”在不同文学形态上的表现作具体分析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选自《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年,第2页。
[2] 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0页。
[3] 汪曾祺 《谈风格》,选自《晚翠文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2—103页。
[4] 汪曾祺《菰蒲深处》,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页。
[5]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6]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页。
[7]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见《独秀文存》,芜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0页。
[8]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0页。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51页。
[10] 倪匡《我看金庸小说》,收入《金庸其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11] 金庸《侠客行·后记》,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