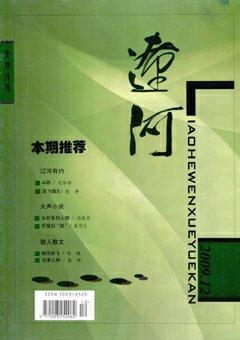往事几种
秦 辉
童年琐忆
小时候我长得很丑,当然,现在也俊不到哪里去。但相比而言,小时候更丑些。
小吊眼,大耳朵,南瓜脸,厚嘴唇。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有段时间还染上了吐唾沫的毛病。
其实,这些也不全是先天带来,也有后天造成的,比如小吊眼。因为那时经常束一个马尾巴,且束得紧,把眼角都拉高了。但据姥姥说,吊眼也有好处,演戏不用画眼。姥姥总能把我伤口上的盐不露声色地抚去然后换成糖。所以,我一直爱她,她活着时我用零食孝敬她,她死后我用泪水,怀念她。
还有南瓜脸,小时候我比较能吃,既然能吃,肯定会胖,这种胖也能胖在脸上。我又爱玩,爱领着一帮子人胡跑,事情就显而易见了。一跑那脸上的肉就向下垂吧,像吃过饭就去运动容易得胃下垂一样的,所以肉都淤积在了脸的下部。也就是在鼻子以下,下巴以上,成了南瓜脸是自然的事。
再比如吐唾沫我认为是因为条件反射造成的,看到有脏的东西就觉得像到了自己嘴里,不吐不快。所幸的是,这个毛病没多长时间就改掉了,没影响到后来找个体面的工作和称心的对象。
总而言之吧,小时候的我不是个让人喜欢的孩子,是只丑小鸭。
那种变不成天鹅的丑小鸭。
学校离家很近,每天我都背着妈妈用花布头拼成的书包摸黑去上学,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是与二年级在一个教室。课桌是用土坯垒的,椅子是用木板搭的。下课后男生相互用土疙瘩投掷并以此为乐,女生则玩一些叫什么贴饼子打墙站折软腰的在我看来既羡慕又惊讶的高难度的肢体游戏。她们玩时我就在一边看,一边看一边默念,快了,快了……果然,一会儿就像散了的黄瓜架一样东倒西歪了,我就跺着脚哈哈大笑,然后心满意足地慢步踱回到教室。
去教室有两条路,一条是西边的顺路,但要经过男生厕所。厕所没有门,里面的情形一览无余,我们经过时,都要用手遮了脸,也有忘了遮的,就挨女生骂或是男生的嚷。这个情形一直到我小学毕业,也就是说我们女生整整遮了五年的脸。以至后来上初中,每每看到厕所前那个大大的“男”字,我都会歪过脸去。
还有一条路是从南边的小胡同转过来,那条路较远。其实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小胡同以前死过人,喝药死的。我们乡下,但凡跳河跳井喝药上吊这些非正常死亡的都叫做屈死,这种人就叫屈死鬼。大人说屈死鬼都拿替身,怪吓人的。听说有人曾在小胡同的墙壁上看到过一只黑手,所以,那条路是轻易不敢走的,除非有大人陪伴或是一群孩子咋咋呼呼着跑过去。
这样的传说在我们学校是很多的,比如靠近厕所的四年级,就说有东西。这个东西像球一样地跳,就在中间从后数第三排的座位上。那个年级有个大胆的女生看到后,上前冲着那东西吐了两口唾沫,那东西就消失了。
当时,我吐唾沫的毛病早改掉了,我还为此后悔了好长时间,早知唾沫有此妙用,打死我,我也不改。
夏天最爱玩的是一种叫砸杏核的游戏,就是把杏核放在鞋底上,用另一个去砸,砸到地下几个就赢几个。下学后放下书包就去街上捡杏核,最盼望的是赶集时,有很多人买了杏后就三三两两地坐在阴凉处吃起来。
记得我与几个伙伴经常站在卖杏的摊位前,看到有买的就跟在人家后面,如果是坐下来吃,我们就蹲在一边。眼睛不眨地望着他们的嘴。有一次,一个人用了极其怜悯的目光看我们,随手摸出几个杏子,说,拿去吃吧,拿去吃吧。我们一手打下,谁稀罕,我们要的是核!
后来还玩过鞭炮壳的游戏,还有用泥做挖捂,挖出窝摔出洞用泥捂,我想应该是这两个字吧。泥最好是红泥,啪啪摔上几下,然后捏捏抹抹做成了一个脸盆的形状,让别人看看,“有眼没眼?”“没眼!”然后站起身来,高抬手重落地,“啪”,盆底开花,花开得越大补的泥越多。收工时把赢的泥搬回家,做成泥塑,等别人拿柴禾来换。
那时候,我们家烧火做饭的引柴从来不用去拾,全是我赢回来的!
对于童年,有多少种记忆就有多少种游戏,我是个内向的孩子,除了游戏之外还有孤僻的一面。
我听到过妈妈跟别人提我时说到一个词,古怪。那时并不知这是个什么意思,是表扬称赞还是批评指责是贬是褒是中性。只是觉得很多想法和做法自己跟别个不同,我喜欢看书,喜欢独处,喜欢收藏,喜欢坐在海洋码头上看夕阳中的渔船,喜欢光着脚丫在浅水里行走然后捉一些小毛蟹,喜欢躲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为一个眼神哭泣或是为一个笑容欣喜,喜欢早早地趴在被窝上在油灯下听姥姥讲故事,我拥有这些喜欢时,只是个孩子。
也许,我该感谢这些喜欢,是这些喜欢让我学会思考,让我在浮躁中能保持一颗还算是清醒和超然的心,是这些喜欢给了我内敛沉默的性格,让我能静静地躲在一个角落任意涂抹自己的世界,是这些喜欢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奇遇,给我的生活添上一笔笔温暖而又亮丽的色彩。
是的,我应该感谢这些孩子时的与众不同,这些喜欢。时光倏忽过去,这一晃就从儿时到了中年,曾经的童年成了往昔。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回忆了。
想起一只猫
近来,常常无端地想起童年,想起那个生我养我的小镇以及在那生活过的人和发生过的故事。
童年往往是与三二玩伴一只小动物几类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记得那时的玩伴是供销社院里的几个孩子,每天放学后就领着她们到大街上,收集冰糕棒点火或捡碎玻璃卖给收购站换五六分钱,再就是大集散后去拾削下来的甘蔗根,节长的寻个没人的地儿分着吃了,短的晒干当成烧火柴。而小动物,我家曾有过一只狗,很忠实也很温顺,但被车轧死后再也没有养过,所以跟狗倒没有过撕扯。这以后,有人送了一只猫,就是这只猫成了我童年唯一对动物的记忆了。
小时候的家乡是一个水陆码头,我们家承包了供销社的招待所,那时常年有贩海货的,其中有个临沂的老白,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住在这里。老白很瘦,门牙缺了一颗,再加上他的外地腔调,说起话来怪里怪气的,但时间长了,也懂得了他的方言。
每次从海洋码头回来后,老白就蹲在门口掏出烟斗点上,先滋的吸上一大口,然后高声喊过我们姐弟几个,斜着眼问“你们商量好没有?到底谁跟我走呢?”每次听了,我们都胆战心惊地望望老白的大重车后驮的那个大号竹筐,因为老白说他是光棍一根,想认我们其中一个做他的孩子放在大筐里带走呢。
一次,老白风尘仆仆地来到已是掌灯时分,他支好车便冲我们招手,“过来,过来,给你们带好耍的来了!”我和姐姐掀开筐盖一看,是只小猫!那时猫在我们那还是稀罕物,不然,老白也不会那么大老远地带一只猫来了。
猫是黑白相间的,眼亮晶晶,脸上带着尘色,一脸的好奇与惊喜。老白说它只有二个月大,它怯怯地一边向上望一边躲着我们摸向它的手。
晚上,我把它放在了炕上的一只箱子里,睡梦中觉得脚痒痒地疼,睁开眼却是它在用小爪拨弄我露在外面的脚趾。我忙把它抱进了我的被窝,温温软软地舒服极了。
它成了我们的暖手炉,我们姐弟为争夺揽着它的权利常常是打得不可开交。
记得有一次,我下晚自习后看到猫不在这里,姥姥说你弟弟抱去揽了,于是我叫开关了的门,掀开睡了的弟弟的被,不顾猫的怪叫二话不说抱了就走。而弟弟更厉害,硬是又穿好衣服在门外又踢又叫,又哭又喊,不抱回誓不罢休的样子,那只猫在我俩的手中哀鸣声声,怪叫连连,气得爸妈直要明个儿起早就扔了去。
因为猫是从外地带来的,我们常常叫它外地猫,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但这个猫却念不好经也根本不念经,把盘内的饭食舔干净后,就洗冼脸擦擦脚找个角落睡觉去了。睡得舒服了,常常是身子摊开,一只前脚伸到脖下,样子十分懒散,完全不是一个勤劳的捕鼠能手的样子。
这只猫在我们的目光中走过了四年,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关于它的小插曲,总之它从一个小可爱长成了一只老世故,从一个小家碧玉变成了一个丰满肥硕的中年以上。
它开始夜不归宿了,而且样子有点笨重,妈妈说它可能是快死了,据说猫有这样的习性,知道自己要死时,就会自己到野地里去,绝不会死在主人家里。
一个晚自习,猫果然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我很伤心,独自躲在猫卧过的地方哭起来,我觉得当时还在心里默念了一些怀念它的文字,我想那应该是祭文的雏形了。
那只猫从那以后就没有回来,妈妈说它死了,但街上有人说,在村东看到过它。不管如何,我宁愿相信它已经死了而不是另投他人,因为那是猫的归宿,就像人一样,早晚会走上那条路的,必然的事就用不着难过。而在别人家过活就不同了,我们家每个人都对得住它,它没有理由背叛。
那只猫没了后,我家又养过几只,但没引起我的兴趣,我想,对猫的喜欢已经随着那只猫的出走而终结了。
直到后来,对猫不但不喜欢反而有点讨厌和害怕了。
工作后,一个同事从老家带了只猫来,那时住单身宿舍,常有老鼠光顾也为打发寂寞,就要下了,不承想,晚上却叫个不停,那叫声像是婴儿,但没有婴儿的稚嫩,那叫声像哭诉,却全无节奏感,我以为是饿了,忙凑上前去端吃的。可是,它却尾巴高高竖起,浑身的毛像是抖开的鸡毛掸子,真是吓人呢,我的天,我忙连同箱子将它扔了出去。
从那之后,我完全讨厌起猫来了,虽然,看到猫就会想起没牙的老白以及老白带来的那只猫,但这并不能代表我会喜欢所看到的引起我联想的猫。
就像刚才,看见一只猫,我极其厌恶地看了它一眼后,就怀念起我童年的那只猫来。
酒心巧克力
我九岁时,大姐作为县里第一批输出的纺织工人,去了外地工作。以后,她每次休班回家,总会大包小包地给我们带一些新鲜的玩具和零食。
有一年的春节,都腊月二十八了,大姐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家。进了屋,她把包一个个放在炕上,先是问姥姥和爸妈的身体接着又讲述这一路的辛苦劳顿。我和弟弟妹妹则挤在炕沿边上,耳朵听着她的话,眼却对着那几个鼓鼓囊囊的包放着绿光。
大姐的话终于说完了!
她把我们叫到跟前,一一问着考试成绩,当得知都是前十名时,高兴地说:“真棒,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我们呼地围了上去。大姐把包一个个拉开,一件一件地往外掏着,有削了皮的甘蔗、弯弯曲曲的面条(后来才知是方便面),四四方方用透明纸包着的压缩干粮还有奇形怪状的鞭炮……
最后,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是心的形状。打开,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一些像是小塔状的东西。它们全用花花绿绿的镀了金光的纸包着,头顶系着一根细细的红丝带。
大姐剥开一颗,光滑的小塔,棕色的。大姐拉过我,“来,尝尝。”一张嘴,顺滑的落在舌头上,牙轻轻一咬,顿时,一股蜜汁流出来。甘甜醇美,还有种酒的香气。弟弟妹妹舔着嘴唇问:“啥味道?”我说:“像酒一样。”大姐哈哈大笑,说,这是酒心巧克力,中间夹的就是酒。
一盒二十颗,我们每人分了四颗,余下的八颗妈妈说送给二伯家的两个妹妹。我们很是不愿,可又没有办法。
弟弟脱鞋上了炕,坐在被卷上居高临下,一边警惕地望着我一边吃。人不大,坏心眼倒不少,我不过抢了他几次糖炒栗子他倒学出经验来了。妹妹则躲在妈妈身后慢慢地解了红丝带剥着纸,看来,他们私底下定是通了气的,她也加了十分的小心。看没甜头可占,我就揣着口袋里的三颗酒心巧克力去了街上。
大街上很热闹,来来往往的,有大人也有小孩。我就找了个人多的地方把酒心巧克力拿出来,然后在周围惊奇羡慕的目光里慢慢地吃掉了。这期间,对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一概不理,走时只留下五个字“酒心巧克力”。
酒心巧克力虽然吃完了,但是酒的香气依然在嘴里作祟,我管不住它,一直到年三十,它还在跟我的味蕾打架。
年夜,鲁北的风俗是,挂祖子,上素贡,吃饺子。各自成了家的弟兄几个,必须在一个时间放鞭炮,烧纸钱,然后全家喝酒夹菜吃饺子。而这个时间每年是不同的,有时早有时晚,所以得有一个人去各家送信。
这一年,爸爸派了我。
我先去了离家远的大伯、三伯家,最后才去了对门二伯家。我对正在灶间忙活的二伯二娘说完就跑到西屋去找大俊二满,她们不在。我出来时,经过外间屋上供的桌子,忽然看到在各色点心水果中竟摆着那八个酒心巧克力!它们端端正正地站在一个白色的小瓷盘里,在烛光下闪着橘黄的光。我好像闻到了它醇厚的香味,不由得走上前去。望望两边,一个人也没有,我飞快地抓了两颗放在了口袋里,然后扭头就跑。出屋门时,脚步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吓坏了,低头一看,是二伯家的狸花猫,我抽身一脚,它喵呜一声跳到院墙上去了。
从二伯家出来,我不敢回家,紧紧捂着口袋,直奔不远处的一堆玉米秸。钻到里面我匆匆吃掉了那两颗酒心巧克力,很奇怪,味道并不是第一次吃时的甜和香了。
我回到家,弟弟上下眼皮打着架赖在炕头,妹妹在左右摆弄她的花灯笼,妈妈正准备下饺子,爸爸拿着烟头去点挂在枣树上的鞭炮。看看一切正常,我就到柜上取了我的花灯笼跟妹妹一起玩耍。
吃过饺子,我们钻进妈妈温好的被窝睡下了,爸爸妈妈则去伯伯们家拜年。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说话声吵醒了。隐隐约约地听到酒心巧克力,我的眼立马睁大了。原来,下完饺子上供时,二娘发现盘里的酒心巧克力竟然少了两块,她去问大俊二满,都说没拿。又疑是狸花猫偷了,二伯说绝对不会,因为这只猫从进了门也没偷吃过一次。想来想去,就想出了事。因为在鲁北农村,常有这样的传说,每到除夕,村里的各色鬼魂都会出来现身,你只要到村外,蹲下身从两腿间向后望,什么样的鬼都能看到。还有,这一天,如果发生怪事,比如少了饺子,少了供品,那就一定是鬼魂享用了。那夜,我们几家的大人战战兢兢,都没睡觉。
一直到正月十五,把祖子供品撤下后,我们这几家人也没从酒心巧克力的阴影里走出来。我好几次都想说出来,可终于没敢。
在没有人时,我躲在一边,试着回忆酒心巧克力的味道,可怎么也觉不出醇香甘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