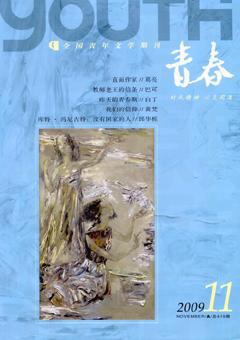葛亮:创作的可能
葛 亮 张昭兵
对话者简介
葛亮:1978年生﹐原籍南京。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文学作品发表于《收获》﹑《香港文学》﹑《联合文学》等两岸三地刊物﹐并为报章撰写文化评论专栏。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第一届香港书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2007年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文字入选《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小说集《谜鸦》﹑《七声》、《相忘江湖的鱼》等﹐入选台湾二零零六年“诚品选书”。
张昭兵:男,山东微山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及当代文学批评。曾担任《芳草》文学杂志(网络版)“现场评刊”评论员,《山花》杂志“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栏目专评,主持过《延河文学月刊》的“博士论坛”,参与创办并主持《青春》杂志的“青春热评”栏目,龙源期刊网“名家名作”栏目的签约作家。已做过多位当代著名作家的访谈,发表文学评论及研究论文近二十万字。
张昭兵:书香世家的出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成长环境,对你的心智、性情以及感受外在世界的方式有何影响?这样的出身和家庭,既是很多人艳羡的“幸运”,也可能是你本人习焉不察的无形的“拘囿”,或无可奈何的透明的“障壁”吧?
葛亮﹕家庭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未对我造成过压力。我的成长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或许我身上所谓时代的印记更为显著﹐比如“独生子女”的标签。对于“家学”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好的方面﹐是我可能拥有了比一般人较早的阅读经验以及某种感知事物的态度﹐但似乎未有什么“拘囿”。我的父母都是教育方式上相当开明的人。身为知识分子﹐谈不上有什么阶层观念。他们早年都插过队﹐吃过苦﹐对于民间会有一种深厚的情愫。这种感情是很天然的﹐和他们的个人经历相关﹐不带有所谓“民粹”色彩。这一点对我有些影响。我写《七声》﹐也是情之所至吧。比方“洪才”确有原型﹐他是一个从乡下随父母迁居南京的孩子﹐是我童年很要好的朋友。此外﹐在学问上我会有一个榜样﹐是我的祖父﹐他多年从事艺术史研究﹐治学方面的严谨﹐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稀见的。我经常翻看他的旧作﹐对我的为人为学﹐始终是一个提醒。
张昭兵: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性格。一般认为“上海”与“香港”互为镜像,“北京”与“上海”则不但在空间上异俗,也在文化上存在较大的时差,北京代表着古代、近代的中国文化,而上海则更多地代表现代、当代的中国文化。“南京”在中国是一个有着自己鲜明特点的著名城市,作为南京人,你觉得这个城市有何与众不同的地方?
葛亮﹕南京在气息上的独特﹐恐怕在中国的城市群落中是不多见的。在现代化的侵袭之下﹐南京一直处于不卑不亢的状态。六朝以降的历史文化积淀﹐是负荷也是底气。这是座有“王气”的城市﹐虽然黯然收场了许多回﹐根基却还是实在的。看得见的是﹐南京的城建发展﹐一直处于“微调”的状态。前段时间《亚洲周刊》的封面报导﹐叫做“保卫南京古都街区对抗房地产暴利”﹐“保卫”一词﹐感觉得出﹐南京已成为“古”与“今”抗衡的代表与底线了。我不太能想象﹐南京在这一层面上的“失守”。中山东路上民国时期种下的法桐﹐陆续消失﹐让人时常有怅然之感。正是这些细节﹐造就了南京的“完整感”。作为南京人﹐我对这座城市的定义﹐是某种“笃定”的性质。或许也是民间常说的萝卜气——大而化之﹐真实甚至有点粗砺﹐但内里却是十分雍容的。所以﹐我曾将我长篇小说《朱雀》中的一章﹐命名为“古典主义大萝卜”。
张昭兵:王尔德在《谎言的衰落》中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点惊世骇俗的观点:“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并以“伦敦的雾”为例来诠释自己的观点。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但文学艺术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作家和艺术家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赵园先生的名著《北京:城与人》,从北京独特的地域文化的角度对“京味”小说做了深入的解读,李欧梵教授的《上海摩登》更是掀起了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的热潮。请问你本人的作品是否也可以从“城与人”、“城与文”的“互动”与“纠葛”中去理解呢?对于文学艺术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葛亮﹕城市对我是重要的﹐它是我解读文学的一个窥口。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就是关于城市文化。在写作上﹐我是比较自觉地进入城市书写中去的﹐因为生长于斯。客观地说﹐我对乡村有审美层面的好感﹐但是城市才是我写作的根基。相对于乡村﹐城市是更好也更精准的人的实验场。城市是人所造就的集合﹐与人的关系却也微妙。很多时候﹐是成败一萧和。我近来更加感兴趣“城市史”方面的一些书籍﹐在我看来﹐城市是一个角色﹐和人一样﹐它有自己的成长历程﹑起伏﹑机缘﹐甚至毁灭与复兴。前段时间在看一个老中医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生活史》﹐是人的历史﹐也是城市的历史。城和人是奇妙的共生体﹐两者的合集﹐就是时代。说到文学艺术和现实世界﹐折射到对城市的表现上﹐是十分复杂的。可以很写实﹐也可以异化到面目全非的程度。这和写作主体本身的生存状态关系十分大。这方面﹐《City invisible》已经成为了一个经典的范例。
张昭兵:“文学南京”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段华美的乐章,但近代以降,渐有曲终人散之衰势,随着苏童、叶兆言、韩东、朱文、毕飞宇、鲁敏等中青年作家的闪亮登场,“南京作家群”在当前文坛已然成为一支非常抢眼的文学中坚。面对这样的潮起潮落,你本人有何感想?对“南京作家群”在当前文坛中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态势,有何看法?
葛亮﹕你提到的这几位﹐大多是我的前辈﹐也都是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笔下的南京给了我不少反思自我的契机。其实就文学谱系而言﹐并没有严格意义界定上的“南京文学”。作为文学形态﹐不像“京派”和“海派”文学。它不代表中国悠远文学传统的承继﹐也没有“近商”的特质。它的存在﹐更类似一种文字的“沙龙”﹐或者说﹐是一种性情的集合。一如这座城市的品性﹐它是有些“散淡”的﹐不具备功利的性质。所以﹐虽然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的作家群落﹐但并不存在某种自觉的自我定位。而他们的出色则是有目共睹的。前段时间读叶兆言的《陈旧人物》﹐写的对象并不是南京的文化人﹐但由于是南京人所写﹐却透射出南京的性情。这种史话类的文字﹐与这座城市的气质十分地投合﹐读起来很熨贴。我偏好这种文字的表达。自己在外面写﹐也仍然喜欢写南京。并不单纯因为是家乡的缘故﹐我想也是这城市某种凝聚力的所在。
张昭兵:作为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一位学院派作家,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在你身上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由创作走向研究,或许要容易一些,也比较常见,现代文学史上有就很多兼做研究的作家,当代作家进入高校搞研究的也不在少数,象王安忆、格非、马原等等;但是由研究走向创作,似乎要难一些,也不太常见,你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请问“创作后的研究”和“研究后的创作”以及“边研究边创作”分别带给你怎样的感受和体会呢?
葛亮﹕我想你说到的“走向”大概代表着某种转型。就我自己而言﹐没有大的问题。因为两方面我都感兴趣﹐两者基本可以达到“互补”的状态。创作实践对我作研究﹐有一种“体验”的意义。帮助我在切入具体的文本分析时﹐把握创作者的心态和思路。这固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也不同一于“作者已死”的解读策略﹐但可以为研究方法提供一重维度。另一方面﹐我对创作格局的掌控能力﹐有相当的部分其实得益于我的研究﹐从叙事到谋篇布局。在写作过程中﹐做到心中有谱﹐不会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比较强调小说细节的真实性﹐在写之前会作一些访谈与调查。这比较接近学术研究层面“田野考察”(field work)。对于早期的素材积累﹐还是非常有用处的。在我看来﹐创作与研究﹐不同于“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看似对立﹐内在有一种融通。当然﹐语言体式的差异则是需要重视的部分。到了具体写作时﹐我会抛弃我在作研究时的行文习惯。这也形成了某种自觉﹐类似于本能吧。
张昭兵:香港的影视和音乐,经常会形成强大的冲击波风靡大陆耳熟能详,而香港的文学多半是偏居一隅的守势鲜为人知。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在香港本土,影视、音乐和文学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葛亮﹕这个原因其实很现实﹐就是﹐影视和音乐在香港是商业行为﹐而文学更似纯艺术行为。后者自然缺乏合适的流通与散播渠道。并且﹐香港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包括强调题材的“在地化”和语言的风格化与方言化﹐这都影响了它的传播。同样﹐内地对香港音乐的理解也更多从狭义的层面出发﹐就是香港当下的流行歌曲。对于香港本土的传统音乐模式﹐比方“粤曲”﹐了解得应该不算多﹐恐怕也没几个人会唱《客途秋恨》或者《帝女花》。但在香港当地﹐白雪仙和任剑辉等粤剧名伶﹐其知名度绝不逊于任何一个香港的当红歌星。在香港本土﹐影视和音乐的联系会紧密些﹐这也是multimedia本身的生产作业模式造成的。这两者和文学的关联则比较淡薄﹐因为本地文学能为电影提供的叙事资源比较少。所以香港的电影比内地和台湾更重视原创性。当然也有一些特例﹐有些作家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改编性﹐或者说作家在创作时就已经有强烈的改编影视作品的初衷。比方李碧华的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电影﹐她也因此成为内地所熟知的香港作家。陈凯歌改编了她的作品《霸王别姬》﹐对这位作家的评价也很一针见血﹐他说”李碧华是个很聪明的作家。她给你提供的第一不是思想﹐第二不是情节﹐第三不是故事。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提供了一种人物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人物关系里升华出来的。在她所提供的人物关系之间有很多的潜力可挖。”换言之﹐就是李的作品给改编带来了某种可以发挥的空间和戏剧张力。这也是她受到电影界青睐的原因。
张昭兵:你的作品在两岸三地都有发表,且屡屡获奖,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肯定和好评,这既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情。虽说两岸三地天然地是一个“文学共同体”,但由于历史原因在价值取向、审美追求上依然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文学诚然是跨地域甚至是跨民族、跨国家的,但要真正跨出去,也并非易事。而你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跨出了很多作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跨不出去的一步,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葛亮﹕我始终相信﹐文学里存在某种普适性的东西。或者这更多是从人性考察的层面出发的﹐非关题材和表达方式﹐更无关意识形态。这也并非我个人的观念。有太多的实证﹐那布科夫﹑阿言德的作品﹐所跨越的不止是民族和国族﹐甚至还包括人们对文学的成见。我不是很欣赏所谓“地域化”或者“本土化”写作的概念﹐有了这个初衷﹐你先把自己圈住了。虽然我身在香港﹐也没有刻意迁就过本土的文学形态。这些年﹐写了很多的关于南京的小说和散文。对于在不同的地区得到的认可﹐首先当然是很大的激励﹐同时也是种启示。一个作者﹐最终得到尊重的是你的文字质量和写作个性﹐而不是在其它方面的投其所好。
张昭兵:你本人的兴趣爱好似乎比较广泛,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影视、音乐、戏剧、绘画好象皆有涉猎,在这几种艺术样式中,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你认为它的长处和局限性分别是什么?
葛亮﹕文学有它在理性层面的表达高度﹐概括性以及给受众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感﹐是其它艺术形式没办法逾越的。以电影为例﹐电影被称为是“一次过的艺术”﹐对于观众具有某种强加性。再说文学改编﹐一部作品电影化的过程﹐也是将之具象化和主动化的过程。电影其实在表达方式上是比较霸权的。文学的局限性﹐也正因为它的传播媒介是语言。阅读的过程也是将符号重组再现的过程﹐对读者的审美能力提出的要求相对较高﹐当然不及影像直接。这取决于受众﹐文学是不迁就懒人的。但这两者之间其实互可借鉴。电影的艺术感觉刺激我重视文字表达的感官冲击力。有电影界的朋友说到我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类似“空镜”的描写﹐我想正是这种感觉使然。
张昭兵:你的写作时间并不长,但创作颇丰。从05年算起,也就是四年的时间,其中07年只有一个短篇,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作品是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集中发表的,目前已经结集出版了两个中短篇小说集和一个长篇小说单行本。从这三本书来看,你已经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完成了至少两次大的写作风格的转变,即从《谜鸦》的“写意”转向了《七声》的写实,再把写意与写实相融合并拉开历史纵深,于是有了长篇《朱雀》。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转变呢?
葛亮﹕这和我对小说的观念在演进相关。最早写小说时﹐我比较重视所谓“戏剧性”元素的存现。并且﹐对于实验性的写作手法﹐也有付诸实践的愿望。这些都是形式层面的东西﹐甚至我有篇小说﹐标题叫做《π》﹐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写作取向的概括﹕未知﹐开放﹐交错﹐无规律﹐是我当时对文学乃至生活的认知。到了《七声》﹐首先我在文字审美方面有了新的转折。这也决定了我叙事的态度﹐更加接近一种真实可触的﹑朴素的表达。这一阶段的写作﹐有了我自己所喜欢的某种民间的气息﹐并因循了成长的轨迹。《朱雀》是为南京而写。它的风格是我对南京的认识﹐或者说是城市本身气韵的影响所造成的。对于历史的诠释﹐也交缠了现代的视角。这使得它在细节的“实”里﹐也氤氲了写意的因子。我想这种变化是比较自然的﹐渐进式的﹐代表了对自己写作上几种路向的实现。
张昭兵:从时间上来看,《谜鸦》似乎是当下情绪的“咏叹调”,《七声》是过往经历的“朝花夕拾”,《朱雀》则是叩问历史的“寻根之旅”了。也就是说,你不停地写下去,实际上却是走上了“返身回家”的路。请问可否这样理解你的写作走向呢?
葛亮﹕我觉得你说得很好。的确﹐在意识深处﹐南京是我写作的重要指归。我初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想写一本关于南京的小说。我对南京有一种情感的重荷﹐仿佛夙愿。当我写完了《朱雀》﹐在心里几乎等同于完成了一桩债务。其实《朱雀》之前的写作﹐更近似一种准备。我始终在寻找﹐哪一种“回家”的方式是真正恰如其分的。这一点﹐不见得要上升到文化身份的探讨﹐但是“还乡”作为一种情结﹐是很实在的。
张昭兵:一直没变的一点,可能是你的“叙述速度”。开头总是波澜不惊,从容不迫,给人以自信、细腻、绵密之感。而一种淡淡的忧伤和略显颓废的柔美,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则如三春丝雨氤氲其间。结尾处往往会有“突变”和“逆转”,但并不过多纠缠,一任叙述如水银泄地般漫过或绕到其后。让人觉得那“突变”纯粹是一个人力无法预料的意外,并且逸出了作者的结构叙述安排。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真诚的作家,在面对神秘不可知事物时,应该具有的一种好奇但不僭越的写作态度,在这一点上,有个“适度”的问题,但很多作家往往不是“过之”就是“不及”。请问你本人有着怎样的体会呢?
葛亮﹕“叙述速度”是文字的内在节奏﹐我相信文字间自有胶着。在叙事上﹐我有一种宿命。故事一将开首﹐便有了独立的生命。我不想去干涉甚至掌控它的进度。沿着情节的逻辑轨迹行进﹐对我而言﹐已经足够。即使有突变的因子﹐也是酝酿已久﹐非一日之寒。这多少也可比拟为对人生的态度吧﹐平缓的﹑顺势而为。说到底﹐大约还是旁观者的角色比较轻松些。至于尺度﹐则很难说。因应每个人发言的欲望﹐克制或是一瞬的急切﹐往往也就毫厘之差﹐但在读者看来﹐也许感觉就迥然了。
张昭兵:你的语言不属于一针见血,力透纸背、掷地有声的那种。往往是剥茧抽丝、纡徐回环,有时甚至是“顾左右而言他”,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太极推手中,读者已经被浑然不觉地“套牢”、“俘获”了。请问在语言上你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有着怎样自觉的追求呢?
葛亮﹕我有过一些语言的师傅﹐我不用回避这一点。在现阶段我已经取得了自己语言上的独立﹐但他们对我的影响依然深远。这种影响并非体现在具体的遣词造句﹐而是某种内在的气质。他们是沈从文﹑汪曾祺﹑周作人﹐国外的则是契诃夫和聚斯金德。我很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看清楚自己文字发展的道路。我有一种对掌故感的迷恋﹐也经常会写一些类似笔记小说的段落作为练习。在阅读上关于语言的审美﹐干净而达雅﹐而在语法上又朴素的文字﹐在我看来是真正好的。
张昭兵:作为一个对现当代文学史比较熟悉的学者型作家,你是如何定位和认同自己的写作在文学史上的“谱系”的?
葛亮﹕呵呵﹐我想目前还比较难以界定自己的位置。因为我还在继续写﹐“进行时”意味着各种的可能性。在写作上﹐我有喜欢尝试的一面。“谱系”多少有些总结性的意思﹐有着线性和规整的特征。而我预见自己未来的写作﹐还是会有某种“逸出”。但“逸出”的形式与内容﹐就都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了。
责任编辑维平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