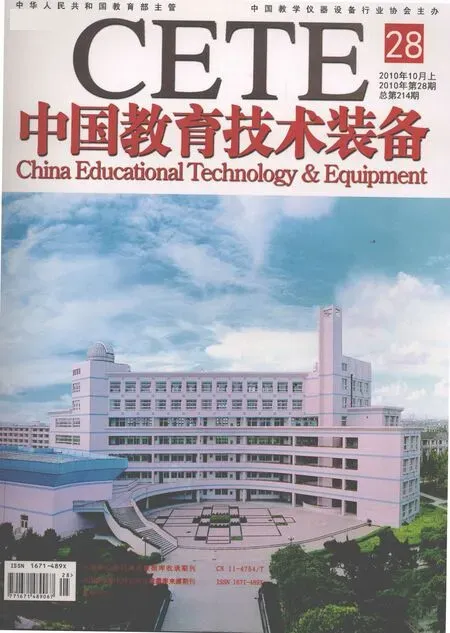新课标下语文教学应凸显诵读理念
樊丽萍
当下一些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令人担忧。四人小组讨论法、小品相声等表演法、多媒体代替法等新型教学手段的泛滥,使得原先诵声朗朗的课堂演变为演艺场或影视厅。传统的诵读被漠视,以致不少学生在诵读时支离破碎,表述时词不达意,更无从谈及对思想情感的准确把握,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的提升。因此,当务之急,重申诵读并凸显诵读理念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应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话题。并且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诵读都是语文教学中提升学生语文综合素质,形成良好语感的重要依凭。
1 先“语”后“文”——诵读的学理基础
初中语文教学与高中语文教学存在较大差异。初中生比之高中生自律力不足而他效力较强,独立性差而模仿力强,自制力弱而好动度高,因此对他们而言更需要进行直观性教学、趣味性教学,如开展“我说我心”活动,“怂恿”他们班门弄斧,等等。虽说有不少成效,但总感觉是仅解了皮毛之痒。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呢?先从“语文”的词源本义谈起。
既然“语文”一词是“语”字在前而“文”字在后,这就暗示“语”先“文”而存在。换句话说,教学还必须立足于语言的教学。古代私塾重视对学生的诵读能力的培养也证明了语言教学的“鼻祖”地位。古代私塾里的先生授课先让学生读书,由初读而熟读,再由熟读而成诵,这就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读书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激活思维,引起联想,增强语感,陶冶性情。故朱子提倡熟读精思,要求“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思时“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这种重视语感积累的诵读方法,对于提升学生的“文”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语文素质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况且,无论从《辞海》对“语”和“文”的定义,还是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来看,诵读的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辞海》云:“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它同语言的关系是依附语言、记录语言。”可以清楚看出,
人类是先有语言(口语),后有文字(书面语)的,人们总是在幼儿时期就学会说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学习使用文字。从表面看,儿童7岁入学,口语早已学会,不用教师操心,只要教他识字、读书、作文就可以。现行的初中语文教学基本上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也就是说,只注重文字的练习,不注意甚至不理会语言的学习。由此可知,天天讲“语文”教学,实际上教的和学的都仅仅是“文”而非“语”,以致开篇提及的不少学生在诵读时支离破碎、表述时词不达意、不能准确把握思想情感等弊端也就有了滋生的缘由。
再者,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来看,先“文”后“语”也不足取。人的心理发展包括感觉、知觉、思维等方面,其中感觉是一种最简单的最低级的心理现象,它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肤觉。最直观地检测人们的言语表达能力的便是视觉与听觉,而它们恰恰又受制于大脑左侧半球的语言中枢。如此可论断,“语”字当先,是有其生理基础的。
2 缘情赋声——诵读的内在理路
既然人的口语水平取决于语言中枢神经,而语言中枢神经的发达与否直接与口语使用频率密切相关,那么,大力提倡诵读教学势在必行。尤其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充分调动初中生的视觉和听觉感官,能使他们在诵读声中摒弃一切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语言环境中。事实上,上文提及的古代私塾的诵读教学法,历来就是我国的传统教学法。宋代陆九渊提倡:“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清朝人唐彪也在《家塾教学法》中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这里提及的涵泳,就是一种强调在熟读基础上自觉感悟语言中的意蕴的教学方法。它提倡不要过早地让学生了解意义,而是让学生在诵读中通过鉴赏玩味,掂量比较,获得审美感、情趣感等。这与本文所提的诵读理念应是一致的。
我国的黎锦熙、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等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无一不强调诵读的重要意义。朱自清先生曾引别人的话说:“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而两者并用“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诵读既如此备受推崇,教师又被誉为“启明灯”,自然,这“启明”的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教师身上。那么,如何“启明”呢?
关键在于教师能否缘情赋声。南朝梁刘勰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意为作者先有了情思再发而为文辞,“情”字当为文之精髓。教师在诵读时需寻得此情(即缘情),才能使之准确完整地再现,从而获得完美的教学效应。同时,作者在缘情达意时,需凭借说话的气氛和语气的声情,形成高下、急徐、轻重、顿挫等声调,那么教师的诵读实际上是把无声的语言文字变为有声语言的一种语言艺术的再创作活动,因此又足见“赋声”的重要性。“缘情”和“赋声”实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初中语文诗歌单元的教学目标为“诗歌的强烈感情”,而且课后练习的编排中都安排了诵读的指导。编写者的初衷极好,希望学生能通过有限的课文资源掌握解读诗歌的技巧。然而在课后的师生交流中,学生反映比较平淡。其实本单元收录的几首诗歌都很有诵读意义,然而学生毕竟稚嫩,若教师不在教学中给予诵读上的指导,或许学生是了解了诗的大意,掌握了诸如“通过……表达了……”的中心思想,但诗的“韵”,作者熔铸于其间的“气”恐怕就难以领悟了。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就应该在诵读上多下工夫。
3 “语”“文”相融——诵读的理想境界
诵读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是“语”“文”相融,最终培养学生的良好语感。《吕氏春秋·音初》阐及:“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这样看来,诵读者(教师)发出的声音应“产乎心”,应“成于外而化乎内”,听者(学生)从这种声音中,能体会到作品作者的“风”“志”“德”;在诵读时,教师除了把握文字作品的思想感情以外,还要有自身情感的投入,可以说,诵读中的情是作品中的情和诵读者的情融合了的结晶。如果教师自身缺乏对作品深刻内涵的独到把握,缺乏对熔铸于其间的情的准确体悟,那么就可能使“通过语言传承而成为人”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在平时语文教学中,要重视教师丰富的情感体悟在语感培养上的作用,可以说,丰富的情感体悟正是实现诵读理想境界的催化剂。毋庸置疑,一个情感体验深刻的人,他对社会生活的感知也是深刻的,他所采撷的生活表象也必然体现他的情感价值取向。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有人说:“艺术品就是‘情感生活’在空间、时间或诗中的投影。”(苏姆·朗格《艺术问题》)这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一方面,创作主体的情感生活(或经验)构成“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是艺术品中语感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当创作主体凭借自己的情感图式同客体(自然界)产生情感共鸣时,必然会对客体作出情感价值判断,而情感的价值判断又受到主体的世界观、思想方式、个人品格气质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情感生活中必然带有理性思维的积淀。那么,作为阅读主导的教师除了具备渊博的知识、过硬的诵读能力外,更需要有细腻的情感体悟、敏锐地捕捉言辞的能力,如此,方能领悟隐含于艺术品背后的情韵。
例如,阅读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最后一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教师只有在了解了词人此时的际遇并对词人的遭遇表示同情时,才能深入地体悟、判断这一“梦”一“酹”中的情感内涵:其中备受压抑的激愤和苦闷,有徒伤老大的无奈,有报国无门的自伤自怜,有遭受打击后的消沉悲衰,更有几分超越与旷达。如此深厚的情感内容,教师仅靠硬译,刻板地教读学生是无法体味到的,没有教师情感经验的催化,没有教师情感判断的渗入,学生是难以感受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