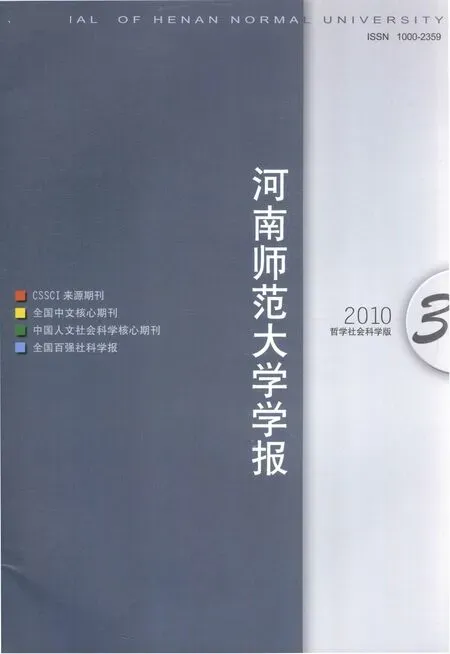朱熹吕祖谦学术之歧的再检视
郭庆财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105)
朱熹吕祖谦学术之歧的再检视
郭庆财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105)
朱熹秉承程颐的为学之训,主张“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不但重视致知进学,也重视涵养本原,希图在求知和明善之间架设一道桥梁,合内外之道。相较而言,吕祖谦的心性之学和文史之学虽各有建树,但却不能通贯,而显得“支离”,即吕氏泛滥诸家,却无益于身心的修养和性命之理的发明。为此,朱熹对吕祖谦博杂的文史之学多有规诫。吕祖谦多次满怀愧悔,向朱熹表示应向理学正道回归,并在后期疏远了文章华藻。
朱熹;吕祖谦;涵养;进学;支离
一、朱吕的“支离”之辩
淳熙二年乙未的鹅湖之会,是南宋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熹与陆九渊就为学方法等问题展开激辩。吕祖谦在中间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不免有依违之论,而他实际赞成的乃是朱熹的立场,如云:
大抵子静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学十分是当无可议者,所议者只是工夫未到尔。[1]别集卷八《答朱侍讲》
吕氏此论明确在朱、陆之间分出轩轾。吕祖谦与朱熹共同倡导性命之学,在继承道统问题上桴鼓相应,如四库馆臣所说:“紫阳倡道东南,祖谦实羽翼之。”[2]卷一百三十五《〈历代制度详说〉提要》在为学方法方面二人也是相似的,即都以“涵养用敬,进学致知”为基本路线,所以吕祖谦对朱熹的声援应是可信的、真诚的。
但是,朱熹对此似乎并不领情,他认为吕学和陆学都有不足:“抚学有首无尾,浙学有尾无首。”[3]2985抚学也即陆学,浙学乃由祖谦所发端。他认为陆学有上达而无下学,显得过于简易;而浙学只有下学的节末工夫,缺乏德性的超越。如果在吕学和陆学间作一权衡的话,他宁可肯定陆学:“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如何故如此。”[3]2957永康之学,实指吕学。而且鹅湖之会后,朱熹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反倒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陆九渊对自己“支离”的批评,认为确有此弊,如云:“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4]卷五十四《答项平甫》
所谓“支离”,乃指“问学”活动具体而繁琐,造成进学致知活动与德性自觉之间的不能圆通。朱熹秉承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为学之训,主张“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不但重视致知进学,也重视涵养本原,即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但是这种做法往往造成知识问题与道德问题的混杂。尤其是朱陆论争中各执一词,朱熹难免对“下学”与“道问学”的求知路径强调过当,才与陆九渊的内省路径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实际上朱熹对“德性”和“问学”之间的矛盾看得十分清楚,于是,他多次强调二者的一致和协调,希图在求知和明善之间架设一道桥梁,合内外之道。比如他多次说到:“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3]295强调使外在格物的努力返归内心,使此心全体大用无不明,最完全地体认天理,达到德性至善之域。即客观物理经由心气之灵而内摄之,而以明善为旨归,这是一种自明而诚的理性主义道路。
这种路径,吕祖谦也十分赞同:“讲贯通绎为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自是人病,非是法病。”[1]别集卷十《与邢邦用》即是说读书讲学为天下常理,学者由此流入“支离”只是个别偏失,不能由此否定这一“百代通法”。祖谦说陆九渊“病在看人不看理”,实际也意识到“德性”“问学”两者并进乃是常理通法,但是不同的人在践行过程中难免会有偏差。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理”和“人”二者相较,为达致成德之教的完满境界,作为通向“理”的入路,“人”的道德实践功夫显得更为重要。学者需要在心性涵养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否则就会显得散漫不力。话虽如此,但吕祖谦本人恰是“人”“理”脱节的典型,上引他的那段话恰可作为吕氏学问之弊的自我概括。早在鹅湖之会前,朱熹已经在吕氏身上看到了这种弊端。如果说在陆九渊看来朱熹的为学之方不免“支离”,则吕祖谦在“支离”之路上走得更远。吕氏早年于涵养本原与讲学致知之间往往有偏,不能兼取并进以臻于协调:或埋头于古人之书而修养功夫略显散漫,或强调反观内省而流于简易。比如淳熙元年吕祖谦曾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训诱之际”教导子弟,就难免流于纯粹体验而忽略了下学功夫。于是,朱熹淳熙元年甲午春给吕祖谦的信中说:“若如来喻,便有好仁不好学之蔽矣。且《中庸》言学问思辩而后继以力行,程子于涵养进学亦两言之,皆未尝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废也。若曰讲习渐明,便当痛下克己功夫,以践其实,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说过,则其言为无病矣。”[4]卷三十三《答吕伯恭》
吕祖谦对朱熹的每封回信态度都极尽谦恭,这封回信也不例外:“开示涵养进学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门,敢不朝夕从事,庶几假以岁月,粗识指归,无负期待诱进之意。”[1]别集卷七《与朱侍讲》表示对致知与涵养两者并进的教谕认真尊奉。但这并非意味着吕祖谦的修养功夫已臻完善,在其一生治学途中,持守和践行之不力往往有之。正如朱熹所云:“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3]2604这个批评很切中吕祖谦的要害。
二、反观内省与格物穷理
吕祖谦与朱熹不同,他不太重视作为德性原则的“性”,而较多地受到孟子的影响,以心为主,主张存心、明心的反观内省功夫。如云:“心犹帝,性犹天。本然者谓之性,主宰者谓之心。工夫须从心上做。”[5]卷九《杂说一》他重视良心的明觉,强调通过“尽心”功夫以达到至善的境界,以放心为邪,存心则为正。“存心”需要一种鞭辟向里的克己功夫,即通过“精一”的诚敬功夫,克除私欲,使“人心”合于天理,达到无妄的“道心”境界。吕祖谦严格区分“人心”和“道心”:“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是子细之意。既能精一,则信能执中矣。”[5]卷九《杂说一》道心,也即自然知道爱敬的良知良能的真心,是善的所在;人心则不免于私欲之杂,为昏气所蒙蔽,纷杂扰攘,容易流于偏邪。欲恢复人的本心和善性,吕祖谦多处强调发扬“诚敬”之功,存理去欲以“正心”:
为学欲至于圣贤,岂可不知其本始……所以教学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一字。[5]卷五《礼记说》
吕祖谦此处表面上强调用敬的恭敬严肃,但所谓“兢业之心,持敬之功”,实际更侧重于“识心”、“明心”的反身内省,以去除良心的蒙蔽,恢复心体至善的功夫。他标举孟子所提出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个人心性修养的重要法门:“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凡事有龃龉,行有不得处,尽反求诸己,使表里相应而后可。如一分未尽,便有龃龉。如果十分正当,天下自然归之。”[5]卷七《孟子说》这是一种反观内省的路子,强调的是主体道德自觉的内向体验,将已放之心收拾入身来,并不强调通过对外物的观察而获得认识。又如:“自小言之,则人之一心善端发见,虽穷凶极恶之人,此善端未尝不复。”[5]卷一《易说》则更具有当下现成的色彩,有似于佛家悟道之直截简易,且与程颢、杨时“反身而诚”的内向体验乃至陆九渊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比较接近。
朱熹认为吕祖谦在强调反观内省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穷理的功夫,欠缺致知的理性努力,因而显得进学不力,因而批评吕氏云:“以此知人心至灵,只自家不稳处,便须有人点检也。”[3]卷三十三《答吕伯恭》道德境界的提高决不能仅恃聪明、单纯靠内心的反观内省来实现,而需要学习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与之内外相印证。于是一方面,朱熹从理性主义的立场上理解持敬涵养的意义,将持敬涵养视为体认客观天理的主观修养,如说:“盖欲应事先须穷理,而欲穷理,又须养得心地本原虚静明彻。”[1]别集卷二《彭子寿》另一方面,朱熹的“敬”以格物为基础,必须通过格物穷理的“集义工夫”去增进内心的纯洁和专一,“知至则敬愈分明”。仅言主敬,则是非未定,故涵养必兼之以察识,居敬必兼之以格物穷理。涵养用敬和进学致知两者并进,乃能优入道德之域。与吕祖谦反身逆觉体证的思路相比,这是一条向外顺取的理性路径。
三、史学之歧
吕祖谦的发明本心的功夫偏重于内,不好遵循;而在求知方面则偏转向于外,过多地埋头文史而忽略了身心的修养。吕氏承续了“不名一师”的家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6]卷三十六《紫微学案》,其学亦以博杂伦类、不立涯涘为特色,在史学方面造诣尤为精卓。但在朱熹看来其学于存心明理非但无实际助益,反而转增蒙蔽。因为朱熹以涵养和致知相统一,穷理与处事一并求,而欲穷理当求之于经学与理学,欲处事则应求之于史学。经学反向内心,史学向外考求,朱熹则主张经史配合,内外兼通,实则重内轻外;而吕祖谦史学更多向外驰骛,于是遭受朱熹的讥评也最多。
吕祖谦史学的思路可以归结为成己、成物两方面。吕氏云:“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己、成物两件。”[5]卷一《杂说一》成己,即本于对“人情”的洞察,使得自我识见和道德境界得以提升;成物,更多的是考究古代治体,明悉典章礼制的迁革,作为当下政治的龟鉴。成己,体现于史事中蕴涵的性理思想的阐发,比如春秋时与母为仇的郑庄公“天理已绝,古今大恶也”,而听了颍考叔讽谏后乃生悔心,母子言归于好,“天理油然而生”[7]卷首《看左氏规模》,显示了由天理沦丧到复萌的变化。这一史实阐发的道理乃指向去人欲、存天理的个人修养境界。
“成物”,实即对治体的关注。如果说“成己”的人生哲学是通过“一人之所以变迁”体现出来的,而“成物”的治道经验则隐含于“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7]卷首《看左氏规模》的治事之中,世道的兴衰治乱尤其通过“礼”的因革损益表现出来:“典常,当代之法也。周家之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讲画,至精至备,凡莅官者谨师之而已。苟喋喋利口,妄欲改更,以纷乱职业,则动摇一代之治体,岂细故哉。”[8]卷三十《周书》
如果从成己方面来看,朱吕二人的治学思路比较相似,朱熹认为:“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即只有凭理以观史,才能立定大本,而不会随古人的脚跟转。这是朱氏史学的基本宗旨和思路。吕祖谦亦认为:“史亦难看,须是自家镜明,然后见得美恶称平,然后等得轻重。欲得镜明称平,又须是致知格物。”[5]卷十《杂说二》即观看史书,考求治乱,应当在胸中义理明彻的基础上进行。朱、吕的言论如出一辙。
但是,从其史学实践来看,吕祖谦对“成己”强调得不多,他的《历代制度详说》《少仪外传》等书在“成物”的治体方面用功甚著,花费了许多精力讨论治道、史事、兵刑等制度,其史学更多着眼于史之功用色彩,而和“成己”之间产生了扞格。与之不同,朱熹的历史哲学乃归结于“为己”的心性之学,尤其强调观史当归于明理:“所谓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见得本来道理,即与今日讨论制度,较计权术者,意思工夫迥然不同。”[3]卷五十四《答康炳道》通古今、考事变只是必要的致知手段,为的是与内在的心性涵泳形成内外印证,以增强体认性理的自觉性,即史学的“道问学”功夫旨在提升“尊德性”、“求放心”的思想境界,史事不过是“推广增益以为补助耳”[3]卷四十七《答吕子约》,本身并无研讨的价值。因此在朱熹看来,吕祖谦只有讨论制度、计较利害的功夫,而相对欠缺回归身心的“成己”功夫。
从理会是非和强调心术端正出发,朱熹对吕祖谦所推重的《左传》和《史记》都没有好感,他认为这两书大谈形势利害、机诈权谋,学者难于辨清是非,而且沉溺其中太久,难免于驰骛向外,往往会败坏了心术。在朱熹看来,治道必以正心、修身为本,从里面做出[3]2686。所以应当先去理会经书,尤其是《大学》《中庸》这样的著作,培养得大本端正,义理明白,再去看史,才不会被机诈权谋所诱惑,自然能够制事无偏。出于这种考虑,他对吕祖谦的专意于史学委婉地提出批评:“恐亦当令先于经书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当预防也。”[3]卷三十三《答吕伯恭》沉迷于史学而无所权衡,往往引导人粗心向外,容易坏了学人心术。
四、文学之歧
祖谦以学术名家,而其文学成就亦颇足以跻身大家之列,正如四库馆臣所评,“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2]《〈东莱集〉提要》。吕祖谦潜心儒业,又热心文事,为文发扬踔厉,难免于二者之间彷徨游移,倚轻倚重;而这又是与其持敬功夫的涣散分不开的。
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信中多次提到自己功夫散漫的弊病,如云:“大抵诚意浅薄,将以动人悟物,而手忙脚乱,出位逾节处甚多。忧患以来,虽知稍自惩艾,而工夫缓慢,向来病痛犹十存四五。”[1]别集卷八《与朱侍讲》又云:“人苦不自知,离群索居尤易得颓弛。”[1]别集卷八《与朱侍讲》所谓“离群索居”,第一段是指乾道四年祖谦居母丧独处婺州时,可谓备极落寞。第二段便是乾道八年至淳熙初年祖谦在家为父守丧。这两段时间他身在丧中,又无朋友切磋督责之益,持敬功夫难免不纯。值得注意的是,吕祖谦涵养功夫汗漫的同时,却在文章方面下了大的工夫,分别撰辑了《东莱博议》和《古文关键》两部文章学的名作。前者是为参加科举的士子作的科举范文,实际是根据《左传》事迹写作的文采富赡、气势流动的史论文。后者乃是精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张耒六家古文,每篇文章皆详加评点,各举其文章布局命意的妙处,铢剖粒较,为使弟子作文有所矜式。
吕氏这两部著作,前者致力于文章华藻,后者津津乐道于起承转合等文法关目,两者皆作于居家守丧、独学无友期间,这并非出于巧合。除了排遣忧闷外,这与吕氏“工夫汗漫弛堕”、“随事汩没”有着内在的因果联系。由于心思散漫,故而有作文的余暇;因为潜心于文章,所以精神旁骛于学问之外。若结合吕祖谦在明招时写给张栻的信来看,这一点似乎更明确:“从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经历之功。思虑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积蓄未厚而发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谈说有余。”[1]别集卷七《与张荆州》所谓“积蓄未厚而发用太遽”,是指心性涵养的功夫尚不精醇,故而情感的发动常常把握不好,不能做到进止有度,达到“中和”的境界。从朱熹开始,理学家大多以为性静情动,而吕祖谦在复信中反省自己不免“以情为性”[9]卷二十五《寄吕伯恭》第二书引,在已发、未发的动静几微之际把持不住,向外的功夫常多,向内察识的功夫常少。
文章写作过程中的构思冥搜和情感发动都是无定向的,会使心智越过理学“敬”的制约而无所底止。为文与为学的功夫,此消则彼长:陷溺于文辞,心思“失却照管”而向外驰骛,必然会妨害了为学功夫。正统理学家张栻对祖谦的好文就曾深表不满:“渠(吕)爱 敝 精 神 于 闲 文 字 中,徒 自 损,何益?”[9]卷二十四《答朱元晦》朱熹虽然好文,但决不主张在为文方面耗费太多精力去刻意求工,而只用一句轻描淡写的“何必苦留意”便作了回答。在朱熹看来,吕祖谦孜孜矻矻于举子业和古文文法,是心性搅扰、治学不力的迹象,故而在给祖谦的信中委婉地指出:“为举子辈抄录文字,流传太多。稽其所敝,似亦有可议者。自此恐亦当少讱其出也。”[3]卷三十三《答吕伯恭》意图是劝吕祖谦放弃对文章之学的孜孜以求,收束身心,回到道学事业上来。对朱熹苦口婆心的劝诫,吕祖谦的回书非常谦恭,且深表愧悔之意:“今思稽其所敝,诚为至论,此等文字,自是以往决不复再拈出,非特讱其出而已也。”[1]别集卷八《与朱侍讲》吕祖谦此言并非搪塞之语,他淳熙元年之后便再也没有过教授举子业的事迹。淳熙元年他在给挚友陈亮的信中便提到:“今年缘绝口不说时文,门前绝少人迹。”[1]别集卷十《与陈同甫》也印证了吕祖谦的悔过是见诸行动的。
对吕祖谦而言,修德治性的圣贤事业乃是最根本的,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虽然他禀有超群的文学天分,且热心于文事,但文学在他的生命中只能居于第二位。朱熹的劝诫其实颇能契合和唤起祖谦的生命价值理想,这使他到了晚期对先前“工夫汗漫”、“喜合恶离”的弊病作了深入的反省,专心一意地去做一个道学夫子。综观祖谦一生,他早年思想的博杂未粹,恰为他留意文事辟出了空间: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他现存的一百多首诗,除了少数年代不详者之外,绝大部分作于淳熙五年之前,而数量上占主体的写景诗则更早作于绍兴年间居福州、信州、杭州之时,以及乾道间在明招独居无聊时;淳熙元年八月自金华游会稽,祖谦有记游的《入越录》,以移步换景之法,文中对溪桥花石等景物描摹入细,写来层次错落,涉笔成趣,而文风清新映发,是难得的游记佳作[1]卷十五;而此后祖谦便很少从事文学写作。淳熙五年他卧病请祠在家,几乎不再写诗。由此看来,晚年的吕祖谦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和圆通,与此同时也疏远了文章华藻。
[1]吕祖谦.东莱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6]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吕祖谦.左氏传说[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8]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9]张栻.南轩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责任编辑 张家鹿]
B244.7
A
1000-2359(2010)03-0005-04
郭庆财(1978—),男,山东无棣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201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