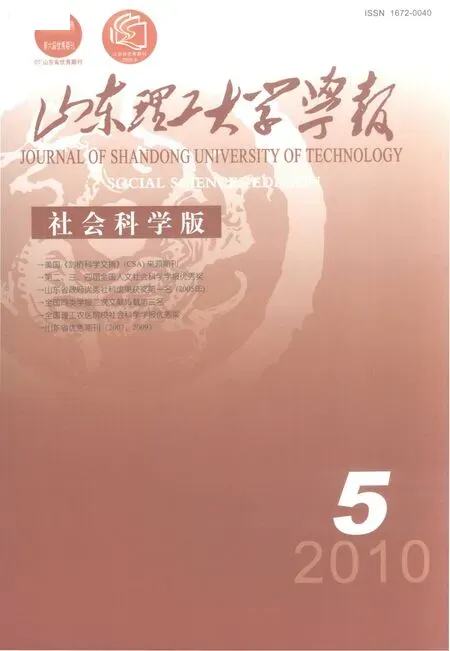从文体学发展线索看古代文学教学理念的转变
刘 涛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高校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所辖的所有课程中,古代文学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丰富,所占学分也最多。然而,受到教学时数的限制,教师很难在课堂上把积淀了两三千年的文学史知识巨细无遗地传授给学生。这样一来,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尽可能多给学生讲授一些知识,就成了古代文学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古代文学教学现状剖析及文体学视角的提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古代文学教师采用传统的、陈旧的“三段结构式”教学方法,即在教学中按照作家生平与创作、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三个层次展开讲授,起初学生反映效果还可以,但时间一长,学生听课很容易产生厌倦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尽管传统教学方法中也有可取的东西,比如重视并加强学生的传统文化修养与基础知识的掌握,但总体看来,毕竟弊大于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大改革力度,教师应该创新教学模式,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具体来说,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突出以作品教学为主的原则,强化基础教学。针对当前大学生的传统文化基础较为薄弱的现状,改变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大都以文学史为主、作品为辅的教学方法,突出强调以作品为主的原则,即是强调以作品教学为主。当然,其间教师还要努力研究探讨教学理论,以理论作为指导,以便于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掘新的教学视角,构建新的教学理念,以此而论,文体学视角当是不可忽视的一种。笔者的教学实践证明,文体学角度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从这一视角切入,有利于学生在学习时树立新的文体学观念,以某种文体的发展演变作为线索,将此前零乱无章的知识点贯穿起来,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
文体学视角是当前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易于操作且行之有效的角度,事实证明,它非常符合时下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实际状况。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史时间跨度长,自先秦至清末鸦片战争(此后至五四时期算作近代),上下绵延两三千年,作家作品数量繁多,文体庞杂,如果按时代先后次序展开讲授,那么仅靠课堂时间很难完成教学任务。然而,如果从文体的角度进行,点面结合,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意欲明析文体学之含义,必须先理清文体一语的内涵。文体,指文学作品的体裁、体制或体式。任何一位作家在创作任何一篇作品时,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势必要首先选择一种最合适的文体样式,然后才能按照相关规定展开创作,由此使文学作品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类别。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凡例》曰:“文辞以体制为先。”[1]9可见,文章体制的确立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古代文学作品体裁不同,其写作特点、要求及风格自然不同。教师在教学中如果能从文体的角度切入,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分析与探讨不同文体的体制特点及创作风格,或同一种文体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或两种相近文体的传承与因革,如此一来,他们才能更好地阅读、分析和评价古代文学作品。关于文体一语,中国古代文论著述或文学批评史著作诠释更为全面。诸书提出,文体除指文学体裁外,还可以指文章风格。如《文心雕龙》中单列《体性》为一篇,其“体”是指作品的体貌、风格;“性”则指作家的个性、性情。文云:“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2]505所列八体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皆就作品风格而言。日本学者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也专列《论体》一篇,其“体”无疑也是指文章风格。《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曰:“凡制作之士,祖述多门,人心不同,文体各异。”[3]150书中所列出的六种文章风格分别为博雅、清典、绮艳、宏壮、要约、切至,并举出每种风格的代表文体种类。文体学,是指研究文体的学科,又称文体论,西方文学理论则称文类学,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教师在教学中建构文体学理念,将文学史与文体史融为一体,可以做到创新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开拓思维,自主探讨,逐步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
二、文体学视角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在教学中如果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为教学而教学,势必很难摆脱那种以灌输知识为主的陈旧模式,事实证明,凝滞僵化的教学路数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的情绪。构建新的教学理念,从文体学角度切入不失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方法。中国古代文学史知识浩如烟海,博富庞杂,如果构建文体学观念,即按照文体发展演进的线索加以梳理讲授,那么效率无疑会提高不少。
以先秦文学为例,文学史中所涉及到文体主要有诗歌和散文,诗歌主要包括《诗经》、《楚辞》和上古歌谣,散文则主要有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类,而教材中的章节编排次序并非以文体为依据,而且诗文之间还夹杂有上古神话,所以编排时不同文体是互相交叉的。由于这两种文体都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因此所取得的成就不会太高。教师如果按照教材章节编排次序,孤立地讲解两种文体所包括的所有相关知识点,费时费力,却往往很难收到好的效果。然而,如果从一种文体入手,分析探讨其演变历程与规律,那无疑可以为学生提供一种新思路与新范式。比如诗歌,上古歌谣中的句式多为二言体,这适应了当时原始人类的简单、短促的劳动节奏。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九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4]243此歌写的是原始人类制作打猎器具并猎取食物的过程,二言体行文,节奏急促,反映出当时人简单的思维和语言表达。当然,此类歌谣都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前,一旦文字产生,诗歌的句式就转向了四言体。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标志着诗歌体式完全进入了四言体时期。其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章叠句的手法,在表达效果上明显优于二言体的上古歌谣。《诗经》中的诗篇以四言为主,句式加长,不同音韵间的间隔也加长,词汇丰富,容量增大的同时,也增强了表现力。如《诗经·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5]3-4重言词、双声词、叠韵词并用,无论是写物摹状,还是拟声传情,无不形象生动,惟妙惟肖,大大增强了表现力。另外,在押韵方面,《诗经》的四言体诗歌用韵灵活多样,不再拘泥于如上引二言体歌谣《弹歌》那种一韵到底的形式,而是努力开拓出多种押韵形式,这对后世诗歌的韵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诗经》中四言体诗歌的用韵方式,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古诗用韵之法》曰:“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诸篇,……,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6]733-734《诗经》以后,楚辞体诗歌出现,屈原的《橘颂》、《天问》基本沿袭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而其他多数篇章如《离骚》、《九歌》、《九章》等无论篇章结构还是语言、句式、风格都表现出迥乎不同的特点,带有浓郁的楚文化气息。其中,从句式上来看,楚辞体诗歌完全突破了《诗经》的四言体句式,参差错落,灵活多样,六言句、五言句、七言句和一些散文化句式都比较常见。从语言上来看,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词汇入诗。这在诗歌发展史上都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由二言体到四言体再到楚辞体,这是诗歌体式在先秦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每一阶段都有其深层次原因及不同体制特点。之所以如此,既是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使然,又收到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教师在讲授时如果能够按照文体的角度加以展开,那么学生在学习时自然能理清某一文体的演进情况,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再如,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体,自先秦至清代,一直以来与诗歌平分秋色。如果教师讲课时不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解,学生势必很难理清它在文学史上的发展脉络。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演进其实是围绕着散体文(奇句单行、不讲对偶与声律的,即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与骈文的交互更替、此消彼长而展开的。这一演进过程包含了骈散合一(上古至汉初),骈散分途(两汉),骈文初成、定型及兴盛(魏晋至盛唐),散体文复兴、骈文变革及四六形成(中唐至宋),骈散并衰(元明),骈散复兴及消亡(清至五四运动)六个阶段。晚清罗惇曧《文学源流》叙骈散演进历程曰:“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7]622-623罗氏借助骈散兴衰对中国两千年的散文发展脉络作出合理而明晰的勾勒。散体文、骈文的交互更替是文学史中散文发展的体现,是文学内部规律的外在表现。在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古代散文发展史中,无论哪方占据主流,另一方都没有绝迹。譬如南朝时骈文处于鼎盛阶段,散体文则仍在潜滋暗长;而中唐古文运动时古文(散体文)主宰文坛,同时也有诸多骈文作品出现。文章存在骈、散两种体式是客观现实,两体本身并无优劣高下之分,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云:“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骈,文之道也。文章体制,如各朝衣冠,不妨互异,其状貌之妍媸,固别有在也。天尊于地,偶统于奇,此亦自然之理。”[8]1814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亦云:“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9]34在散文教学中,教师梳理出古代散文演进的线索,引导学生从宏观上把握这一历程,如果仅仅截取散文发展中的一段,那势必很难再现其真实风貌。
又如,赋体是汉代文学的主要体裁,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既具有诗歌的特点,又具有散文的特点。对于这一特殊文体,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就事论事,而要追根溯源,全面客观地分析评判。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出公允的结论。关于赋体的归属问题,历来多有争议。概括而言,当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赋不属于散文,郭绍虞、曹聚仁、朱光潜皆持此说。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郭绍虞先生在《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体制就是‘赋’。中国文学上的分类,一向分为诗、文二体,而赋的体裁则界于诗文二者之间,既不能归入于文,又不能列之于诗。”“就总的趋势来讲,赋是越来越接近于文的一类的”。[10]80此说尽管指出赋很接近散文,但并未将其归于散文。曹聚仁在《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一文中说:“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诗人之赋近于诗,辞人之赋近于散文;赋的修辞技巧近于诗,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它是文学中的袋鼠。”[11]361该说亦认为赋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与其观点相似者还有朱光潜。“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接”。“赋是韵文演化为散文的过渡期的一种联锁线”。[12]185朱氏认为,赋具有诗和散文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同于诗和散文,它在韵文演变为散文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陈柱的《中国散文史》即将赋排除在外,其“散文”实取与韵文相对之义,无韵的骈体文和散体文则在其范围之内。当代的一些散文专著,也多有不包括赋在内者,如韩兆琦的《汉代散文史稿》、熊礼汇的《先唐散文艺术论》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赋应归于散文之列。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本是一部散文选,其中分文体为十三大类,除论辨、序跋等类外,辞赋一门也赫然在列,可见姚氏即认为赋属于散文。今人谭家健在《六朝文章研究之我见》中也说:“赋之为体,从大范围来讲,应该属于文章,即广义的散文。”[13]3另外,冯其庸的《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等都把赋作为散文的一个门类加以论述。如郭氏论及汉代散文时说:“汉代最有时代特征的文章是赋。汉赋是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从文章形式说,有的虽名为‘赋’,实为赋体之文,有的虽名为‘文’,实为文体之赋。”“秦汉之赋,就作用说,不近于诗,而近于文。虽然命名为赋,其实也是文章”。[14]198基于赋与散文存在很多共性,部分学者往往将赋归于散文范围之内。
笔者认为,鉴于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尽管它具备了诗和散文的某些特征,但它毕竟不同于诗,也不同于散文。它与散文应是两种独立的文体。散文产生比赋早,即使到汉代辞赋大盛时期,散文也一直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虽然有些散文因受辞赋的影响而采用了赋的创作手法,但二者之间终究有着明显的界限。两汉以后,大赋隐退,魏晋南朝,写景、抒情小赋居于赋苑主导地位。其间赋虽有骈化、律化的现象,但始终以独立的形态存在,并未融入散文之中。就散文而言,也经历了骈化的过程,并且形成骈体文。尽管骈文受到辞赋的影响而加剧了骈俪程度,但它终究还是由传统散文演变而来,根本没有脱离散文的范畴。由此可见,赋与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两种并行的文体,不存在赋从属于散文之说。
赋与散文虽是两种独立的文体,但散文骈化以后形成的骈文受到赋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汉代辞赋也受到战国楚辞的直接影响,这样一来,楚辞、汉赋与骈文三者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关系。王逸《楚辞章句序》云:“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15]49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16]1778清代学者孙梅《四六丛话·叙骚》指明了《楚辞》对后世辞赋及骈文的深远影响:“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自赋而下,始专为骈体,其列于赋之前者,将以骚启俪也”。[17]39-40此说认为,由楚辞到赋再到骈文,彼此之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为进一步明确《楚辞》各篇与后代赋及骈文的承传关系,孙氏借助具体作品加以说明:《离骚》→《幽通赋》、《思玄赋》;《东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甘泉赋》、《藉田赋》;《湘君》、《湘夫人》→《长门赋》、《洛神赋》;《山鬼》→《感旧赋》、《叹逝赋》;《国殇》、《礼魂》→《马汧督诔》、《祭古冢文》;《涉江》、《远游》→《西征赋》、《北征赋》;《怀沙》→《鵩鸟赋》、《鹦鹉赋》;《哀郢》→《哀江南赋》;《橘颂》→《小园赋》、《枯树赋》;《招魂》、《大招》→《恨赋》、《别赋》;《天问》→《经通天台表》、《追答刘沼书》、《辨命论》、《劳生论》;《九辩》→《七发》;《卜居》→《东方像赞》、《归去来辞》;《渔父》→《解嘲》、《答宾戏》。所列篇目之间相似的风格显示出前者对后者的深刻影响。至于隋以后的作家,如四杰、王维、燕许、柳宗元、李商隐的骈文无一不受楚辞的润泽。关于楚辞与骈文之间的承传关系,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原序》所言更为明晰:“中国文章中极侈丽者,有四六文,欲知四六文,必解一般骈文,欲知一般骈文,必解汉赋,欲知汉赋,必解楚骚;此其为一贯系统,摘出其一,则不免支离矣。楚骚,汉赋,一般骈文,四六文四者,虽概可以骈文称之,然骚赋者,有韵;骈文四六者,无韵也。”[18]1此说由流溯源,极为清晰地梳理出骈文的发展历程。综上可见,骈文实肇始于屈宋骚赋,但与其更近者却是汉赋。
要之,文体学视角是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教师从这一视角切入,更有助于理清某一文体的完整发展演进历程,从而引导学生在学习中不断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培养创新意识,真正能够自主学习。
[1]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于北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4] 赵晔.吴越春秋校注[M].张觉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6.
[5]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
[7] 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周本淳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 李兆洛.骈体文钞[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0]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 傅东华.文学百题[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12]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3] 谭家健.六朝文章新论[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14]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孙梅.四六丛话[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8] 铃木虎雄.赋史大要[M].上海:上海正中书局,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