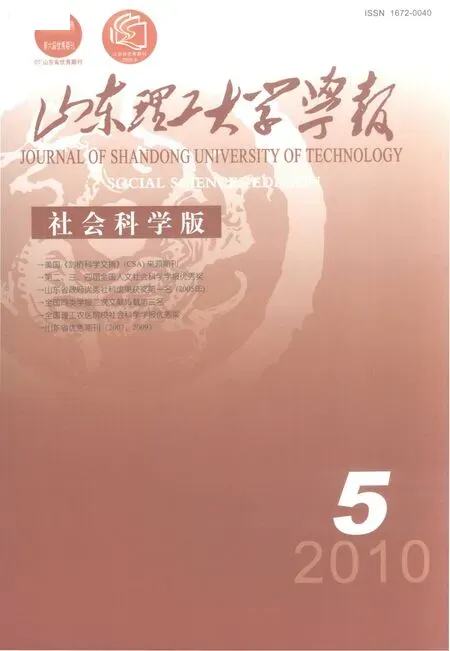模糊决策研究进展综述
杜秀芳,张科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模糊决策研究进展综述
杜秀芳,张科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模糊决策是决策学研究中一个极具特色的领域。对于模糊的定义,国外学者对模糊本质的认识可归纳为无视模糊、二阶概率表征、信息缺失和信息来源四种类别。针对经典范式的不足,现有研究主要从对表征模糊的概率形式进行扩展、模糊的语言表征和概率表征、增加对被试间设计、考察模糊决策中的个体差异以及增加损失——收益背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扩展。同时,除介绍五种传统的模糊决策观点外,文章还介绍了以Tversky的“相对无知”理论为代表的新理论。文章最后,结合现有模糊决策的现状,提出了未来研究应指向注重个体差异、研究手段多样化。
模糊;决策;模糊规避
人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决策问题大多属于不确定决策问题。1921年,Knight将不确定决策(uncertainty decision)分为两类:决策者能够对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作出精确估计的称为风险决策(risk decision),[1]而不能作出精确估计的称为模糊决策(ambiguity decision)。而学者将模糊决策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提出则从对模糊规避的研究开始,Ellsberg则第一个对模糊规避展开了研究,提出了经典的“双色问题”。在“双色问题”实验中,有A、B两种罐子,而从A罐抽中一种颜色的球的概率是50%,而B罐中抽中特定颜色的比例却是不确定的——即存在模糊。当奖励相同时,期望价值理论认为被试对两种选项没有明显偏好,但实际上大多数被试选择了A罐子。这种同时面对明确概率和模糊概率时,被试选择前者的现象,Ellsberg将之称为“模糊规避”(ambiguity aversion),也称Ellsberg悖论。该实验正式将模糊作为一种影响决策结果的因素假如实验研究过程中,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模糊决策研究。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模糊决策的研究已经形成体系,但我国学者却对该领域甚少涉足。因此,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总结,为国内模糊决策研究提供方便。
一、模糊的界定
虽然模糊决策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但国外学者对到底什么是模糊仍未达成一致的看法。[2][3]目前对模糊本质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无视模糊
这种观点是根据是否存在模糊,把决策情景分为存在和不存在模糊两种。其中最激进的是彻底的主观期望理论支持者,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认为期望效用值等于选项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与效用值的乘积,而在实际评估过程中,由于所有事物发生的可能性只是一种主观评价,事件的效用值(value)本身也只是一种主观评价,因此不存在概率不确定的“模糊”事件。对于这种观点,Weber指出:“这或许是一个合理的描述性的观点,但对于解释模糊规避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帮助。”[2]由于无视模糊(ambiguity ignorance)这种观点本身在理论假设和解释力上的缺陷,所以已极少为学者引用。
(二)二阶概率
首先,这里的二阶概率(second-order proba-bility)是指利用一组概率区间表征模糊程度的方法。例如,Becker和Brownson用概率的间隔定义模糊规避的强度,例如,缸子里有10枚彩球,红球和黑球的比例未知,那么抽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在0到1之间,而不是单一的概率点0.5。[4]他们认为概率间隔越大,模糊规避的强度越高。二阶概率是传统模糊决策研究中的较为主流的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人们是根据对某个事件发生的信念进行决策,不同模糊情景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并且模糊的程度可以用二阶概率进行表征。Ellsberg是持有二阶概率观的学者之一,他在二阶概率观点的基础上,设计出上文提到过的经典的“双色问题”及“三色问题”实验。[3]
尽管很多模糊决策理论都采用了二阶概率的观点,但该观点同样存在缺陷。首先,模糊不能完全由二阶概率所替代。实验表明,当明确的二阶概率与不做数字表征的模糊情景同时呈现时,被试更愿意选择已知的二阶概率。Weber也指出:“假如混合下注的赌博转化为等价的一阶段赌博,那么二阶概率和确定概率只能导致相同的决策。”此外,当根据Savage公理进行数理逻辑推导时,二阶概率同样不能验证违反主观期望理论的现象,这与实际情况相悖。Yates和Zukowski[5]的研究详细讨论了决策者感知到的模糊以及决策情境中的模糊能否与主观二阶概率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实中二者是不能等价的。
(三)信息缺失
该观点认为信息缺失(missing information)是造成模糊的本质原因。持该观点的学者并不限制模糊的表征形式,而是试图描述模糊产生的过程,形成能反映模糊本质的操作定义。Ellsberg认为“双色问题”中B罐中球的构成比例就是一种缺失信息,可以通过被了解而消除,他还提出了一种操作定义,即认为“(模糊)是影响到个体对选项相对可能性评价的自信程度的事物属性,其程度依赖于信息的数量、类型、可靠性以及‘群体一致性’”。除此之外,Einhorn和Hogarth的定义将焦点集中在可获得信息的数量上,他们认为:风险是了解全部信息,但结果是用一个精确概率值来表示的状态,而模糊则是处于风险和对相关信息完全不了解之间的状态。[5][6]另外,Bleaney和Humphrey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出:“通常模糊是相关信息没能被认识或理解的一种状态。”[7]
(四)信息来源
信息的不同来源作为构成模糊的原因之一,信息来源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其主要包括信息来源的数量、权重、可靠性,以及不同来源信息的一致性。本质上来说,这种对信息来源的考虑并不是希望直接获得操作定义,或形成一种表征模糊的方式,而是通过分析模糊的来源进而说明模糊的本质。
首先,信息来源数量的增加与模糊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传统观点认为信息来源的增加有助于信息交流从而消除模糊。但也有研究表明可获得信息来源的增多并不能消除决策情景的模糊性。[8]其次,早期研究发现信息具有“含义”和“权重/数量”两种纬度,多种不同信息有可能同时在这两种维度上存在多种不同的状态,从而导致在对模糊进行评估时增加情景的模糊程度。[8][9][10]同时,决策者对信息来源可靠性的评估也会影响对模糊程度的评价。最后,多种信息之间的不一致性会大大提高模糊性。Ross利用不同专家之间的差异观点模拟了意见不一所造成的模糊,并进一步证明这种模糊会延长决策层的决策时间,同时使决策者更加关注不同意见中的消极信息或与自身偏好相反的信息。[11]
上述观点中,前两种观点是试图利用数值分布来表示模糊,而后两种则主要是对模糊的本质进行阐述。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更好进行实验控制,大部分学者还是利用概率分布作为模糊的表征或引发模糊感的工具。
二、模糊决策研究的经典范式及其演变
长期以来,大多数模糊决策研究采用了Ellsberg的“双色问题”或“三色问题”的经典实验范式,但随着模糊决策理论的不断发展,许多学者也在很多方面对经典范式进行了细化和改进。
(一)模糊决策研究的经典范式
自Knight对模糊和风险进行区分之后,很多学者都试图在实验中将二者分开,在排除风险的条件下对模糊决策进行研究。但是只有Ellsberg于1961年提出的“双色问题”以及“三色问题”成为了其中的经典范式,[4]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采用。“双色问题”实验假设有A、B两个罐子,各装有100枚台球的,其中A罐中有红球和黑球各50枚,而B罐中两种颜色球的比例未知。实验要求被试从其中一个罐子中取一枚球,但在抽取前,要首先对将要抽出的球的颜色进行预测。当所抽出球的颜色与猜测的颜色相同时,被试获得现金奖励,否则没有奖励。按照期望理论和主观期望理论,A、B两个罐子的主观价值相同,所以被试选择两个罐子的比例也应基本一致,但实际上大部分被试选择了从A罐中抽取。而“三色问题”则是从“两色问题”改进而来。该实验中,决策者面对的不再是模糊不清的风险问题,而是不涉及损失收益的纯粹的模糊决策问题。
(二)经典模糊决策研究范式的演变
经过多年的发展,许多学者正对这种经典范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并且不断地从单一的研究模糊规避现象扩展到全面的模糊决策问题的研究。这些改进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对概率表征的细化。
在对模糊的表征上,“双色问题”采用间接的二阶概率来表征模糊情景,而学者们则从多方面对这种设计进行了改进。首先,实验多运用数字表征的方法,例如Knight[1]、Ellsberg[3]及Tversky[11][12][13]为代表的多数学者采用数字值来表征模糊。但是,这种表征方式受到了质疑,Savage提出二阶概率并不能完全代表模糊的本质。其次,二阶概率的表述一般是间接给出的,并没有明确的概率区间分布。研究者在后来的实验中不仅加入了明确的概率区间表述,还详细研究了不同区间范围对模糊决策的影响。一般认为,当决策者面对的二阶概率为中等概率水平时,会倾向于模糊规避;而面对低概率和高概率区间时,则会出现模糊寻求的趋势。采用数学逻辑的方法解释模糊决策时,学者们对表征模糊的概率值是否具有“非加性”(no addictive)存在争论,经典“双色问题”并没有对此进行讨论,而后来的研究则证实了概率表征的“非加性”。
2.引入对模糊的其他表征。
作为对数字表征的形式,研究者首先采用了语言形式(Verbal measure)来代替二阶概率,而Budescu和Wallsten[14]及Windschitl和Wells[15]先后在实验中利用语言表征代替了数字表征,并证明数字表征形式可能会对决策者构成误导。在最近的研究中,Windschitl和Wells[15]分别利用语言和数字两种不同的方式向被试呈现不确定事件,最终通过三个不同的实验不仅说明被试对于语言描述更为敏感、较为偏好,更证明了语言描述条件下能够实现对行为意图的更好预测。除增加语言表征形式外,也有学者利用情景重现的办法取代直接呈现数字。例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Bleaney和Humphrey[7]将被试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实验中,主试只向控制组呈现数字形式的模糊表征,而实验组除数字形式表征以外还能对赌博事件进行一段时间的实际观察。实验结果表明,实际的情景呈现比数字呈现似乎有更多的信息,从而降低了模糊,减少了模糊规避现象的出现。
3.考察比较情景。
在原有的“双色问题”实验范式中时间是将模糊项和精确项同时呈献给被试,并要求被试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是Tversky[11][12][13]对实验的这一特征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正是这种比较条件的存在才产生了模糊规避现象,假如两种条件分开呈现则模糊规避将不再存在。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在实验中将被试随机分为A、B、C三个组,其中向A组被试在具有精确概率的事件以及具有模糊概率的事件两个选项分别进行估价,而对被试组B只呈现精确选项,而被试组C只呈现模糊选项,并分别进行估价。最终试验结果发现,在同时呈现两种选项时,模糊规避现象显著;在对两种选项分别进行呈现时,模糊规避现象却消失了。根据该实验的结果,Tversky提出了全新的模糊决策理论——“相对无知假设”和“能力假设”。[16]
4.考虑个体差异。
在原有的经典“双色问题”范式中,只是将被试作为有限理性的决策者进行统一处理,假设所有被试都不存在个体差异。但是,随着实验证据的积累,不断有新的观点提出来。例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Tversky的研究就证明了包括知识、经验和技巧成分在内的“个体能力”对模糊决策有直接的影响,[11][12][13]Goodie提出“控制感”也是影响模糊决策的重要因素。[17][18][19]最近,Borghans与Heckman在实验前要求被试回答包括瑞文测验、“大五”人格量表以及认知能力测验在内的三种量表,然后再对同时包含风险决策情景和模糊决策情景的实验进行回答,结果其研究结果发现人格及智力因素不会影响模糊规避的出现,而在性别上,女性被试偏好模糊寻求,风险规避;男性被试偏好模糊规避,风险寻求。[20]
5.模拟应用情景。
许多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模糊决策研究本质上应当是对存在模糊的决策事件进行抉择的过程,因此,模拟现实情景、观察应用环节上的模糊决策问题也同样十分重要。
在医疗健康领域中,在一项对住院病人的研究表明,[21]在治疗过程中无论医生告诉患者多少信息,患者都想额外知道更多与病情有关的信息,但患者对自己的手术方案或治疗方案由拒绝作出抉择,转而依赖医生。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模糊规避造成的。而Ritov和Baron对儿童接种疫苗问题进行的模糊决策研究,同样得到了类似的结果。[22]
在公司经营中,Keller和Sarin等人的实验证明了:决策者面对模糊情景时,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对作出更好的决策并无帮助。[23]Udo和Eckwert最近还对公司的模糊决策对市场转变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市场中存在价格上展开竞争,在市场份额上构成威胁的公司存在时,公司所占市场份额就与招工数量和公司核心技术上的模糊决策有密切的联系,并且认为市场前景明朗时——即市场前景模糊性低时——更容易达到理想的决策效果。[24]
除以上五个方面的改进外,针对“双色问题”和“三色问题”进行的改进还包括:对双色问题中每个罐子里包含的台球数量进行变更、将台球改为扑克牌、加入对现实情景的模拟等,这些研究均是针对具体研究指标进行的修正和扩展,这里不再做重点介绍。
三、模糊决策的理论解释
模糊决策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实验范式的演变过程相类似,也经历了从对专注于解释模糊规避现象的理论,逐渐发展为较全面的模糊决策理论的过程。
(一)传统模糊决策理论
多数学者在对各种模糊决策进行解释时多是以主观效用理论或期望价值理论作为基础的,他们只是试图解释模糊规避现象,经过总结分析,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别。
1.敌意本质假设(hostile nature hypothesis)。[5]
该假设认为,在二选一模糊决策中,两个选项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竞争或相互敌对的关系,因为被试认为其中一种选项具有的信息更多(Roberts,1963),或者可控性更强,从而使得该选项胜出。[24]这种假设缺乏明确的比较标准,且容易证伪,但却对后来的“相对无知假设”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2.他人评价假设(other-evaluation)。[1][25][26][27]
由于个人总是希望在他人面前保持优秀的、正确的、有能力的积极形象,因此在模糊决策过程中,如果决策者认为所作决策会被他人评价时,就会选择更可能获得积极评价或避免消极评价的选项,以维护自身形象。
3.自我评价假设(self-evaluation)。[28]
该假设与他人评价假设类似,不同在于该假设认为决策者会进行自我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决定进一步决策所采取的策略。
4.被迫选择假设。[5]
该假设认为当所有选项的效用基本相同时,被试会自然选择模糊程度较低的选项,但这种观点已为多个实验所证伪。[4][25][28]
5.锚定调节理论。
该理论认为:所谓模糊规避和寻求是由于被试首先对所获得的概率估计设定锚定概率值再进而对概率估计进行调整的结果。例如,Einhorn和Hogarth要求被试在冲突的证据基础上对事件的概率进行估计(例如,两名目击证人看到一场车祸,一个说肇事车辆为蓝色另一个声称是绿色),实验结果说明被试再进行判断是确实存在首先设定“铆钉”的行为。[6][28]
最早提出时,这五种理论都是在单一的解释模糊规避现象出现的原因,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开始放弃原有的理论,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试图用普遍的决策心理机制来解释模糊决策问题,而不再仅仅局限于解释单一的模糊规避现象。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二)回归模糊决策——对传统理论的改进
在Curley和Yates[25]的总结之后,虽然也有新的理论假设提出,但大部分都未能突破上述五种假设的范畴。随着在实验设计和哲学基础上的突破,一些学者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新解释。例如英国学者Roca、Hogarth和Maule就在他们的实验结果基础上提出了模糊寻求来源于现状偏好(state quo bias)的观点。[29][30]该理论在实验中同时要求被试在当下发生的事件与未来的事件同时进行估价,通过估价反映被试对不同选项的偏好。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对当下发生的模糊事件的偏好高于对未来事件的偏好。研究者认为该结果表明被试对模糊的偏好只是一种来自对当下发生事件的偏好。
此外,Tversky通过被试间设计得到的结果提出了全新的“能力假设”。[11][12][13]该假设认为:当要求在确定概率的随机事件(chance event)和模糊事件之间进行选择时,决策者首先会根据两个选项所属的不同领域,对自己具有的能力水平(即决策者的技能、经验、决策者能够掌握和已经掌握的客观知识的总和)进行评估,进而选择具有较高能力的选项。因此,当能力较高的选项为模糊选项时就出现模糊寻求,否则就出现模糊规避。
随着研究证据的积累,Tversky对其理论也进行了发展和补充,提出了“相对无知假设”和模糊来源的概念。[13]“相对无知假设”是指:当面对模糊决策情景时,决策者会将面对的情景与模糊性相对较少的情景进行比较,同时还会将自己在该领域具有的能力水平与其他人的水平加以比较,如果存在模糊性较小的情景或更有能力的个体会表现出模糊规避,反之倾向模糊寻求。与“能力假设”相比,“相对无知假设”增加了决策者与其它相关对象之间的比较。另一方面,Tversky在“相对无知假设”中强调:“模糊决策不仅依赖于模糊程度,同样也取决于模糊的来源……”。这种“模糊来源”一方面是指决策者具有的多个模糊情景所属领域的能力水平;另一方面则指决策者对于不同模糊来源事件的敏感程度。
“相对无知假设”提出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验证和扩展,[31][32]例如Goodie[17][18][19]就曾经进一步提出了“控制感假设”。他的理论认为,所谓“能力”只是产生控制感的条件,实际上是被试对其在决策情景具有的控制力的评估——也被其成为“控制感”——决定了最终的决策结果。在实验中,他要求被试对自身具有能力但没有“控制感”以及具有“控制感”但没有能力的单个选项进行选择,结果与“能力假设”相反,被试没有选择具有“能力”的选项,而是选择了自己具有“控制感”的选项。然而,在该理论的解释力未能超过“相对无知假设”。[33]
四、模糊决策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首先,现有模糊决策研究经常将对模糊规避现象的研究作为切入点,甚至有将模糊规避研究等价为模糊决策研究的误解。但实际上,模糊规避研究只是将模糊决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较为狭隘的研究领域;模糊决策则强调存在模糊的决策情景中人们决策机制,是一个更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二者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非等价关系。
其次,在模糊决策研究中对个体差异的考虑较少,而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被试的模糊决策的研究则是完全空白。文化背景很有可能影响模糊决策过程的最终结果。已有研究证明:在中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个体,其思维结构、认知方式以及行为特点都有显著的差异。[34]现有的研究都是以欧美被试最为决策者进行的研究,是否中国人在模糊决策过程中会有相同的表现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对模糊决策问题的跨文化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第三,现有的模糊决策研究手段过分单一,研究视野存在局限。从所用范式来看,大多数实验还是集中在传统决策研究的二选一问题上,本质上仍然是对“两色问题”和“三色问题”的重复和再现,并没有考虑到多个选项之间的决策问题;从方法上看,仅采用单一的实验法,这虽然保证了对无关因素的控制,但忽略了生态效度。此外,统计方法过于单一,只是运用方差分析或差异检验对已有数据进行分析,并不能全面而深入地挖掘数据的含义。
[1]Knight F.H.Risk,Uncertainty,and Probabil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Keynes,J.M.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London,Macmillan.1921.
[2]Sarin,R.K.and M.Weber.Effects of Ambiguity in Market Experiments,Management Science 1993,39,603-615.
[3]Ellsberg,D.Risk,Ambiguity and the Savage Axiom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1,75,643-669.
[4]Becker.Selwyn W.and Fred O,Brownson.“What Price Ambiguity?Or the Role of Ambiguity In Decision-Mak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4,72,62-73.
[5]Yates,J.Frank andLisa G.Zukowski.“Characterization of Ambiguity in Decision Making”,Behavioral Science 1976,21.19-25.
[6]Einhorn.Hillel J.&Robin M,Hogarth.“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in Probabilistic Inference”,Psychology Review 1985,92,433-461.
[7]Michael Bleaney and Steven J.Humphrey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Generalized Ambiguity Aversion Using Lottery Pricing Tasks Theory and Decision 2006,60,257-282.
[8]Keynes,John Maynard.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London:Macmillan,1921.
[9]Fellner,William.“Distortion of Subjective Probabilities as a Reaction to Uncertain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75,670-694.
[10]Cohen.Michele,Jean-Yves Jaffray,and Tanois Said.“Individual Behavior under Risk and under Uncertainly:An Experimental Study”.Theory and Decision 1985,18,203-228.
[11]Heath,Chip,and Amos Tversky.“Preference and Belief:Ambiguity and Competence in Choice and Uncertainty”,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1,4(1),5-28.
[12]Fox,Craig R.,and Amos Tversky.“Ambiguity Aversion and Comparative Ignoran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110(3),585-603.
[13]Fox,C.R.Rogers,B.A.and Tversky,A.Option traders exhibit subadditive decision weights,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6,13,5-17.
[14]Thomas S.Wallsten,David V.Budescu and Amnon Rapopor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86.Vol.115,No.4,348-365.
[15]PaulD.Windschitl&GaryL.Wells Measuring Psychological Uncertainty:Verbal Versus Numeric Method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Applied 1996 Vol.2.No.4,343-364.
[16]Keppe.Hans Jorgen and Martin Weber.“Judged Knowledge and Ambiguity Aversion”,working paper 1991 No.277.Chrislian-Albrechts-Universitat.Kiel,Germany.
[17]Goodie,A.S.&Fantino,E.An experientially derived base-rate error in humans.Psychological Science.1995,6,101-106.
[18]Goodie,A.S.Paradoxical betting on items of high confidence with low value:The effects of control on bett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2003,29,598-610.
[19]Goodie A.S.&Diana L.Young.The skill elemen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Control or competence?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2007 Vol.2,No.3,June,pp.189-203.
[20]Lex Borghans.Bart H.H.Golsteyn.James J.Heckman.Huub Meijers Gender,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 Ellsberg Paradox,In press.2009.
[21]Slrull,WilliamM.,Bernard Lo,and Gerald Charles.“Do Patients Want to Participate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84,252,2990-2994.
[22]Ritov,liana and Jonathan Baron.“Reluctance to Vaccinate:Omission Bias and Ambiguity”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990,3,263-277.
[23]Keller L.R.Sarin R.K and Jayavel Sounder pandian An examination of ambiguity aversion:Are two heads better than one?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vol.2,no.6,December 2007,pp.390-397.
[24]Langer,Ellen J.“The Illusion of Control”.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5,32,311-328.
[25]Curley.Shawn P.Frank J.Yates and R.A.Abrams,“Psychological Sources of Ambiguity Avoidanc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86,38,230-256.
[26]Viscusi,W.K.and H.Chesson.Hopes and Fears:The Conflicting Effects of Risk Ambiguity,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9,47,153-178.
[27]Frisch,Deborah and Jonathan Baron.“Ambiguity and Rationality”,Journal of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I,1988,149-157.
[28]Einhorn,Hillel J,&Robin M.Hogarth.“Decision Making under Ambiguity”Journal of Business 1986,59,S225-S250.
[29]Merce Roca.RobinM.HogarthA..John Maule.Ambiguity seeking as a result of the status quo bias J Risk Uncertainty 2006,32,175-194.
[30]Stefan T.Trautmann&FerdinandM.Vieider&Peter P.Wakke.Causes of ambiguity aversion:Known versus unknown preferences J Risk Uncertainty 2008,36,225-243.
[31]Fox,Craig R.,andMartinWeber.“Ambiguity Aversion,Comparative Ignorance,and Decision Context”,Organizational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2,88(1),476-498.
[32]Arlo-Costa,H.and Helzner,J.“Ambiguity Aversion: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ndeterminate Probabilities”,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mprecise Probabilit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Pittsburgh,Pennsylvania,2005.
[33]Christopher Koch and Daniel Schunk The Case for Limited Auditor Liability-The Effects of Liability Size on Risk Aversion and Ambiguity Aversion 2007.
[34]侯玉波,朱滢.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2,(1).
(责任编辑郑 东)
B842.5
A
1672-0040(2010)05-0102-06
2010-06-13
杜秀芳(1969—),女,山东沂南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