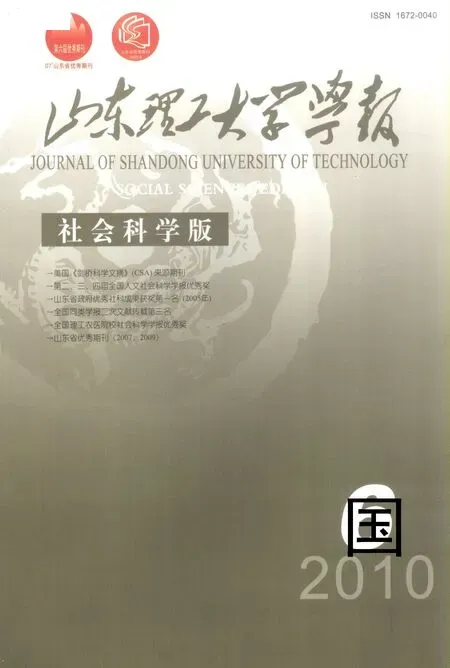生态美学下的原始神话阐释——论《山海经》中的生态美学意蕴
杨 倩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是20世纪后期,中国学者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在各种生态理论不断丰富发展下提出的一种美学观念,也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实际上,它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延伸和新超越。”这种“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1]生态美学理论虽产生于后现代化时期的工业社会,却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生态美学中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和谐共生观念是中国哲学思维的起点之一,且早在原始社会时就已初见端倪。徐恒醇提出中国传统的生态意识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的主题,即“‘天人合一’的自然本体意识,‘亲亲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念,‘取之有度用之以时’的生态经济观念,体证生生以宇宙生命为依归的生态审美观念以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永续发展的价值取向等”[2]34事实上,上述思想在集上古传说文化之大成的《山海经》中就已有具体展现。《山海经》约成书于春秋末至汉初,当时正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生态存在论哲学思想逐步形成之时,此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除了涉及到历史、地理、天文、宗教、民俗等多个学术领域外,还以直观的思维方式和好奇的眼光观察、记录世界。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体系
“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既指自然与人在生存方式上密不可分、相应相合的整体性,也强调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的暗合共通、和谐统一性。生态美学赖以建立的“生态论存在观”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杜维明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三个“基调”:一是存在的连续,即“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二是有机的整体;三是辩证的发展。[3]59这三个方面即概括了《山海经》中雄伟瑰奇的生态之美,也凝聚了我国古代的存在论生态观念。
首先,“天人合一”中的“天”并非先秦儒道两家所强调的是“神道之天”,而是指构成有机的整体系统的自然宇宙,包括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天地万物。是禹所言的“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海外南经》)。在此之下,人和其它生物虽形状相异,却同为“神灵所生”,彼此相交融,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之美,更是处在“生态关系”之下的原生态大美。“所谓的生态关系,则是指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是除了人和社会以外的自然事物、各种生物和其他物质系统的总和”。[4]书中以山、海为坐标划分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自然界中所有物象:山川海洋、河流矿产、飞禽走兽、奇珍异宝,甚至对日月雷电等天文现象也穷尽其中。书中记载了约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条水道;介绍了193种鸟兽鱼虫(鸟56、兽89、鱼37、虫11),其中有形态介绍者共有188种(鸟53、兽89、鱼35、虫11),占总数的97%左右;[5]42收载158种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涉及到植物分布、生态、形态特征和功用诸方面,书中也出现禾、稻、菽,稷等植物,并有“后稷始播百谷”的记载。[6]268-276书中甚至还有矿产及其产地的记录,矿产可分为石、玉、碧、丹垩、金属等,而以石、玉两类最多。如:“岐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珉,其上多金玉”(《中山经》)等。在这一体系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万物不仅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认识实体,还成为人的悟性的直觉对象,与人和社会融为一体。
能的生命中体会万物其次,生态美学观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生态整体主义原则,其核心观点是“生态平等”,即主张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自有其价值而处于平等地位。《山海经》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严密的自然世界,正是因为万物的共存,生态之美才展现于其中。人与万物同处一域,“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万物同人一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内在价值,人、甚至是神也只是生态体系中的一个因子,而不是主宰者和统治者。这种平等体现在物种的外在形体上。书中的许多生物是人兽或人禽的组合体,如“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海内南经》)、“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海外北经》)、“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大荒南经》)等。神、动物、人的形象融合了人与动物的形体特征,反映了初民以已度物将自身与自然置于同等地位来交流之心态。即天地所生之物均有自己存在的权利和价值,虽然物竞天择,但这不影响其各自的发展,诚如《中庸》所言“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与物在生命的意义上是相同的,人类只有从自身的生命中体会其他生命的价值,才能尽其性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北宋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即“无一物非我”,进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是上述思想的典型表述。同时,这种平等还表现在初民的“生命一体化”观念,他们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草木禽兽等皆与自身具有相同的生命本质,彼此之间可以沟通、交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就类似于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vlor,1832~1917)提出的“万物有灵观”,泰勒同样把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自然力加以拟人化或人格化,将其视为与人类自身一样具有生命和思想情感。《南山经》载肃慎国有树雄常“先入伐帝,于此取之”,郭璞曰“其俗无衣服。中国有圣帝代立者,则此木生皮可以衣也”;《西山经》载“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有兽焉,其白首赤足,名曰朱厌,见则大兵”、鳐鱼“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鸟、兽、鱼等自然万物皆与上天的精神相通,正是在这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中,“天人合一”的生态体系得以构建完成。
二、敬畏自然的生态感悟
在原始社会,由于自然对人的绝对性统治和人类抽象思维的限制,先民对日夜更迭、暴风雷电等周而复始的自然现象甚感神秘和恐惧,有神论和崇尚万物有灵的思想使他们坚信自己的命运与上天庇护、保佑存在必然性,因此对于自然极为敬畏。这种“敬畏”既包括对自然的畏惧,也包括对自然尊重和的崇拜。
对自然的敬畏首先表现为对自然中的物象的神化。人类有意识的将它们具有的某些人所不及的特点夸张、放大,而是这些物象被神化。他们的外形多为人与一种或多种兽的杂合,且兼具人与兽的能力,其中以人面蛇身、人首龙身、人首鸟身居多,如:《海外北经》记载“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海外北经》载:烛阴“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海外东经》载“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事实上,这些人兽杂合的形象或许出于人类对自然的惧怕,他们将可能对自身有威胁的动植物创造成神抵,通过对其祭祀与尊崇,使自身免于伤害。以山为例,《山海经》中的山几乎都有各自的山神。山神的外貌多为人与常见动物的组合体,既神秘威严,又具亲和力,如《西山经》所载的昆仑之丘,“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崇吾之山“其神状皆羊面人身”,先民们对他们顶礼膜拜,祈福求禳。如“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汤之以酒百樽,婴以纯粹的牲畜,还要一百樽酒,环绕陈列一百块珪和一百块璧。百珪百璧。其餘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羭山,祭祀时要用烛斋戒一百天,用一百种毛色。这里的神与后世的人格神不同,他们所承载的是自然界中无所不在的神秘力量,而这种力量至今人类仍没完全破译,更不用说人完全的支配。对此,恩格斯讲过了一段著名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场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460
对自然的敬畏还表现为对“巫”的信仰和崇拜。中国古代的萨满式(Shamanistic)文明认为世界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并能相互沟通,进行沟通的人物就是“萨满”(shaman),也就是氏族中的巫师。在周代之前,巫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通过“绝天地通”来预测国运、占卜战争、祈祷求福、驱邪避祸。《山海经》中,有关“巫”的描述比比皆是,如:“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对巫和巫术活动的重视,是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的直观反映。事实上,敬畏自然,与其说是一种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也是对生命的敬畏。
三、生生不息的生态存在认识论
“生态美最根本的性质是它的生命性。生命是美的重要性质,美只能是对生命的肯定形态,从这个意义讲,美在生命”[8]9《周易·系辞上》指出:“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系辞下》也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是指个体生命和系统生命的生活与存在,也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山海经》中对此有多处涉及,如“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名,弄名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大荒北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海内经》)都是先民对“生”的延续和谱系的记录。生态美学是从生命的普遍联系来看待生命,重视“易”,即重视生命的联系性和循环性。伴随“易”的动态过程,生命处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南山经》载鯥鱼“冬死而夏生”,能从冬眠中苏醒复生。《海外北经》载“无启之国”,郭璞注称其人“死百廿岁乃复更生”。但人与物毕竟不同,生命恒久的存在人类永恒的希冀,《海外南经》载有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郭璞注:“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大荒西经》称有“三面之人不死”;《海外北经》中的无晵国,“其人无嗣”。郭璞注作:“其人穴居,食土,无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岁乃复生。”但这种希冀却又注定无望,于是“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化”就成了先民对“生”另一种追求。人死后可以通过化的形式以其它生物的形态存在,使生命延续。人可化为动物,如人面龙身的“鼓”,被“帝”诛后,“化为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黄文白首”。(《西山经》);人可化为植物,如“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枫木,蛋尤所弃其梗桔(郭注:蛋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是谓枫木。”(《大荒南经》)人还可化为新的人,如“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埂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除此之外,“化”还有其他的情形,如载“鱼妇”在“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之时“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大荒西经》),刑天被断首后“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等。
除了在生殖观念中有所反映,“化”还有着深层的精神价值。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鲧复生禹所显示出的是先民在对自然敬畏背后的抗争,在“天行健”的生生不息精神中,肉体融入自然和生态,生命和精神得以延续和超越。这是先民在懵懂中对生生不止、自强不息精神的追求。
四、人与自然价值关系中的生态之“道”
人与自然除了审美关系还存在价值关系。生态美的提出并不意味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否定,极端的“自然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都是不可取的。曾繁仁先生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中指出人与自然的平等并非绝对的平等,人类和动植物在生命链中所处的位置也并不完全相同,每个存在物在生命链条中都具有生存、繁衍和体现自身价值的权利,这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生态整体观指导思想。陈望衡也明确提出“生态美的第二性质是宜人性”[8]《山海经》对自然的宜人性极为重视,几乎所提及的物种都突出它宜人的效用,仅以《南山经》中所载为例,其中记载宜人的植物有:祝余,“食之不饥”、睾苏“食之不饥,可以释劳”、薰草“佩之可以已疠”、杜衡“食之已瘿”、荀草“服之美人色”;兽类有:鹿蜀“佩之宜子孙”、玄龟“佩之不聋,可以为底”、溪边“席之皮者不蛊”;禽类有:灌灌“佩之不惑”、数斯,“食之已瘿”;鱼类有:赤鱬“食之比疥”等。
人类可以利用自然,但要遵循其“道”。“道法自然”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出发点,在中国道家范畴中“道”乃万事万物之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切事物只有遵循道,才能最终达到至善境界,反之,出现的只能是灾难,《山海经》就描述了破坏自然平衡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如《海外北经》载“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溪泽。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大荒北经》载“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由于九头蛇贪得无厌的消耗山中的食物,造成了凡是它经过的地方就会成为沼泽,气味苦辣,飞禽走兽都没法居住的后果。为此,“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为民除害杀相繇,又随之而成的水患同样使人无法生存。而这与美国当代著名的生物海洋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在1962年出版的文学生态批评的经典之作《寂静的春天》中所讲的“是一个将各种生物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再也不能对它漠视不顾了,它所面临的现状好像一个正坐在悬崖边沿而又盲目蔑视重力定律的人一样危险。自然平衡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它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有时这个平衡对人有利。有时它会变得对人不利。当这一平衡受人本身的活动影响过于频繁时,它就会对人不利”[9]23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可见,自古至今人类在利用自然中所出现的社会发展和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可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为在物与物关系的背后归根还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生态审美的角度看,万物不仅仅是人的对象化客体,万物存在的意义即是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
五、诗意栖居的生态家园
“诗意的栖居”是德国哲人海德格尔在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歌时提出的美学命题,也是海氏存在论哲学美学的内涵。“栖居”作为一种审美的生存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成为生态美学的重要范畴。而“家园”是人类栖居的场所,同“栖居”一样,“家园”也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德语“生态学”okologie正是自希腊语“oikos”,即“人的居所、房子或家务”。“家园”既是每个人繁衍生息之地,也是精神上的最终归宿之处,这些命题虽有西方哲人提出,但无独有偶,中国的《山海经》中对至乐净土般家园的描写也体现了先民渴望“诗意地栖居”在“家园”的追求。《山海经》中除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描述外,还展示了一副有如西方伊甸园般的至乐净土。《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凰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愛有百兽,相群爱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大荒南经》中的民之国“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愛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愛有百兽,相群愛处,百谷所聚”。《海外西经》载“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有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这种类似于后人桃花源般在这种世界中,万物生灵皆能和谐相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四种声音在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这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但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地自为地持立和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任何一方是有限的。或没有其他三方,任何一方都不存在。它们无限地相互保持,成为它们之所是,根据无限的关系而成为这个整体本身”。[10]210
事实上,生态意识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某种不和谐关系,人对自然过度的主宰给彼此都带来了对抗性的痛苦,对生态美的追求也正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和对自身理想存在状态的设想。《山海经》中对“天人合一”哲学的崇尚,对“敬畏自然”观念的感悟、对“生生不息”的践行,以及对“诗意栖居”家园的终极追求,无不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思想。同时,这些思想也是建设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之中的重要资料,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完善和现实行为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1] 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J].文学评论,2005,(4).
[2] 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M].北京:三联书店,1999.
[4] 鸥宗启,庄小彤.论自然美与自然生态美[J].广西社会科学,2006,(2).
[5] 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6] 丁永辉.《山海经》与古代植物分类[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3).
[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 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9] [美]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0]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