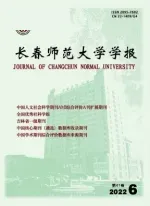“暴力”何以“甜蜜”?
——评伊格尔顿“只有西方文化才有悲剧”说
隋欣卉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伊格尔顿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可谓声名赫赫,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文学的一些见解直至今日依然撼人心魄:文学有其特定的历史性而非一个普遍的定义,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文学,任何东西 (甚至莎士比亚)又都能够不再成为文学。[1]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下,我们期待同一作者能够对悲剧这个虽然过时的话题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然而,当我们在20年后的这部洋洋近40万言的《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中看到只有西方文化才需要、才有悲剧这种形式时[2],很难不产生这究竟是否伊格尔顿所言之疑问;另一层使人不安的疑问来自“只有”(only)。因此,理清其内在的理路并揭示该说背后的悲剧观念就势在必行。
事实上,上述令人起疑的断言并非伊格尔顿的己见,而是顺着苏珊·朗格对悲剧的看法推导出的结论。朗格在其《情感与形式》中说“悲剧是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不是世界各地都有的。悲剧概念要求一种个性感 (A sense of individuality),这是某些宗教和某些文化——甚至是高度文化——所未曾孕育的。”[3]如果说朗格还只是泛泛而谈个性对悲剧的重要,而伊格尔顿则由此走上了极端——从某些文化没有悲剧到除了西方文化都缺少悲剧。关键的问题是朗格的“个性说”能否站稳脚跟,如若不然,伊格尔顿的推导自然也就轰然倒塌。
在朗格看来,“只有在人们认识到个人生命是自身目的、是衡量其他事物的尺度的地方,悲剧才能兴起、才能繁荣。”[3]照此说来,古希腊悲剧理所应当如此;然而,古希腊人是否具有她所说的“个性”是值得怀疑的。毕竟,人们有着如下的共识:个性在西方是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才开始兴风作浪的。而在这种悲剧成因“个性说”的观照下,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就开始了欧洲悲剧的“伟大传统”——因为它是一部“关于自我判断、自我预见、自我毁灭的伟大剧作”[3]。显然,朗格是从悲剧的个案抽象出普遍的意义,然后再推诸整个悲剧世界的。仅仅从内在逻辑上看,这里并非严丝合缝,从某些个体抽象出的框架何以必然能框住另一些个案呢?转向具体的分析,问题就被逼到一个无可回旋的角落——如何理解《俄狄浦斯王》乃至整个古希腊悲剧。毋庸置疑的是,后世对古希腊悲剧的每一次解读都是一次再创造,带有自己时代意识特殊印痕的再创造。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塑造古希腊悲剧,朗格自然也不例外。问题是,我们在重新塑造时不能无视文本的证据,不能以今日之见强加于先人。雷蒙·威廉斯在对古希腊悲剧的这种流行见解提出批判后语重心长地提醒说:“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古希腊的悲剧行动并不源于个人,也不源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心理学。它植根于历史,而且不仅仅是人类的历史。它的动力不是某一个人的性格,而是最终超越个人的继承权和家族关系。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被普遍化了的个体行动,而是被个体化的普遍行动。我们了解到的是变化无常的世界,而不是人的性格。”[4]可以清楚地看出,威廉斯对悲剧的“个性说”进行了坚决的否定。当这个理论的根基塌陷之后,朗格的断言抑或猜测、伊格尔顿的推论就都失去了先前的效力。
实际上,不单朗格与伊格尔顿两人,对多数西方理论家 (悲剧论著)来说,非西方国家的悲剧经验都处于被否定的状态,这无疑会引发东方学者的愤怒与抗争。针对颇具权威性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悲剧在东方戏剧中的缺席”之论,刘东先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批判,这里不再赘言。我们关注的是另外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理论家也居然断言中国没有悲剧呢?其根据何在?理由是否充分?也是以西方为中心来审视中国的戏剧吗?诸多的质疑汇聚到大名鼎鼎的朱光潜先生1933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之上。在这部创见颇多的对各种悲剧快感进行批判研究的著作中,朱光潜视野下的悲剧无论作为戏剧形式还是作为术语都是起源于希腊的,即是说,希腊悲剧是其理论起点。以此来衡量世界其他民族的戏剧,中国、印度就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就中国而言,没有悲剧的具体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世俗的伦理哲学,其二是大团圆结局。[5]他认为中国人最讲究时机,最从世俗角度考虑问题,把所有的苦难与不幸都归诸“天命”而不是希腊人的“命运”——反复无常的女神,因此中国人有一种不以苦乐为意的“英雄主义”,正是这一点阻碍着国人对人生悲剧性的感受。这是一种有很大市场的否定中国有悲剧的论调。有学者甚至以此 (命运意识的缺席)判定“中国的悲剧实际上都是伪悲剧”。关键的问题是:把苦难与不幸归于“天命”就一定意味着对人类的不公没有一点感受进而没有悲剧吗?还有,这种认为中国人具有看淡苦乐的“英雄主义”的断言究竟有多大的普适性?就具体的戏曲作品而论,至少我们从“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中看不出多少窦娥的英雄主义倾向来。就“中国悲剧”都是“伪悲剧”而言,何谓真悲剧呢?既然一方面承认中国有自己的悲剧,就应该考察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异同何在,何必硬要以一个本质主义的悲剧链条将其锁死呢?伦理哲学的层面折射在中国戏剧上就是备遭诟病的大团圆结局。朱光潜指出,中国戏剧的关键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突变”中 (也是有趣处)而很少在结尾;因此,尽管其间是如何的悲惨,结尾处一定皆大欢喜。不管这是多么真实概括了中国戏剧的全貌,无论如何它不能成为证明元代五百多部剧作中没有一部悲剧的理由。即便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六要素 (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唱段)的要求,也依然无法断然否认元代戏曲是悲剧,而且,亚里士多德明明说“悲剧中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6]。既然朱光潜也认可中国戏剧的关键及有趣之处在于怎样转危为安的“突转”上,又何必斤斤计较于结尾的或喜或悲呢?对于大团圆结局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使朱光潜认为《赵氏孤儿》是将“悲剧题材”写成了“喜剧”,在中国戏剧=喜剧。[5]这里不必援引王国维所说该剧即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名言予以反驳,仅仅就西方的悲剧来看,“大多数悲剧以不幸收场,但相当多悲剧并非如此。亚里士多德本人对这个问题,虽然说不上自相矛盾,但却特别马虎。悲惨的结局对于希腊悲剧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尽管它占有主导地位。”[2]伊格尔顿还指出,对于传统主义者来说,悲剧的结局关系不大,重要的是它们的主要行为者必须身份高贵。不难看出,悲剧的结尾或喜或悲对于西方悲剧而言并不那么重要,我们不必总是因为大团圆结局而感觉低人一等,换一个角度看,为什么就不能将它看成中国文化特有的美学追求呢?
纷纷扰扰的中国有无悲剧的论争向人们发出警示:当单一的悲剧理论与复杂的悲剧实践狭路相逢时,对于两者的冲突不应有丝毫的惊诧,早在尼采《悲剧的诞生》中就将此对立追溯至苏格拉底;理论家应该思考的问题是究竟是先在的实践有问题,还是试图笼络住它们的理论存在问题。这要求理论家开阔心胸,扩大理论的视野,雷蒙·威廉斯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他的一部旧作《现代悲剧》中的洞见与卓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威廉斯指出,悲剧意义总是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双重限定。如此的金玉良言对于那些否定中国有悲剧的论者来说无异于醍醐灌顶。尽管他认为与悲剧理论相比更重要的是具体的悲剧实践,但遗憾的是不少理论家对悲剧理论也并未有通透之见。如果看到文化的因子,这样的推理就会顺理成章:“悲剧的意义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只在特殊的文化之中才有普遍性。”[4]看到了历史的因素,我们就会明白某些热情的理论家固执己见地寻求悲剧本质的努力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任何将丰富而无序的悲剧实践“抽象为悲剧定义的努力,要么误导我们,要么使我们对自己文化中的悲剧经验仅仅采取僵化的态度。”[4]面对现代的悲剧感,旧有的悲剧理路捉襟见肘,这时候就不得不承认现代的悲剧感有别于过去,它自然也需要另外的传达方式。然而,这种不言而喻的观念却常常会受到顽固的传统悲剧定义的骚扰。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把那种亘古不变的悲剧起因抛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刷新我们的悲剧观念:只要“是以戏剧形式来表现具体而又令人悲伤的无序状况及其解决”[4]的作品就可以成为悲剧。威廉斯在这里实际上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宽阔的理论大道。具体而言,既然悲剧的话题早已陈腐不堪——远在1933年撰写博士论文的朱光潜就发出了这样的喟叹,那么,悲剧理论究竟凭借什么勾起人们的兴趣呢?威廉斯敏锐地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往往能从它们身上窥见一个具体文化的形态与结构。但是,一旦我们把这种理论当作是对某一个单一的悲剧现实永久的陈述的话,那么所获甚少:“我们只能够得出已经包含在这一假定之中的形而上的结论”[4]。该假定主要是本质永恒不变的人性,如果我们予以认同的话就必然以此为标准来解释悲剧。但如果我们拒绝这个假定的话就是另一番天地:因为悲剧就不再是先前那种特殊的、永久的既存事实,而变成了不断变化的“一系列经验、习俗和制度”[4]。既然如此,旧有的教条就被打破,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悲剧理论必然成了孤家寡人,我们就可以踌躇满志地根据关系之中的标准走向多姿多彩的悲剧经验。
[1]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12.
[2]特雷·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M].方杰,方宸,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76,90.
[3]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86-387,410,409.
[4]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M].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80,44,44,44-45,37,37.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张隆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15-220,218.
[6]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4.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