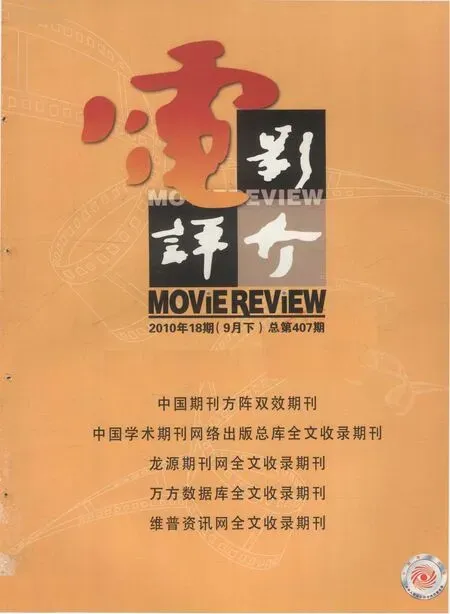基督教圣乐在推进和谐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宗教之所以能适应于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是各宗教自身存在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和宗教历史进程的规律,我国宗教要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必须与之相适应。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号召,要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此,本文从文化层面思考基督教圣乐文化参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基督教圣乐是基督徒信仰文化生活的重要体现
基督教被称为“歌唱的宗教”,其经典《圣经》中的诗篇很多是作为圣乐在教会崇拜中咏唱的。
基督教圣乐(Christian Hynm)以传达上帝给人们的启示,又表现基督徒对上帝的崇敬、赞美、信靠和祈求为内容,以音乐为载体,是基督教的最高艺术。其“圣”字,有“分出来”、“与不洁之物”分离出来之意;此外还有“圣洁”、“蒙悦纳”的意思,它有“人”与“神”两个幅度。其形式与风格有别于俗乐(Secular;Music),它的表情是严肃的、沉着的,速度较慢、节奏平稳、旋律均衡,歌词必须符合教会的真理,并能引人进入神圣、美善的气氛。
早期基督教圣乐为一致合唱(Plainsong),一直被教会所沿用,经过多个世纪不断的发展,约在十五世纪,教会唱诗班的模式已成为基督教圣乐很好的载体,随着复调音乐的使用,圣诗的咏唱已经从单一的唯一旋律发展到多声部的合唱。许多作曲家大多以圣经中的话语或圣经人物为题材,通过圣乐歌唱的形式表现出来,增进人们对信仰的认知和理解。圣乐在教会中是为信仰服务的,最具代表性的有巴赫的《约翰受难曲》、《马太受难曲》、《B小调弥撒曲》;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以色列人在埃及》;海顿的《创世纪》;门德尔松的《以利亚》;马丁•路德的《上帝是我坚固保障》等。这些凝结着人类智慧的优秀音乐艺术作品千百年来被人们所传唱,历久不衰。无论从旋律之优扬,还是词句表达之精准,逻辑修辞之严密,意境之深远,乐曲架构之宏大,都是无与伦比的。正如1743年亨德尔《弥赛亚》在伦敦上演,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亲临剧院,当唱至其中的《哈里路亚》时,乔治二世被深深打动,情不自禁地庄严起立,直至曲终,遂成为国际惯例,足见基督教圣乐文化蕴涵着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任何一种宗教艺术,都是“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精神、宗教仪式与艺术形式的结合。”[1]基督教圣乐也不例外,它将人们对造物主的崇敬与赞美和对人类真善美的颂扬藉以音乐艺术形式外化出来,“最有说服力地表明福音的文化融入之可能性、必要性、可取性和多样性。”[2]“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 因而基督徒通过咏唱圣乐以表达朝拜、感恩、祈祷、悔罪和属灵的热忱等最深入的宗教情感。圣乐成为教会信仰生活最为关键的部分,“它之所以关键,原因在于它能抓住会众的心灵”[3],因而能贯穿于基督徒信仰文化生活的始终。这也使基督教圣乐有别于其他音乐而独树
基督教圣乐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局限于教堂中的崇拜,它已经成为世界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基督教圣乐对于人们在生活中各种遭遇都起着安慰、鼓舞、激励的作用,引导人们积极追求正义和公平,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与和平,如巴赫的《在和平的土地上》、牛顿•约翰的《奇异恩典》等。音乐艺术与基督教文化在漫长的两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孕育出了绚丽的高雅音乐。
基督教圣乐是群众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基督徒来自社会各阶层,基督教圣乐具有广泛的群众文化基础,随处可见,不但在聚会崇拜或重大节日庆典时必须要唱赞美诗,而且平时只要有基督徒聚集的地方(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其他场合)就有歌唱,歌唱成为必须,伴随其间,因而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看,它成为基督教最具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基督教群众文化艺术。
群众文化艺术的最突出特征就是群众广泛参与文化艺术活动,而基督教在举行崇拜、圣餐、洗礼、婚礼、葬礼等各种礼仪时,参与者大多是基督徒;举行的专场歌舞赞美会、圣诞晚会等活动,也大多是由非职业文艺人员参与的,不少节目是基督徒(非职业文艺人员)自编自演,其实施的主体明显地体现出了广泛的群众性这个特征。
“群众文化之所以历久不绝,代代展新,其奥秘之一就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群众文化都具有鲜明的自娱性。”[4]这既“是人们的一种基本精神需求,也是群众文化的一种基本动力”[5]。广大基督徒通过自主参与文化艺术活动,不仅可以从中获取美的精神享受,以实现自身才能的价值,从而获得心理与生理的满足,而且他们将信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在以多种形式展示才艺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信仰的追求,对造物主的崇敬、赞美与感恩,从而使自己获取精神上的愉悦。如在贵州省贵阳市基督教会举办的“圣诞•和谐•繁荣”大型圣诞歌舞晚会上,贵州农村少数民族基督徒创作了赞美诗《和平颂》,流露出新农村建设者对世界和平的憧憬和对祖国欣欣向荣、和谐社会的赞颂;又如云南神学院的师生将圣经文学与中国文化以及十八个民族的元素融会在一起,创作出六十二首具有本土特色的赞美诗歌 ——《圣歌新作》。
基督教圣乐文化具有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人类文化学泰斗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描述了文化的诸层面的内容:“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他将文化与长期社会生活中的人类所特有的状态关联起来。由于宗教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对各民族的文明产生影响,是“一种以超世信仰为核心而形成的综合社会文化体系”[6],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包含了丰富内容,不仅有政治、经济等层面,而且文化也应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个层面。就基督教而言,基督教圣乐体现于基督教信仰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基督教的许多圣乐又作为世界名曲而享誉全球,我国社会上举办的各类音乐会,基督教圣乐常以世界名曲的身份而被广泛演唱和演奏,如贝多芬的《欢乐颂》、舒曼的《茨冈》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由于圣乐贯穿于基督徒的精神文化生活始终,并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因而构成了圣乐文化。基督教圣乐文化在推进和谐文化建设中具有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积极参与,构建和谐 “基督教作为一个信仰体系,至少应包括两个大的层面,一为其精神追求和信仰本真,二为其教会构建与社会参与。”[7]近年来宗教界举办或参与了各类群众文化艺术专场演出,如湖南省宗教界为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举办了“五教同光,共致和谐”大型文艺演出(2007年);贵阳市基督教圣乐合唱团应邀参加了贵州省委老干部局、贵州省文化厅等主办的“喜迎十七大,颂歌献给党”文艺演出(2007年);云南省宗教界举办了“云南省首届宗教运动会暨文艺演出”(2010年)。这些“优秀的音乐能帮助人们培养良好的品行,鼓舞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增进人类之间的和谐和友爱。”[8]
一方面“基督教圣乐在社会道德的培养上,在艺术的发展上,在对于美的追求上都起了非凡的作用。常有些人们到教堂来并不全为了信仰,有的只为听听和谐美感的宗教音乐。在这肃穆、庄严、快乐的音乐中,人们不仅得到了美的享受,也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心灵上的沉静。”[9]通过这些圣乐可以使人们体验美与爱的精神,达到精神文化的和谐,进而作用于社会的和谐。另一方面通过这些专场音乐文艺演出,如“云南省首届宗教运动会暨文艺演出”中所展示出丰富多彩的优秀节目体现了健康向上的文化内涵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主旋律,从而在文化层面上促进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群众文化艺术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具体实践。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所说:“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教育、净化、精神享受。”[10]这恰恰是这个社会人们所需要并竭力追求的,无论是基督教圣乐还是其他音乐,对于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和追求都有异曲同工之效。
繁荣群众文化艺术 近些年来,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日益活跃,尤其合唱艺术蓬勃发展,基督教圣乐不仅丰富多彩,合唱也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形式,而且充满了崇高的圣洁感。因而各地基督教会组织合唱团队,不仅在教会内演唱圣乐,同时也迈向社会,积极参与群众性的社会音乐活动,繁荣群众文化艺术,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每星期举办音乐欣赏会;1991年,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WCA)与天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YMCA)联合开办了天津YWCA、YMCA青友合唱团,已经成为天津市群众文化艺术舞台上的一支生力军;还有云南富民小井村苗族合唱团(即小井村唱诗班)以舒曼的《茨冈》参加了第13届全国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贵阳市基督教圣乐合唱团以《哈利路亚》、《平安夜》、《祖国,慈祥的母亲》等曲目从2007年至2009年连续三年应邀参加了贵阳市文联、音协举办的“贵阳市新年合唱音乐会”;2008年7月代表所在的延中辖区办事处参加中天杯“多彩贵州”贵阳市选拔赛。基督教合唱团队通过参加这些歌唱比赛、演出等社会音乐文化活动,既拓展了视野,吸纳了营养,搭建了平台,构建了和谐,增添了凝聚力,传递了爱与和平,又为群众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成为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的一支有生力量。
营造基督教融入社会的良好氛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社会变革进程的加快带来了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存在物欲横流、道德缺失、诚信危机、贫富悬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需要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而稳定和谐的社会要求把治国理政的视野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等方面。当今党和政府“对宗教的认识日益深化,肯定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明确了宗教信徒是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这种新观点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宗教的成见,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1]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使基督教及其文化的发展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和空间。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在文化方面的具体体现,基督教文化虽与中国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但又与人类的文明成果、伦理准则及道德规范有共通之处。和谐包括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内在的和谐是高层次的,而基督教的信仰追求和睦和谐,基督教圣乐所表达的正是高层次的内在和谐,如《爱的诗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新约•歌林多前书》第13章4-8节)因而在和谐文化的建设中,基督教文化完全应该“通过阐扬基督教的和谐思想,参与和谐文化的建设”[12]来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民共建,没有宗教参与的构建就谈不上全民共建;没有宗教参与的和谐,也就谈不上全社会的和谐。基督教需要融入社会,才能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作用,体现自身应有的价值;基督教圣乐团队走出教堂,参与一系列社会文化艺术活动,既诠释了基督教教义中的爱与和谐思想,又得到社会各界的接纳、认可及好评,进而营造了基督教融入社会的良好氛围,是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构建和谐文化方面切实可行的美好途径。
注释
[1]蒋述卓《宗教艺术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陈泽民《中国教会赞美诗与文化融入》,载《金陵神学志》2007年第2期。
[4][5]郑永富主编《群众文化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
[6]牟钟鉴《中国社会主义者对宗教认识的新高度》,载《中国宗教》2010年第7期;大批宗教学者提出“宗教是文化”的“宗教文化论”已得到社会广泛认同。
[7]卓新平《基督教信仰与中西文化》,载《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8][9]张晶《探索基督教音乐的社会意义》,载《福建艺术》2005年第5期。
[10]何乾三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11]王作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前景》,载《中国宗教》2006年第7期。
[12]王作安《我们期望一个什么样的基督教》,载《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