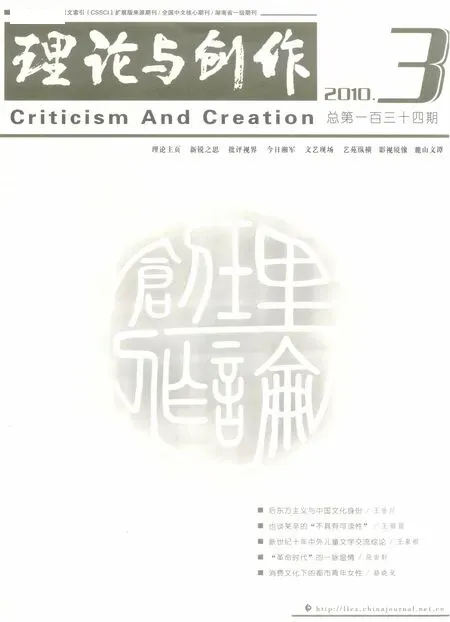为谁写作:论西部作家的底层意识
■ 王贵禄
一个作家在何种价值立场上看待底层,以何种情感和眼光评价底层人物的生存方式、命运遭际、精神状况等,这往往形成其底层意识。作家的底层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文学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作家已了然这是为谁而进行的创作,其作品隐含着何类读者,这样的创作到底在呼唤和催生什么样的社会生态。换句话说,富于底层意识的作家,其创作之根已深植于现实生活中,深植于底层民众中,而在精神层面又超越了底层。在这个意义上,直面底层、再现底层生活,这是作家底层意识的基本状态,而最为关键也最为动人之处,则在于作家以主体身份介入到底层的矛盾张力中,为底层遭遇的苦难真诚地呼吁,而同时却能够真实传达底层的利益诉求、人生期待和政治愿望;则在于密切关注底层的文明进程,以提升底层的精神境界为己任。底层表述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也正源于此。
一、革命话语主导下的底层表述:作为美学主体的底层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围绕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论证与新的国家精神的确立而展开的,以革命历史图景的展示和民族国家的再想象为其特征,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指向。也是在这种革命话语主导的语境中,西部作家的第一代(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开创了西部叙事的先河。他们是在陕甘宁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就其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的区域而言都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作家不同,文学地理上的这一转变,“表现了文学观念的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表现的变化。”①他们从创作的早期,就将眼光投向底层,以底层表述而登上文坛,底层关注甚至成了他们一生的选择。他们眼中的底层却远不是怨天忧人、自暴自弃及精神迷惘的底层,而是具有阶级主体性和历史能动性的底层,是处于急剧上升时期的底层。也就是说,他们是将底层作为美学主体进行表述的。这种底层表述,“会提供关注现代文学中被忽略的领域,创造新的审美情调的可能性。”②
早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常常将底层编码为愚昧、麻木、冷漠的群体,如鲁迅笔下的乡村文化形态。启蒙话语与真实的底层人生其实是相当隔膜的,启蒙者的底层想象过于悲观和单一,导致了底层对启蒙话语的排拒。尽管启蒙话语对底层并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作为一种表述底层的方式,却在知识阶层普遍流行,致使底层的本真面目越来越模糊。启蒙话语之后,三十年代革命话语背景下的底层仍然失语和缄默,这种状况直到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才有了好转。由于其时《讲话》精神的广泛传播,加之解放区政府利用了行政调动力,底层方有可能以其原生形态进入到作家的视野,周立波、丁玲、李季等的创作显示出了崭新的底层气象,他们的创作也为柳青等西部作家的底层叙事做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
柳青的《创业史》不像《红旗谱》、《青春之歌》等“成长小说”,没有过多地叙述主人公梁生宝的成长经历,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再现这个底层人物的阶级主体性和历史能动性方面,以凸显“新底层”的本质为旨归。但如何凸显?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无法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而将梁三老汉设置为梁生宝的继父,显然切断了梁生宝这个新底层身上的宗法遗留,为其投向心仪的“父亲”——党的怀抱预设了令人信服的逻辑前提。然而,关于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即使在《创业史》(第1部)发表的初期就遭遇质疑。质疑者并不是直接向梁生宝这个人物发难,而是反复言说梁三老汉形象的真实性,这的确是一种富有深意的解构策略:如果梁三老汉形象的真实性能够成立,那么,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自然就失去了依据。但梁三老汉却是一个彻底的旧式农民,他的身体充分显示了其底层性和被规训性:满面很深的皱纹,稀疏的八字胡子,忧愁了一辈子的眼神,脖颈上一大块死肉疙瘩。他活像一个五十年代的闰土,眼神中亦不乏祥林嫂的遗留。是的,梁三老汉是够“真实”,倘若将其生活的时代后退到二十年代;但在一个改天换地的年代,其所作所为所想却暴露出荒诞性和令人憎恶的保守性,他断然不可能昭彰底层的未来和希望。
如果是这样,质疑者为什么还要穷追不舍?反复抬高梁三老汉这一类底层人物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何?不难看出,质疑者仍然在沿袭着二十年代的启蒙话语,他们认定底层只能像梁三老汉一样狭隘、自私、勤劳、纯朴和容易满足,其人生梦想无非是“做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怎么可能是思想先进、无私慷慨和有能力组织穷哥们奔赴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呢?正如底层不能理解文化精英夸夸其谈的启蒙话语或现代性话语,高高在上的文化精英也同样不能想象底层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自省力量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智慧。某种程度上说,《创业史》的出现打破了文化精英的惯性思维,梁生宝的形象也冲决了文化精英关于底层的知识边界,这使他们不能容忍,不能再保持沉默。实际上,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新世纪初,文化精英或隐或显地否定《创业史》和梁生宝这一底层人物的声音从来都不曾停歇,这反而给人们一种提示:支撑柳青创作的不是精英意识,而恰恰是底层意识。
柳青等西部作家是《讲话》后在陕甘宁解放区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个成长经历奠定了他们健朗的底层意识。在《讲话》中,毛泽东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倡导知识分子到底层去锻炼和接受改造,他认为底层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③。现在看来,毛泽东所器重的是淡化了精英意识而以底层审美为志趣的作家,其底层观深度影响了解放区作家的创作。柳青就是一个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坚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与《讲话》提出的知识分子改造相一致,柳青在建国前后多次深入到底层,在艰苦的工作岗位自觉地磨练自己,苦行僧似地进行知识分子改造,最终淡化了精英意识。这是柳青区别于来自国统区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早期的叙事如《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就是根据底层工作的观察和体验完成的。正因为这种对底层群体坚决的情感皈依,他的笔触也就能够沉潜到草根深处,在时代的大变动中自如地再现其心灵运行的轨迹。
不仅柳青,而且王汶石、杜鹏程等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西部作家都是将底层作为美学主体进行表述的。王汶石不同于柳青的苦心建构史诗般的巨制,他往往从底层人生中截取一个个片段,凭借对底层新生活的热情和社会新事物的敏感,及时发现处于上升时期的底层身上的亮点,并通过铺陈这亮点的时代生活动因,以形成自己的底层表述。杜鹏程的短篇主要涉及和平年代的底层建设者形象,他善于通过底层平常生活的展开来折射人物的心灵之美,从而凸显底层的美学主体性。从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上看,柳青等第一代西部作家的底层表述已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对后辈西部作家的影响极其深远。
二、底层是天使,抑或是庸众:当文化精英遭遇底层体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在大陆知识界产生了一批“右派”。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从受人尊敬和待遇优厚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贫瘠的乡村或偏远地区接受“改造”,从此像沉默的底层一样失去了话语权。这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使他们真正体验了、经历了底层生活,一定程度上说,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他们也是底层的构成部分。“文革”结束后,当他们重新拥有失去的社会地位而告别底层时,他们会以何种情感和眼光审视曾经与他们相濡以沫的底层?他们会以何种话语方式表述底层?重估新时期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思潮,我们却惊奇地发现,再次踏上“红地毯”的知识分子所描述的则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与精神史,而那些为人称赞的文本又多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塑造、自我辩解和自我洗刷。“右派”作家的底层表述不仅与真实的底层令人遗憾地相隔膜,而且显示了其有意疏离底层的倾向,底层在他们的笔下往往是缺乏美学主体性和历史理性的一群。“右派”作家与底层人生的这种貌合神离,既说明了其精英意识的顽固性,也预示着其底层表述的暂时性。然而,作为一种难以释怀的文化记忆,底层体验却在“右派”作家刚刚踏上“红地毯”的那个历史时刻难免要左右他们的创作,尽管底层在这里仅仅是作为“陪衬”而出现的。
张贤亮和王蒙都是从“反右”斗争中始遭遇底层体验的西部作家,近20年的底层体验不可能不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痕迹,事实上,他们新时期初的创作多涉及底层。虽然他们与其他“右派”作家一样,并没有形成和柳青们相似的与底层同呼吸、共命运的审美情感,但毕竟他们笔下的底层面目尚不狰狞,甚至在某些文本中,底层还变身为“天使”——心地纯良、善解人意、可以无怨无悔地为“落难”的知识分子献身。但是,随着这些作家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底层便走向了可怜、可恶或可憎,越来越不讨人喜欢,如张贤亮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创作;或底层从记忆中彻底消失,不再被关注,如王蒙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底层形象从“天使”到“庸众”的滑落,无疑是由于张贤亮们的底层意识的更替使然。我们不妨重读张贤亮新时期问世的文本,以观察其底层意识的演变轨迹。
张贤亮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以引人注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等作品而重返文坛。此时的作者仍身处社会的底层,尽管其时的小说不无悲愤慷慨的情绪,但锋芒内敛、哀而不伤,行文之中流溢出的是对底层人物的欣赏、同情和赞美之情。可以说,此阶段张贤亮的底层意识不仅健朗,而且就他而言也是最接近底层真实的时期。
在《灵与肉》发表四、五年之后,张贤亮又陆续推出引起更大争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短短的几年时间,张贤亮进入了权力层,其人生境遇得到极大改善,已完全摆脱了底层的困苦与艰辛。伴随着他精英意识逐渐增强的是,其底层意识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变化。症候之一便是,底层人物由前期的主人公身份退居为陪衬性人物,他们的一切活动似乎只是为了突出落难知识分子的存在。如《绿化树》中安排马缨花、海喜喜这些底层人物的活动,都无非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使精神人格遭遇阉割的知识分子章永麟恢复做人的自信。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皆为落难知识分子,他们孤独、脆弱而且敏感,故事的演进也主要是根据主人公的情绪变化,在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流动中映像底层人物,故底层人物无一幸免都被做了主观化和平面化的处理,呈现为静止的“失语”状态。
因为底层真实的存在被作者有意无意地遮蔽,于是作品的幻想性质便凸显出来。以底层女性与落难知识分子的纠结而论,叙述的重点已不是知识分子被教育、改造和受感化的种种心情,而是着意渲染底层女性对落难知识分子的怜悯、恩赐和爱抚。受难者身边的此类底层女性,往往可以为心目中的“好男人”牺牲自己的一切而在所不惜。那么,吸引底层女性的到底是什么?倘若从正常的标准衡量的话,落难知识分子既无政治地位,劳动能力又低下,且其囊中也羞涩,这样的人怎么能让终日奔波在生存线上的底层女性动心呢?为了给读者一个理由,作者便不惜虚构一个个“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场景,并借底层女性乔安萍之口做了简单的交代,“右派都是好人”,“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土牢情话》)。“好人”或“有文化的人”——这样的理由就能使底层女性为之倾情、为之赴汤蹈火?显然,诸如此类的交代于情于理都很勉强,不过是作者对爱情生活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而已。
如果作者对底层人物的精神活动的遮蔽仅仅以罗曼蒂克的形式出现也就罢了,问题是作者在神化底层的同时,又时常对底层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映照出来的是张贤亮底层意识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从根系上看,张贤亮始终以“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身份自居,即使身处灾难的深渊,即使为两个稗子面馍馍也不惜露出卑贱相,那黑色囚衣包裹下的仍是死而不僵的精英意识,仍是一种优越感。旷日持久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改变的只是他的身体,并没有有效触及他的灵魂,也没有使他能够更好、更深刻地理解与认同底层的苦难、欢乐和希望。在他落难的时候,是底层不止一次地将他救赎,这其实仅仅使他对底层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因此,在某种情况下他也还能够写活底层形象。但他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底层表述,而是借底层经验以传达其精英意识。这样,在张贤亮进入权力阶层后,便时时有底层意识与精英意识的冲撞、消长与更替,这便是导致底层形象在“天使”与“庸众”之间徘徊,直至完全滑向“庸众”的缘由。当他彻底告别底层经验而全面书写其精英意识时,又在多大程度上可能给读者带来惊喜?像《习惯死亡》和《我的菩提树》,充斥于字里行间的无非是知识分子自作多情的痛苦、孤寂和无望,是犹豫彷徨而又自怨自艾的情绪,是知识分子一次次的云雨之欢和心如死灰,曾经的章永麟们极力张扬个人价值的勃勃雄心已消失殆尽、无影无踪。
张贤亮是幸运的,因为他有着丰厚的底层体验,这使他在八九十年代之际成为领潮的作家,他以现代的方式注解了文学“穷而后工”的道理。张贤亮又是不幸的,因为精英意识的执拗与作祟,他最终还是没有将文学之根深植于底层厚土之中,故进入九十年代后其创作便泄露出强弩之末的尴尬,尽管张贤亮从不缺少才情与灵气,尽管他一直很勤奋。
三、底层并不等于苦难:现代性话语裹挟下底层表述的多向度拓展
在张贤亮、王蒙这些“右派”作家黯然抚慰灵魂创伤的同时,一批更年轻的西部作家开始崛起,如路遥、张承志、贾平凹、扎西达娃。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底层,从小体验的底层磨砺和苦难经历,不是让他们逃离与背叛,而是将他们的哀乐牢牢地粘附于底层,以至于在他们成名之后多年,虽然有的已进入了权力层,底层仍是他们梦魂牵绕的所在。这代西部作家与柳青一代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亦将底层关注当作他们一生的选择,即使在新时期以来多种思潮的频繁更替中,也不曾动摇他们的底层意识。但新时期文学又是以现代性话语为主流的,呈现为多元话语共存的格局,这不能不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人”的觉醒与发现、文化寻根与反思、底层神话的崩塌与重构等题旨,都是这代西部作家的底层意识的构成中不同于前辈的地方。他们的底层表述正是在现代性话语的裹挟下所进行的多向度拓展,其努力大大丰富了西部小说底层表述的可能性,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T1时刻:根据风力、光伏的实际出力情况、负荷需求、储存电量水平等,进行生产调度调整,如指定电源出力、管理负荷、控制交换功率等。
路遥从八十年代初发表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步入文坛,到九十年代初完成长篇《平凡的世界》后突然谢世,十年时间里奉献了数量惊人的底层文本。他的文本是巨变时代底层人生的忠实记录,其最动人之处在于深度描述了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激情,及其由此而来的不得不时时直面的挫折、抑郁和焦虑。这也是路遥不同于柳青的地方,在柳青那里,上升时期的底层青年虽然也有碰撞,有不如意,但底层在政治上的优势却足以缓解乃至于化解一切挫败,而路遥时代的底层显然已经复归于草根状态,底层青年向前跨出的每一步都意味着沉重与艰难,都意味着孤军奋战的血的代价。但路遥并不忧伤,也从不悲观,他以极其细腻的笔法记叙了底层青年遭遇不幸后,其父辈们以黄土地一样的宽容和诚挚来接纳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重建生活的信心。路遥的底层叙事因此便具有了不可替代性——以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历史动机为中心,尽可能全景式地映像底层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将眼光辐射于非底层人群。面对孤立无助而又不甘心重蹈先辈命运的底层人,他的笔端常常流溢出不可遏止的温情与同情,他太理解这些底层人了,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感同身受,因之他的底层表述也就能够抵达同类题材难以企及的真实性与丰厚度,特别是那些对底层人悲剧般的尊严、绝望般的希望和西西弗斯般的奋斗历程的描述更是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冲击力,感动了几代的底层人。列宁曾言,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它必须在群众中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④路遥的文学人生无疑对之做出了形象化的诠释。路遥底层意识的突出表征,还在于将底层人物置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大背景中,但始终能够站在底层的价值立场上,探察底层群体的人生出路与未来前景,再现底层的疾苦和欢乐,反馈他们的愿望与心声,路遥已完全把自己预设为一个“底层作家”。陈忠实曾这样评价路遥的意义,“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理解这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⑤并非无的放矢。
如果说路遥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全景式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底层人生,那么,张承志则以浪漫主义的创作姿态,着力表现了底层在苦难和不幸面前召唤出的坚强、韧性与豁达,以苍健而悲凉的笔调歌颂着底层。正本清源地看,奠基张承志叙事底色的不是精英意识,而是底层意识,这与其成长经历有关。他曾在偏远的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四年,是底层给这个异乡来的已进入青春期的少年以无私的关爱和奉献,这使他深深地为底层的淳厚、素朴和诚挚所感动,他躁动而漂泊的心从底层那里获得了少有的慰藉和安宁,底层于是成了他永远的精神故乡。这个经历几乎决定了他闯入文坛的那一时刻的基本选择,他曾真诚地说:“我非但不后悔,而且将永远恪守我从第一次拿起笔来时就信奉的‘为人民’的原则。”⑥那么,张承志又将如何实践“为人民”的创作理性?他走的显然不是柳青、路遥的现实主义路子,也与张贤亮的底层表述形成了反方向运作。他更关注的是底层的心灵世界的变迁与展示,挖掘底层在各种非常态的情境中何以爆发出惊人的耐力与韧性,从其成名作《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广受争议的《心灵史》,他从两个端点上对讴歌底层进行了链接。但由于张承志深受精英文化的熏陶与濡染,其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与底层读者的期待却是判若云泥,这也就不难理解,他的作品为什么不可能在底层产生多大影响了。
张承志的种种书写,如对底层人生的颂扬、对权力社会的否定、对自然美景的留恋和对宗教文化的皈依,极易使人产生误读,似乎张承志叙事文本的精神诉求极不稳定,并造成这样的错觉:神圣的姿态与虚无的内核。⑦但如果联系中国社会八十年代以来的实际状况,就不难洞悉,张承志其实一直在为底层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他在冥冥之中预感到现代性进程也许将会使底层变得更加一无所有,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记忆亦将荡然无存,这种底层焦虑是如此的深刻,竟使他有时不得不以一种过激的方式加以表现。要正确认识张承志的底层表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话也许最具启示性:“从理论角度看,浪漫主义之新纯属无意:它确实如同肌体躲避打击一样,可以视为一整代人试图保护自己的方式,以此回避世界的总体性的空前的大转变,即世界从此进入中产阶级资本主义贫瘠的物质主义的环境。因此,一切封建世态和政治白日梦,一切宗教事物和中世纪事物的氛围,对旧式等级社会或原始社会的复归,旨在还原旧貌的复归,都应该首先理解成防御机制。”⑧如果我们从“试图保护自己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张承志叙事文本的内核其实很具体:捍卫底层的尊严。
在路遥和张承志之外,扎西达娃等作家八九十年代的底层表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都把各自熟悉的底层生活作为主要创作资源来展开,形成了西部小说底层表述的多元格局。就扎西达娃的底层表述而论,既不同于路遥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张承志的浪漫主义,他怀着强烈的启蒙冲动,通过营造那些如真似幻的宗教文化背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来映像底层人生的悲剧性与荒诞性,故扎西达娃的底层表述显得空灵、缥缈而意味深长。
从扎西达娃的后期创作来看,其精英意识与底层意识始终缠绕在一起。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等待拯救的底层,他们愚顽地重复着某种宿命,不注意时代的变化,也不相信自己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在这些时候,扎西达娃表现更多的是精英意识,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观照,这样,我们能看到的也只是扎西达娃启蒙话语中的底层,底层本真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流程在此被过滤掉,或被高度抽象化和寓言化。扎西达娃的这种叙事策略的实施,可能在寻求某种更高意义上的“哲学的真实”或“文化的真实”,但毕竟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底层,因此也限制了其底层表述的再拓展空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读出扎西达娃深沉的底层意识,弥散于他后期文本中的情感主要是一种“现代性焦虑”,是渴望底层踏上自由之路的紧张,是因为底层的行动滞缓而生发的绝望过后的悲哀。扎西达娃一直在试图“拯救”底层,预设着凭借其启蒙话语将他们从宗教的沉溺拉回现实中来,并创造和享受现世的幸福。因是之故,我们从他的文本中根本就读不出辛辣,而是对底层爱极生恨的焦虑、紧张与悲哀。
四、走向“底层文学”:消费时代的底层表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规模转型,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度的裂变,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无限蔓延趋势。在这样一个由消费文化、强权和资本合谋的语境中,社会底层被持续再生产,于是,沉寂已久的革命话语在不知不觉之间复兴起来,其重要表征是“底层文学”的横空出世。底层文学虽然以革命话语为其主要的话语形式,但显然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主流话语有着内在的差异,底层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并不主张通过阶级对抗和政治革命的激进方式来改变底层的生存境遇,而是直面客观存在的两极分化和阶层分化,强调复归“革命文学”的人民性传统,呼吁权力社会关注底层的艰难民生,关注底层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呼吁通过建构一种平等、和谐的社会秩序,使底层的存在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使他们重获失去的政治地位。我们可以将底层文学的话语方式看作是“后革命话语”,或“新左翼话语”。
西部小说从其发端就是以底层表述为其标识的,我们在此论及西部小说之走向“底层文学”,无非是说,在中国社会已进入市场意识形态为主导、消费文化为主流的语境,西部小说与方兴未艾的文学思潮形成遇合与对接是水到渠成的必然。在这一过程,受强势文学思潮和地域性文学传统的合力影响,此阶段西部作家的底层意识同样会呈现出某些特别的时代烙印。贾平凹、雪漠、石舒清、王新军等作家的创作是这种时代印痕的极好体现。
八十年代初期的贾平凹为社会变革带来的底层富裕气象而欣喜不已,其时的底层表述师法沈从文、废名等京派名家的乡土神韵,表现出底层人生的诗化倾向,风格明朗而清新,《商州初录》等文本把底层面对触手可及的幸福时的情态已和盘托出。八十年代中期创作的众多中篇,如《天狗》、《山城》、《远山野情》,贾平凹表现出欣喜过后的一丝隐忧,历史是进步了,底层是衣食不愁了,但人们的道德水准却在下降,浮虚之风正在生长,这是底层的幸还是不幸?长篇《浮躁》将其喜忧参半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而其风格渐趋沉郁。进入九十年代,贾平凹似乎离开了底层言说,连续创作了《废都》、《白夜》和《土门》等涉及都市上流社会的长篇,而这些叙事中却出现了一个悖逆的现象,即权力人物一个个处于醉生梦死的状态,不难读出作者对上流社会的厌弃之情,其实也是他底层意识的别一向度的表述。如果说《废都》和《白夜》的表述风格以沉郁较著,则《土门》一变而为凝重。在《土门》中,作者的底层意识中携带着沉重的忧患,农民告别了土地将何去何从?并没有人给那些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安排一个更好的出路,他们想象中的幸福却越来越模糊,他们已被城市文明抛向了不可知的窘境。从底层表述的意义上看,《土门》是一个标识,它是贾平凹转向底层文学的契机,其所昭示的悲剧性意蕴将在贾平凹新世纪的创作中得以延续和深化。
贾平凹于新世纪初推出《秦腔》,这个长篇可以看作是《土门》的逻辑延伸。《高兴》给我们展现了乡下人进城后的悲惨境遇。在更高的意义上,又不能不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惑:现代性的终极意义何在?这不仅是我们的追问,其实也是贾平凹的追问,他在《高兴·后记》中写道:“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⑨
在西部作家中,贾平凹的底层意识是独特的。尽管与柳青相比,他缺乏的是柳青那样的大度与融洽;与路遥相比,他缺乏的是路遥那样的真诚与谦卑;与张承志相比,他缺乏的是张承志那样的慷慨与热烈;甚至与张贤亮相比,他缺乏的是张贤亮那样的袒露与感激,与扎西达娃相比,也缺乏扎西达娃那样的焦灼与悲情。但贾平凹却自有一种执著、一种从容和一种深度,这又使他形成了一种格局。他能始终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精英意识,而是与底层同患难、共富贵之外的远景凝视:底层将如何发展?现代性进程给底层带来了什么?底层的最终归宿又在何处?因为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贾平凹的底层表述便有了长久的驱动力,这使他无法停止,无法不时时思考底层的命运流变,无法不以自己的笔来言说底层,他三十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为奥凯西画像的威尔士艺术家曾给奥凯西写信,质疑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创作和一个“阶级”捆绑在了一起,并劝他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不应该属于任何阶级。《西恩·奥凯西传》的作者大卫·克劳斯,替奥凯西做了这样的回应:“对于某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且有独立经济来源的美学家文学家来说,这样一种超然的艺术观或许是很不错的;但对于奥凯西来说,倘若他不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人,凭借自己的经历和信念使自己始终与工人阶级休戚与共的话,他就根本不会成为一位艺术家了。对他来说,不隶属任何阶级的艺术家或不隶属任何阶级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在他看来,艺术家对他的同胞所肩负的责任应当更大于普通人,而这种责任又与他对艺术肩负的责任密切相关,无法仳离。”⑩
我们在此引用这个故事,是因为大卫·克劳斯的回答也许对说明西部作家的创作与“底层”这个阶层的关联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自柳青以来,底层意识就一直左右着西部作家的创作,他们以富于正义感的声音为改善底层的境遇而呼吁。他们不可能去创作某种“纯艺术”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书写的每一个文字都担负着底层的希望与诉求。他们是作家,是因为他们曾经替底层言说,或正在替底层言说。舍弃了底层,他们将宁愿沉默。
注 释
①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6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2-913页。
⑤陈忠实:《悼路遥》,《小说评论》1993年第1期。
⑥张承志:《老桥·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⑦涂险峰:《神圣的姿态与虚无的内核——关于张承志、北村、史铁生、圣·伊曼纽和堂吉诃德》,《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⑧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李自修译:《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⑨贾平凹:《高兴·后记》,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⑩大卫·克劳斯:《西恩·奥凯西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