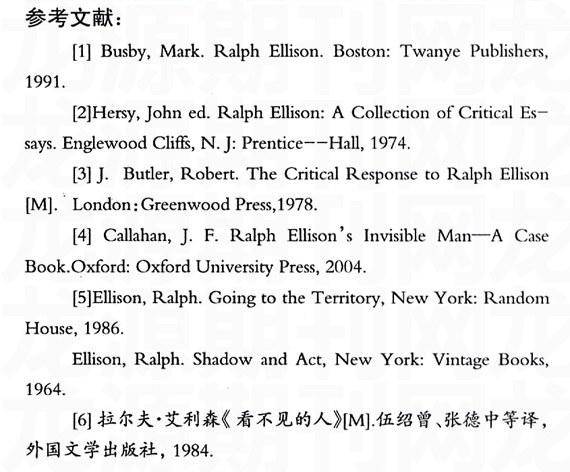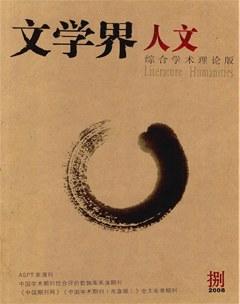《看不见的人》:文化视域下的多元互文性
张学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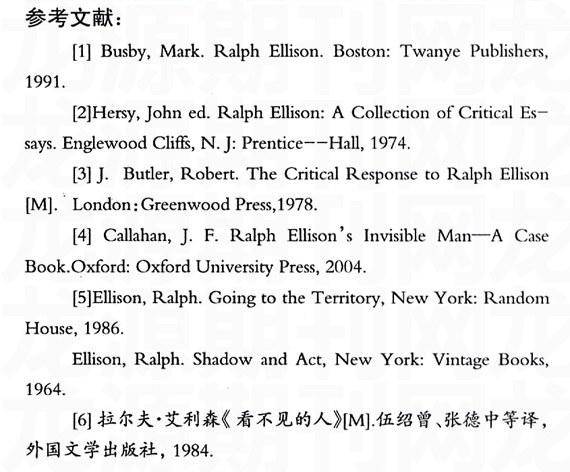
摘要:“互文性”作为当今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问的映射关系。拉尔夫·艾利森的代表作《看不见的人》可以说是灵活运用“互文性”文本理论的典范。艾利森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欧美传统经典作品的广征博引、兼收并蓄,对历史、神话的娴熟驾驭和广泛指涉都印证了“互文性”理论的特征,从而赋予作品更笃厚的内涵。因此,小说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之作,除了作者以黑人的独特视角触及到了“身份”这一人类共同关注的敏感主题。使小说超越了黑人文学的界限,具有了普遍意义之外,“互文性”可以说是对小说魅力经久不衰的另一个绝妙诠释。同时也说明艾利森作为一个黑人作家具有难能可贵的开放心态和探索精神。
关键词:《看不见的人》;文化;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17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43-04
引言
1952年,《看不见的人》的问世使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利森在美国文坛上“一鸣惊人”,成为美国历史上仅凭一部作品走红的少数作家之一,从而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1965年《图书周刊》(BookWeekly)和1978年《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开展的民意测验中《看不见的人》都跻身于二战以来最重要作品的行列,“标志着一种文学传统的结束,另一种文学传统的到来。”当时小说如此受青睐推崇的重要原因是作品从黑人的独特视角阐述的身份主题——“看不见性”——超越了种族界限,具有了普遍意义,唤起了世人的共鸣。
多少年后,重读这一力作还会发现小说存在于主题思想以外的魅力同样令人震撼。艾利森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对欧美传统经典作品的广征博引、兼收并蓄,对历史、神话的娴熟驾驭和广泛指涉,以及对各种创作手法的创造性运用,赋予了作品丰厚的内涵。这说明小说文本丰富的内涵源于对其他文学文化文本的创造性运用,这恰好吻合了“互文性”这一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文本理论。不管是从小说情节的内部参照关系、主题与创作手法上与其他欧美经典作品的相似之处,还是从小说当中零零散散的神话、民间习俗的指涉上来看,《看不见的人》可谓囊括了“互文性”特征的方方面面,是解读“互文性”文本理论的典范,折射出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思想。可以说小说《看不见的人》是艾利森站在历史的高度,固守黑人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博纳世界文化经典之精华而烹制的一道文化大餐。
目前国内外的艾利森文学评论者对《看不见的人》的研究往往以小说的主题、艺术手法为切入点,对黑人的自我异化、身份的解构与重建、种族文化观、反讽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小说的音乐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然而,从文化的宏观角度来解读这部世界经典的论作却不多见。鉴于此,笔者试图借助“互文性理论,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一、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互文性”的思想源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后来经过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熟奈特、里法特尔、米勒、布鲁姆等人的努力,互文性理论的
内涵不断丰富,逐渐成为一个包含多重意旨的文学批评概念。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Bakhtine)认为对话性是所有语言的构成性成分:人们的言语不可避免地会吸收他人的词语,渗透着他人用法的痕迹,人们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会与他人的观点相契合或碰撞,而且人们在具体情景交流中所选择的词语总含有“他性”,总是属于特定的言语类型,总是附有前面话语的痕迹。法国后结构主义巨匠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在1973年为《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本论》中认为,文本实为各式表述片段的交汇处,所谓新文本不过是从现存文本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凡文本都有“互文”。由于文本不过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所谓“作者”也就只不过是那已有文本的组织者,而不是原创者,他唯一的权力就是将各种书写混合起来,以一种抵消另一种。因此,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相互指涉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来自本文化的或者他文化的其他文本进行着对话,“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文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
互文性理论具有极大的涵盖性,不仅打破了孤立文本分析的僵硬和固化,为理解文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对把文本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语言封闭体的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一种超越,认为文本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其他文本的存在,因为某事已被先在地书写了,一个文本从一开始就在其他文本的控制之下,必须把文本从文本的生产者那里解放出来,放到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去理解。互文性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借用,而是思想的互相碰撞,它涉及到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语言等各方面的交融。本文试从文化的视角,以广义互文、内互文、外互文、积极互文、宏观互文为切入点对《看不见的人》的多元互文性进行实证解析。
二、广义互文性:历史的戏剧性重演
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提出的广义互文,打破了狭义互文性仅限于文学文本之间联系的局限性,把非文学的艺术作品、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表意实践、甚至把社会、历史、文化等都看作文本,认为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各种语言、知识代码和文化表意实践间都相互指涉,这些知识、符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文本网络。
《看不见的人》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全景图,更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小说以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刻画了来自不同阶层的众多黑人,辽阔的生活画面跨越了自蓄奴时期至20世纪中叶的漫长历史过程,作品与其所产生的整个社会历史文化都形成了互文。Klein认为看不见的人的经历都是历史的,穿越了从解放运动开始的整个美国历史。Susan L.Blake发展了Klein的历史结构的观点,认为小说中的每一个插曲是与具体的历史阶段是相对应的。主人公在黑人大学的逗留映射的是美国的重建时期,即美国内战结束后对南部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造与重新建设。民主重建以南北双方的妥协宣告结束,所以南部的民主改造是很不彻底的,广大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处于无权地位。重建没有没收奴隶主阶级的大地产,没有给广大黑人和贫穷白人分配土地。广大黑人继续被束缚在种植园主的土地上。刚刚从奴隶制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广大黑人很快又沦为租佃制种植园主的分成佃农或分成雇农,各州种植园主采取各种合法与非法手段限制佃农的自由流动与自由雇佣劳动制的发展。因而在内战后的一个长时期里,南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十分缓慢。小说中主人公名义上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似乎摆脱了黑人前辈的卑劣处境,却处处受到校长布莱索博士的限制与刁难,身心
备受煎熬。他尴尬的个人境况象征了重建时期广大黑人佃农和雇农非人的苦难生活。
他以屈辱为代价获取了上大学的奖学金是对黑人解放运动的一个讽刺性仿拟,因为奖学金并没有使他彻底解放,反而差点儿断送了其前程,正如黑人解放运动虽然使黑人处境有所改变,但要与白人平起平坐还要走很长的斗争之路;后来他和一个一战老兵被迫离开大学则折射出“大迁移”的踪影:北上纽约的经历和西迁苦旅都是美国梦破灭的典例;他在纽约的几个星期是充满希望的20年代的写照:工业就是上帝,自立就是教条,工会主义则是异端邪说……他在兄弟会的经历反映的则是大萧条时期,那时被驱逐是人们最普通的抱怨,共产主义是知识分子的良药;小说最后的暴乱也暗示了1943年的哈莱姆暴乱。小说不仅戏剧性地重现历史,而且还映射未来:艾利森的文学遗产执行人J.F.Callahan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特征,这部小说也引导了后来美国小说的发展,成为民权运动的文字催化剂。
三、内互文性:“布鲁斯”的神奇力量
内互文性是指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在小说《看不见的人》中,黑人音乐作为一种主旋律贯穿始终,使得小说具有鲜明的内互文性。自幼对黑人音乐情有独钟的拉尔夫·艾利森,其文学创作深深植根于美国黑人音乐。他将黑人音乐以不同的形式娴熟地穿插在小说中,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总会让音乐出现,反复演奏,不断加强,就像一座隐形的桥梁使小说中众多的故事情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种对话。
小说中“特鲁布拉德这一插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故事,更是其他故事的“元故事”,正如评论家休斯顿·A·贝克所说,这一插曲中充满多种声音,与小说中其它插曲相互照应:“像其它系统象征现象一样,特鲁布拉德这一插曲,与其它各种符号系统形成对话关系,从而产生并获得意义。佃农这一章,作为一个文本,从与其周围的和内部的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获得其逻辑意义,并且也使其它章节的意义更加复杂化。”
吉姆·特鲁布拉德是一个勤劳而深受人们喜欢的佃农,是一个黑人圣歌和“布鲁斯”歌手,时常被请到大学,用校方官员称之为原始圣歌的音乐款待白人客人。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冬天缺乏基本的取暖条件,只好全家挤在一起后,睡梦中与女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乱伦关系,给了白人歧视黑人的把柄,更让他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他的“丑闻”手斤射出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在美国这个物质极度丰富的社会里,黑人却挣扎在温饱无法保障的贫困之中。这让读者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那一对黑人老夫妇因缴不起房租被强行撵出他们居住了20余年的公寓,他们的东西被胡乱扔放在大街上,老夫妇绝望地坐在冷风中哭泣,悲惨的哭声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布鲁斯音乐中的哀伤。这一幕却如同袅袅的布鲁斯音符萦绕在义愤填膺的黑人群众耳畔,激发了他们要与不公斗争到底的决心。特鲁布拉德的处境再次唤起了小说前言中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歌声,“我造了什么孽?为何我周身漆黑,如此忧伤?不难看出,布鲁斯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声音对白人的垄断霸权进行消解,揭示出社会批判的主题,暴露了“机会均等,人人都有成功可能”的“美国梦”的谎言。
布鲁斯不但使小说中声讨社会不公的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也是小说中展示黑人坚强与爱心情节的粘合剂。特鲁布拉德发现与自己的女儿乱伦后,来自家庭、内心和社会的压力迫使他离家出走。自我放逐的日子“有一天夜里”,他“开始唱起歌来……我也不知道唱得什么歌……我只知道末了我在唱“布鲁斯”……我一边唱着“布鲁斯”,一边认定了一个事实:我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从吟唱“布鲁斯”中得到启发,认识到沉迷于过去的悲哀是于事无补的,于是吉姆重新振作起来,回到家,摆正犯罪和责任的位置,将生活继续下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全家人的谅解并为他们谋幸福。正如艾利森在《与音乐共生》中所写,生活有时可能是艰难的、嘈杂的和不正常的,但是流畅的音乐风格可减少生活的混乱以恢复常规,表达一种肯定的生活态度。”布鲁斯是他坚强起来的源泉。无独有偶,小说中玛丽·蓝博这个哈莱姆区有名的黑人好大妈也是通过布鲁斯表达了她的坚强和慈爱。看不见的人经历了在油漆厂的不幸遭遇,摔倒在伦诺克斯大街上后,玛丽·蓝博收留了他,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她把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弄到她的寄宿房子里却不向他讨债。当一周三次闻到卷心菜的味道时,看不见的人意识到玛丽肯定缺钱了,但玛丽将自己的苦衷埋在心里面。他在思考时听到玛丽在楼下的门厅里唱歌,唱的是一首布鲁斯歌曲,一首有关烦恼的歌,可是她的声音清脆而宁静。离开她家时,看不见的人最后听到的还是玛丽·蓝博在唱歌,歌声向他飘来,在他的周围荡漾,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南产生一种蒙恩的感受。这位平凡的黑人大妈作为“布鲁斯”使者的化身,表现出来的是她在困境中折射出的难能可贵的博大仁爱之心。她凭借顽强的精神战胜个人苦难和艰难的岁月,所以看不见的人不仅仅把她当作朋友,更当作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的、熟悉的、使他没有崩溃的力量。在玛丽无微不至的母性关怀下,看不见的人发现了哈莱姆区鼓舞人心的民间精神,使他勇于面对自己痛苦的过去和前途未卜的将来。玛丽经常以她清晰而平静的嗓音哼唱忧伤的“布鲁斯”歌曲表明驻守于她心中的应该是她那时刻不忘的黑人民族情结,她具有生活在堕落的社会里而不使自己堕落的能力。忧伤的布鲁斯歌曲背后是一个没有被困难扭曲的真正好女人。布鲁斯不但没有使黑人沉迷于忧伤,反而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正如
“鲜血和白骨之歌”所唱的那样:
那意味着希望!
唱一首艰难和痛苦之歌:
那意味着信仰!
唱一支谦卑和荒谬之歌:
那意味着忍耐!
唱一支黑暗中斗争不已之歌,那意味着:
胜利
四、外互文性:与世界文学经典的共鸣
外互文性是指不同文本间的参照关系,在这种互文参照中融进了文化内涵与知识结构。法国批评家热奈特从修辞分析的角度阐述了互文性理论,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术语,“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认为从根本上讲文字是“跨文本的”,或者说是一种产生于其他文本片断的“二度”结构。指出跨文本性是文学性的一种普遍形态,“没有任何文学作品不唤起其他作品的影子,只是阅读的深度不同唤起的程度亦不同罢了;因此所有作品都具有“跨文本性。”小说《看不见的人》闪烁着欧美文学经典中多部作品的影子,其中最典型的要属《地下室手记》和《炼狱》。
艾利森虽然师承黑人反抗小说大师理查德·赖特,但是他却一再声明,他的小说不是反抗小说,“我是一个人,不仅仅是理查德·赖特的继承人。反省我的经历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远比‘抗议这两个字体现的意思复杂得多。”他是从全人类的视角来写作的。因此他的小说源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NotesYrom Underground),而不是赖特的《土生子》(Native
Son)或其他作家的反抗小说。艾利森将将《看不见的人》的叙述者比作《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认为二者都具有各自的才智:“我的叙述者,同陀氏的一样,都是思想家。虽然我的主人公没有陀氏的主人公思考的那么周到和清楚,但是我的主人公意识上具有一种哲学思维的高度,他依靠思想而存在,他是一位知识分子。”看不见的人在序曲的一开始就提到《地下室手记》,对陀氏主人公的观点进行了改造,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重述,表明自己的非洲身份和条件。看不见的人利用陀斯妥耶夫斯和他的主人公,暗示他将进入方言土语、文学和民俗的传统中,成为一个艾利森所谓的“疯狂国家”的作家。地下室人和看不见的人对外面的世界都具有高度民主的认识,但又充满恐惧,都认为它是充满着潜在危险的领地。两部小说中的独自都具有个人与政治的双重性。但艾利森的独自具有史诗的庄严性,这是陀氏独白所望尘莫及的。两部小说都采用了回忆录的形式,都具有诱人的地下日记的忏悔文学的特点。此外,两部小说在结构和主题等其它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的互文性是很明显的。
《看不见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地下室手记》的创造性翻版,无独有偶,但丁的《炼狱》和《看不见的人》相互回应,同样存在极大的相似性。《看不见的人》一开始就说,“在听爵士乐的时候,他不仅能够进入到音乐当中,而且像但丁一样,能够降临到其纵深处。”这表明艾利森和但丁开始了默契的对话。艾利森的小说以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由一系列的插曲构成。整部小说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每一部分由三个插曲组成。而但丁的诗也可以被分成三个基本的部分,而且每‘部分也被细致地分成小部分。因此,两者在总体结构上是平行的。两部作品都是从幻想到现实的一个复杂而必然的微妙过程,在最后的尾声中达到高潮,经过“炼狱”的洗礼主人公对现实世界中的自私、暴力和欺骗有了清醒的认识,醍醐灌顶,回归自我。像但丁的作品一样,艾利森小说的主人公也让人产生一个复杂的双重视觉,“既谴责又肯定,既说是又说不”:尽管他意识到生活是“坏的,恶劣的”,但他内心深处还是相信它是“庄严而美好的”,因为生活当中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此外,《看不见的人》也传达出了许多其他作家的声音。在小说中读者可以重温《荒原》和《尤利西斯》当中的许多古代神话和仪式;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边境神话和民间习俗,“使他的习语美国化,拓宽了他的文本感染力”;《看不见的人》广阔的覆盖面再现了梅尔·维尔的《莫比·迪克》中的书信、布道、格斗,歌曲、政治演讲、梦幻以及对私人住宅、会议室、办公室、妓院、酒吧和教堂的描写等等。
结束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不见的人》中艾利森对传统文化的推敲妙用,让我们看到小说的互文性关系不但为文本提供一个新的阐释空间,而且也使他文本得到再阐释。透过文化性互文解读,我们既可以深入领会艾利森作品的文体风格,又能揭示作品的隐文效果,真正体会到互文关系在文本中的穿越及其蕴涵的文本多元性和异质性。正是在这种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把握中,艾利森将文化因素作为文本的坐标,将传统中潜在的文化模式激活,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现实进行对比和述评,从而凸现现实生活的痛苦,透过文化的表象揭示被遮蔽的本质,使现实生活的情感具有了穿透力和表现力,给人们带来了联想的印象。这种视角同样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文本皆具互文性,互文性无处不在,我们生活在互文性的巨大网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