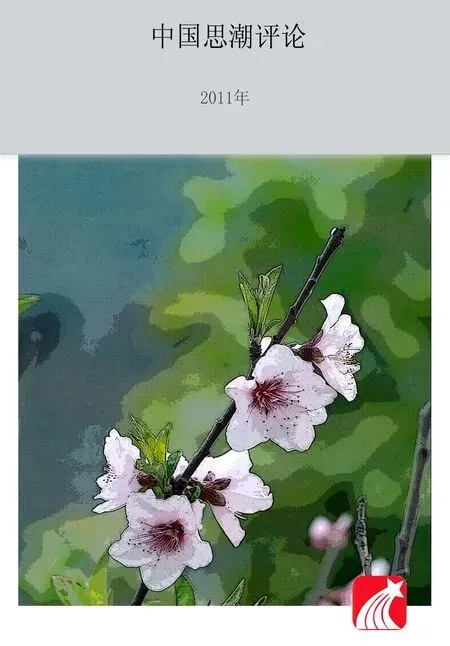“行走的观念”:20世纪中国思想的特质及其研究方法的思考
胡伟希
一、方法论问题的奠基:明确作为“参与型思想观念”出场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
在描述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难题”,即假如真正用“观念”两个字来涵盖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思想时,会发现这些所谓思想家们的思想并非是那么纯粹的观念。换言之,假如认为思想通常是指称所谓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又是指某种理性思维的观念的话,那么,人们只能得出一种看法,即单纯从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家们的思想观念出发,很难构建起思想史。但为了表明这些近现代思想人物的思想能称得上“观念”,人们不得不去发现这些思想人物思想中的“微言大义”。一句话,为了构造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人们不得不去赋予这些思想人物的思想观念以其原初并不具有的涵义。此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对于思想观念的“过度诠释”。
这种对于思想人物的思想观念过度诠释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是赋予了这些思想人物的观念本身本来没有的涵义,脱离了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是,思想观念史容易走向实用化,即认为这些思想人物的思想观念早已穿透历史与超越时空,甚至对后世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具有观念的引领作用。纵观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不可否认的是:虽说某些思想人物的某些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而且确对后来社会历史中出现的问题可能提供某些观念上的启迪,但这并非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就是说,假如回到历史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大多数所谓思想家,或者我们将其纳入思想史研究范围的思想人物,其思想观念就观念本身而言,不仅不是那么的纯粹,甚至也并非想象的那么深刻。他们要么是对于当时某些社会问题发表的常识性见解,要么是以观念的形式出现,其实却只是古代或者西方的某些观念的贩运或者改装而已。一句话,假如说将社会思想视之为纯粹“观念”的话,那么,20世纪中国这些思想人物能提供给人们以真正的思想观念意义上的启发的观念其实是少之又少。换言之,尽管20世纪中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人物,但这些思想人物的思想却缺少观念意义上的原创性。
那么,怎么办呢?既然中国近现代思想人物的思想观念一般而言缺乏原创性,又不能像过去思想史研究经常采取的做法那样去拔高思想人物的思想高度,看来,唯有一种可能,即否定中国近现代有所谓的思想史;或者,即使勉强去写成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也会认为这是一部相当“贫乏”的思想史。这样的思想史,其唯一的作用是告诉人们: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是如何的思想贫乏。这样的思想史,提供给人们的更多的是思想的教训,即社会历史如何导致一个没有真正观念出现的时代。
假如思想史的意义在于提供历史的教训,而它提供的教训又是如此,那么,这不能说是真正的思想史。思想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的方面在于:它除了要说明思想观念产生的历史与社会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对思想观念本身进行辨析,哪怕这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作为思想史而非一般历史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哪怕是贫乏的思想本身进行观念的分析。即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它们究竟是否贫乏。其实,任何作为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之反映与表征的思想观念,其本身并没有贫乏与否的区分,而只有它是以何种形式与方式体现了社会时代的内容之区分。质言之,思想史的研究与其说花很大力气去探究思想观念丰富或贫乏之原因,不如将主要力气用于辨析这些思想观念究竟是以何种样式与方法去体现与表现时代与社会的内容与要求的。一句话,注重思想观念内容与当时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而非仅仅着眼于思想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这才是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通则,也是它与哲学史研究的区别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思想观念贫乏的时代,而只有研究思想史方法贫乏与陈旧的时代。换言之,所谓思想贫乏的时代,是贫乏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结果而非它的原因。
假如这样来看待问题的话,我们发现:20世纪的中国,其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不仅异常的丰富,而且其思想观念也相当的精彩。要注意的是:我这里是指思想的精彩,而非思想的深刻。思想史要关注的常常并非是所谓深刻的思想,而是精彩的思想。而所谓精彩的思想,自然就是看其与社会和时代的联系上,究竟提供了以往历史上其他时期所没有过的何种思想样式。
所谓思想样式,简言之,乃是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变革发生关联的方式。在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思想观念都要与社会生活发生关联与发生作用,但这种发生关系与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假如将其作为类型来划分的话,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反映式的,另一种是参与式的。所谓反映式的,是指思想观念是对社会生活与时代变革的思想观念的反映。这种反映式的思想观察,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其实是“颠倒过来的现实”,此也即黑格尔所谓理念是本真,而现实生活才是理念的展开形式。从历史上看,这种反映式的思想观念长期以来一直主宰着西方的思想传统,至少也是西方思想史家们研究思想观念的通常模式,即强调思想史是对于观念本身的研究。既然观念已经内在地包含着现实,那么,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也就可以通过把握思想观念而获得。假如将思想观念定位为反映式的思想观念,自然而然地,语义分析与诠释思想观念本身,就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通则。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对于思想的理解,即不将思想观念视为现实生活的反映,而视之为应对现实,甚至变革现实的工具。假如从这一维度来对于所谓思想观念加以理解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地,对于思想观念的研究,包括对于思想观念的涵义与意义的理解,就不是仅仅通过语义分析与诠释思想观念本身所能获得的了。这种工具式的思想观念由于其社会功能是要作用于社会生活,因此,研究其思想观念的内容,假如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脱离了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的参与角度,是不得要领的。其实,任何思想观念都有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面(即使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形而上学思想观念亦如此),为了与主要是作为社会生活之反映的思想观念相区别,这里,我们将这种主要是强调其参与和改造社会的思想观念称之为“参与式的思想观念”。一旦作如此划分,可以看到,占据西方思想主流的,是反映式的思想观念。而中国自来就有以思想观念来改造社会生活的传统,这种思想传统在近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以延续并强化,并且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形态。可以认为,假如将这些参与式的思想观念排除于外,仅仅选择那些似乎“纯粹”的观念作为研究对象,这样撰写出来的思想史将不能被称之为一般的思想史,而只能是学术思想史。但是,假如虽然以这些参与式的思想观念作为研究对象,却采取反映式的思想观念研究方法,那么,得出来的思想史也不会是思想史,而只会是被歪曲或阉割了的思想史。
迄今为止,这种被阉割了的思想史还左右着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书写。其研究方式表现为:由于强调观念的语义分析与诠释,不得不沿用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观念及思想模型,来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史研究方法,是首先视思想观念为一种理性的结构,然后才是其他。由于视思想观念为一种理性的结构,重视的是它的理论逻辑,强调的是它的纯粹观念层次的意义空间。一旦以这种方式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我们发现,常常出现这样两种不同的结局:不是思想贫乏,就是极具思想观念的高度。以“五四”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陈独秀与胡适为例:人们不是视其思想浅薄,缺乏理论“深度”,就是将其中一人予以拔高;而这两者孰为高,通常又由研究者主观的偏好与思想立场所决定。
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对于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不能采取像以往那样的观念分解的方法进行,而必须正视其首先是一种参与式的思想观念并引入新的研究方法。那么,这种对于参与式的思想观念的研究,必须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要对参与型思想观念的特质有所把握。所谓参与型思想观念,由于强调思想观念对于社会改造的参与作用,因此,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追求观念的现实效果,以行动来检验观念;2.强调观念的现实来源而非理性反思(工具主义的经验论);3.追求观念的最大有用化;4.行动优先于观念,观念的图解化与标语化、口号化;5.行动可以说明观念,最终以行动取代观念;6.对单纯观念或纯粹观念的鄙视。
可以看到,以上一些特点,都为20世纪的中国社会思想所具有,并且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话语形态。因此,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思潮史的研究,首先就要求把握20世纪中国思想观念的这些特征并且进行分析。
从这样一种对于思想观念的先行领悟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20世纪的中国思想观念非但不贫乏,而且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观念“称霸”的时代。就是说,这非但是一个各种思想观念“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各种思想人物将“其道易天下”的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并且最后又以某种思想观念的力量完全改写了20世纪中国历史地图的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其意义已超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本身,它还揭示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社会变革的深层思想动因。
二、“启蒙观念的异化”:20世纪中国思想观念演化的中轴原理
其实,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导致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革之诸种复杂因素的理解,它对于一般的世界近现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也具有范型的意义。
之所以说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可以为世界范围内的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提供某种范型,是说通过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于近现代思想观念的一个根本特性——现代性的涵义具有更好的领会与把握。所谓思想观念的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发生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事件,而且是理解世界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普适性观念。那么,所谓思想观念的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解,思想观念的现代性意味着思想观念从注重价值理性到强调工具理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对于工具理性的强调,可以作为衡量思想观念是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考察,所谓思想观念的现代性,不仅仅是强调工具理性,更重要的应当是强调思想观念的实践性与变革社会的能动性;而工具理性作为现代性思想观念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将其置于强调思想观念改造社会的能动性与实践性这一基础上才能得以理解。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中所说的“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观念,才是一个更为恰当的刻画思想观念的现代性的定义。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代性起源于启蒙理性。而所谓启蒙理性尽管包括工具理性,但工具理性却不足以涵盖启蒙理性。或者说,启蒙理性较之工具理性来说,更能传达出现代性思想观念的精神。但是,启蒙理性仅仅是表达现代性思想观念的一个具象性观念,它还不足以揭示现代性思想观念的本质性含义。但通过对启蒙理性发生与演变的历史性考察,我们发现:启蒙理性其实是跟社会生活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历史事件的大众参与或者说群众性社会运动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离开了群众性的社会动员,也就无所谓启蒙理性。从西方启蒙话语的兴起来看,它首先是针对社会大众(也包括参与社会运动的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的,而非沙龙式的对话。这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启蒙话语的勃兴可以得到证明。
启蒙理性除了强调其社会性的启蒙与大众动员这一社会改造目标之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观念,它还意味着观念的“异化”。就是说,当启蒙理性刚刚兴起时,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观念而出场的,尽管它的目的指向相当明显:是致力于通过社会启蒙而改造现实社会;但当启蒙运动进一步发展,乃至于其社会改造的意愿更为紧迫时,原初以启蒙姿态登场的思想观念却发生异化:从作为一种观念的出场转化为行动。这时候,尽管它表面上可能仍然是“观念”,其实,它已丧失了观念的先导性,而流为行动的附庸。也就是说,它其实已失却了思想启蒙的意义,而成为社会行动或者社会大众的代言者。因此,启蒙理性作为一种现代性诉求来说,其思想内部蕴藏着异化的胚芽。从这种意义上说,近现代的社会思潮史既是一部启蒙话语的历史,更是一部启蒙话语的异化史。
然而,这并非启蒙思想的“意义失落”。也许,作为一种理性的启蒙话语,它是变异了;但是,作为一种原初就强调其社会实践功能的思想观念来说,却又似乎是“完成”了;至少,它通过社会运动或者社会变革的成功实现了它原先的要求。因此,也可以说,启蒙理性作为实践理性,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得以“涅槃”。社会变革的成功,既抛弃了原先的启蒙话语,但同时却又是这种启蒙理性的展开以及得以彰显其意义与价值。
通过以上对于启蒙理性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思想观念的现代性其实是一种启蒙理性,这种启蒙理性具有强烈的变革现实的实践品格;然而,随着启蒙话语与社会变革实践活动的结合,它必然会发生异化。如果说在近现代以降的世界历史上,曾经普遍地演出过这种启蒙话语登场旋又异化的戏剧的话,那么,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这种启蒙话语的实践品格及其发生变异的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里,我们不对启蒙话语的历史命运与意义作过多的展开,而是要从启蒙话语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抽取出它的一系列特性。对于启蒙话语的这些特征的认识,会给我们以提示:对于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观念(严格说来,近现代思潮史)的研究,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研究策略与路径?
其一,大思想史观:不能就观念而论观念,而必须将观念的范围延伸到观念之外,如各种行动(行动即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切现代史都是思想史,而思想史也表现为“行动史”。
其二,明辨观念的深层结构:对思想观念的表面与深层作出区分,此也即思想观念的“意义”与“意味”的区分。现代性的思想观念的“意味层次”皆有强烈的行为指向,而非纯然思辨的游戏(观念的意向性对象是行动)。
其三,观念的图式化与“标签化”(现代性的思想观念要唤起社会大众的参与热情,就必然如此)。
其四,观念的乌托邦化:一方面固然是工具主义的,另一方面又是乌托邦式的——观念要提供某种理想与信念,才能有某种“向心力”,从而对社会群众运动起到凝聚作用。
其五,观念表达的社会诉求:此乃指观念的内容要围绕社会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展开;尤其要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期待。这可以解释20世纪中国思想观念的内容与兴奋点所在。
其六,观念的载体:小知识分子或者边缘化知识分子。此可以解释思想与学术的分离,沙龙(象牙塔)与街头的分离。
其七,对观念意义的理解与解读,也必须联系到社会运动。例如对梁漱溟思想的理解。
以上种种,既是“行走的观念”所具有的特性,亦可以说是对于“行走的观念”的研究所应当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三、乌托邦观念的否定辩证法:20世纪中国思想观念的普遍宿命
作为启蒙理性的原初思想观念,是一种乌托邦观念。所谓乌托邦观念,是指观念具有理想性。任何一种具有变革现实社会指向的思想观念,都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观念;否则,它难以激发起人们投身于变革现实社会的热情。然而,任何乌托邦观念又具有悖论的性质。就是说,一旦它激励起人们投身于现实社会改革的热情,并且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与助燃剂的时候,它又无所逃于被异化的命运,失去其原先具有的“革命性”与思想的颠覆性,而力图使思想向行动靠拢与妥协,让观念为行动提供注解或顶多是策略性原则。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乃20世纪中国思想的必然归宿,各种社会思想与思潮均无所逃于此一结局。此不独具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为然,即使以稳健著称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以保守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思想亦然。
否定辩证法是乌托邦观念的普遍宿命,此乃由其内在包含着的悖论所引发与决定。这是因为:观念终究是观念,行动与观念之间始终构成一种张力。这两者虽则在短期之内会联手,从长久来看,终究会分离。故殷海光认为,从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看,“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动理”的结果。而对于观念自身来说,此则意味着观念的变形与异化:一方面,观念的能量与价值已提前支付(思想的“透支”严重),带来的是对思想观念的不信任与观念无用论或观念实用化、虚无主义的流行;另一方面,对付观念虚无主义或观念实用化的,是另一种观念乌托邦的兴起。此乃尼采所谓“永恒之轮回”。此种情势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最为突出,既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性所引起,亦由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所决定(中国传统观念强调思想观念的“入世”品格,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种思想遗产)。
由此我们看到,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其实是乌托邦观念异化的进一步展开与下一个思想环节: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否定”。两者的相异之处在于:后者的否定发生于某种思想观念的内部,而前者则指后起的乌托邦思想观念对在先的乌托邦思想观念的否定,它发生于观念与观念之间。一部20世纪中国思潮史,就是这样的一种乌托邦的异化以及乌托邦思想观念相互更替与取代的历史。
四、从“行走的观念”看当代世界观念的走向
观念的异化以及观念的否定辩证法是观念在现代的必然宿命,唯其在20世纪中国,它采取了更为典型的形态,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而已。马克思早就说过:哲学必须改造世界。此乃观念现代性的谶语(一语道破了观念现代性的实质:即现代性观念的行动与实践指向)。20世纪世界(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均如此。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也是一种行走的观念乌托邦)会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与小知识分子)中获得极多的信徒,而且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以后,“形而上学观念”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代之以“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考。而当代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乃至于经济哲学、生态哲学等的盛行,无不是此种“行走的观念”的思想谱系的延续与表征。与其结伴而来的,是后现代主义及其观念的兴起:去观念(其实是去乌托邦观念)、去中心(去乌托邦中心)、去理性(理性已堕落为行动,故无存在之必要与价值)。此种思潮在哲学上的最新表征,乃身体哲学的兴起与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