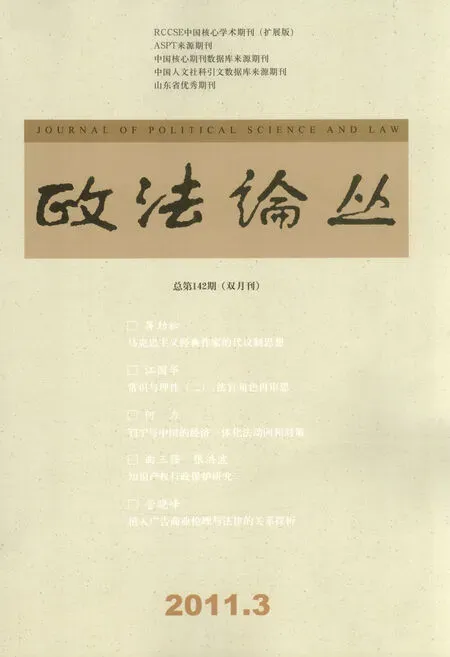寻求法律与国情的平衡
——北洋政府时期亲属法立法与司法活动评析
翟红娥 陈 昊
(1.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昊舜律师事务所,山东 济南 250014)
寻求法律与国情的平衡
——北洋政府时期亲属法立法与司法活动评析
翟红娥1陈 昊2
(1.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昊舜律师事务所,山东 济南 250014)
北洋政府时期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结合司法案件的审理,灵活运用其大理院判例和解释例,不但满足了当时的社会实际需要,同时也为成文法的制订和完善提供了现实的素材和资料。他们这种稳定求实的法律移植态度、重视司法实践、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现实等做法,正是我国当代民事立法所应借鉴的。
民事习惯调查 判例 解释例
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动荡,旧的传统制度迅速解体,中国在外来势力和内在动力的不断推动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主动和被动地受到来自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冲击与影响。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也开始全面转型,固有的中华法系一步步走向瓦解,步入了法律制度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亲属法的立法备受争议,也使立法者倍感困惑,因为亲属法与本国的传统习俗密切相关,一些固有的传统观念如男尊女卑的夫权制度、妾制等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但又与近代“自由”、“平等”观念格格不入,使得亲属法的变革处于两难境地,比起民法的其他制度来,移植国外立法与本土习惯法之间的冲突更明显。因此当时的立法者们在没有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吸取西方先进立法思想和尊重国内风俗习惯的困惑中摸索前进,既要保证引进的法律先进,又要考虑到本国的国情和民情,把其改造成适合中国现实社会需要的形式。那么,民国时期立法者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应该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立法、司法活动的得失与效果?我们可以从北洋政府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管窥一斑。
一 、北洋政府时期亲属法的立法背景
(一)政治与外交的压力迫使北洋政府加快立法进程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中华民国,但是对于治外法权的收回却屡遭西方列强的拒绝。所以民国以来的历届政府继续为之努力。1914年一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上,北京政府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正式提出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但是未得要领。由于西方列强允诺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条件是,中国律例及审断办法等“皆臻完善”,[1]所以,1918年(民国七年)七月份,北洋政府设立了修订法律馆,继续进行各项法律的修订。1921年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北洋政府代表王宠惠再次提出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一问题,请求到会各国确定期限放弃领事裁判权,但西方各国对于王宠惠所提出的领事裁判权问题在会议上只是对中国这一状况表示了同情,而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不过会议最终形成决议,决定由西方各国派员到中国实地调查中国的司法状况,并依据调查情况决定西方各国在中国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问题。在这一事项的影响下,北洋政府责令修订法律馆加快立法进程,积极编纂各项法律。
(二)社会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和进步思潮的影响有力推动和影响着北洋政府立法
自辛亥革命以来,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深入,使女性的经济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从而对以维系家族延续为目的的婚姻家庭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者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就提出了一系列家庭变革的思想,后来这些思想在民国成立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履夷在《留日女学会杂志》第1期发表了题为《婚姻改良论》的文章,提出:“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打破家庭间重重魔障……为男女同胞辟一片新土。”[2]P56后来《三纲革命》、《家庭之革命》、《女子家庭革命论》等文章陆续在各类进步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提出了倡导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等进步思想。金天翮所著《女界钟》更是详细论述了伸张女权的思想,提出女子应享有的入学、交友、营业、掌财、出入自由、婚姻自由等权利,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所以适应当时社会实际需要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观念的变革,这些婚姻家庭变革也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立法和司法。正如当时大理院院长所说:现今我国新旧思想极不融合,大理院近正踌躇此平见之判例。如关于婚姻问题,在昔日为父母代订,今则讲自由婚姻,且因潮流所趋,离婚案件日渐增多,审判衙门安能据旧规理判不离。新闻杂志对于新思想极力鼓吹,司法当局不能不顾现代思想。[3]
二、北洋政府时期立法概况
(一)北洋政府亲属法立法过程
1.1915年(民国四年)亲属法草案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成立了法典编纂会,后又裁撤了法典编纂会而设立法律编查会。法律编查会对《大清民律草案》中的亲属编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于1915年(民国四年)完成了修订工作。这一草案同样分为七章,共141条,章目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大致相同,其中第一章总则改为通则,第二章家制中只设了总则一节,第五章的第一节未成年人之监护,分为了监护之成立、监护之职务和监护之终止三款,并且增加了第三节保佐。由于在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动荡不安,袁世凯又在一心筹划恢复帝制进行复辟,再加之北洋政府组织本身就严重不完备,使这一部草案的立法意义进步不大,从草案的内容上来看,也没有十分明显的内容变化,在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方面也是基本上按《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所进行,均没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这部草案可以说基本上是清末婚姻家庭立法的翻版。1915年(民国四年)亲属法草案由于袁世凯解散议会而没有能够付诸议会进行表决,结果该部草案无疾而终。
2.1925年(民国十四年)第二次民律草案的制定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来不及制定新法,暂时援用清朝的法律。除此之外,还继续各部门法典的制定活动。在亲属法方面,曾起草过三部亲属法草案,第一部主要是在清朝法律和法律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其立法宗旨和内容与之相差不多;后来北洋政府的法律编查会又进行重新修订,在修订民律过程中,不但详细参考了《大清民律草案》,并且结合全国的民商事习惯的调查结果,进而又认真参照了各国的最新立法例,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民律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各编草案,这也就是民国法学家通常所称的第二次民律草案。
在1915年第二次民律草案的制定过程中,修订法律馆在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后,制定了《民国民律草案》。其中亲属法草案同样分为七章,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为家制,在本章中增加了“家产”一节;第三章为婚姻,第一节改为婚姻之成立,分为“定婚”、“结婚”两款,第三节婚姻之效力,分“夫妻之权利义务”和“夫妻财产制”两款;第四章增加了“亲子关系”、“养子”两节;第五章第三节改为“照管”。
据修订法律馆总裁江庸所列举的理由,之所以进行上述修订的原因在于:“旧律中亲属继承之规定,与社会情形悬隔天壤,适用极感困难,法曹类能言之,欲存旧制,适成恶法,改弦更张,又滋纠纷,何去何从,非斟酌尽美,不能遽断。”[4]P748
(二)北洋政府亲属法的立法特点
1.立法者注重民商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立法
由于民国时期亲属法与清末亲属法有着天然的衔接性,虽然清朝末年的民律草案亲属编时间短暂,并且没有颁行,但却是后来民国亲属法立法的基础和开端。因此北洋政府在修订民律过程中,详细参考了《大清民律草案》,并且还结合了清末时进行的全国民商事习惯调查结果。后来修订法律馆认为清末所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因为时间和过程均过于仓促,所采用的方式是问答式,其内容也不尽人意,收集资料对于法典制定的参照意义不够。再加之当时民国没有颁行正式民法典,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无法可依”的问题,大量民商事案件均需依传统习惯断案,因此为了解决实际司法审判工作的需要,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在这次的全国性民商事调查中,调查的方式由原来的问答式调查改为陈述式调查,并力求取得调查情况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次民事习惯的调查,由北洋政府司法部负责,在各省均设立了民商事习惯调查会,对于调查活动订立出了详细的操作规程。这次民商事调查活动的起因与调查的目的与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并不完全相同,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是为了制定《大清民律》,并使所制定的《大清民律》能够适于中国当时的国情需要。而民国的这次民商事习惯调查的直接起因则是由于1917年(民国六年)奉天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一篇呈文,在该呈文中写到:“奉省司法衙门受理诉讼案件以民事为最多,而民商法规尚未完备,裁判此项案件,于法规无依据者多以地方习惯为准据,职司审判者苟于本地各种习惯不能尽知,则断案即难期允惬。习惯又各地不同,非平日详加调查不足以期明确,厅长有鉴于此,爰立奉省民商事习惯调查会。”[5]P2北洋政府司法部在批文中认为“该厅所拟设奉天省民商事习惯调查会,专任调查各地习惯,所见极是,殊堪嘉尚”。[5]P3后北洋政府司法部于1918年(民国七年)向各省下发“通令各省高审厅处仿照奉省高审厅设立民商事习惯调查会,并限自令到日起四十日以内报部”的训令,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随之展开。这次民商事习惯的调查活动由1917年(民国六年)一直持续到1921年(民国十年),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由施沛生、鲍荫轩、吴桂辰、晏直青、顾鉴平共同编纂了《中国民事习惯大全》,之后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前后,又陆续编制汇总成《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等资料,这些资料不但直接满足了民国初年民商事案件审理的需要,也为下一步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这种重视社会调查的做法正如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天津《大公报》的时评文章所写到的那样:“按亲属继承两编所规定者,悉为身份关系,故于法律的社会生活,最为密切,其立法亦缘是十分困难的,间尝详绎内容,虽不必一一当意,然大体上要能于新旧思潮中,辟得一立足点。”[6]P256这里的立足点恰恰就是中国亲属法立法的取舍点和基本点所在,而辟得这一立足点的过程就是民国政府社会调查的传统习惯与外来西方先进法制的结合点所在,是对西方婚姻家庭制度移植的立足点和取舍标准。民国时期立法者在法律移植过程中,这种对中国的传统习惯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排挤,而是以开放式的方式给予一定程度的接纳,将符合社会需求的一部分民间习惯上升为国家法,并以此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机制的做法,对于今天的法律移植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单从我国现行婚姻家庭立法看来,虽然现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早已超越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但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制依然受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法族规、村规民约及地方习惯等民间性法律制度的严重冲击。虽然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秩序结构已经逐渐解体,但这些中国民间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国家法”之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冲突和排挤。所以说“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不单单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更是观念与利益选择之间的冲突。如果说现行“国家法”所追求的理念是现代的法制秩序,而“民间法”则体现出了道德、传统习惯和现实利益的均衡,二者之间因理念不同,就不可避免地在现实中产生冲突,并在实践之中的适用和选择上出现相互间的排挤和排斥。这一冲突必然让我们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之中,应该注意到我国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传统性,对国家立法与民间依然保留的各种习俗性规范进行必要的整合。这样才能即有助于树立国家法的权威,又有助于民间婚姻家庭秩序的现实调整。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上讲,对于制定法关注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对习惯法权的体现和对于现有民间习俗的调查研究,尊重确实存在的法律本土文化,对于有价值的习惯以制定法的形式赋予其独特的法律价值。
2.立法者重视法律与中国固有的传统习惯、司法判例相结合,避免法律与现实的脱节
1925年(民国十四年)亲属法草案中,最突出的变动在于加入了当时现行刑律的民事有效部分以及历年的大理院判例,这也反映出立法者注意到《大清民律草案》中的亲属法与现实的脱节问题,并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修正。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比如在“婚姻之成立”一节,不但顺从了我国的民事习惯,并且参照了大理院判例,在此基础上又参考了德国、瑞士民事法典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定婚”的内容。定婚的条款中,在保障传统法中的尊长和家长的主婚权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比如在第39条中规定:“男女双方虽经定婚,但仍不得以之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但父母或监护人于定婚后反悔,而当事人两相情愿结婚者,不在此限。”[7]P93在第三章第三节“婚姻之效力”的部分,增加了“夫妻财产制”的相应条款。这一条款规定夫妻财产制分为“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两种,其中“约定财产制”规定得较为简略,“法定财产制”规定得则较为详细。这一立法做法与当时的社会实践也较为适应,并且进一步照顾到了日后的立法进步和发展的空间。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约定财产制的做法极为少见,如果对其做出详细规定的情况,一是没有现有的案例和习惯可供参照,二是其效果及具体情况尚无实践性资料给予支持,三是约定财产制的规定本身代表了一种立法取向,而这一立法取向是家庭婚姻立法的发展方向。对于“法定财产制”的规定,相对于“约定财产制”来说则要详尽许多,也更加体现出了立法者在传统规定与近代立法之间的权衡与选择。首先,夫权依然得到法律的肯定,第81条规定对于妻的特有财产“夫有使用收益之权”,同时第83条规定“妻之特有财产,由夫管理”。对于妻的特有财产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妻在家庭地位上提高,使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
三 、北洋政府司法活动的特点
由于北洋政府时期民法典的缺席,在实践审理案件之中所实际援用的,均是《大清现行刑律》的民事有效部分,这一部分成为了当时的婚姻家庭法律规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由于该立法是属于传统立法的内容,所以其中有着许多传统宗法伦理的规定,与近代宪法所提倡的“平等、自由”等民主精神严重不符,这就与法律规定出现了冲突。如何调和这一冲突,成为了当时司法实践的突出性问题。
(一)判例与解释例和“条理”具有良好的适用力
1.判例与解释例
北洋政府时期,在以《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基础上,以大理院判例、解释例和法律“条理”做为审判依据,通过对于社会实践中案件的审理和处置,不但较好地满足了不断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为下一步正式《民法典亲属编》的制定打下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在民国初期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大理院的判例、解释例始终能够得到全国各地各级审判组织的遵守和执行,这本身也说明了大理院判例、解释例的良好适用力和比较权威的法律水准。
为了解决法律规定与现实的冲突,又由于现行法律中的条文有限,北洋政府的大理院大量地制作判例做为成例,因为其灵活性和适应性,逐渐成为了当时处理案件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同时由于当时的审判人员法律知识浅薄,又缺乏司法经验,所以经常将遇到的法律上的疑难问题呈请上级法院解释,于是逐步形成了与大理院判例处于同等位置的还有“解释例”。1915(民国四年)六月公布的《修正法院编制法》第33条规定“院长有权对于统一解释法令做出必应的处置”。 大理院的解释例事实上就是由“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做出的解释。民国初年,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曾针对一些案件对于做出解释,大理院的解释例由统字第1号至统字第2012号止。民国十六年( 1927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大理院改为最高法院,解释例的编号由统字第某某号改为最高法院解字第某某号,并从第1号开始重新编号。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开始,民国政府司法院也开始就一些法律法律问题做出解释,编号为院字第某某号,这些法律解释也可以归于解释例的一部分。上述这些解释例与判例同时成为了当时的重要法律渊源。
2.援引“条理”
在民国初年,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还可以援引 “条理”来作为断案依据。 所谓“条理”,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法理”、“法律原则”等概念。民国初期的法学家也是持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法学家胡长清所著的《民法总论》中就提出:“即通常之原理,例如,历来办案之成例及法律一般之原理原则。”[8]P68同时期的其他法学家如梅仲协、陈克生等人也均持类似的观点。这也表明资本主义民法原则开始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二)司法实践援用判例、解释例的社会效果与意义
北洋政府时期,判例和解释例中对于婚姻家庭的法律规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判例和解释例在承认传统法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具体案件的审理和援引西方法理等方式,使这些法律规定能够顺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些判例和解释例更符合婚姻家庭立法的本身规律,也更加符合当时过渡时期的社会实际需要。
通过一些实践中司法案例的审理结果,可以十分清楚的体察到上述情况:
刘志怡等
据刘王氏供:年三十一岁。二十一岁嫁到刘家。翁姑已故。刘家有屋一进,今年添造一进,都是三间两厢。田地四十余亩,十年以来并无口角。就是不曾生育,所以刘志怡要与小妇人离婚。据刘志怡供:年三十二岁。无叔伯兄弟。妻王氏是规矩的,惟不曾生育,无后则不孝罪大,纳妾则养活为难。所以商恳岳父王心礼请与王氏离婚,以便另娶。据王心礼供:女儿嫁刘志怡十年多,从无过犯。今因无子在七出之条,职员亦无可奈何。但女儿如何安身,求恩断。质之族长刘尚仁,据供:刘王氏勤俭作家,亲族皆知。刘志怡因无子离婚,亦是出于无奈。闻说王氏不愿再嫁,王心礼又家道平常,要求堂上做主。各等语。查人子无后为不孝,固有明训。妇人无子则应出,亦著科条。但本县窃有疑焉。无后不孝之说,盖为不娶者言娶焉,而不父则天也,天则无可如何之事,岂能加以不孝之名。女子身为人妇,岂有甘心于无子者。妇焉而不母亦天也,而乃列在七出之条,此虽载之礼经,详之律注,而揆诸情理,总觉未安。况乎气血有强弱之不同,形体有参差之相限。固有男子初娶无子,别婚则又生。女子初嫁不生,别醮则生子。是其所以无子之故,固不专由于女子也。今刘志怡以王氏十年不育,辄欲弃旧谋新,以图似续。征之宪典不为无辞,而对于王氏则浇薄已甚矣。人家最难得者,内助。内助得人,则居积有余,蒸蒸日上。否则颠倒错谬,日败坏于零销暗蚀之中而不之觉。检查刘志怡户册,该户光绪二十四年田只二十四亩,地只四亩七分。而自是年至宣统元年,陆续加田至三十九亩,地至九亩七分。察度情事,苟非刘王氏助理得宜,安得有此境地?乃知刘尚仁所称勤俭作家,确非偏护之语。是王氏于刘志怡无子问题姑且勿论,即就其持家言之,固亦所谓柴米夫妻也。乃刘志怡全无香火情,竟援无子之律请求离异,夫也不良,刘王氏可谓不幸。此案本应责令照常完聚,惟情既乖离,势难强合。欲谋善处之方,惟有分炊之法。应令刘志怡将住屋后进三间两厢分与刘王氏居住,拨出田十六亩、地四亩,又耕牛牲畜农器什物匀分一半,统给刘氏自行管理。田地不得以瘠壤充数,即著刘尚仁、王心礼协同分派,予限十天处理呈报,以凭核夺。刘志怡宗祊为重,买婢纳妾,刘王氏不得干预。刘王氏如欲乞养女孩,以娱晚景,刘志怡不得阻挠。既据允服,均著具结存查。此判。[9]P98
上述这一判决中,刘志怡引用《大清现行刑律》中关于“七出”的规定,呈诉离婚。“载之礼经,详之律注”,应当说是法律依据相当充分,但审判者的判决在认定时却因“揆诸情理,总觉未安”,没有援引“七出”之明文规定做为依据进行断案,并且对于“无后则罪大”解释为“无后不孝之说,盖为不娶者言娶焉,而不父则天也,天则无可如何之事,岂能加以不孝之名”。[10]P241更进一步在判决中指出:“是王氏于刘志怡无子问题姑且勿论,即就其持家言之,固亦所谓柴米夫妻也。乃刘志怡全无香火情,竟援无子之律请求离异,夫也不良,刘王氏可谓不幸”。[10]P241从这一案件的审理结果可以看出,审判者在审理的过程中适用法律时并没有拘泥于《大清现行刑律》中的相应法律条文,而是根据民国初年的社会现实,依情理断案。在这一案件中,审判者不但没有依“七出”的法律条文判准离婚,反而将家中财产,分出相当一部分交由妻来管理和使用,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当时司法中参酌情理的传统,又能采纳外国先进的法理原则,并且也与近代宪法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相一致。
上述特点同样可以在民国时期的大理院解释例中找出踪迹,大理院统字第576号解释例:“居丧嫁娶及出妻义绝皆旧律为礼教设立防闲,遇有此种案件,适用该律仍宜权衡情法,以剂其平,不得拘迁文义致蹈变本加厉之弊。”[11]大理院统字第591号解释例:“妻虽具备无子之条件而有三不去之理由者,仍不准其夫离异。至所称无子之义,系指妻达到不能生育之年龄而言,此项年龄应准用立嫡子违法条内所定五十以上之岁限。”[12]从上述两则解释例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些解释例对于传统法律中所规定的“嫁娶、出妻、义绝”“无子”均根据社会的实践发展状况赋予了新的内容,对于实际案件的处理,则要求“权衡情法,以剂其平”,从而使这些旧有的法律规定所包含的法律内容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审判机关不断地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在处理案件时通过种种解释使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一步步向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比如一方面承认了固有传统法制中的定婚制度,确认定婚是婚姻关系的成立要件,并对于家长、尊长的主婚权予以认可,但另一方面,又一步步确认了男女自由订立婚约制度,对于家长、尊长的主婚权进行限制,赋予成年子女对于婚约、结婚的最终决定权。对于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地位的提高也是通过一系列不同案件的处理,一步步赋予妻与夫同等的权利,使妻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渐渐提高,包括离婚呈诉权、财产所有权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进步。这些司法案件和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到后来民国正式民法典中亲属编的制定,应该说正是大理院等审判机关通过自身对于实际案件的审理,在实践中一步步推动了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近代化。美国法学家梅利曼曾写到:“法律根植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做出回应,从根本上说,法律是人们认识、阐述和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一定的历史方法。”[13]P155民国时期的这一司法实践,正是对于这一说法的最好注释。
(三)司法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立法的发展
从大理院的司法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出司法实践对于立法的有力推动作用。司法实际中的审判活动以司法案例的形式深深影响着立法。在1930年(民国十九年)正式《民法典亲属编》实施之前,习惯法是一种重要的断案依据。在民国初年大理院的审判实践中,大理院1913年(民国二年)上字第三号判例,对于“习惯法”的成立要件做出阐述,习惯法成立之要件有四:(1)要有内部要素,即人人有有法之确信心。(2)要有外部因素,即于一定期间内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之行为。(3)要系法令所未规定之事项。(4)要无悖于公共秩序、利益。[14]P30这一规定直接界定了司法过程中对于习惯所认可的四个要件,习惯只有全部符合上述四个要件才能被认为构成了“习惯法”,成为处理案件的依据。民国五年(1916年)上字820号判例也指出:“法无明文规定则应遵从习惯及条理”。所以民国初年的大理院及各级审判组织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十分尊重判例及判例中所认可的习惯。正是由于大理院及各级审判组织对于习惯的重视,所以在实践中均十分注重民商事习惯调查的价值,大理院在采用这些民事习惯的时候,也不是无原则无摘选的全部录用,而是依据西方婚姻家庭立法过程中所确立的一些原则有选择的给予认可和适用。一般来说,对于立法已有明确规定的,通常不适用习惯法。其次,对于所援用的习惯,必须符合“公信公认”的标准,“须以多年惯行之事实及普通一般人之确信为基础”。第三,须不违背公共秩序和利益,对于传统的中一些与“平等、自由”等基本原则的陋习,如果违背公共秩序和利益,则可以摒弃,而改用条理作为断案标准。这些司法判例中的很多判例直接为《民法典亲属编》提供了立法资料。
对于我国现行婚姻家庭立法来说,也应该认真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各种情况,对于我国现行立法进行不断的完善。比如在婚约问题上,由于婚约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尤其是广大的农村还广泛存在,在基层法院有大量的实际案件涉及婚约的内容,表现为财礼的退还问题,解除婚约的赔偿问题等多个方面,但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于上述问题均未做出规定,可以说是采取了回避的立法态度。法律的天职就是解除各种纠纷,与其回避,不如总结司法实践,做出符合社会实际的立法,以满足调节社会关系的需要。
总之,北洋政府时期立法者所面对的是与中国传统社会格格不入的西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婚姻习俗,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结合司法案件的审理,灵活运用其大理院判例和解释例,不但满足了当时的社会实际需要,同时也为成文法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现实的素材和资料,从实践的角度为立法者把握着亲属法的步伐和取舍,从而使其沿着由浅及深、由法律原则到法律制度的方向一步步深化,并最终完成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这种稳定求实的法律移植态度,重视司法实践、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现实等做法,正是我国当代民事立法所应借鉴的。因为现在在制定法律时,过多地注重吸收国外的法律,强调与世界接轨,而忽视本国的民间习惯,不适合中国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背景,导致法律与社会出现“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因此在我们当今社会,应该借鉴这一宝贵的经验做到司法实践与立法相结合,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注重对本土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调和国家立法与民间依然保留的各种习俗的冲突,对之进行必要的整合。这样才能既有助于树立国家法的权威,又有助于民间婚姻家庭秩序的现实调整,使法律在其内涵、精神和智慧等方面真正贯注入中国社会,并发挥调整生活的作用,真正实现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1] 张生.民国初期民法的近代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 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 余启昌.民国以来新司法制度[J].法律评论(第5卷),1925,3.
[4] 谢振民编著,张知本点校.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 民商事习惯调查录.民国北洋政府司法公报(第二四二期)[J].1917.
[6] 肖爱树.20世纪中国婚姻制度研究[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5.
[7] 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8] 胡长清.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9] 许文濬著,俞江点校.塔景亭案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谢林,陈士杰,殷吉墀编.卢静仪点校.民型及裁判大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 维基文库网.大理院统字第576号解释.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A4%A7%E7%90%86%E9%99%A2%E7%B5%B1%E5%AD%97%E7%AC%AC576%E8%99%9F%E8%A7%A3%E9%87%8B&variant=zh-cn.
[12] 维基文库网.大理院统字第591号解释.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A4%A7%E7%90%86%E9%99%A2%E7%B5%B1%E5%AD%97%E7%AC%AC914%E8%99%9F%E8%A7%A3%E9%87%8B&variant=zh-cn.
[13]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二版)[M].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4] 王新宇.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SeekBalanceBetweenLawsandNationalConditions——AnalysisontheLegislativeandJudicialActivitiesDuringPeriodofNorthernWarlordsGovernmentofChina
ZhaiHong-e1ChenHao2
(1.Law S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nan Shandong 250014; 2.Shandong Haoshun Law Office,Jinan Shandong 250014)
The legislator applied the prejud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law of Supreme Court in a flexible way combined with the judge of judicial cases in th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Northern Warlords Government of China, in such way, it not only met the actual need of society, but also provided data and material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perfection of statute law. The contemporary civil legislation in China can borrow the ideas from their stable and realistic behaviors such as the transplanting attitude to law, valuing juridical practice and emphasizing social investigations and social reality and so on.
civil customs investigation;prejudication;interpretation case
DF08
A
(责任编辑:张保芬)
1002—6274(2011)03—106—07
翟红娥(1973-),女,山东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法史学;陈昊(1973-),男,山东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昊舜律师事务所律师,研究方向为法史学、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