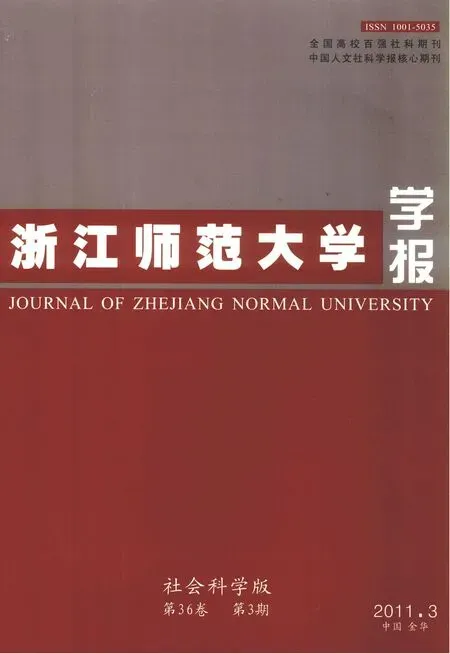世俗生活中的卑微人生
——“重返”汪曾祺“八十年代”①小说创作*
陈发明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7)
一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1949、1963年分别出版了两部小说集:《邂逅集》与《羊舍的夜晚》。但毋庸置疑,他小说创作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却是1980年《受戒》发表以后,“八十年代”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丰收期”。
如何理解汪曾祺之于20世纪80年代的意义?如何重返他这一时段的小说创作?在“重返八十年代”甚嚣尘上的当下,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话题。如果立足20世纪80年代主流创作背景,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无疑是一个相当“另类”的存在,用“伤痕”或“反思”等文学话语无法阐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曾祺始终是当代小说研究界颇为关注的作家,对他的小说的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话题。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笔者认为,重要的观点大致有三:一是从小说创作的艺术渊源角度,挖掘其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将其界定为“笔记体小说”。②二是将汪曾祺的小说界定为抒情小说,有的研究者甚至更为关注其与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的师承关系。③正是基于上述的文体归类,其作品的“散文化”文类特征是很多研究者都谈到的话题。④三是将汪曾祺小说放在“寻根文学”流派论述。汪曾祺小说蕴含的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是评论界热衷的话题,有些论者在此论基础上,把他的小说界定为“寻根文学”的滥觞。⑤总体而言,研究界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着眼于对其创作与传统的关联,着眼于其小说的文体特征、叙事结构等意义。把汪曾祺小说归为“笔记体小说”也好,“抒情小说”、“寻根小说”也罢,在某种意义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也能在某一小说流派中揭示其艺术价值。但笔者认为,对有着独特创作特色的汪曾祺小说的研究,并没有走出主流文学史叙述的藩篱。众所周知,主流文学史论述明显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和进化论史观的影响和束缚,将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概括为一个接一个创作潮流的更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新写实文学。这类叙述现在已经成为目前通行文学史的“共识”,这一研究成果基本体现在目前比较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中。⑥主宰这一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观念是建立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是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待文学,带着明显的功利主义立场,带着浓厚的历史目的论色彩,将“文革”后的文学理解为“文革”前文学的承继和恢复,继而是文学摆脱主流政治的制约回到人学自身,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文学自主发展模式的文学史观。将汪曾祺的小说纳入这一叙述框架,将其纳入“新笔记小说”、“抒情小说”甚至拉入“寻根小说”之中来展开叙述,尽管可以揭示其文本外在的某种形式特征或与传统的关联,但笔者认为这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笔者认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对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变革与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二
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源自于他对主流创作的自觉背离,这是无需赘言的事实。正如汪曾祺常说的那样,他的小说与政治、时代结合得不紧。他曾明确表示:“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1]基于这样的文学创作追求,在“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潮流风起云涌之际,在文坛痛批“四人帮”的罪孽,揭示血淋淋的“伤痕”之时,汪曾祺却把笔触伸向了琐碎、庸常的世俗社会,把自在、自为的世俗世界和卑微人生带进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世界。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些世俗社会中的庸常个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既没有高远的奋斗目标,也没有宏大的人生理想。他们有自己的世俗生活轨迹,也有自己的生活情趣,虽也有生之艰辛、命运之无奈,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怡然自乐,从容潇洒。阅读汪曾祺的小说,我们有种恍如隔世之感,20世纪80年代之初盛极一时的重大题材、宏伟主题、崇高形象杳无踪迹,他的小说聚焦的是高邮、昆明、北京等地的世俗生活,讲述的是凡夫俗子的吃喝拉撒,展现的是世俗社会中的庸常人生。
笔者依然从他的名篇《受戒》谈起。作品中的菩提庵与其说是佛门净地,毋宁说是一个世俗化的日常生活世界。按通常生活理解,当和尚就意味着了却尘缘,过一种非同常人的苦行生活,但离家修行的明海却在他容身的菩提庵享受着一种无拘无束的世俗般的人生欢愉。小和尚明海,除了早晚跟师傅念经,完全是一个俗家的子弟。他在菩提庵的俗化世界里健康成长,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小英子家出入,帮助她家干活,和小英子无拘无束地谈情说爱。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明海受戒之日,正是他们的爱情抵达高潮之时。在菩提庵这个世俗化的自为世界里,在明海出家到完成受戒仪式的过程中,汪曾祺为我们叙述了一个纯美、淳朴的爱情故事,塑造了明海和小英子这两个原生态世俗社会中自由、舒展而又纯净美好的个体形象。
《大淖记事》给我们展示的同样是一个世俗化生活世界。“大淖”是一个怎样的生存世界呢?小说用了三节来记述当地的风土人情,大淖的世俗化生存景观在读者的视野中不断延展,只到第四节才出现人物。作家首先给我们描绘了淳朴、明净的水乡风光,小镇的格局,小镇的风物、人情。接着,作家娓娓道来,向我们叙述了大淖两边两丛住户人家。西边低矮的瓦屋里住着各处来的生意人,他们中有“卖紫萝卜的”、“卖风菱的”、“卖山里红的”、“卖熟藕的”,还有“卖眼睛的”、“卖天竺筷的”。东边挑夫们呢?他们“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他们一到吃饭时,就蹲在草房门口,“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大口大口地”吞食;他们“每逢年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旁观的闲人也不时大声喝彩,为他们助兴”。作家向我们揭示的是一个日常性、世俗化的生活世界。作家不仅描绘了城镇、村庄、街道、房屋等物质形态,他还特别擅长拓展空间的外延,通过风俗、人情的描绘,把我们深深吸引在作家所营造的世俗生活世界里,和人物一起去感受、体验他们的世俗人生。锡匠们的生活简单而单调,但作家却不厌其烦、津津乐道地把锡匠们传奇般的技艺尽情地描绘,使我们对锡匠们的生活世界有了更近一层的体味。在介绍挑夫们的生活时,作家还有意热衷于揭示他们不一样的风俗:“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这些“奇风”、“异俗”当然能吸引读者的兴趣,更重要是,让读者沉浸在一种独特的风俗民情的生存空间里,更好地品味人物、体悟人生。风俗是同一生存群体生活习俗的延续,风俗描写无疑使人物的生存世界充满了更为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了更为浓郁的世俗生活情调。
这种风俗化的世俗生活场景,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比比皆是。“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这是《岁寒三友》中陶虎臣放焰火时一段风俗化生活空间的描绘,处处洋溢着热闹欢乐的世俗生活情趣。
世俗生活世界的发现是汪曾祺对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在世俗生活中发现了庸常的“卑微人生”。汪曾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立足点是人物。《受戒》的灵魂,无疑是纯情、美好的明海和小英子,《大淖记事》则是巧云。巧云是“大淖”里成长的精灵。淖里富家子弟的光顾,她不放在心上,因为她有自己的人生向往。父亲的意外摔伤,使她的命运急转直下,但她从未想过离开父亲,她靠自己的双手织网、编席维持父女二人的生计。她喜欢心地善良、重情重义的小锡匠十一子,却不幸被刘号长破了身。命运对巧云的打击是惨重的,但巧云并没有像革命文学中受迫害者那般奋起反抗,在大淖这个的世俗生活世界里,这算不了什么,巧云残废在床的父亲当时就知道了,他“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也没有多议论,巧云按大淖的习俗坦然接受了这一命运,只是感觉对不起十一子,一切都在自为的世俗生活逻辑中展开。在十一子被打成重伤后,巧云没有说什么,她顶着生活的压力,把十一子接到自己家里,悉心照料。生活的种种磨难没有压垮巧云,她坚强地挺起了胸膛,她毅然拿起父亲的担子,像大淖里的媳妇们一样,优雅地走在挑夫的队伍中,她是大淖世俗世界中的巧云。《徙》叙述的是乱世寒士高北凕平凡、卑琐而高洁的一生。高北凕家境贫寒,求学时老师免其学费得以终业,后来做了小学教员。作为乱世中的读书人,他并非是一个有着崇高人生理想的读书人,他秉承老师谈甓渔教诲,洁身自好,教书育人。他自己生活艰难,但为了给老师出版遗稿,他省吃俭用,甚至牺牲女儿一生的前程。尽管没有轰轰烈烈的重大事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常琐事,但高北凕独立、自由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钦佩。《鉴赏家》写的是靠卖果子营生的小贩叶三。叶三生活于什么年代,文中无从考察,作家对此显然没有兴趣。小说着眼于叶三与画家季匋民的艺术交往。叶三是一个提着篮子走街串巷的小生意人,但他酷爱看季匋民画画,两人因画而成为知音。叶三在他50岁后,不顾儿子反对,坚持自己的生意,但他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季匋民,对他来说,与其说是送果子,不如说是接近艺术,鉴赏绘画。叶三不仅喜看季匋民画画,而且能发表自己独特的艺术见解,成为画家唯一的知音。他酷爱季匋民的画,把他赠给自己的画放在自己的棺材里,别人怎么高价也不卖,直至死后带入棺材。叶三是一个普通而艰辛的小市民,他对艺术的酷爱令人钦佩,很难想象他在困窘的生活之余对艺术的执着与非凡的热情。视卖馄饨为艺术展览的秦老吉(《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为人和气而又诚信经营的酱园老板连万顺(《茶干》);生活艰迫、半饥半饱但怡然自乐,种竹、养花、放风筝、斗蟋蟀、赏田黄石的靳彝甫(《岁寒三友》);面河垂钓、闲适恬淡、治病救人不计前嫌的民间医生王淡人(《故乡人·钓鱼的医生》)等等,他们都生活在自在、自为的民间世界里,在日常性、世俗化的庸常生活里,自然地生,静静地死。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不到阶级意识,领悟不到家国情怀,他们都是庸常世界里的凡夫俗子,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原则,有自己的生命追求,无一不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毋庸置疑,世俗生活和生存其中的世俗生活个体,是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陌生的题材,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里常常被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所改造、利用,创作主体从政治、社会、经济等视角对之进行理性的审视。世俗生活,是庸俗的生活,是有待改造的生活;世俗生活个体是落后的、卑微的个体,有待启蒙、有待觉醒的个体,它们是崇高形态的文学批判、改造的对象。与以倡导启蒙和社会变革为己任的精英知识分子作家和革命作家不同,汪曾祺在处理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时,把它们作为小说关注、欣赏的对象,把它们作为小说中合法的主体,这无疑是汪曾祺对这一表达对象独特的文学呈现方式。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里,作家力图放下高高在上的俯视视角,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个体投入了真诚的关注,世俗生活成为合理、合法、和谐的生活世界,卑微个体成为被认可、肯定甚至颂扬的对象,他们不再是被压抑、被奴役的个体,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他们被赋予自由、平等、率真、质朴的品性,他们坚韧地活着,在对和谐、美好的民间世俗生活信念的坚守中,抵抗着生活强加给他们的磨难,张扬着他们顽强的生命意志。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了和谐与美好,看到蕴含在这种生活里的诗意追求,更能看到人物身上闪烁的道德、习俗、善恶观念、爱恨情仇所升华出来的自由、独立的个体意识,个性精神。在谈到创作时,汪曾祺曾说,“我要运用普通朴实的语言把生活写得很美,很健康,富于诗意,这同时也就是我要想达到的效果”。作家想要怎样的效果呢?“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2]或许正是这些真实、美好与诗意,触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在时代走出“文革”的阴霾,人们沉浸在“伤痕”自悼中时,为我们想象了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将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引入了20世纪80年代文坛。
三
中国20世纪,是一个不懈追求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世纪,这一追求,汇成一股声势浩荡的历史洪流。自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就踏上了追求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漫漫长途。从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到“五四”时期的反帝爱国斗争;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抗战救亡到三年解放战争;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种运动,到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人民以不同的方式融入了这一追求民族独立、自主、解放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时代需要英雄,呼唤英雄,崇尚英雄。抛弃一切卑微思想、世俗利益,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奋斗,成为时代向国民提出的历史要求。作为20世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以服膺社会历史进程为使命,文学在追求宏大叙事过程中,形成了以崇高为精神特征的典型叙事样态,文学以启蒙和改造社会、人生,倡导超越式人生追求为旨归,自觉参与到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洪流中。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主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融入了这一历史洪流。
1980年代,是中国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段。在这一时期,极左时代结束,阶级斗争意识逐渐淡出人们的思想意识世界,中国进入“后革命时代”。“后革命时代”的现代化运动,一方面号召人民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而奋斗,无疑仍然需要崇高、壮美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旧有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淡出,表现为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新的变化,从文化思想和物质层面为人的世俗化生存——这样的世俗生存从启蒙、革命的话语系统看,是卑微的——提供了存在的可能。“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现代社会大多是世俗化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公只可能是凡人,而不是教徒或圣者,这个社会的英雄也只能因为奠定和维护了平庸的凡人生活而成其为英雄。”[3]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对世俗卑微人生的改造是一个漫长而坚定的历程,但这一历程在1980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其权威性面临着质疑和挑战,世俗化的卑微人生成为一种合理而合法的存在。正是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在“伤痕”、“反思”、“改革”创作主导文坛的创作背景下,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故里杂记》、《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等小说浮出历史的地表,它们以对世俗生活中卑微人生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中,有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重返一九八〇年代”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这无疑是研究1980年代文学的一个新视角,但“重返”者并未拆解既有文学史框架,只是从反思现代性的视角对既有叙述的相关问题做些清理工作。毋庸置疑“重返八十年代”,一方面需要批判与解构,对既有叙述的理性反思;另一方面,需要叙述的重建。目前,“重返”者在反思与解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⑦但批判与解构之后的重建工作,却进展缓慢。笔者以为,“重返”汪曾祺1980年代的小说,是一个有效的建构视角。在1980年代之初,汪曾祺把世俗生活引入小说创作视域,把目光转向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在崇高形态小说创作关注重大事件、壮美人生的时刻,这无疑是对崇高形态叙事习规的冲决,是一次具有变革意义的小说创作转向。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更有着众多的追随者,甚至被评论界奉为“新笔记小说”的开创者,引发了一波不大不小的“新笔记小说”创作热潮,甚至间接触发了“寻根”热潮。所谓“新笔记小说”,其创作实质正是一种世俗生活叙事,无论是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一夕三逝》、《雪霁》,还是阿城的《遍地风流》、李庆西的《人间笔记》,无论是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太白山记》,还是林斤澜关注改革的《矮凳桥风情》,无一不是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关注,对卑微人生的叙写。邓友梅等某些“寻根小说”家所关注的也多为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那五》叙写的就是被扒开了外衣的贵胄子弟的吃喝拉撒,写尽了他的软弱、卑怯、清高和虚伪。《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一些现代派小说,刘心武、陈建功等人的京味小说关注的也都是凡夫俗子的世俗生活。19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则以“原生态还原”的姿态,再次把文学的目光转到经验世界的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中。由此,从汪曾祺到新写实作家,日常、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构成了1980年代小说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资源,构成了1980年代小说创作的另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一脉络终在1990年代成为最为重要的创作模式。在1980年代这一小说创作脉络的源头,矗立着汪曾祺,这或许正是汪曾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对文坛更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注释:
①“八十年代”是一个并不科学的“文学史指认”,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诸多同类概念一样,并不是严格的和纯粹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它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也有特定历史内涵。根据文学史对这一时期的叙述惯例,一般把它限定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期。
②庞守英的《汪曾祺与笔记小说》从思想内蕴、叙事方式和文本结构等方面探讨了汪曾祺小说与古代笔记小说的联系与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第64-69页);冯晖的《汪曾祺:新笔记小说的首发先声者》不仅论述了汪曾祺在笔记小说发展中的地位,而且从情节、结构等方面论述了其小说的笔记小说特征(《云梦学刊》2001年第22卷第3期,第69-71页);孙郁的《汪曾祺的魅力》一文则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与古代笔记小说在精神气质和艺术特征上的相似性(《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6期,第65-69页)。
③夏逸陶《忧郁空灵与明朗洒脱——沈从文汪曾祺小说文体比较》从文体角度探讨了沈从文创作对他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第75-80页);董建雄的《现代抒情小说的开拓与发展——废名、汪曾祺小说比较论》从关注对象、小说结构和语言方面论述了其与废名小说的联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年第22卷第5期,第40-44页);柯玲的《汪曾祺与京派文学》(《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33-37)等也都有相似的论述。
④张洪德的《汪曾祺小说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90-93页)、许宗华的《浅论汪曾祺小说的非情节化》(《淮北煤炭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105-108页)等论文从人物描写和情节结构方面探讨其作品的散文化特征,讨论其小说笔记体特征和抒情特色的文章也几乎都涉及散文化的特点。
⑤季红真在《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一文的开篇就谈到“寻根”最早的潮汛要追溯到汪曾祺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第69-74页);钱理群、吴晓东在《汪曾祺:寻找文学的根》中也认为汪曾祺的创作潜藏着文学“寻根”运动的深刻心理动因(《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第125页)。
⑥关于对1980年代文学的论述,本文所论及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主要为: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金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⑦参见程光炜、李杨、张业松、赵牧等人的研究。(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的若干问题》,载《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李杨的《重返“1980年代文学”的意义》,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1页;赵牧的《“重返八十年代”与“重建政治维度”》,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第13-17页;张业松的《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第12-20页。)
[1]汪曾祺.关于《受戒》[M]//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40.
[2]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M]//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5.
[3]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