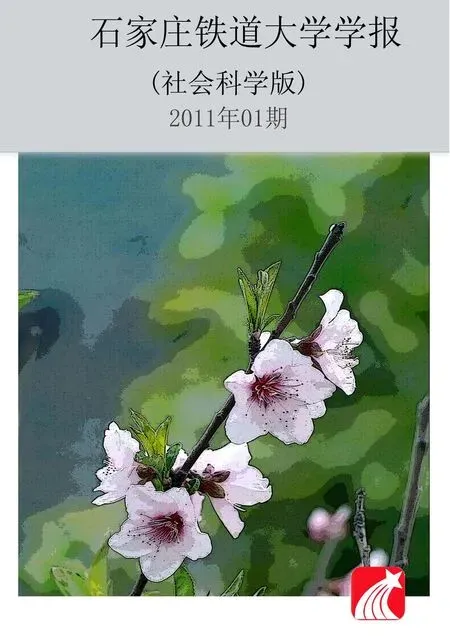论宗白华美学人格理想的形成
马 慧 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论宗白华美学人格理想的形成
马 慧 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人格理想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核心,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这其中有一以贯之的地方,也有逐渐发生变化的方面。宗白华美学人格理想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格理想的草图(“超世”与“入世”)、人格理想的具体体现(歌德之人格)和人格理想的成熟(“晋人之美”)。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贯穿了宗白华的整个人生。
宗白华;人格理想;形成
中国美学的最高价值不是自然美或艺术美,而是人格美。二十世纪初,民族生存、社会生存和士人个体生存三种具有生存意义上的矛盾突然激化并纠缠在一起,磨砺着当时的知识人。现代中国美学在此背景下确立了建构生命形象和设计理想人格的取向,并得到了“群体人格”、“个体人格”和“审美人格”三种方案。作为“审美人格”方案的代表,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与生命意识,他以审美的方式来回答乃至解决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危机,试图为人的灵魂寻求一条“安顿之路”。
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是中国哲学浸润下的产物,也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背景。宗白华对人格理想的论述与其形上思想密不可分。唯理崇真的思想、生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背景使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神采飞扬。这种人格理想是“空灵”与“充实”在美的关照下达到和谐、富有节奏的理想人格。“空灵”的美学内蕴是自由玄远的心灵以“静照”的态度去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以审美的精神来看待自然、艺术、人生和整个宇宙,从而创造出具有超然绝俗的玄学的美。 “充实”的美学内蕴是“真”之美和“动”之美。 “空灵”与“充实”的二元冲突在美的介入达到和谐,展现出具有张力的节奏之美。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是逐渐形成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人格理想的蓝图——“超世”与“入世”(1917—1920年)
这个时期人生观问题是宗白华关注的中心,他发表了《说人生观》、《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青年烦闷的解救法》、《怎样使我们生活丰富》和《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等一系列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并开始对人格理想进行学理建构。
在学术生涯的开端,宗白华就开始了对人格理想的建构,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萧彭浩哲学大意》立专节介绍和讨论了叔本华的人生观及伦理观。一九一九年宗白华发表了《说人生观》,较为全面的探讨了人生观的问题,总结出三种不同形态的人生观:乐观、超然观和悲观,分别举出了这三种人生观体现出来的不同派别,并对各个派别的特点、表现形式以及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说明。接着他又发表了《理想中少年中国之妇女》,在审美意义上提出建构理想人格的观点。不久之后发表的《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中,宗白华提出要发展一种健全的“新人格”。一九二零年《怎样使我们生活丰富?》一文中提出理想的最高的人格。同年发表的《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一文中,宗白华认为 “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似的人生。这是我个人所理想的艺术的人生观。”[1]这个时期宗白华对人格理想的思考集中表述在《说人生观》和《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中,在这两篇文章里宗白华提出“超世入世人生观”和“小己人格观”。
概而言之,该时期宗白华对理想人格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生观问题的思考中,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在其唯理崇真思想影响下,侧重以实际的现实为基础,从学理上深入探讨社会文化和青年人生改造的问题。其次,这个时期宗白华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已经带有了审美的性质。在《青年烦闷的解救法》中,宗白华敏锐地关注到革故呈新的现代运动中、新旧交替的文化转换之际青年人中普遍流行的“烦闷”现象,及时提出了“唯美的眼光”、“研究的态度”和“积极的工作”三条解救办法,尤其强调“唯美的眼光”。这里所谓“唯美的眼光”,即“审美的眼光” 也可称“艺术的眼光”,就是把生活“当作艺术品看待”,无论它是美善还是丑恶。他把这一宗旨表述为“纯粹的唯美主义”,即在丑恶黑暗中看出美,在无秩序中看出秩序,从而减轻厌恶愤恨,排遣无聊烦闷。《新人生观之我见》中,宗白华进一步把“唯美的眼光”与创造行为结合起来,表述了“艺术的人生态度”。艺术是将物质对象理想化和美化的创造过程,生命也是不断走向合理化和系统化的过程,故“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美化”,就是艺术的人生态度。再次,宗白华对“人格”的个体意义很重视,在 《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对于小己人格的创造”一节中, “小己”一词被频繁使用。另外,宗白华注重人格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他使用了“新人格”、“健全人格”、“更高人格”、“超人”等词汇,认为人格就是人类小己一切天赋本能的总汇体,而天赋本能是应当发展、进化的。因此,他将歌德的名言“人类最高的幸福就是人类的人格”改为“人类最高的幸福在于时时创造更高的新人格。”还有就是宗白华所建构的理想人格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充满了张力。他提出“超世入世”的人生观,提倡“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所谓“叔本华的眼睛”,是静观的、审美的精神。而 “歌德的精神”,就是积极创造、不断奋斗的精神。超世与入世、超越静观与自由奋斗、自强不息与乐天知命、 “无为”与“无不为”已经构成了现代生命形象、人格理想的二元,一种紧张的冲突蕴涵在其中。这些特点在宗白华以后的人格建构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人格理想的具体呈现——歌德之人格(1920—1933年)
宗白华在“少年中国”时期建构的理想人格还仅仅是一幅蓝图,而歌德的人生启示则使宗白华美学人格理想由纯理论意义上的建构转变为具体的呈现。
对歌德的研究是宗白华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成就,也是他全部美学研究的一个闪亮点。台湾学者、诗人杨牧为洪范版宗白华文选《美学的散步》所作序文,标题即为《宗白华的美学与歌德》。文章认为,要认识宗白华,体会他的诗,了解他的美学,必须体会他的感受,了解他心目中的欧洲传统,尤其是歌德在那个传统中所代表的特殊地位。杨牧还称宗白华为“现代中国之歌德权威”,并说宗白华“强烈的歌德认同,不但在中国绝无仅有,比冯至和梁宗岱更彻底,即使在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以外的欧洲人当中也不易多见。”[2]
事实上,宗白华对歌德的仰慕由来已久。一九一八年,宗白华在 “少年中国学会”学术座谈会上第一次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歌德与〈浮士德〉》。早在一九二零年一月,宗白华在与郭沫若的通信中就流露出对歌德进行研究的想法,其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又表示自己要从哲学的研究转向文学,认为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而他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量加入这首诗的一部分”。这里的“宇宙诗”也就是泛神论的诗化哲学,而启示着宗白华进入这诗化哲学的就是歌德的泛神论精神。由此可见,宗白华美学生涯的开始是与对歌德的喜爱同步的。
宗白华对歌德研究的热情一方面缘自他对歌德的喜爱,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人格理想建构的思考。他最初研究歌德的课题为《德国诗人歌德Goethe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在他看来,歌德的人生和艺术提出了近代人的根本问题,并暗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宗白华认为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人类已经失去了希腊文化中那种人与宇宙的和谐关系,也失去了基督教那种对于一个超越人世的“上帝”的虔诚信仰。人类的理性和精神虽然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依傍。人们彷徨摸索,在苦闷中追求、寻找,试图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之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歌德的思想及其文艺创作,正是这种近代文化、近代人生全部问题的反映。歌德及浮士德的一生就是这种近代人生的体验并指出了解救之道。宗白华认为歌德以自己的作品和人格给德国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带来深不可测、不可计算的影响,歌德代表的“是一个整个的文化”——“荷马的长歌启示了希腊艺术文明幻美的人生与理想。但丁的神曲启示了中古基督教文化心灵的生活与信仰。莎士比亚的剧本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人们的生活矛盾与权力意志。至于近代的,建筑于这三种文明精神之上而同时开展一个新时代,所谓近代人生,则由伟大的歌德,以他的人格,生活,作品表现出它的特殊意义与内在的问题。”[3]
在对歌德及其浮士德精神的阐释中,宗白华提出歌德精神中“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4],他一再强调歌德合二而一的精神象征在上升和奋斗之中,是如何处理向外无限扩张与向内追求和谐这对矛盾的。宗白华说:“探索歌德人格与生活的意义时,第一个印象就是歌德生活全体的无穷丰富,第二个印象是他一生生活中一种奇异的谐和,第三个印象是许多不可思议的矛盾。不过,这两种相反的印象却是互相依赖的。他认为歌德的人生问题,就是如何从生活的无尽流动中获得和谐的形式,但又不要让僵固的形式阻碍生命前进的发展。”扩张与收缩、流动与形式、变化与定律、生命与秩序在“一个圆满的具体的美丽的瞬间”达到和谐。可以看出,表现于“超世入世”人生观中的矛盾具体化、深入化了,这些矛盾在歌德和浮士德那里也只有在美的瞬间才能得到平衡,这种人格的紧张在晋人那里进一步强化。
三、人格理想的成熟——“晋人之美”(1933—1942年)
隋唐以降,对魏晋风度和魏晋文艺的评价便成为热门话题,其中毁誉参半,见仁见智,不一而足。近代以来,魏晋研究成为了一门显学。鲁迅、汤用彤、贺昌群、陈寅恪、郭麟阁、容肇祖、王瑶、刘师培、朱光潜等不少学者都青睐魏晋时期,热衷于研究魏晋时期的历史、思想和文化精神。谈古喻今,这些研究魏晋的文章实际上显现了研究者的现实情怀和问题意识——这些学者大多对于魏晋六朝的人格问题倾注了较多的热情:汤用彤认为魏晋时代“一般思想”的中心问题即是“理想的圣人之人格究竟应该怎样?”他认为“魏晋乃罕有之乱世,哲人们一方面立言玄远,希冀在形而上的思辩王国中逃避现世苦难,以精神之自由弥补行动之不自由甚且难全其身的困苦。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逃避铁与血的现实关系之网,因而对何为自足或至足之人格不能不有深切的思考。”[5]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研究者自身的剖析。刘大杰的《魏晋思想论》以进化观的观点,将魏晋人的人生观特征名为人性的觉醒,探讨了人性觉醒的原因,分析了魏晋人的几种不同的人生观和它们的特质。认为魏晋人醉心于人格之美,最重抒情。冯友兰的《论风流》则将晋人的风流归于其玄心、洞见(对真理的直觉体悟)、深情和对美的深切感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社会历史的背景考察魏晋人格与文学风格的形成。而宗白华从美学家的角度直接阐释和称颂魏晋的审美人格,并以此发展了他对于理想人格的建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是我国第一篇从美学角度研究《世说新语》的力作,也是我国学者研究魏晋风度的最好文章之一。
宗白华后期对于人格理想的主要论述集中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和《清谈与析理》中。在这两篇文章里宗白华的美学精神与晋人的美学风韵融为一体,展现了一种极度紧张的人格,这种人格充满了内在的张力、表现出生生的节奏。宗白华写《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前后,正是一个缺少自由、沉闷苦痛的年代,他对于晋人自由精神的讴歌,对于晋人审美风韵的向往,是其内心苦闷的反映。宗白华从有着血性韵致的晋人身上看到了解脱他个人生存矛盾的因素,也看到在混乱、黑暗的年代培养壮阔人格的希望。他对于晋人美学精神的发挥弘扬,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毫不掩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乡愿习气的厌恶,对各种各样专制独裁的痛恨,以及对当时中国普遍缺乏勇者精神的喟叹。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和《清谈与析理》这两篇文章中,宗白华展现了一种极度紧张的理想人格——简约玄澹与热情放诞、空灵与充实融于一体。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的开篇,用五个“最”、两个“极”展现了一个异常紧张和矛盾的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强烈、矛盾、热情、浓郁生命彩色的时代,富有真情、血性和韵致的晋人展现出极度紧张的人格,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宗白华说,晋人的美,是那全时代的最高峰,他们的理想人格是一往情深的“天际真人”——深于情但又“事外有远致”,美到了极处后反而“雄强之极”,这种紧张到即将破裂的人格的二元在晋人对美的体验中达到和谐。
四、人格理想的隐性建构
宗白华对人格理想的思考也隐含在那些论画、论艺术的文章中。他在一九三五年发表的《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一文在文字上酣畅淋漓,是宗白华行文中少有的“快文”。宗白华在该文中所赞赏的诗歌无一例外都与战争有关,他不仅把“出塞曲”看作是唐诗的杰出代表,而且认为这些诗是民族诗歌的结晶。宗白华为何如此看重“出塞曲”联系那个时代答案就不言而喻了。宗白华在这篇文章赞颂慷慨激烈的诗歌,弘扬民族坚定的自信力,隐含着对尚力健动生命力的赞叹,是对理想人格的隐性建构。
完成了对“晋人之美”的建构之后,宗白华再也没有专门撰文论及他的“人格理想”,而是开始钟情于对意境理论的创构。对意境的探究是宗白华美学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宗白华那里,艺术意境与理想人格是一种彼此映射和互相涵养关系。人格精神涵养着审美意境。宗白华认为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是“澄怀观道”。这种境界既要有屈原的缠绵徘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徘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宗白华明确指出:艺术意境的诞生,归根结底在于人的性灵中;艺术意境的创造,依赖于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在活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同时,艺术意境也涵养着人格精神。“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宇宙的深境。”[4]意境与人格在本质上是同一生命境界的两种维度,艺术意境归根到底是一种理想人格形象的隐喻。它不仅仅指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因此,意境特点之一的“舞”也是人格的理想境界;宗白华对体现意境的艺术的探讨也与他对人格理想的建构密不可分;甚至他探讨意境的起因也和他对人格理想的思考分不开。[6]
宗白华对人格理想的思考也体现在他的人生实践中。他一生对艺术的热爱与探寻,其“散步美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意蕴,以及它所标示的艺术化、审美化人生的生存方式正是对人格理想的具体表达。宗白华的一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其理想人格的践行。
总而言之,宗白华的学术是对其人格理想的隐性建构,他的人生是对“晋人之美”的坚守与印证;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贯彻了他的全部美学研究和整个人生。可以说,宗白华的人格理想既附着于他的美学与人生,又提纲挈领的关照着他的美学与人生。
注 释:
①本文对宗白华人格理想形成阶段的时间分期只是一个大概的分段,事实上宗白华对人格理想的思考是连续的,并无确切的时间分段。另外这个分期参考了胡继华的《宗白华文化幽怀与审美象征》。
[1]宗白华.宗白华全集(一)[M].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22-223.
[2]杨牧.美学的散步·代序[M].台北:台北洪范出版社,1981:6.
[3]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6.
[4]宗白华.宗白华全集(二)[M].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2,376
[5]汤一介.魏晋玄学论稿·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
[6]王德胜.意境的创构与人格生命的自觉——宗白华美学思想核心简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51.
Development of Mr. Zong Baihua’s Esthetic Personality Ideal
MA Hui-n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jing 100875, China)
The Personality Ideal is the core of Mr. Zong’s esthetic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r. Zong’s personality ideal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stage of draft,the stage of performance and the stage of matur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sonality ideal almost occupied Mr. Zong’s whole life.
Zong Baihua;personality Iideal; development
2095-0365(2011)01-0082-05
2010-11-26
马慧娜(1980-),女,博研,研究方向:中西比较诗学。
G4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