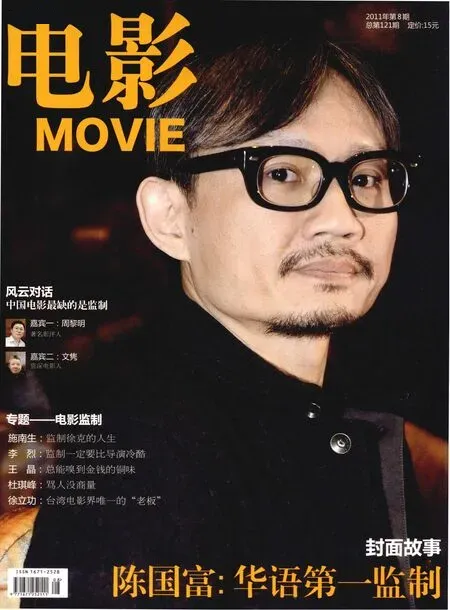李烈:监制一定要比导演冷酷
文/马翠轩
李烈,台湾身份最多元的电影人之一,被誉为当今台湾电影界“监制一姐”上世纪70到80年代家喻户晓的演艺红星,曾主演多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及电影作品,后来跨足电视制片、演员经纪人行业。2008年首次担任电影监制,力捧新生代导演杨雅,让《囧男孩》重现台湾电影许久未见的儿童友情电影类型热,在观众口碑与电影票房皆获双赢。第二部担纲监制的黑帮动作类型片《艋舺》,创新台湾商业电影行销模式,从电影前期便加入整体宣传概念,带动一波波话题风潮,更创下首部国片首周破亿的奇迹票房纪录。连续两部电影的亮眼表现,证明“演而优则制”的李烈,拥有对于台湾电影市场的精准眼光及行销操盘功力,也成为台湾电影的品牌保证。
2010年,在媒体的年度权力榜盘点中,有个清丽台湾女人意外地一跃进榜,香港著名监制文隽点评她是实至名归。没有背景,没有财团资助,仅靠个人眼光、能力和才华,使台湾电影重燃希望的大旗手。在所有的颁奖礼上,她总是淡定自若,笑容灿烂,素面朝天不减俏丽,绝对的无龄美女,当你的目光落在她的名片上,当你看到李烈两字,你突然如受电击,是的,你会想起《一剪梅》、《含羞草》这些年代久远的台湾剧,然后你又想起上世纪90年代末陪伴在罗大佑身边的她,从玉女到知己,再到干练的台湾电影监制一姐,李烈这大半生过得可算异彩纷呈。
最红的八点档女星,转去当音乐教父的女朋友
父亲给她取名“李烈”,与大多台湾女生的名字相比,太过硬邦邦。或许真是名字暗示了性格,李烈从来就没有台湾女子的温婉低回,她著名的是急噪、暴脾气。
但就是这样的李烈,放在屏幕上,却是《一剪梅》、《天长地久》中楚楚可怜的女主角。上个世纪80年代是李烈最红的时代。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八点档都可以看到她主演的不同的连续剧。当所有人以为她享受于其中时,李烈却已经在计划逃离。“我觉得自己是工厂的流水作业。觉得日子如果这样过下去,整个人就会被榨干。”
她首先选择的逃离方式竟然是结婚。对象是《蒂蒂日记》中的搭档毛学维。那一年李烈23岁。“其实结婚前一天已经后悔,发现自己根本不爱这个人。可是那时候已经不能不结了。”就是这样一场“儿戏”,两年后宣告结束。
然后她下海经商,到大连做成衣生意。事实上,无论是来内地,还是做生意,都离她之前的生活太过遥远。但她说:“就因为没做过,才觉得好玩”,结果一头扎进去,5年赔掉了1000万新台币。
回到台湾,李烈沉寂了很久。事业没有了,好在,当时的她已经有了恋人罗大佑。
音乐教父,广大女文青的爱慕对象,但对李烈而言,“他的歌我没大听过,也从来没有崇拜过他,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这个人的特质,而不是你是什么人,才华只是你的一部分而已。”其实是,李烈22岁和罗大佑认识时,罗大佑只是一名实习医生,还在和张艾嘉谈那一场著名的恋爱,谁也不知道他后来会出名,“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在朋友开的小店里打牌,林凤娇、叶闳文、张艾嘉、秦汉、叶倩文……喔,偶尔还有林青霞,整家店里都是明星,吓得没有客人敢来,你想想,有张艾嘉帮你递茶水,那有多吓人”。
等她离完婚出来,他俩开始约会。后来她做生意,分隔两地,打电话倒是有许多甜美的回忆。再后来,她跟着他到了香港,又跟着他转去纽约,那些年,她的身份是“女朋友”。

做艺术家的女朋友有时就是做艺术家的保姆,要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更要照顾他的精神生活。艺术家脾气大,又任性,比如迷养鱼的时候,可以在家里放九个巨型水族箱,每个水族箱的清洁都是李烈在做,一旦不喜欢了,鱼和水草就丢给女友来善后。更要命的是罗大佑时刻都在创作,睡觉要放最大声的《歌剧魅影》,如果关掉,他会生气地说:“如果我一个人的话,就没人管我了。”后来,李烈被训练到音乐再大声都可以入睡。
一直没有结婚,据说是两人共同的意思。等到罗大佑想结婚时,李烈已经心灰意懒,一身黑衣走去注册,那是李烈给自己的一个小小仪式,悲哀的仪式,用来表达对自己这段婚姻的不祝福。果然,这段相恋12年修成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零9个月。
女人五十的胆与识,破产也要拍电影
李烈是绝对的文艺女青年,她从两段婚姻里走出来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而她和普通女人的区别就在于她敢于在42岁时断然告别,甚至在台北租房子的钱还是硬着头皮跟朋友借的。她明白自己在幕前已没有空间,于是转做幕后,做经纪人,监制,“当你一次又一次地跌倒,你的身段一定会更加柔软”。

2008年,李烈监制的《囧男孩》卖出了3000万新台币的票房,10年没买台湾电影的日本NHK,火速买下《囧男孩》日本版权。很多年后若回顾台湾电影史,2008年会是其中一个特殊的年份,李烈和她的《囧男孩》,以及另一部电影《海角七号》,创造了一个之前从未被人想象的可能性:在这之前,台湾本地几乎是没有电影工业。
李烈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有3000万,“根本就不可能想得到”。但在“不可能想到”里,有李烈多年训练出的对艺术的敏感,有她贷款举债拍电影的豁出去的气魄,还有她去世的好友舞蹈家罗曼菲的影响。
2006年罗曼菲因癌症去世,让李烈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她是那样健康的一个人,吃有机食品,从来不抽烟,也不熬夜”,看着好友曾经“那么强健的双腿,一日一日萎缩下来”,她一瞬间明白了生命的残酷与无常。
李烈开始怕自己的人生来不及,“我很怕自己活得长寿,而不精彩”。这样,在看到《囧男孩》剧本之后,李烈喜欢得两眼一闭,就跳了下去,哪怕知道一旦投入之后,很可能因此而破产,哪怕心里害怕,“这或许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战斗了。到这个年纪,破产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事实证明,她成功了。

作为一个监制,我一定要比导演冷酷
“做为一个监制,我一定要比导演冷酷”,在《艋舺》的拍摄片场,李烈有着自己的坚持,为了顺利完成电影,她与钮承泽“吵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李烈也为《艋舺》制定了一系列的营销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出一部真正的台湾商业电影!
李烈心中对商业片的定位,“不是指向削弱故事的精神内核,或者墨守成规,我商业片的范畴很广,好卖的片子都是商业片,《悲情城市》的票房也是非常好,就是我心中的优质商业片。我的标准就是电影只有好看跟不好看,我拍电影为了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别人眼中的高不高级。我觉得正是这种狭隘曾经打散了独树一帜的台湾电影,《囧男孩》是我想要试试台湾电影究竟能不能活,而到了《艋舺》那就要试试破掉这个狭隘。”


我的标准就 电影 有好看 好看 我拍电影 自 的判断中的高 高 我觉 这种狭隘曾 打散 独树 帜台湾电影 男孩 是我想要试试台湾电影究竟能不能活 而到 艋舺》那就要试试破掉这个狭隘。”
李烈与钮承泽在08年金钟奖典礼上的偶遇,促成了《艋舺》这个已经酝酿近四年的计划重新启动,“我们最开始就是在一起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有个直觉吧,感觉做《艋舺》的时机到了。当时台湾电影开始正在往上爬,观众开始重新去看台湾电影了,《艋舺》是很适合做成商业电影的题材,我就跟豆导说,台湾电影需要一部真正的商业电影。他就把剧本重新拿出来,继续讨论,决定做了。”
此时的李烈,正在享受着自己第一部监制的电影《囧男孩》带来的喜悦,这部电影台湾本土票房卖到了3600万新台币。当搜狐娱乐问起李烈监制《囧男孩》的这段经历时,她说“《囧男孩》如果收不回投资,我就得去出外打工了。” 李烈话里所说的打工,就是指去演戏,而拍戏对李烈来说,早已不愿再去重复,“演来演去都是同样的角色”,所以再次进入演艺圈的李烈把自己锁定在监制的角色。
《囧男孩》的经历让李烈对电影监制有了很大的了解,“其实《囧男孩》的成功对我做《艋舺》的判断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囧男孩》原本计划用1200万拍完,后来也出现超支了,因为我是一个很要求品质的监制,电影要求品质,就要花钱。《囧男孩》时我自己下了一些判断,就是要让戏更好更精致,一定会超出预算的,后来也证明我的判断是对,这个经验让我在做《艋舺》的时候,什么东西要花钱,我就给他花下去。”
李烈很烈,人如起名,要不不做,要做就得惊世骇俗。戏还没开拍,她就给《艋舺》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目标——《艋舺》要上2010年春节档。
你可能很难相信,在《艋舺》之前,已经有二十余年没有台湾本土制作的电影挤进过院线的春节贺岁档。这样的背景下,《艋舺》能够在开拍前一年就先确定好2010年春节上映的档期,其意义不啻于一场革命。
2009年2月,李烈带着《艋舺》的导演钮承泽拜访三大发行片商之一、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台湾分公司总经理石伟明,主动提及该片规划。石伟明说:“如果你们能把片子做得让观众有‘哇!’的感觉,就让你们上春节档。”

《艋舺》剧照
为了这一个“哇!”字,钮承泽、李烈几乎完全修改了《艋舺》的拍摄策略,无论资金、演员还是销售的规格计划,全部变成“大片”的模式。李烈说:“我们算一算,三千万做不出‘哇’的感觉,至少要五千万……我们一路上就拼这个东西。”最后他们找到了六千万台币投资。这意味着与戏院分成之后,如果还想回本,《艋舺》至少要冲出一亿五千万台币的基本票房门坎。
所以从一开始李烈就知道《艋舺》必须大卖,或者说,整部电影所有环节的选择都建立在一个毫不含糊的假设之上:如果这样做,观众会乐意买账。
从电影确定档期到电影开拍,李烈坦承自己压力很大,“拍这个电影时,监制和导演的压力是最大的,我就是帮助豆导把电影拍好,我们两个都要求戏好,要品质好,但我们还要有预算的考量。很怕交不出片,每天压力很大,跟时间赛跑,电影是个很精致的绣花的功夫,快了东西就粗糙。他希望把戏弄到最好,但为了赶档期,我每天都会催他,所以这也是我跟导演争执的一个重要因素,吵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在片场的辛苦,令李烈颇为难忘。吃饭、租借的机器、底片费,所有的东西都要钱,作为监制都要操心,“我会尽量达到导演的要求,但是那些要求是要在控制内的。”李烈也有一个底线,“对我来讲,没有别的要求,因为档期已经排好,必须春节档交出片子来,其他的我都可以支持你,但没有人可以打破这个时间。”正是这些辛苦和坚持,在影片的杀青宴上,情绪激动的李烈泪洒当场。
在电影结束拍摄后,进入剪辑阶段,李烈与钮承泽又进入了下一轮的争执,“我们第一次剪出来的片子,其实很长,因为那是导演的作品,他会觉得每一个画面都很珍贵,他都想要,而对于监制来说,片子这么长,戏院一定不会要的。我就必须考虑商业考量的东西,跟导演有很多的争执,有很多的争吵,哪些戏需要留下来,哪些需要剪掉,肯定有很多摩擦。”
我们算一算,三千万做不出‘哇’的感觉,至少要五千万……我们一路上就拼这个东西。”
现在的李烈还是很穷,还是租住在那间空荡荡的没有什么新家具,惟一的法国蓝沙发是水渍打折品的房子里,没有信用卡,写剧本,找投资,剪接,笑着和人说她如何为拍电影焦头烂额,“哪怕我还是一无所有,但我都已经感受到了自己人生的完整,因为知道每天在努力些什么,知道正在一点点地扎实地去了解自己……我简直,简直就要爱死现在的自己!”李烈很烈,花了五十年的时间,终于从一个名男人附属品变成了她自己,这个过程,有点长,但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