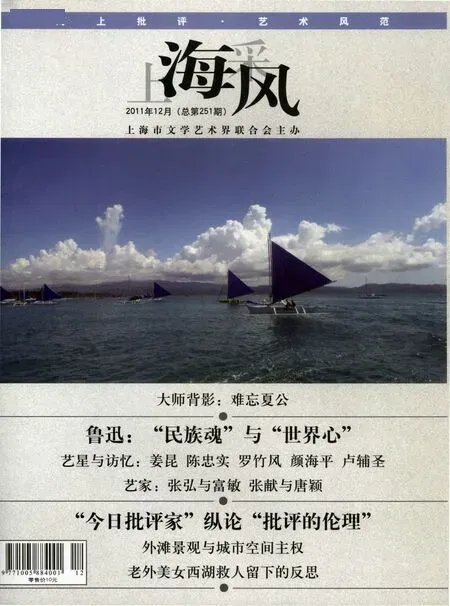颜海平:从《秦王李世民》开始的“旧邦新命”写作
文/本刊记者 杨 子


颜海平
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留校任教;1983年底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欧洲现代戏剧、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专业,1990年获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艺术与人文终身教授,兼华东师大紫江教授。2011年上海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任上海交通大学讲习教授。1999年美国广播电视公司(CNN)以其在英语和汉语世界的学术贡献和创造性著述将她评为“新世纪最具有跨国影响力的六位中国文化人物之一”。入选《二十世纪杰出学者录》(英国;2000年)、《美国杰出女性录》(美国;2004年);历任全美戏剧文化与妇女问题研究协会主席、全美戏剧文化研究协会常务理事、年度最佳学术著作奖评审委员会委员、高等教育戏剧学科及研究和出版委员会委员。早年发表十幕历史话剧《秦王李世民》,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主要英文书著包括《戏剧与社会:当代中国戏剧选》《别样的跨国:散居的亚洲及其表演艺术审美》《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想象:1905—1948》等。中译本《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2011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3年10月,颜海平到朱东润先生寓所探望恩师。朱先生在师友琅琊行馆题下书法条幅一幅,作为送给学生出国前的礼物。告别时,朱先生从楼上送到楼下,直到门外的草坪。
颜海平至今记得,她走出一段,回过头去,看见朱先生依旧站在原地。看见他回头,便扬起手挥一挥。“也许是太年轻,那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已经88岁高龄。他题写的是苏东坡的一首诗,‘两本新图宝墨香,尊前独唱小秦王。为君翻做归来引,不学阳关空断肠’。浩瀚无边的中国古诗里他挑了这一首,而且这么贴题,是嘱咐我,要记住祖国。”
1982年夏天,复旦大学77级中文系毕业后,颜海平凭着优异的学业成绩留校任教。接着,人生发展中的三个抉择降临面前:“师从朱东润先生学习传记文学的研究;师从南京大学的陈白尘先生继续戏剧创作;第三是出国留学。”颜海平最终选择了出国留学。
少年心事当擎云
某种程度上,由于时间上的历史性转折及人们从十年内乱桎梏压抑中解放思想的诉求,复旦大学77级中文系成就中国文坛诸多“第一”,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别符号。最先是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被张贴在中文系四号楼走廊7711班级墙报上,在校园里引起广泛讨论,其后,小说被《文汇报》的一位编辑注意到,发表在《副刊》上,《伤痕》很快走出复旦园,引起全国性的争论。1978年秋天,在复旦校园举办的讨论会上,与会师生辩争激烈。在复旦中文系教师吴中杰发表了批评意见之后,本科一年级学生颜海平站出来,表达了不同看法,支持卢新华的小说。会后,吴中杰来到学生宿舍时,对这位带着稚气的圆脸女生表示赞许,“虽然你的意见和我相左,但女孩子勇敢说话,好!”
颜海平更为公开的一次“勇敢说话”是在两年半后。1981年1月,她于1979年3月开始构思、1980年夏天完稿的十幕历史话剧在《钟山》杂志发表,“震惊了整个中国剧坛”。李世民的兴兵反隋、建唐立国等系列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在颜海平笔下以一种“精致典雅的语言”及“创新的舞台技巧”呈现出来,这部探索“君位与民意的关系”的历史剧,以其深刻的主题、早慧的作者、及其对历史题材的深度把握引发了文化评论界的热议。1981年春天,上海青年话剧团导演胡伟民将此剧搬上舞台。其后,该剧获得1981—1982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文化部所授予的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
直至今日,颜海平仍然认为历史剧写作和写历史剧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丰富多重相互作用的关系。她强调,当时是想通过“对历史的一次重访,针对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的可能。”这部受人瞩目的剧作,似乎预示着作者日后在中美学界作为一名探寻中国文化现代之路的史学者的开端。
少年心事当擎云。1981年8月,颜海平在《秦王李世民》单行本序言中以“精卫鸟”自喻,为自己看似颇为“平淡”的名字寻找意义。她引用唐诗人王建《精卫词》中的一句“高山未尽海未平,愿我身死子还生”,表达自己要像“弱小而倔强的精卫鸟,孜孜不倦、一木一石地奠造理想大厦的根基”。30年后,当被问及对自己这段文字的看法,颜海平停顿片刻,笑了起来,“有一句希腊名言说,人的起步和结束是有内在关系的。黑格尔又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有经历的人,引用同一句格言时,内涵是完全不同的。人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所以也无法评价自己当时或者说过去的文字。”
1983年,颜海平考取公费留美,同时获得包括康奈尔大学在内的三所大学的奖学金。带着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和中文系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的支持和鼓励,颜海平开始了“万里之行”。在两位先生看来,跨出国门,“看到世界的状态,才能感受到、认识到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必须怎么做,我们应当怎么做。”朱先生亲笔题写的书法条幅跟随颜海平越过重洋,现今被安放在她上海居所的书房里。

从不可见到可见
“我很欣赏这个设计。”颜海平用手指在靛青色的封面上划了一条弧线,最后停顿在与红五角星交叠的红色玉兰花图案上。在康奈尔大学一年学术假期中,已过去的十个月,她是在国内繁忙的学术活动和教学研究工作中度过的。对她来说,这十个月能够连续不断地、长时间近距离感触中国和每日发生的变化,“是个很深的磨练和体会”。最近,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上海首批“千人计划”,意味着她将被正式引进回国。在此之前的十余年间,她频繁往来中美两地,与华东师大、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皆有不同方式的合作与交流。
今年6月,她著述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该书英文精装版于2006年3月由纽约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付梓出版。在这部被学界同行称为“目前读到的最为经典的一部关于女性解放和女性写作的史诗性文献”的著作中,颜海平深入探讨了秋瑾、冰心、王莹、白薇、萧红、丁玲等女作家的写作与生活,将她们的写作史和社会史相结合,通过讲述 “弱国、弱势、弱女子”再造人生的故事,指向一种生命形态氤氲发生的进程史;以对“强”与“弱”的辩证法深厚有力的把握,重访现代女性的革命性写作,重访“现代中国”。
颜海平对1905年到1948年期间中国具有开创性且影响久远的女作家的书写,缘于“在国际环境中,感到长期以来中国女性作家被认知的程度非常不够,中国整个现代文学和文化被认知的程度非常不够,其中涉及到认知方法和路径的问题”。十年三易其稿的过程,也是她亲身体验在国际环境下,“中国”的一切,如何历经从被冷战思维所主导的视角与叙事所掩盖而“不可见”的状态,走向“可见”的可能。这是一个漫长摸索的过程,也是一个敞开的实践过程。将“不可见”的事物转为“可见”的人生的人文叙述,见证了她尝试突破欧美中心主义的文化想象、机制构建和思维定势,超越冷战逻辑下区域研究的惯性常规的一次认知实践;与她同时出版的关于欧洲和第三世界文化现象的著述一起,构成她探索进入美国主流学界的学术路径。
在作者笔下,精卫鸟的喻像在女性作家的文学与日常生活中不断重现,仿佛在示意作者自身30年时光砥砺打磨的“历史连贯性”。在2009年夏天于上海举办的一次中美学术会议上,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青山用“一以贯之”来定位她,“从《秦王李世民》中对以人为本的主题关切,到出国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以民生为重、民族复兴的关切,她的思维逻辑在学术生涯里是一以贯之的。”
颜海平自己也承认,走到今天,确实是按照内心的一种呼唤一路走来:父母作为抗战期间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时投入地下革命工作,从浙江一路辗转走遍整个中国。家庭的影响镌刻在童年、少年的成长时光中,成为一种内心的“历史连贯性”。在她的书写——无论是文学性或学术性的文字——中保持对祖国的一份坚守,身居海外多年依旧保留中国护照,这些只是“历史连贯性”的一个个具象表现而已。
从八十年代初的“尊前独唱小秦王”,到当下对全球剧变时代中国大问题的关切,三十年的书写历程,颜海平援引冰心的母亲说过的一句话加以概括,“一个人的文字,关乎一个人命运。”她呈之于众的文字的核心意旨可归纳为“旧邦新命”四个字。用她的话来说,这里的“新命”,就是在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探索如何主动地包容和超越既定的现代认知体系,有效地把握、处理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叙述及想象更新。
记者:大学时代创作十幕历史话剧《秦王李世民》,当时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颜海平:文革刚结束时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个社会问题,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是从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开始界定的。我记得当时我的问题是,中国的传统中有没有内在活跃的现代元素,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没有自己指向现代的资源。我想到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在大唐盛世的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现代性的可能。当时有不少公演的关于李世民的戏曲,主要是谈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我在阅读史料过程中,觉得还有更根本的思路。读史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过程,不是理念先行,也不是纯粹直接的借古喻今,实际上是求对历史的重新发现进而重新把握。
记者:为什么采用话剧,而不是小说或者其他文学样式?

《秦王李世民》剧照
颜海平:我从小喜欢戏剧,这和父亲的影响有关。幼时父亲带我去看话剧《南方来信》,演出结束了,别人都走了,我却不肯走。现代历史剧说到底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的更新和传承,一方面是历史记忆的再呈现,另一方面,其呈现的根本形式已经是现代的了,历史记忆即由此获得现代转化。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是对英国民族国家发展现代进程的一种思考、把握、表达和赞美,这种含有多重内容的赞美很深邃、很丰满、很精致,它形成一套文化的创造、一种现代语言的诞生,而成为经典。我喜欢如《桃花扇》这样的历史剧,包括古典的和现代历史剧版本,这里有民族文化的渊源、传承、变革,有民族生命记忆在起作用。当时,我非常急迫地渴望学习。文革结束不久,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时代要求我们以创造性的精神快速补课。学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创作结合起来,是强化学习和深化学养的方法之一。
记者:77级成为中国教育史、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别符号。能否以剧作家及学者的双重身份谈谈77级文学现象?
颜海平: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通过高考入学的,即77级。我们77级、78级、79级被称为“新三届”。相比华东师大,我们复旦中文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学者,如陈思和、周斌在复旦做教授,王云在上戏做教授,张胜友任出版社老总,同学中还有成为经济学家的。那时候我们和华东师大走得很近,记得赵丽宏当时结婚没有房子,我去过他住的一间暗乎乎的屋子,在这里他写出很多很美的散文和诗歌。九十年代陈思和和王晓明发起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华东师大中文系形成作家群,都值得感佩赞赏。我觉得无论是成为作家还是人文学者,在新闻出版或其他岗位,大家都没离开自己的根本宗旨,就是坚守并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两者内涵是一致的。
记者:文学创作需要感性,学术研究需要理性。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或曰感性与理性的合一,你如何把握感性与理性的界限和结合?
颜海平:我在美国求学时的导师Dominick LaCapra教授,是美国研究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史的第一人;美国文理院院士。师从于他,我全面进入了一个不同文明体系的精神世界;同时,从他那里,我触摸到、领悟到、最终自觉开拓的重要思想路径,是如何批评地学习和处理西方思想传统和人文经验。我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学术路径,和这样的教授分不开。如何把握理性和感性的界限和结合,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现代学术方法的基本前提是研究者作为认知主体研究对象:我研究的对象是客体,我是主体,这个关系不平等。尤其是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这个关系,哪怕意图是好的,结果可能是偏的。从学理上说,我觉得对现代学术传统逻辑需要有超越,这是一个理性的思考。学者和研究对象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认知的、审美的、政治的、最终是伦理的一个决定,你在多大程度把自己和它连起来,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拉开距离;我们其实说到了比较深的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各种具体方式的把握问题。期待我们国内的学界同行之间,在提升我们国际能力的历史发展期,有更多讨论这个话题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