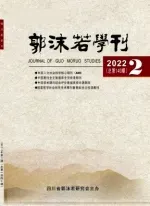是自叙性“小说”,还是自叙性“散文”?——关于郭沫若《鸡之归去来》体裁的辨析
李存光
(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1)
问题的提出:小说还是散文?
1933年9月26日,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在寓所写了一篇题为《鸡》的作品,未在报刊发表,直接编入1934年1月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沫若自选集》,后收入北新书局1937年12月出版的散文集《归去来》,并改题为《鸡之归去来》。
《鸡之归去来》直接表露了郭沫若对受欺压的在日朝鲜人的深切关注和深厚同情,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涉及朝鲜人的一篇重要作品。这篇作品写的是郭沫若亲身的经历和独有的感触,内容的自叙性毋庸置疑,但究竟是自叙性“小说”(“身边小说”)还是自叙性“散文”?这个问题看似不大,却不容小视,很值得研究。
最早把这篇作品作为“身边小说”看待的是日本的藤田梨那教授。她在《郭沫若〈鸡之归去来〉中的变形抵抗与对韩意识》①和据此文修改调整而成的《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的抵抗文学》②中,将《鸡之归去来》归入“身边小说”,她解释说,“所谓身边小说是指以作者自身为主人公,写他自已的经历和感触的一种自叙性的小说。”[1](P37)藤田教授的论文发表后,韩国学者沿用这一看法,将《鸡之归去来》纳入“韩人题材小说”的重要篇章加以论述,比如朴宰雨的论文《三四十年代中国韩人题材小说里的对韩认识与叙事特点:20世纪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变迁研究》。③
藤田教授从郭沫若宏富的著作中发掘出《鸡之归去来》这篇与朝鲜人密切相关的重要作品,并撰文详加论述,功不可没。她爬梳诸多史料,对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现实依据和作品思想的深广社会性,逐一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细致分析,材料丰富,说理绵密,令人钦佩。但她把这篇作品作为“小说”解读,窃以为多有不妥,值得商榷。
郭沫若的处理和中国学者的共识
辨析《鸡之归去来》体裁,首先需要看看作者郭沫若是怎样处理这篇作品的。
郭沫若在首刊这篇作品的《沫若自选集》序文第二段说:“这儿所选择的一些是比较客观化了的几篇戏剧和小说,为顾求全体的统一上凡是抒情的小品文和诗,以及纯自传性质的一些作品都没有加入。……我目前很抱歉,没有适当的环境来写我所想写的东西,而我所已经写出的东西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在闸门紧锁着的期间,溪流是停顿着的。”[2](P1-2)
藤田教授根据《序》,对《鸡之归去来》的体裁归属,得出了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那些‘比较客观化’的作品中加上了《鸡之归去来》。从他的序文看,我们对《鸡之归去来》可以粗略理解为‘比较客观化’的,不是‘抒情的’,也不是‘纯自传性的’作品。”[3](P37)
郭沫若为什么要将《鸡之归去来》编入自选集并冠于卷首?《鸡之归去来》是不是同集中其他作品一样属于“比较客观化”的、非“抒情”的小说或戏剧作品?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先简介一下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1月版《沫若自选集》。自选集是应乐华图书公司之约编辑的,收文12篇,共428页,卷首是《序》(1933年8月26日作),12篇作品依次为:《鸡》(1933年 9月 26日作)、《湘累》(1920作,剧本)、《广寒宫》(1922作,剧本)、《鵷雏》(1923作,小说)、《函谷关》(1923 作,剧本)、《王昭君》(1923作,剧本)、《无抵抗主义者》(1923作,对话)、《歧路》(1924作,小说)、《行路难》(1924作,小说)、《湖心亭》(1924作,小说)、《聂讔》(1925作,剧本)、《马氏进文庙》(1925作,小说)。④
这个目录可以看出:一、《序》写于1933年8月26日,《鸡》写于1933年9月26日,《序》比《鸡》早写整整一个月;二、除首篇《鸡》写于1933年外,其他作品都是1922-1925年写的;三、除首篇《鸡》外,收文的顺序完全是按照写作年代的先后排列,不区分体裁。
以上这三点,能够说明一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发现《序》作于8月26日而《鸡》作于9月26日,这两个日期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郭沫若是在选好作品、编好集子并写成《序》以后,才补入新近写成的《鸡》。因此可以说,《序》中所作的说明只针对11篇作品,与后收入的《鸡》无关。《鸡》是独立于其他11篇作品的另一单元。明白这一点,方能解释为什么在《自选集》中,《鸡》在写作时间、排列顺序、作品体裁诸多方面都与集子不协调的原因。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把《鸡》放进这个集子并冠之于卷首?当时,郭沫若在国内受通缉,在日本遭监视,“所已经写出的东西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因此,借出版旧作选集的机会,把刚刚写成的这篇指向明确、爱憎鲜明的新作“塞”进去,使之得以发表;将它置之卷首,是因为这篇作品与按既定意图编好的选集不协调,只能放在卷末或卷首,将之置于卷首,是无言的抗争:我仍在写作,我仍要呼喊。这正如藤田教授的诠释“就是要向读者表示被封锁着的溪流仍未失去它强劲的生命力。”[3](P38)
把《鸡》硬加到《自选集》中,是一个无奈的选择。郭沫若回国后,生存环境大变,因此,随即将它正式编入散文集《归去来》(北新书局,1937 年12 月)。后又收入小说、散文、杂论集《抱箭集》(海燕书店,1948年1月)的第五辑即散文集《归去来》(含《鸡之归去来》《浪花十日》《东平的眉目》《痈》《太山扑》《达夫的来访》《断线风筝》七篇散文)。
《沫若文集》是经过郭沫若亲自校阅修订的文集,其第八卷的总目题为“革命春秋(沫若自传第三卷)”,以下包含的细目为《北伐途次》《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海涛集》《归去来》。[4]这些作品都是自叙性散文。
再看看被称为“收集编目最丰富、注释最准确的郭沫若著作总集”《郭沫若全集》。其中的“文学编”是在《沫若文集》的基础上编成的,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共20卷。前5卷均为诗歌,6-8卷是戏剧,9、10两卷收小说与散文,11-14卷为自传,15-17卷是文艺论著,18-20卷收杂文。编者的“第十卷说明”称:“本卷收入作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七年所作小说十八篇,散文三十篇。……‘其他’包括散文八篇。……《鸡之归去来》(原题(《鸡》),曾收入《沫若自选集》。”[5]
不难看出,郭沫若一直把这篇作品作为散文(自传散文、自叙性散文)处理的,《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正是遵循作者的处理精心编排的。
《鸡之归去来》作为散文(自传散文、自叙性散文)的体裁归属,中国研究者众所认同,从无异议。这里举出部分相关研究专书和作品选集便足以说明。
一、王昭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书中录入的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在《鸡》后标明“散文“;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分类书目”将《归去来》列为“自传 日记 书信”类,显然也是作为广义的“散文”处理的。[6](P1069-1078)
二、王继权、童炜钢编《郭沫若年谱》。1933年9月条下“26日 作散文《鸡》。通过白母鸡失而复归的故事,表现了对受压迫的旅日朝鲜工人的同情,并预示着人民必将起而反抗。收《沫若自选集》。现收《沫若文集》第8卷,改题为《鸡之归去来》。”[7]
三、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增订本。一九三三年 九月条下“二十六日 作散文《鸡》。通过家中养的一只鸡‘去而复返’的故事,表现了对流落在日本的朝鲜人的同情。收《文集》卷八《归去来》时,改题为《鸡之归去来》,现收《全集》文学编十三卷。”[8](P281)
四、王锦厚主编《郭沫若作品辞典》。“散文记叙了作者家养白鸡‘去而复还’的事件,……散文采取欲扬故抑,由此及彼的手法,结构清晰,感情真挚,叙议结合,既是作家一段个人生活真实记录,又是一幅历史发展照相。”[9](P55)
五、李晶标主编《简明郭沫若词典》。书中将《鸡之归去来》列入二、创作(四)散文,在介绍了作品思想内容后说:“作品用了小说笔法,笔触细腻,重于人物心理刻画。”[10](P80)
六、多种郭沫若散文选集选收《鸡之归去来》。如王锦厚编《郭沫若散文选集》(现代散文丛书·百花散文书系,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年,2004 年);李晓虹选编《名家名作精选·郭沫若散文》(学生阅读经典,内蒙文化出版社,2006 年,200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郭沫若散文》(插图珍藏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刘屏编《路畔的蔷薇》(大家散文文库,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年)等。
七、将《鸡之归去来》列为“散文”收入的综合性选集。如四卷本《郭沫若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漓江出版社编《郭沫若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4 年)。
以上资料集、年谱、词典和选集作为有关郭沫若的专书,编者都是郭沫若研究专家或对现代文学史料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共识足以代表中国研究者的看法。
谈到这里,顺便澄清三个细节:
第一,《鸡之归去来》在收入《沫若文集》时,第四部分的文字有几处小改动。第四部分共五段,其中第三段中的“草叶”改为“草药”,“事情也就穿破了”改为“事情也就穿了”;第四段中共有四处“风说”,除第二处外,其他都改为“流言”。鉴于引者大都依据《沫若文集》或《郭沫若全集》的文本,故作说明。
第二,以上所举两种《郭沫若年谱》都说《鸡》“收入《沫若文集》第8卷时,改题为《鸡之归去来》。”这是错误的。如上所述,《鸡》在收入北新书局1937年12月出版的《归去来》时,作者就将题目改作了《鸡之归去来》。海燕书店1948年1月出版的《抱箭集》在收入这篇作品时,沿用这个题目,后来的《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均据此。
第三,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上,增订本)在介绍《郭沫若自选集》的收文情况时很不确切。年谱“1934年1月”条说:“同月《郭沫若自选集》由乐华图书公司出版。《选集》收戏剧四部、小说六篇、论文二篇,均系1920年至1925年间的作品。”[8](P285)这段介绍三处有误:第一,该集中没有论文;第二,《自选集》收文的实际情况是,收作品12篇(部),其中,剧本5部,小说5篇,散文1篇;⑤第三,除《鸡》作于1933年外,其他11篇均系1920年至1925年间的作品。
作品的特色和辨析体裁的意义
辨证《鸡之归去来》的体裁是不是小题大做呢?非也!这个问题虽小,但关系甚大。如果把这篇作品作为小说,会衍生出种种不小的问题。比如,《郭沫若全集》文学编重版时相关卷就需要调整篇目或重写编辑说明,现有的郭沫若年谱、词典需要修改词条,诸多版本的郭沫若散文选集要抽去这篇作品,等等。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更在于,这将妨碍对作品整体的艺术诠释,影响对作品内容和细节真实性的判断,最终降低这篇作品在郭沫若创作中和现代文学有关朝鲜人作品中的位置。
既是小说,就要用“小说”视角打量。小说与散文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表现手法也有交错和融合,但是,作为文学体裁的两大门类,总是有区别的,最重要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小说允许而且应该有虚构,而散文特别是纪实性散文在环境、人物、事件上不能够虚构;第二,小说主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自身的发展体现作者的倾向和思想,而散文既可叙事,写人,绘景,也可抒情,议论,可夹叙夹议,可借题发挥,可由此及彼。当然,现代小说的观念、模式有很多变化,但至少对这篇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应作如是观。
《鸡之归去来》中的环境、人物、主要情节乃至细节,都没有虚构,都是实际存在的。全文不足七千字,分为四节。作品中正面出现的人物有“我”、“我的女人”安娜、丈夫在东京某会社做事的S夫人、H木匠的老板娘四个人,以及“我”与安娜的五个儿女中的儿子博、四女淑子、半岁的洪儿三人,村中的朝鲜人只在女人们的谈话中提到,一个也没有出现。第一节写我家居住的环境和房屋的情况,白母鸡丢失;第二节写白母鸡复归,引起我和妻子安娜的揣测:是谁偷走了鸡?为什么又送回来?第三节写安娜找来H木匠的老板娘辨认归来的鸡,我听见三个女人猜测偷论鸡人时几次出现“朝鲜人”三个字,由此引发对在日本的朝鲜人牛马般处境的长篇感叹和议论,我断定鸡的“去”和“返”是朝鲜人所为,鸡的“复返”,是因为偷鸡的朝鲜人知道了我家和他们是“一样时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义理得了胜利;第四节写谈话的女客走后安娜又告诉我一件朝鲜人“吃人”的流言,我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深怀对“在剥夺者的手下当奴隶”的朝鲜人同情和理解,揭示构成这类流言的主要原因。作品第三节用一千余字篇幅借题发挥,叙述在日朝鲜劳工境遇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倾述作者对他们的关注和同情,并为他们鸣不平。从小说的角度看,对鸡“失而复归”情节的叙写和几个人物的描画,显然体现不出长篇幅议论中那样广泛深刻的思想。在作品中,大篇幅议论,并非势所必然地来自生动细致的具体描画,不是通过人物和情节得到表现,而是游离于人物和情节之外硬加上去的“思想”。
难解的是,这些议论恰恰是作品的重心所在,关键所在,要害所在,意义所在。去掉这些议论,《鸡之归去来》只是一篇妙趣横生的记叙身边琐事的小文;把议论抽出来,则可以写成一篇有独立存在价值的锐利杂感。一方面要肯定作品中议论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又无法解释议论与作品人物、情节的内在联系,藤田教授也深感这一两难境地,她说:“用了很大篇幅叙述了朝鲜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内容很明显已脱离了身边小说的范畴,而且郭沫若的着眼点毋宁是在朝鲜劳工问题上的。”(p38)“虽然采用了身边小说的形式,但实际内容却已超过身边小说的范围,对在日朝鲜劳工的描写和问题的揭示已显示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性。我们或许可以说,郭沫若的描写主题其实并不在鸡的失踪,而是在朝鲜的劳工的问题上。”(p43)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成了表达某种思想的道具,很大篇幅的题外发挥游离于人物和故事,从艺术上说,这难道不是一篇思想大大超越形象的小说吗?
换一个角度,从“散文”的视角看,情况就大不同了。困惑忽然开朗,疑窦迎刃而解,上述缺陷成为了优长。作者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家养的一只白母鸡不明不白地丢失,又莫名其妙地回来。面对这件小而又小的事件,“我”有所感悟,生发联想,乃至禁不住大发议论,直抒胸中块垒,是自然而然的。因小见大,由此及彼,借题发挥,不正是散文常用的手法吗?围绕鸡的“失”和“得”,悬疑由此而生,感叹和议论因此而起。作者的思想通过议论直截了当地得以表露,作品深广的社会意义由这些议论而得以确立。如此看来,作品中的两处议论,不仅不是赘疣,恰恰是整篇作品的精彩之笔,精妙之处。作者采取欲扬故抑,由此及彼的手法,因事抒怀,叙议结合,议由事生,不仅使丟鸡事件的原委“柳暗花明”,“朝鲜的劳工的问题”的题旨得以充分表达,更体现出作者汪洋恣肆、无拘无束的思想力和笔力,这不正是郭沫若散文一贯的风格和特色吗?
作为散文,《鸡之归去来》因其叙写生动、联想精妙、内蕴深广、特色鲜明而获得诸多选家青睐;而作为小说,恐怕任何一本《郭沫若小说选》都不会选这篇议论胜于描写、思想大于形象的作品。可见,把《鸡之归去来》纳入“小说”行列,反而会减低作品的自身价值,进而降低它在郭沫若自叙作品中的地位和现代文学有关朝鲜人作品中的地位。
最后要说的是,藤田教授在她的论文中认为,《归去来》这本集子里的《浪花十日》《东平的眉目》《达夫的来访》《痈》《太山扑》等“从作品性质上看,它们都应算作身边小说。”(p37)既然题目已明示是记丘东平、郁达夫等友人,亦可归入“身边小说”,那么,以此类推,能不能把《少年时代》《学生时代》《革命春秋》《洪波曲》中的若干篇章也归入“身边小说”呢?众所周知,郭沫若的自传文学卷帙浩瀚,体式博杂,囊括小说、杂文、散文、戏剧各类文体,研究者应仔细区分,不能随意扩大其中“小说”的范围,包括《鸡之归去来》在内的《归去来》中的作品,显然有别于《未央》《残春》《阳春别》《落叶》《漂流三部曲》等“身边小说”。模糊“自叙性散文”同“身边小说”的界限,其结果只会削弱这些纪实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和细节真实性,削弱自传材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从而淡化甚至消解消郭沫若自叙性散文的存在和自叙性散文中呈现出的鲜明、多样、真实的自我形象。这对解读郭沫若的自传性作品和研究郭沫若生平传记,恐非幸事。
注释:
①韩中言语文化研究第9辑[M].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2005 年9月.
②《郭沫若学刊》,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主办,2007 年第1期。
③韩中言语文化研究第19 辑[M],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2009 年2月。
④篇名括号中的写作年代和体裁是本文作者加的。
⑤剧本:《湘累》《广寒宫》《函谷关》《王昭君》《聂讔》(后改题《聂嫈》);对话:《无抵抗主义者》;小说:《鵷雏》(后改题《漆园吏游梁》)《歧路》《行路难》《湖心亭》《马氏进文庙》(后改题《马克斯进文庙》);散文:《鸡》(后改题《鸡之归去来》)。
[1]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的抵抗文学[J].郭沫若学刊,2007 ,(1).
[2]沫若自选集[M].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4 年1月.
[3]郭沫若学刊[J].2007 ,(1).
[4]沫若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5]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6]王昭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C].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7]王继权,童炜钢编.郭沫若年谱(上)[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
[8]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增订本(上)[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
[9]王锦厚主编.郭沫若作品辞典[M].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 .
[10]李晶标主编.简明郭沫若词典[M].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