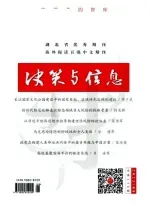关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理论问题
文/汪仲启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法治国家建设研讨会”日前在古都西安召开。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等13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集中就人大制度与民主法治建设、党的领导与法治国家建设、百年宪政、公民社会与中国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党的执政来实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来,历经磨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任务。1949年成为执政党后,也走过一些弯路,但党始终能适时调整自己的领导策略。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重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教授说,“马上治天下,还是法治天下?是以党治国,还是依法治国?至今有些党政干部不能说已完全搞清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应该从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开始。党章、“党法”不能与国法有抵触的地方,“法治建设发展到今天,执政党要依宪执政,全体党员,特别是某些党的官员要成为实施宪法和法律的工具,而不是把宪法和法律当成实现自己政策主张的工具。”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表示,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离开了执政党的推动,加强宪法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会是一句空话,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从宪法开始,而是否可以考虑从党章开始”。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中心主任虞崇胜教授同样认为,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是制约该国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问题,只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执政方式才是值得肯定的。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场景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充当了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的双重角色。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如果角色错位,将导致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的混乱,因此,“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党的执政来实现”。领导权是政治权威,主要靠政策指导与号召,执政权是国家权力,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领导权对党负责,而执政权对人民负责。因此,法律,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应该比党规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郭为桂教授认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国家构建逐步恢复到常规的理性化道路上来,群众路线总体上演化为惠民亲民的政策主张,“但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问题不断,党群关系依然紧张,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这是因为“群众路线”本身存在着内在缺陷,当代群众概念更多地继承了传统语境下“民”的概念的消极、被动、受治者的含义,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下者地位,是被领导、被保护、被关爱、被服务、被尊重的。“作为一项根本的政治路线,缺乏基本的制度依托和机制保障,其运作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偶然性,需要上层不断地警示以求得中下层领导干部的重视和遵行。”中央编译局朱昔群研究员说,有人认为当前我党面临执政能力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两大挑战,党在化解执政能力危机的时候采取了许多有成效的举措,但执政党执政中的合法性危机,如群众对政府、官员不信任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维持良好的党群关系,我们不能再靠运动,要靠制度化保持优势,要实现党群关系的制度化。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桂维民认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而我国宪法实施工作目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许多公民,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不强,人治习惯根深蒂固,对宪法赋予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保障还不力,强行拆迁、滥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宪法实施的紧迫任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实施的关键环节。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教授表示,当前基层政府一些官员滥用公权力,屡屡侵犯老百姓的人权、生命权、财产权等基本权益,“跨省追捕”,“被神经病”、“暴力拆迁”等蛮横不讲理的做法,击穿了为政者的伦理底线,严重背离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宗旨。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真正做到胡锦涛同志所说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说的“权为民所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在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树志教授看来,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极端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尚未完全铲除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即使制定了宪法,真正实现宪政并不容易,中国应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著名宪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先生认为,宪政即民主政治。危害我国宪法尊严及其实施的思潮来自两个方面:自由化思潮和打着反“西化”旗帜的极“左”思潮,“把‘宪政’片面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专利,无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认为实行‘宪政’就会招致西化的观点,极为荒谬”。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宪政社会主义”。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华炳啸认为,宪政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合法性基础,脱离宪政,党的事业就有脱轨的危险,要实现长治久安,只能走宪政民主与共同富裕之路,也即走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如果不能找到解决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对策,高成本维稳只能把一时一地的怨气转移和蓄积到更脆弱的时空点上,社会动荡难以避免。而要避免社会动荡,就只能走科学发展与全面改革之路,即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人大不应成为政府干部的“养老院”
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然而,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何处理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在操作机制上并不明确,人大自身也面临着工作机制的不完善问题。中国世界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常士门言表示,人大和党的关系中存在张力,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反映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存在着双头领导且一定程度上的矛盾状况,“这导致我国政治生活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有权威而缺少规则,有监督又监督不力的尴尬局面”。
党和人大到底是何关系,“领导”和“作主”如何能统一?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认为,党的主张对于人大或其常委会而言,只是一种建议而非命令。党的主张经常能被人大转变为国家意志,就体现了党对人大乃至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带领与引导),如果党的主张不能经常转变为国家意志,则党对人大和国家的领导就难以保证。“从理论上讲,人大或其常委会可以转变,也可以不转变,人大或其常委会是否将党的某项主张转变成国家意志,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力。”
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教授则认为,全国人大代表超过3000人,人数过多不便于讨论和决定问题;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69人(第十届以前150人),人数过少,虽便于讨论和解决问题,但又缺乏代表性。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较短,议程较多,使代表们的利益表达受到时间限制,难以保障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充分表达意见。周伟建议,将代表人数由3000人左右减少到1200人左右(1954年第一届人大代表的人数)。除保留各民族、台湾地区、特别行政区的代表配额外,均按照人口比例产生,约100万人产生一名代表。增加常委会人员职数,恢复到1949年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人数的600人左右为宜,还可增设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全部担任常委会成员。
对于专门委员会,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副教授廖原指出,由于工作机制不顺,缺乏明确的议事规则,各专门委员会之间工作量差别极大,工作范围和职责划分不清晰,人员年龄整体偏大。“以九届人大专门委员会为例,60岁以上的占73%以上,而50岁以下的则不到7%。在某种意义上,专门委员会起到了安排退休领导干部的作用”。廖原建议,把人大专门委员会建设作为完善人大制度的突破口,除制定专门的议事规则,明确工作职责之外,应重点调整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结构,“人大工作机关不应成为政府干部的‘养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