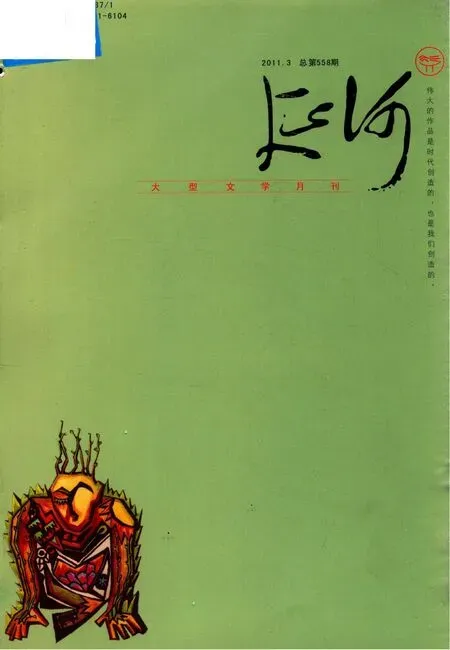受难的身体
吴克敬
受难的身体
吴克敬
受难的脖子
麻绳从细处断。民间流行的这句话,是最不好听的,偶尔闻之,让人的脖子总有一种冷嗖嗖绝命的感觉。
这不能怪罪人的意志不够坚强,而只有怪罪律法规定的夺命方法太过残忍。翻阅中国古代律学,发现处人死刑的条例,无一不惨绝人寰,使人发指。如奴隶社会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再如五刑之后的封建社会,又要加上笞、杖、徒、流、死诸种。判官的惊堂木响亮地拍下来,判了犯人凌迟,行刑者就要一刀一刀地切割人犯身上的肉,凡120刀以上体无余脔,然后剖腹断首,明崇祯皇帝对他的忠臣良将袁崇焕狠心的判处了此刑。此外还有斩首、剥皮、炮烙、烹煮、抽肠、沉水、绞杀、鸩毒、火焚、钉颅、活埋、锯割、饿死、梳洗种种,不一而足。这许多死刑方法,大多还好理解,而温柔的“梳洗”之刑,绝没有平常人梳头洗脸那么舒服惬意。受梳洗的人犯,被行刑者剥光了衣裳,绑一张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裸体上浇,浇过一遍后,就用钢铁的刷子在人犯的裸体上刷,刷过一遍,再往人犯裸体上浇开水,然后再刷,直到把受刑人犯身上的皮肉一层一层刷尽,露出森森白骨,而后咽气为至。凡此死刑法则,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一点一点地摒弃着,至今已不再使用。为此,我们是要鼓掌欢迎的,但还不能消除累积在我神经末稍上的悲伤,回过头来去探究那惨无人道的种种死刑范式,有许多是直冲人的脖子而去的。譬如慈禧太后对“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他们的斩首,以及大唐皇帝代宗李豫对元载施行的绞杀等。
元载所以要受绞刑,他是罪有应得的。
有唐一朝,大诗人代有杰出者,例如前期的李(李白)杜(杜甫),例如后期的李(李贺)杜(杜牧)等,再者还有一个元(元载)白(白居易),都是要让后来人望其项背,崇敬膜拜的。身负大名的元载,如能保守一个诗人的操守,他是会高誉善终的,但却没有,他被唐代宗李豫抓住了毛辫子,把他下到禁中大狱,施行了绞杀之刑。我不知时人是怎么看他的,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审视元载的悲剧时,是要为他扼腕悲叹的。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 《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全唐书》还收了他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候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元载的这首七绝,但已朦胧地感知他谶语般为自己预设了一个结局,他是没法好死了。
元载不得好死,归根结底一个字:权。
他的权力太大了。苦心孤诣,处心积虑的元载,在他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时,偌大的长安城都要装不下他无限膨胀的欲望了。“志气骄溢,每众中大言,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史书的这一段评语,扣在元载的头上,一点都不冤枉他。有几个小故事可以为证,说明元载的权势到了何种疯狂的程度。
代宗皇帝旨令查处元载,领旨者到他的府上去,仅只查他在长安城里的大宁、安仁两里,就使查检者瞠目结舌。后来处理他的房产,分配给朝廷里的百余官吏使用,也还绰绰有余。即是这样,还不包括东都洛阳他的一处园林私宅,充公后,竟能改做一座皇家大花园。

痛苦的碎片 培根 1950年 油画 139×108cm
如此似还不能历数元载的贪欲。他大历元年入朝为相,作了十二年的高官,李豫下旨让人抄家,不仅抄没了他结连数条街巷的房产,还抄没了他藏之巍峨屋宇里的奇珍异宝,其中竟有“钟乳五百两,胡椒八百石”。钟乳者,我们知道是为一种贵重的药材,晋人好食的“玉石散”,配料中断然少不了钟乳一味。五百两是怎样一个概念呢?恕我寡识,难以尽言,但我知道,代宗李豫的老祖宗,盛世之主李世民曾用他的臣下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特赐钟乳一剂以为奖赏,并且以言嘉勉“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这么看来,五百两钟乳该是非常难得的了。
钟乳难得,那么胡椒呢?想来也是不好获得的。
汉唐以降,凡泊来之物,加入中华文明之列时,习惯在此物之前冠个“胡”字,什么胡琴、胡豆、胡瓜、胡桃、胡萝卜……多了去了。胡椒是其诸多“胡”物中的一种,我们今人的餐桌上,常会见到此种香料。“但在元载那个时候,恐怕就不常见了。有位名叫段成武的文人,在他所著《酉阳杂俎》里,详细地记载了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味履支”。摩伽陁“属中天竺,距长安九千多里。”好乖乖,如此远的距离,如此多的胡椒,让我们借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唐武德元年的铜权换算一下,知道当时的一石等于今天的公制79320克。那么元载的八百石胡椒差不多就是60余吨,现在用火车拉运,一个车皮就够,可那时没有火车,运输的大吨位工具是为丝绸长路上的骆驼,一峰骆驼的载重不敢过了500公斤,如此说来,得需120余峰骆驼满载摩伽陁的胡椒,从印度洋的海滨,绕道喜马拉雅山南麓,经克代米尔,过新疆南部,最后运抵长安。
想想看吧,胡椒的价值该是非常昂贵了。不过,昂贵归昂贵,元载的权势大,不等于他的脾胃也大,那么多的胡椒,他吃用得了吗?
绞杀……代宗李豫旨批了对元载的用刑,但还照顾了他的体面,只让行刑者在监牢里监督元载的自尽。气势熏天的时候,元载是半个眼儿也不理会狱卒的,到要死了,他央求狱卒“愿得快死!”狱卒嫌他啰嗦,“乃脱秽祙塞其口而杀之”。
哈!臭袜子塞口,亏得狱卒的想像力,也是太过丰富了。
我多么想要嗔骂那个想像力丰富的狱卒了,你让元载的脖子受难的时候,怎么还要让他的嘴巴受苦呢!我试着张了张口,终于没能骂将出来,因为我知道,元载的脖子是该受那一难的,之所以脖子受难,根由可不就在他的嘴巴上吗?
此为脖子受难的一种,活该。但另有一种,就该是别样一个说法了。
典型如一代爱国忠臣王鼎,他以“尸谏”的方式,甘心情愿地让自己的脖子受了一次难。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的时候,蒲城人王鼎作为亁嘉时代的遗老,还是很受道光皇帝敬重的,派他督察治河,可他闻知清军屡遭英国侵略军侵袭,朝廷内以穆彰阿为首投降派,主张与英军议和,王鼎在治河工地上坐不住了。他返回北京,在朝廷上与投降派针锋相对,力主抗英,“语及议和,公垂泪操秦音争之强”。“侃侃力争,忤枢相穆彰阿。”并多次“力荐材则徐之贤”,以为人才难得,应予重用。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站在枢相穆彰阿对立面的王鼎,有时连皇帝的尊严和忌讳都不顾了。这是因为,年老病弱的王鼎发现,他与穆彰阿的此次廷争,孤立无援的是他一人,道光皇帝从感情上虽还倚重于他,但在理智上,已然偏向主张议和的穆彰阿一派。
是年四月二十九日,这是王鼎拖着病弱之躯最后一次上朝,强烈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迫使他要在朝堂上作背水一战。此前一个晚上,年事已高的王鼎“扶案不食”,草拟了一封奏章,袖手带到朝堂上来,依然历声诟骂穆彰阿为“秦桧、严嵩”,力保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抗英禁烟。王鼎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却未使道光皇帝有所觉悟,反而令“同列不阅,上亦稍稍厌之”,一次次地岔开王鼎的话题,说他“病体未愈,可多调养数日,不必如此着急。”王鼎听得懂道光皇帝的岔路话,他是不管不顾了,继续着他的滔滔廷争,这让道光皇帝甚是不快,自龙椅上起立欲去,王鼎大踏一步,抢在道光皇帝举足之前,伸手牵住皇帝的龙袍,大声地晋言道光: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
穆彰阿是投降派的总代表,琦善是投降派的急先锋……王鼎向道光皇帝廷谏此二人未果,他回到圆明园先皇赐于他的寓邸内,思前想后,气愤难平,遂以春秋时卫灵公史鱼尸谏的范例,决心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向道光皇帝作他最后的抗辩了。四月三十日晚,他研墨展纸,写了一份遗疏: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用,林不可弃。待纸上墨迹稍干,王鼎又看了一遍,然后揣进怀里,找来一条白绫,悬于梁上,自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样的脖子,不一样的受难。元载遭绞杀,罪有应得,遗臭万年;王鼎悬索自缢,死得其所,流芳百世。
先不说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一批进步思想家在王鼎自缢后,是如何为悬梁救国的王鼎呼号的。只说不算很有能耐的道光皇帝,在闻听王鼎死后,即以太保赠之,并入祀贤良祠,谥“文恪”。纵然如此,道光皇帝还受穆彰阿一党蒙蔽,不晓得王鼎的遗疏,不晓得王鼎是自缢报国,他感念这位忠直刚烈的老臣,谕赐了恤文、祭文、碑文,并将王鼎的大学士位,空缺三年,不授他人,以示他的圣意笃念。
此其时已,林则徐为穆彰阿一派排挤受贬西行,正在王鼎的故乡西安,身患疟疾停留治疗。忽闻恩公王鼎噩耗,震惊之余,又万分悲恸,抱病撰写了悼词和挽联,抒发了他“伤心知已千行泪”的痛切心情,赞扬王鼎“甘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泪难禁”,把他与史鱼尸谏和晋卿祈死相提并论,称他“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高度评价了王鼎的尸谏壮举。魏源的悼念诗,较之林则徐来,似乎更加直言不讳和悲愤难抑:“身后被谁禁谏草”,“尸谏谁闻古荩臣”。对此,受道光皇帝谕旨为王鼎题写墓志铭的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祁隽 藻,难掩心中的愤怒,慨然写道:“史传不能载,孤愤盈万口。直哉史鱼节,纯臣心可剖。”
啊!脖子……受难的脖子啊!
死的滋味
忘了是从哪里看到的老笑话,其中二人探讨死的滋味,一人说:“人皆有死,不知死的滋味如何?”另一个想了想说,“可能还不错。”一个就又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另一个就很明白地告诉他,“还没看见那个人从那边逃将回来。”
因为老笑话幽默好笑,我看到后再没忘记,只是觉得这么调侃人生大限,可有什么意义?原因在于人的本质要求,对于生的依恋,总是大于死的向往,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通透明了的概括了人的这一价值趋向。孔老爷子的学生,曾经天才地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老师更加天才地回答里他的学生,曰:“未知生?焉知死?”这一手太极玩得妙,把去那边报道的人,不肯重回故地的问题,聪明地神秘起来了。从此叫人不断追问,见仁见智,人言人殊。
是夜翻阅《梦溪笔谈》,其中涉足了一个名尹洙、字师鲁者的故事,仔细读来,倒觉颇有味道。这位豪杰的尹洙,平生坎坷,活到四十大几时,被远贬均州,代为朝廷征收酒税。他的命程真是太苦了,遇到的上司只会一味迎合权贵,对他就十分苛刻了。好友范仲淹恐他遭受迫害太深,向朝廷请旨,把他接到他在南阳的治所避祸疗疾。尹洙翻山涉水到了南阳,安居下来不几日,忽然托书向范告别,要他帮他料理后事。范仲淹心里疑惑,当即派了幕僚长朱炎前去查知。幕僚长朱炎前脚踏进门来,便见尹洙已沐浴一毕,具衣冠而坐,对朱炎说,“洙死矣!”言罢,头伏桌案而殁。朱炎哪敢怠慢,紧急命人驰报,范仲淹应声而来,哭声甚哀。死去的尹洙却抬起头来说,“早已与公告别,安用复来?死生常理,公还不懂吗?”遂起身向范稽首,复再次伏案而亡。过了一会儿,范仲淹仍然悲切着,尹洙又举头说与范仲淹,“亦无鬼神,亦无恐怖。”言毕,瞌然长逝不醒。
亦无鬼神,亦无恐怖。尹洙往返在死生道途,最后说给范仲淹的这句话,我以为是不错的。死没有什么可怕,滋味也没有什么不堪。
然而事有蹊跷。100多年的大清军机大臣赵舒翘的死,却没有这么轻松,他死得太难了,怎么都难咽下那口气。
今西安市长安区大原村出生的赵舒翘,字展如,号琴舫,晚号慎斋。他家世贫寒,细时即父母双亡,叔母董氏淳良,把他如同已出般养育成人。好在他极懂事,尤喜读书明理。乡绅柏景伟热心教育,办了所“学稼国”私塾,教书授业。赵舒翘的叔母省吃俭用,把赵舒翘送到柏先生的门下,成了先生最为喜爱的一位门生。16岁时,赵舒翘向柏先生写下“羽毛满,一飞上瀛洲”的宏愿,深得先生的厚望,随即出资送他去了西安城的关中书院深造。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赵舒翘26岁了,参加乡试高中后,旋即入京考试及进士第。翌年,27岁的赵舒翘再应礼部试,一举高中榜首,是为北方人难得一中的状元。
其时,同邑薛允升在刑部任职郎中。薛“精法学,卓卓无伦比,舒翘以同邑后进随允升后,公余问业,昕夕不倦”。因为他的好学,“潜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诵,凡与大小案件无不迎刃而解”。正是赵舒翘的诸多优势,四川东乡发生的袁廷蛟案,妄杀了数百无辜百姓,被时人谓之“奇冤”。1879年昭令重勘此案,赵舒翘受命勘理,报实为袁廷蛟们平反昭雪,川督丁宝桢等官吏被革职。这一时期,按现在人的话说,赵舒翘像坐在了火箭上,职务一升再升,先坐阵补提牢主事,再升福建司员外即,次年即迁升刑部郎中。
赵舒翘在刑部任职期间,不媚权贵,善察疑难案件,曾获朝野“西曹之英”的赞誉。他亲自调查、审理、平反了诸多民间冤案。其中至为典型的一例,是为声震当时朝野的河南“王树汶临刑呼冤”案。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八月,开封府刑场布置森严,刽子手刀光闪闪,将要处决一个标名为抢劫集团首犯“胡体安”的犯人时,五花大绑的犯人却拼命高呼,“我叫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开封知府唐盛仰闻言,当即下令停刑,并急禀河南巡抚涂宗瀛。涂旋即将此案转呈刑部。
这不是一件难察的案件,刑部郎中赵舒翘发下批文,命河南地方认真复查。然河南巡抚涂宗瀛调任湖北,新任李鹤年与河道总督梅启照,是两位奸滑的官场油条,他俩在查清冤情后,却唯恐连累自己受处分,便官官相护,四处找人活动,最终请出一位清室王公,转托藩祖荫游说赵舒翘,想要赵给予左袒。藩为清廷老臣,历任工部、兵部尚书,入值军机,最关键的,藩一向对赵非常启重,多有褒掖,赵是有情人,知道藩对他的恩望,然而,当藩祖荫来到赵舒翘的府上,明确示意赵要设法搪塞此案时,赵没有给藩祖荫面子,当面告诉藩,“民命至重,可迁就耶?其可去,此案不可移言。“在赵舒翘的全力督导下,是为15岁的幼童王树汶案大白天下,元凶胡体安一伙歹徒,以及受到重贿的镇平县衙里的差役头目等人,被捉拿正法。此案不仅救了王树汶一条小命,还使李鹤年与梅启照两位大员被革职,南阳知府王兆兰及以下县令二十多位贪官庸吏被惩处。
赵舒翘在仕途上顺风顺水的走着,很快坐到刑部尚书的高位上,并受慈禧太后青睐,入值了军机。突然地,以英、法为首的八国联军,假借开放中国口岸以利商易的口实,兴兵攻入北京城,迫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朝政府,经由宣化、大同、太原西行而来,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00年)十月十六日逃至西安。西安为赵舒翘的桑梓之地,赵陪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左右,一路回到西安。此其时也,陕西连年大旱,饥民甚多,地方官设“舍饭房”赈济灾民。赵舒翘在西安眼熟,耳目自然也熟,他听说主管官吏贪污赈粮,为补亏空,竟给粥饭里暗掺石灰。赵舒翘听得肝胆欲裂,当即索来一身破衣,假扮成饥民模样,混藉在饥民之中去领舍饭。掌勺小吏如狼似虎,对领舍饭的饥民呵叱有余,赵舒翘又岂能幸免,但他为了亲尝舍饭的滋味,恭敬歉卑地恳求了一勺。他当场喝了一口,即刻尝出石灰味,这便大喝一声,亮出自己的身份,并立即严查了主管官员和掌勺小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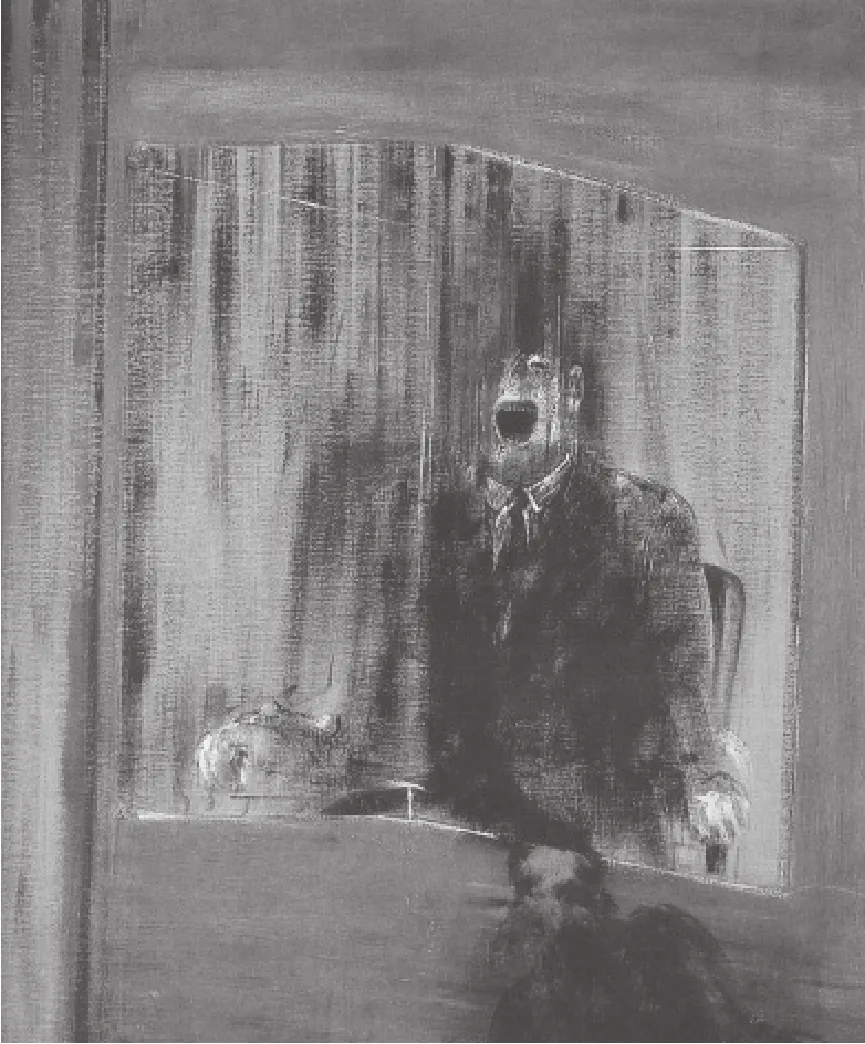
箱内的男子 培根 1949年 油画 147×130cm
西安的民众正颂扬着赵舒翘的爱民精神,忽剌剌几月过去,从北京城传来清政府留守代表李鸿章的书札,把刚毅和赵舒翘列为支持义和团灭洋的“祸首”,坚持处以极刑,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才肯罢兵,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才能西巡返京,坐回到紫禁城里的权力宝座上。
慈禧太后旨准了李鸿章的条件。因为刚毅在西巡途中,已于山西侯马病死,赵舒翘成了浇灭八国联军气焰的首恶之人,他是必死无疑了。
面对死的判决,赵舒翘开始并不担心他会死。赵舒翘是干什么的?他是主持刑狱的最高长官,即便依照联军的定罪条件,也不该判他死刑呀。因为1900年的夏天,义和团杀洋人并不是他主使纵容的。因此,在赵舒翘接到“斩监候”的圣意,随后押在西安的衙门里,他一点都不悲伤,他认为所以如此,只是朝廷向洋人做的一个样子,等洋人不穷追不舍,他就会被释放出来。关押了他一些时日,他倒比穿着刑部尚书官服时还要安神自若。
不断地有人探视他,其中就有他的家眷们,探视了他以后,不想走,就还受到了特许,住下来,陪侍在他身边。赵舒翘耳聪目明,大家探视他,不只给他说些模棱两可的安慰话,同时还要告诉他,陕北的民众甚为不服,这些天,不断有人向军机处为他请命,起初有数十人,后来有数百人,到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二(公元1902年2月17日),西安府城为赵舒翘请命的人竟已达数万之众。请命者有声言劫法场的,还有声言如杀赵舒翘,他们就即请太后回北京。军机处的大臣们,与赵舒翘平日相处都还不错,借势还入奏太后,来为赵舒翘的“斩立决”矫旨为“赐自尽”。
是年正月初六日,新任陕抚的岑春煊,接受朝廷的谕旨,前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巡西安临时设立的臬司,监视赵舒翘自尽。岑春煊当面向赵舒翘宣示了盖有光绪大印的诏书,赵舒翘依然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不仅他心存幻想,与他在军机处一同入值的大臣们,也还心怀着幻想,最后时刻,结伴求见慈禧。岑春煊不敢草率行事,就陪着赵舒翘在臬司坐等……他们等过了中午,等到了下午,差不多等到惨淡的太阳,把他羞涩的脸蛋枕在西安城墙的堞垛上,岑春煊不敢再等了,他陪着小心对赵舒翘说:赵军机,上谕在此,赐你自尽,要求下午五时回去复命,我求您了,您就自决了吧。
赵舒翘到了这时,才觉他的命尽了。
但是赵舒翘还愣愣地坐了一会儿,希望能有慈禧下来的新圣旨。他还想,他是慈禧宠信的大臣哩,军机处的同僚与他交情都不浅……赵舒翘自己幻想着,他深明大义的夫人却不再幻想了,她陪在赵舒翘的身边,轻声地给他说,“不会再来圣旨了,咱们一起死吧。“赵夫人语毕,即从身上拿出一包金子,他匀了一些给赵舒翘,他自己抢在赵的前头,把留给她的金子吞进肚子。
夫人的确命薄,吞金不久便命归西天。可是赵舒翘,吞金后没事人一样,像吃了什么激素类药物,亢奋得面红耳赤,朗声告诉身边人,应该怎样料理他和夫人的后事。他说着话,红红的眼圈还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来,他想起九十多岁的养母董氏来了,渧泪愧悔,“高堂老母,不能养其老,送其终,是今生最大的憾事!“监督在一旁的岑春煊,听他说话声音雄壮清晰,丝毫不像要死的样子,心里着急,就又命令手下取来鸦片给赵舒翘吃。赵舒翘大口地吃了,他在等死,等了三柱香的时间,依然没有将死的迹象,甚至连肚子要疼的痕迹都没有。岑春煊唯恐误了圣旨规定的时间,就还着人从大街上的药铺里买来砒霜,用水化开,灌进赵舒翘的嘴里。
巨毒砒霜起作用了,赵舒翘倒在了地上,他只觉口干舌燥,不停地大喝凉水,爬在地上翻来滚去,呼喊不止,说他太难受了。但不论赵舒翘怎么难受,他就是咽不下最后那口气,结果折磨得他脸庞肿大,手舞足蹈……恰其时也,慈禧指派李莲英来了臬司,这个冷血的家伙,把赵舒翘看了看,没好气地斥责岑春煊,“怎么这么慢?老佛爷等不及了。”李莲英的斥责让岑春煊大为慌恐,可是赵舒翘金也吞了,鸦片也吃了,砒霜也喝了,就是不能咽气,他还能有啥办法呢?
慌恐迷惑的岑春煊,那一刻竟迷信地想起他们家乡的一种风俗,族里人犯了处死的罪逆,用过三种死的方法,这人还不能死,就不能让他死了。不仅不能让他死,还要把他神仙一般供起来,好吃好喝……他不该死呀!阎王爷不收他。
岑春煊心里想着,就给李莲英说:赵军机不死你说怎么办?
李莲英对岑春煊是很看不上眼的,他瞪了岑一眼,怪声怪气地说:你想放过赵舒翘吗?洋鬼子放得过你吗?
岑春煊束手无策,急得出了一身汗。他手下一个尖嘴猴腮的小子,把他的嘴伸到岑春煊的耳朵边,给他说:小人倒有一个办法,把麻纸在烧酒里浸一浸,拿出来封住他的七窍,把他闷死得了。官场上不少这样的小恶吏,正事做不来,坏心思歪点子倒很多。尖嘴在岑春煊的耳朵上那么一咬,让黔驴技穷的他一阵窃喜,紧忙让人把赵舒翘横躺着绑死在一条长凳上,照着尖嘴猴腮的主意来办。那家伙出得了瞎点子,手上功夫却一般,两只手抖抖索索,揭上一页麻纸,在酒浆里浸过,便往赵舒翘的七窍上封,他如法封了一次,以为赵舒翘该咽气了,却不然,他还就是不咽那口气。尖嘴猴腮的东西因为心慌,手在抖索,脸也白了,牙齿在嘴里打着架,得得得,得得得,乱搅的舌头求起赵舒翘来:“赵……赵爷爷,求你咽气吧,我……我不敢再看爷爷受罪了!”
也不知尖嘴猴腮的求告起了作用,还是他一层一层的给赵舒翘的七窍上封麻纸,封到第五层时,赵舒翘才完全地闭上眼睛咽了气。而时间在滑动,到岑春煊伸手在赵舒翘的鼻根上,试探气息,确信赵已死去,他便虚脱似的坐回椅子上,抬眼去看臬司的窗门,发现长长的一个晚上已经过去,次日的太阳,仿佛血染一般,亦然照在臬司大院的一面青砖高墙上。
赵舒翘的死是冤枉的,他的死并非西洋人的压迫。时人鲍润漪著有《赵尚书被冤述略》的书,明确写到,瓦德西入住仪鸾殿后,在光绪帝的御案下发现了赵舒翘一卷反对利用义和团的密奏。翻译人员向瓦德西说明了情况,他迅即转送李鸿章,要他去电西安行在救赵。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只把瓦德西转来给他的赵舒翘奏折,在京城几位留守谈判的官员手上来回流转,以致误了时机,故而使赵罹难。下旨赐死赵舒翘的慈禧,后来内疚不已,多次同她左右亲信相谈:“惟赵舒翘不是他们(载漪、载勋、刚毅等)一派,死得甚为可怜。”慈禧每说一次,都要流一次泪。
赵舒翘的死又是艰难的,是比砍头还要艰难呢!
我不明白,同样的肉身凡胎,赵舒翘怎么就死得那么艰难呢?
责任编辑:胡晓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