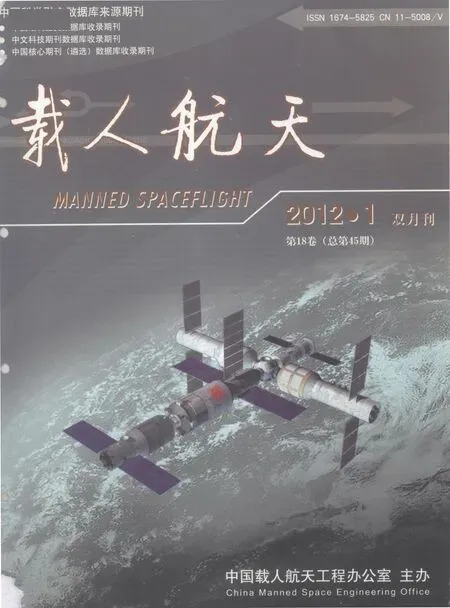论中国载人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法律环境
夏春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3)
1 引言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成就斐然,引发了主要航天大国媒体的一系列反应,有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赞叹和祝福,有希望扩大同中国合作的意愿,也有对自身优势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实施和首次无人交会对接圆满成功之后,世界更加关注中国的航天工程,国际合作会更加频繁;美国航天飞机终止服役,国际空间站于2020年达到设计寿命,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面临着较为有利的航天市场机遇和共赢的局面形势。中国一贯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坚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并主张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增进和加强空间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中、德两国合作的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即是这一原则立场的具体实践,也为今后我国载人空间站的国际合作创立了良好开端。
本文以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上的国际合作原则为基础,探讨与分析国际空间合作这一特殊国际合作形式的理念、现实与前景,揭示我国载人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法律环境,并以国际空间站的国际合作法律框架为参照,研究构建我国载人空间站国际合作法律框架的重要因素,为其他国家参与我国载人空间站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2 国际合作原则与国际空间合作的理念和现实
2.1 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的国际合作原则
自现代主权国家成立以来,冲突与合作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两种重要模式。《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明确将“促进国际合作”作为联合国宗旨之一。1945年以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对“国际合作原则”作出规定,并将该原则上升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例如,1955年亚非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就提到了“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的原则。1970年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确立了七项原则,其中第四项规定了“各国依照《宪章》有彼此合作之义务”。1974年联合国大会相继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指出“所有国家有义务个别地和集体地进行合作”,并把“国际合作以谋发展”规定为所有国家的“一致目标和共同义务”。从以上文件来看,国际合作已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加快以及环保问题、难民救助、毒品控制、恐怖主义等新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各国开始在反恐以及国际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开展大规模合作。但应看到,并非在所有领域的国际合作都取得了有效进展。著名国际法学者安东尼奥·卡塞斯指出,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合作主要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在农业与发展、环境保护、儿童福利以及人权保护方面较有成效,而在一些敏感领域——例如裁军和核不扩散,国防合作的成就最小。他认为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这些问题的决定权仍然控制在主权国家手中,而相互冲突的经济、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利益已经深深地使这些国家分化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政治分为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其中高级政治是指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而低级政治则是指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之间在高级政治领域里主要关注的是相对获益,这里充满了冲突,因此很难协调;而在低级政治领域中国家关注的是绝对获益,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对容易找到共同点,因此合作的可能性较大。非传统安全问题多为低级政治领域中的问题,易于谋求合作。
2.2 国际空间合作的理念与现实
2.2.1 国际空间合作的国际法
人类探索外层空间的活动始于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空活动被打上了冷战的烙印,外层空间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彰显国家实力的战场。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空间大国由对立转为适度合作。
最早规范外层空间活动的国际文件中已经提及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1961年联合国成立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并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外空和平使用之国际合作》决议,提及加强外空领域国际合作的迫切需要,但该决议主要是强调了联合国应在外空和平探测及使用方面成为国际合作的焦点,负责协调和协助有关空间物体登记以及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1967年生效的《外空条约》是外空活动的国际法基石,该公约第三条指出缔约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增进国际合作与谅解而进行;该公约第九条具体规定了外空活动的合作和互助原则,并指出缔约国进行外空研究和探索时对可能产生的有害干扰应负有进行国际磋商的义务,这是外空活动中国际合作义务的具体体现。1968年生效的《营救协定》对发射国与缔约国就航天员营救和外空物体归还方面的规则,表明了外空领域国际合作的进一步深化。1972年生效的《责任公约》以及1976年生效的《登记公约》所制定的规则和程序,也都有助于加强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1984年生效的《月球协定》除了再次确认国际合作原则之外,还在第15条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应查明其他缔约国从事探索及利用月球的活动确是符合本协定的规定,并为此目的,在月球上的一切外空运载器、装备、设施、站所和装置应对其他缔约国开放。”以公约条文形式,规定了缔约国的月球站所和装置应对其他缔约国开放的义务。199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还特别通过了《关于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并特别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宣言》(简称《国际空间合作宣言》),该宣言鼓励各国在公平和可以相互接受的基础上、采取最有效和适当的方式、自行决定参加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并要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由此看来,多个国际文件提到了外空国际合作原则。此处有必要对这些国际文件的效力作一分析。《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列举了几种重要的国际法渊源,分别是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和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家学说。一般认为,前三种是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渊源,而其中又以国际公约为最便于使用的国际法。《外空条约》、《营救协定》、《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月球协定》这五大外空条约对缔约国来说是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这些公约均不同程度地提及了国际合作原则。除了《营救协定》和《月球协定》为营救航天员和归还空间物体以及开放月球站所及装置设定了较为具体的国际合作义务之外,其他针对国际合作的规定较为概括,并未明确外空活动的国际合作的实体性或程序性规则,也未规定不进行合作的法律后果,可以说,这些规定多为倡导性的指南。而《月球协定》迄今为止只有13个成员国,主要航天大国均未参加这一协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协定的效力,也反映了航天大国对承担外空国际合作义务的保留态度。
2.2.2 国际空间合作的现实
自人类开始探索外层空间以来,不乏国际合作的实践。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以后,美、苏两个航天大国也开始进行适度的空间合作。目前,国际空间合作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各国通过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分委会以及其他国际平台,共同应对外空活动的新问题,比如空间碎片减缓等。
第二,成立区域性空间合作组织,协调区域性空间活动。例如,欧洲18个国家于1975年成立的欧洲航天局(ESA)通过其理事会制定空间探索计划、共同开展空间探索活动。再如,中国等八国于2005年成立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以期推动亚太地区空间科学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合作。
第三,通过双边或多边形式,在具体工程或项目上开展深入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空间站这一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空间合作项目,其法律框架不仅继承了现有联合国五大外空条约的原则和规则,又通过特有制度丰富了国际空间法的内容。
从我国的空间国际合作实践看,主要是与阿根廷、巴西等多国签署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协定和空间项目合作协议,与一些国家建立了航天合作分委会或联委会合作机制、或签署了空间合作谅解备忘录,与巴西开展地球资源卫星合作,与德国开展载人航天空间科学实验研究。同时,与法国在空间科学、卫星应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重要进展,还为其他国家提供整星制造与发射服务。通过具体工程和项目的深入合作,是目前国际空间合作的典型模式,也更容易取得明显的成效。
3 中国载人空间站国际合作法律框架的构建——以国际空间站法律框架为参考
3.1 国际空间站的法律框架
建设国际空间站的目的是探测、研究和开发空间,以美国和俄罗斯为首,包括加拿大、日本、巴西和欧空局(其中的11个国家)共16个成员国参与研制建设。国际空间站的成员国通过提供空间站的组成部分,获得对空间站一定的使用权。随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必将在更大领域和范围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因此,我国有必要了解国际空间站的法律框架,并提早筹划与其他国家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所应遵循的法律框架。
以国际空间站成员国于1998年在华盛顿签署的《加拿大、欧空局成员国、俄罗斯联邦、美国政府间关于民用国际空间站合作协议》(简称《协议》)为基本法,辅以成员国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系列执行安排和合同等,共同构成了国际空间站的法律框架。依据内容和发挥作用的不同,可将该法律框架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是现有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体系的规定。《协议》首先宣布其活动遵守国际法、特别是外层空间条约的规定,继承了《外空条约》关于外层空间无主权的规定;肯定了各成员国依据《登记公约》对其提供的空间站组件进行登记并由此享有管辖权、控制权和所有权;《协议》并未否认《责任公约》规定的两种责任形式,但是鼓励通过空间站进行外空探索、开发和利用活动。
第二是根据国际空间站实际情况所创设的特有制度。主要包括:(1)《协议》首次开创性地制定了交叉豁免制度,即对不同成员国(包括其相关实体)之间在参与“受保护的空间活动”时所产生的损害赔偿之请求给予责任豁免;(2)《协议》第22条规定,针对出现在国际空间站的刑事犯罪活动,一国除了可以行使属人管辖权之外,还可针对其他国家国民的犯罪行为同犯罪嫌疑人所在国进行磋商,而在犯罪分子所在国允许、或者虽未允许但在90日内未承诺将该犯罪嫌疑人送本国有权机关起诉的情况下,该国可以对他国的国民行使刑事管辖权,同时该国可以将《协议》视为引渡该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基础,这一刑事管辖权的创新突破了原有国际空间条约仅规定对空间物体的管辖权和控制权的规定,是载人航天活动催生的法律制度;(3)《协议》第21条为保护知识产权,将在空间站各组成部分上进行的活动视为在该组成部分登记国领土上进行的活动,从而符合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以及有关国内法律的规定。
第三是成员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及规范国际空间站人员行动的《行为守则》。谅解备忘录是处理较小事项的条约,对签署国也有法律约束力。
第四是更为具体的执行安排以及成员国之间、或者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以及私营主体之间签订的一系列使用空间站的合同。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际空间站项目具备了一套完备、但并不算复杂的法律制度,这套法律制度既继承了现有国际空间条约的规定,使参加国在空间站法律下的权利义务与其在外层空间条约下的权利义务保持一致,又切合实际地发展了新的法律制度来应对国际合作的需要。这套法律制度的构成,既有总括性的基本法、从而保证重要制度的基础性地位,又允许更为灵活多变的谅解备忘录、双边协定和合同的存在,满足了各参加国空间探索活动和国际合作活动的需求多样式。《协议》作为契约型多边条约,有序地指引着成员国参加空间站的活动。
3.2 中国载人空间站的国际合作法律框架构建
中国载人空间站的法律构建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内层面的载人空间站法律,主要规定空间站的建设和管理主体及管理机制,国内参与者、参与方式和活动内容,以及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融资、保险等一系列制度;第二个方面中国载人空间站的国际合作法律框架,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在未来载人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当中,国际合作不可避免,而法律框架的构建有助于我们在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实现共赢。
构建中国载人空间站国际合作法律框架,应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首先,应承诺遵守我国已经加入的主要联合国外空条约(《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营救协定》)的规定,并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础。但同时在一些敏感和关键问题上,要把握主动权。比如,《外空条约》规定缔约国应专为和平目的使用月球和其他天体,并承诺不在外层空间设置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学者将这一规定笼统地解释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原则,但是对于何为“和平利用”,各国有不同的解释。《协议》将国际空间站定性成为和平目的而设的民用空间站,但是对于在某个空间站组成部分上进行的空间探索活动是否符合和平目的,由提供该组成部分的成员国决定,这一规则给空间站组成部分的提供国以一定的主动权。我国载人空间站的建设让一些国家怀疑我国将对空间进行军事利用,因为这些国家可能误认为中国的太空计划“实际上是由人民解放军主导推进的”。其实,其他许多国家的太空活动均有军事人员参与,这并不意味着有关太空活动就成了对外空的军事化利用,何况《外空条约》也“不禁止为了科学研究或任何其他和平目的而使用军事人员”。但尽管如此,对于诸如“为和平目的之定义”等敏感问题,在构建载人空间站国际合作法律时,我国应掌握定义的主动权。
第二,应根据我国允许外国参与我国载人空间站建设和使用的程度和范围,同时考虑外国参与的意愿与能力,来设计我国载人空间站国际合作的基本法。从宏观方面,该基本法应定明此种国际合作的前提、原则、重要决策规则和程序;从微观方面,应规定载人空间站的管辖权、可独立区分的空间物体的登记管理办法、在空间站进行实验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等具体问题。基本法的设计可以参考国际空间站的法律框架,但同时必须注意到国际空间站的建设模式与我国载人空间站的建设模式的不同,应在充分维护我国权益的基础上,设计国际合作的各种基本原则。
第三,可以通过双边协定或者谅解备忘录形式,与有关国家开展具体合作。对与神舟八号飞船上中德合作项目相类似的活动,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其特点是更为具体、灵活。
第四,应考虑到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外空商业化利用的趋势,法律设计应具有前瞻性。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为促进以空间资产为担保进行融资,正在起草《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2011年2月第五次专家委员会会议之后形成的草案文本,将提交给2012年2月在柏林召开的外交会议,以便讨论通过。目前看来,中国以及其他航天大国很有可能会批准这个议定书,该议定书会在很大程度上便利卫星、空间站、太空舱、指令舱以及其他可独立识别的航天器或者有效载荷等高价值空间资产的跨国融资和流转。中国在设计国际空间合作的法律规则时,要考虑到该议定书的影响,并作出有效应对。
4 结束语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以及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增进和加强空间领域的国际合作,一直是我国政府在航天领域的政策和立场。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后续研制建设过程中开展s国际合作符合上述原则,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国际合作原则不仅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外空法上的重要原则。若仅作为一项倡导性的原则,国际合作并不难被各国所接受。然而,通过多边公约、在一般意义上设定更为具体的合作义务的动议,则很难获得广泛支持,主要航天大国拒绝加入《月球协定》就是一个明证。国际合作原则的实现首先取决于国家的意愿,其次则需要在具体航天工程中推动规范合作的法律框架的构建。国际空间站完备的法律框架为国际空间合作提供了良好范本,中国载人空间站项目应及时筹划国际合作层面的法律框架,在遵守主要外空条约的基础上,根据各国的参与程度,设计以我国为主导的空间合作的基本法来规范空间合作的一般性重大问题,并辅之以双边合作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来规定具体合作内容。空间合作的法律既要适应现实需要,又要具有前瞻性,特别是应对日益发展的空间商业化利用的要求。 ◇
[1][意]安东尼奥·卡塞斯.国际法(蔡从燕等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He Sibing.What Next for China in Space after Shenzhou.Space Policy[J].2003-19(3).
[3]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贺其治.外层空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5]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7]王秀梅.论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合作原则.世界经济与政治[J].2005(7).
[8]夏春利.论国际空间站的法律框架与国际空间合作立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0(5).
[9]赵长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探微.现代国际关系[J].2005(1).
[10]中国科学院空间领域战略研究组.中国至2050年空间科技发展路线图[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