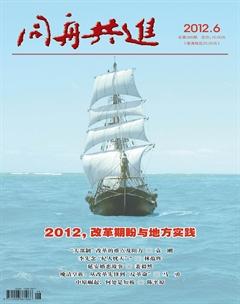“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及阻力
袁刚
“大部制”改革遇到“官僚制顽症”
我国改革起步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推行?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已大力推行了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起步甚至比?改更早。邓小平早在1981年1月就说过:“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30多年下来,政府上下推行了好几轮以“精简机构”为内容的改革,2007年中共十七大更提出“大部制”的改革目标,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大幅压缩,改革的雷声一直很大。
不能说改革没有取得成效,但因触及长时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既有利益格局,涉及众多官员干部的饭碗钱袋,改革阻力很大,多有反复,有的甚至流于形式。很多地方是机构减了人不减,不减和尚只拆庙。近日爆出某市的大部制改革,?来的局长们在合并后的大部统统挂名副局长,以致有的局竟然有副局长19个。有主管编制的领导表示,这是大部制改革“过渡”时的“合理”现象,由此引发民众热议,被斥为“假改革”。
“假改革”的说法我并不赞同。行政改革30年来上下几乎没停顿过,邓小平、朱镕基等改革家对机构改革决心很大,出手很猛。朱镕基任总理时,甚至表示“就是地雷阵也要闯”!他主持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制止住“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大幅裁减合并重组了中央政府机构部门,取得了很大成绩。
然而,精简机构中央相对好办,裁减下来的官员可以下到地方,有些部门甚至想出了公家出资送年轻部员到高校读研究生的“妙着”,使精简预案得以完成。但地方上尤其是县市基层政府就难办了,机构减了官员没地方转移,人头硬是减不下来。在中国,工人可以下岗吃社保,干部却没有下岗一说,尤其是带“长”的,岗位裁减了,官号待遇等却一点也不能减,于是就有了上述一个局十多个副局长的“大部制”现象。
其实,这种情况在全国非常普遍。?也不敢怠慢当官的,只得广设副职,百般优宠,等他们年老退休以作“过渡”,这反映的其实就是“官僚政治”之顽症。即英国政治学家帕金?(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所描述的官场病,部门都会有部门利益,且有无限扩张的倾向,官员为自身利益而抵制减员、抵制改革,此乃世界性难题。
“大部制”其实是历史传统和国际惯例
等级官僚制顽症,正是苏联政治?济体制的主要特征。苏联建立之初,第二国际工运领袖考茨基、卢?堡等人就对它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苏联体制被称为“国家官僚制”。
毋庸置疑,我国建国之初就全面移植了“老大哥”苏联的政?体制,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则搞苏式“灌输”,高校也按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等。总之,是全方位移植,按照新儒家的说法,是“全盘西化”。现在我国上下都已深刻认识到苏联计划?济的弊病,但对其他方面的弊害,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实,苏联模式在政治行政等方面也很落后,我国盲目移植吃了很大的亏。“大部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剔除苏联模式,借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长处,为我所用,与国际接轨。
苏联“国家官僚制”,乃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各方面都设衙门、设官进行管理,高度集权。结果是干部多、衙门机关多,形成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骑在人民头上,工人农民并未真正得到“解放”。托洛茨基很早就敏锐地看到干部官僚化问题,列宁更痛恨政府机构的无限膨胀,临终前口述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提出精简国家机构,指出:“要尽一切可能撤销各种委员会,阻止成立各种新的委员会,因为其中十分之九是多余的。”但苏联虽多有机构调整,却一直未能阻止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中央政府部级单位发展到上百个,1982年有110个,到苏联解体前夕,全国各类干部总数已达2100万人,占总人口的1/14。各机关领导多、副职多,有的部副部长达十多个,机关中带“长”字号的职位竟占到干部的1/3,出现了严重的官场病和腐败现象。
反观我国历史,古代历朝政府衙门其实规模都不大,秦汉有“三公九卿”,隋唐是“三省六部”,及至清末包括宫廷服务、监察等“部级”机关,也从未超过20个。行政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乃承袭《周礼》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前后行用约3000年,其实就是“大部制”。
近代戊戌变法,康有为提出以“十二局”取代“六部”。清末颁行的“皇族内阁”是: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等10个部。辛亥革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9个部,北京临时政府是11个部。此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虽多有变换,中央部门也一直是10到20个之间,实行的也是“大部制”。
再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大部制”更是常例,部级单位一般不超过20个。如美国长期保持14个部门,英国则在18个左右,法国约15个,日本现在是13个。苏联解体后建立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也只有17个部,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都实行“大部制”。
“大部制”古今中外的政府都行用,说明它并非什么新鲜玩意。这是国际惯例,又是历史传统。唯独苏联以及移植苏联模式的国家,才不搞“大部制”,反倒是异数。历史已证明“国家官僚制”是一个失败的体制。
我国建政之初就学苏联,1949年政务院设部级机构35个;1953年增为42个;1954年成立国务院,扩充为64个部门,1955年激增为81个;后反复下放调整,但减了又增,增了又减,减了又增,形成“怪圈”。到“文革”时有76个中央部门,1981年终于达到100个,以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成为改革的重点对象。此后30年“精简机构”搞了八九次,也是反复增减,中央下了很大力气,向“官僚主义”顽症开战,要突破“历史怪圈”。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名义上是27个,但仍显其多,仍要改革压缩到20个以下,以便尽快与国际接轨。
“大部制”改革留不得死角
“中国特色”在于创新,但仍有不少人士,感情上放不下苏联政?体制,甚至留恋计划?济,认为其总体优越性是“集中国力办大事”。
铁道部可谓我国政府保留的苏联计划?济模式的最后堡垒,不仅党政企不分,还学苏联拥有自己的“公、检、法”,垄断?营,衙门积习深重。历?多次机构改革包括“大部制”改革,铁道部竟能纹丝不动。这就使“大部制”改革留有死角,使改革不能彻底。
“国家官僚制”对于推进苏联工业化,起初也曾起过重要作用,用行政命令主导?济,也的确办了许多大事。我国上世纪引进苏联模式,很快建立了一整套工业体系。这也使得改革之前,我国政府机构异常庞大,光工业主管部门就达20多个。机械工业部就有第一到第八,简称“一机部”、二机部??另按类还分有化工部、石油工业部、冶金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等,都是学苏联。苏联甚至党也搞“工业党”、“农业党”,党政企不分,坐办公桌不事生产的干部多如牛毛。然而,以上所有二十几个工业部,还包括商业部、外贸部等,在日本就一个“通商产业省”,官员数只有其百不到一,效能却超过中、苏工商各部之总和。它引导了战后日本?济起飞,相比之下,“大部制”显示出了更大的优越性。
2011年温州“7•23”动车追尾?覆事故,彻底摧毁了苏式铁道部无须改制的神话。高筑债台修铁路,部长刘志军和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却爆出特大贪污案,这更凸显铁道部高度集权、暗箱操作的弊端,说明“大部制”改革留不得死角,政企要分开,铁道部应拆改归并于交通部。
上世纪70年代,以香港为基地的“世界船王”包玉刚通过市场运作,竟使其商船吨位运力超过了苏联全国,而其上面却并没有多少官僚机构和政府官员管他。前苏联光农业方面就有管理干部300多万,而美国全国农业工人也不过此数,生产的粮食却比苏联多得多。苏联官僚化的集体农庄办了70年,其粮食产量竟没有任何一年能达到私有制下的1913年的水平。管理并非设官越多、机构越多就越好,少而精干反倒更有效能。政府无须管琐碎的微观细部,而只需作宏观政策调控。
改革没有回头路
“大部制”是行政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启动并持续30多年的以“精简机构”为内容的多次改革的继续及归宿。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以破除机构重叠、职权交叉、政出多门等弊端。
前述机构归并造成副职过多,设十多个副局长的情况,在苏联也很普遍,但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欧、美、日等国行政体系有政务官、事务官的严格区分,事务官即文官,最早创制于英国,即我国的公务员。公务员抱案牍做技术性服务性工作,政治中立不随党派去留,具有稳定性因而是“铁饭碗”。政务官即带“长”字号可拍板定策的人,他们随党派去留,上位需要竞争,一旦去职就要自谋出路,国家并不包养。
那我国为什么不区分政务官、事务官呢?这就牵涉到政治体制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也搞了公务员制度改革,近日政府有发言人声称,我国全部公务员只有700万人,但鲜有人相信。因为界限不清,不仅区分不出政务官、事务官,而且党政不分,还有其他一系列“干部”等,全由国家财政供养,仍遵?着固有的苏联模式。那如何能知道?是公务员,?不是呢?700万只是政府系列干部,但他们可以和“事业单位”甚至法院干部互调,职级待遇差不多,或者抽调至“党委”,或者调“工、青、妇”吃清闲。改革不彻底使许多问题被官话所掩盖,而一旦拆并机构搞“大部制”,官场病又浮出了水面。
我国古代就有官和吏的严格区别,官的选拔有科举,虽不像当今政务官那样随党派去留,但抱案牍的刀笔吏则有如当今公务员,稳定地从事文案事务性工作。而我国从苏联引进的干部体制却含混不清,分类不明,教师也曾是“干部编制”,官和吏没有区别,更遑论政务官、事务官的区分。当官仍然是终身职业,官满为患,官场病“帕金?定律”依然盛行,各部门部分官员追求自身利益,“三公消费”居高不下,使行政成本高企。官场上、职场上由国家财政供养“吃皇粮”的人始终减不下去,冗官冗费一直十分严重;官场官僚主义积习未除,监督机制缺位,这些都需要改革才能解决。
所以,与行政“大部制”改革配套,必须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行政改,如党政分开,分清干部类别,厘清公务员编制,制定政务官的选拔与退出规程,事业单位转型,“群众组织”真正归群众,扩大社会自治空间,加强监察监督机制等。而更重要的是,应大力声张民权,在宪法框架下,摆正官民、党群关系,扩大民主,加强法治。只有政治清明,行政才能顺畅。
“大部制”改革还要清除观念上的障?,解放思想,反思历史,深刻认识“全盘西化”移植苏联模式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彻底摒弃落后的苏联政?体制干部制度,回归常规与国际接轨。中国向西方学习已有百余年,学习要择善而从,必须立足本国实际,才会有成效。
“大部制”不能包医百病,若不因时因地权变,改革也会“僵化”。如中国古代的行政“六部”,虽行“大部制”,却几千年因袭不变。儒者说是周公“制礼作乐”所定,以《易?》象数来设官分职,将其圣化意识形态化,造成政府运转不灵。唐代中期即因僵化的“六部二十四司”脱离实际,只能随事补苴临时设“使”以相补救,如青苗使、转运使、节度使等,结果形成极不规整的“使职差遣制”,?有政府行政系统几乎崩溃。后元、明、清虽也遵《周礼》不改“六部”,但部以下的司、科机构却因时因地大有增补,使行政“六部”勉强维持到1906年。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大部制”改革要破除意识形态的桎梏,既要反对僵化,也要反对盲从,要按照中国国情,做好“顶层设计”。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阶层及既有利益格局,会有强大阻力,但“大部制”改革方向是对的,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不改革还会出现新的“僵化”,遗患将更加可怕。在认准了目标之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应排除一切阻力,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大业。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