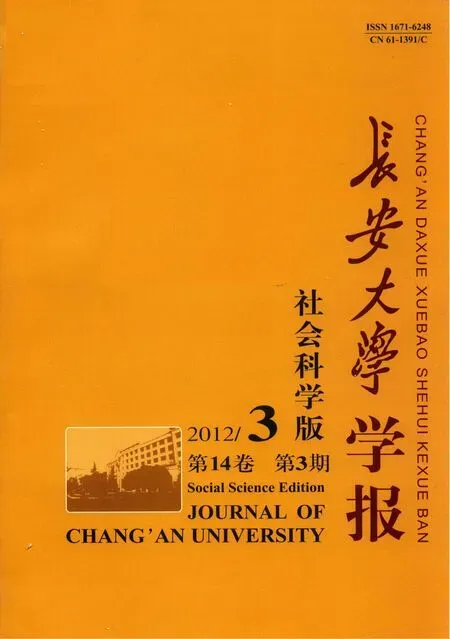基于问题生成语境的法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解读
庞海峡
(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基于问题生成语境的法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解读
庞海峡
(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从法确定性的问题生成语境出发,对理性与法律确定性联盟建立及破裂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分析认为:法的确定性问题是理性危机在法律领域的必然逻辑推演;拯救法的确定性,需要在理性反思“理性”的基础上,赋予法的确定性以新的时代内涵,应清醒认识中西问题语境的差异,确立对中国法治“坚守中适度超越”的应有态度。
法的确定性;法的不确定性;理性;问题生成语境
问题总是以问题域的存在为前提的,思想总是以思想的泥土为根基的。法的确定性问题是20世纪以来西方法学领域一个重大的理论热点问题,几乎所有的法学大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一问题的争论之中。中国的法学者们也在积极跟进。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法的确定性或批判或解构或捍卫,并据此形成对中国法治的不同评说。然而,发端于西方的这场大辩论有其特定的问题生成语境。理性地参与这一话题,辨清问题争论之实质,发现问题争论之中国意义,避免语境错位的单向度思维,我们需要从问题的生成语境出发。
实际上,法的确定性问题并不是法学领域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和西方哲学领域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论传统所遭遇的确定性问题、理性危机问题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它就是后者问题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者在法律领域里的一个必然的逻辑推演。因此,对法确定性问题的理解和探讨,离不开理性这一广阔的话语背景。笔者系统梳理了理性与法律确定性联盟建立及破裂的演变过程,以期在理性反思“理性”的基础上,赋予法的确定性以新的时代内涵,并进而确立我们对中国法治的应有态度。
一、法的确定性的确信
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俞吾金教授将哲学划分为知识论哲学与人本主义哲学,并认为近代西方哲学主导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在知识论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知识论哲学是一种以寻求客观知识、真理性认识为宗旨的思想方式。在知识论哲学中,探索知识的“确定性”是其基本命题和目标追求,而理性主义是知识论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
作为西方精神的特质,早在希腊哲学诞生之际,理性的因子就深深根植于其中并成为古希腊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拉图的思想更是古代希腊理性主义的典范,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我们的感官能够接触到的现实世界。他认为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不真实的,强调理性是通向理念世界的惟一道路,从而确立了理性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不仅最早提出“人是理性动物的命题”,而且通过建立相应的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则,使理性具有了特定的思想形式。从此以后,知识论哲学、理性的观念也就深深扎根于西方的语言和逻辑中,甚至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家也概莫能外。不过,在基督教思想中,信仰被引入知识论体系并且被赋予高于理性的地位,人们对事物的领悟被导向神圣的迷思和神秘的内心体验中。但理性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不过这时的理性不再是人的理性而是神的理性。
启蒙时代思想家借助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高举理性与人性的旗帜,把人的理性视为人类生存的最终依据或者本质特征,当作一切知识的最后标准,成功地将神学驱逐出自然科学领域,将理性从神那里交还给人类并使之牢牢确立。从思想方法上看,近代启蒙思想家基本上抛弃了17世纪以前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的方法,代之以分析、还原、理智重建的建构论思维,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和思想方法的实证性、经验化,是近代哲学显著的思想特征[2]。
知识论思想传统和人的理性能力重新启动,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现和发展,而近代科学的发展又给了知识论思想传统和人的理性能力以有力的支持。科学是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近代科学技术是人类运用其理性的思维和活动,来理解并支配其生存世界的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尝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和宇宙间万物有规律可循,通过探讨和掌握这些规律可以过一种确定性或者有秩序的生活。这种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确信从此变成了一种强势话语,并最终走向理性的极度自信。现代社会成了全面理性化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知识论思想和理性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代。
这种极度自信深深地影响着近现代法律,法律借助理性获得突破性发展并藉此与理性结下了牢固的联盟关系。人们确信,不仅自然界存在人的理性能认识和把握的确定客观的东西,而且人类社会、人际之间依然也有其自身的存在规律,人类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去发现这种普遍的正义准则,而且能够通过严谨的科学作风和执着的理性精神去建构一个适合现实世界的包含完美法律体系和法律控制极致的法律世界。在这个法律世界中,法律的逻辑是统一的,法律的形式是完美的,法律的内容是确定的,法律的适用被认为是机械的、形式主义的,法官根据抽象的规则进行形式逻辑推理,从而得出确定的、惟一正确答案的判决。在这样一种认识观念的主导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确定性法前所未有的强烈诉求下,法的确定性在启蒙时期以后的资产阶级法治实践中逐渐成熟和制度化,人们甚至把它们提升到一个无可辩驳的高度。
二、法的确定性的怀疑
在理性主义一路高歌猛进、从自信走向自负的同时,在法确定性被空前绝后地牢固确立之时,颇为吊诡的是人们却越来越感觉生活在一个无限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科学的发展、知识的膨胀并没有因此而根本地解决人内心深处的恐慌和不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反而使社会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生活中难以把握的非理性因素越来越多[3]。与此同时,科学上一系列的进一步发现也使人们对确定性的信念发生动摇,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挑战了关于事物确实可知的定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又使客观性概念和因果概念受到冲击,玻尔的互补性原则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的决定论世界观[4]。当种种过去被人们无视或忽视的生活世界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令人震惊地渐次被掘抛出来时,思想界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了对理性的严肃反思。在反思与批判大潮中,与知识论哲学相伴随的人本主义哲学发出了挑战的最强音,尼采明确批判西方思想中对普遍性与永恒性的追求,他甚至认为,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导致了西方精神的堕落。作为尼采思想传统的承继者,后现代主义者更是对现代性的社会问题、对理性主义的绝对性、普适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甚至解构,他们致力于瓦解一个又一个理性主义的宏大建构,深入揭示在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掩盖甚至压制之下的各种社会内外矛盾。
在理性遭到怀疑、批判乃至颠覆的思想背景下,人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拆毁法律与理性之间的联盟,进而对作为现代法最主要特征的,也是现代法治基础的法的确定性发生怀疑。
首先扛起怀疑法律确定性大旗的是20世纪初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法学派。藉此,法的确定性问题成为法学理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现实主义法学派从法适用的过程入手进行解析,他们认为不仅法律适用者判决依据的渊源是复杂多样,而且法律适用者本身也具有复杂品性,因此,“人们只能极为有限地获得法律的确定性,对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要求总是不能获得满足……认为法律是或可以是稳定的、确定的这一观念并非理性的观念,而是应该归入虚幻或神话范畴的观念”[5]。法律现实主义运动之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批判法学继续对法律的确定性发起猛烈的抨击。他们复兴、修正了法律现实主义者的批判观点,借助语言学和解构手段,力图从文本和认知2个方面,对法的确定性进行釜底抽薪似的攻击[6]。批判主义法学家提出基本矛盾理论、特殊的矛盾结构以及法律推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等观点,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法确定性的信念。后现代法学通过消解自治的、有自觉意志的理性主体,对法的确定性话语更是进行了彻底和完全的解构与颠覆。后现代法学不仅否认被批判法学批判的惟一的、正确的法律答案传统认识,还否认与此相关的法普遍性、同一性、基础性、客观性等一切法确定性因素,取而代之以非基础和非本质的、多元性的、地方性和局部性等不确定性观念[4]。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对法的确定性所做的质疑尤其是否定,对于法律来说,几乎是根本性的和颠覆性的。在日趋壮大的怀疑与批判声中,作为现代法最主要特征之一的确定性从牢固树立的极度自信到被怀疑,甚至最终走下一统天下神坛的命运也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可能了。
三、法的确定性的理性解读
从理性与法律确定性联盟建立及破裂的过程可以发现,法的确定性成为问题而提出,其原因实际上并不仅仅在于近现代法律本身,更是在于作为近现代法律哲学基础的知识论传统、理性主义正在面临挑战。这种挑战虽然直接面对的是意识形态化的科学主义,但是,由于它揭示了理性内在的矛盾,拆毁或者动摇着支撑现代法治大厦的伦理、心理以及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现代法治、法的确定性的命运岌岌可危。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在理性反思理性的基础上,对法的确定性予以重新定位,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辨清法确定性问题在中西不同问题语境不同意味的基础上,确立我们对中国法治的应有态度。
理性的局限性或许意味着人类社会不可能产生一部完美的、包罗万象的解决未来社会所有问题的绝对确定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就应当产生绝对确定的法律,或理性不能产生相对确定的法律以及法律因相对确定就丧失了其确定性的品格。
第一,从应然意义上,人类并不需要这样一种绝对确定的法律。人的需求是多向度的,人类既有对确定性的需求,以期获得安全感和降低交往的成本等;人类也有对确定性的抗拒,人性渴望多样性、丰富性和变化性,从而难以容忍由确定性所导致的单调、机械和刻板[7]。在人类的多重需求之间,不能武断地认为确定性的价值就是惟一的或最为重要的价值,从而要求法律应当绝对确定。另外,法律是人类基于过去的生活而创立的理性秩序,绝对的确定性意味着绝对的秩序,以过去的认知成果绝对僵化地约束奔腾向前的当下社会生活,对人类来说未免不是一种法律的专横。理性从本质而言是不完满的,难以创造绝对确定的法律,即使理性是完满的,人类也难以接受一种绝对确定的法律。因此,不应把理性的危机看成确定性的灾难。
第二,理性的危机不意味着理性无能,有限的理性能够产生某种相对确定的法律,相对确定的法律依然能够满足人们确定性生活的需要。实际上理性的有限性、法律的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哲学上也是容易证明的命题。从纯粹逻辑的意义讲,真理都是有限的,人类的知识都不是绝对可靠的,所有的确定性本来就是相对的。不过,“理论含有纯粹性,而实践则总是一定度上的东西”[8]。纯粹逻辑上终极意义的知识的不确定,并不排斥其“语境的”确定性,或曰“历史的”确定性。法的现实不确定程度远没有理论家拿着放大镜观察的那样夸张,实践中人们对法的确定性的确信也没有因哲学上对确定性的颠覆而荡然无存。我们之所以习惯性地、不加验证地相信某些判断,坚持使用这些确信,并非它们事实上确定不移,而是因为相信它比不相信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助益或避免更大的麻烦[9]。
第三,法律不绝对确定并不意味着法律就不确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确定性的理解。如果认为法律的确定性就是指法律一望可知,法律文本含义的绝对精确性或法律问题答案的惟一性上,那么我们会失望地发现,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法律确定性。因为,不仅法律的语言载体即文本本身不可能是确定的,而且法律运作过程中人们对文本的解读与推理也充满语境或主体等各种因素歧义,如果再考虑到理性有限这样的重大因素,这种绝对确定性的理解不仅是稚嫩而且是苛求的,从价值上看也未必正当,我们对这种确定性的追求在现实中会处处碰壁。因此,时代变迁昭示我们,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识不能固守传统话语而一成不变,我们需要在理性认识理性的基础上,寻找关于法律确定性的当代话语体系,给予“法律确定性”涵义以新的内容。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足以对付实际生活的确定性”。而不再是那种基于极度自信理性的终极意义上的实质确定性,这种“足以对付实际生活的确定性”不是绝对的,但也不是漫无边际无法把握。司法裁判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或大致范围的确定性。这种“足以对付实际生活的确定性”是对主观恣意的否定,对法治则是从终极意义上实质确定性的追求向法律运行客观性追求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新时代的新要求,也是法治及确定性原初意义某种意味的回归。
第四,我们在理性认识理性,探究法确定性新的时代涵义时,还要清醒体察法确定性问题在中西不同问题语境中的不同意味。西方社会对法确定性的怀疑是在文本和理性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形式主义法治因素已经沉淀到法律文化的最深处而无可动摇,并且法官的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也已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他们完成法治使命的背景下展开的。他们对理性和法的确定性的质疑更有助于法治的完善和社会的前行[10]。然而,理性主义在中国并未经历同样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尚处于现代化的正在进行时,社会主体对法治的态度并未完全达到某种程度的同质化,法治的自我内化并未在社会层面达到某种的完成,因此,现代化的语境中对法确定性的普遍追求依然应是我们当前的核心要务。如果盲目以西方现阶段的法学思潮甚至是社会生活作为分析法律问题的参照系,将陷入某种语境错位的单向度思维程式。这种程序下对法确定性的过度质疑或许会成为我们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阻力。
四、结语
总之,对于同时处在现代与后现代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来说,适度超越法确定性的现代性阐释,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然而,超越是为了坚守,为了更好地坚守,坚守更高层次上的法治理想。
[1]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葛洪义.法律与理性[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王国龙.法律方法:问题与语境[C]//谢晖,陈金钊.法律方法: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12-145.
[4]朱继萍.论不确定性对法律的基本建设作用[J].法律科学,2006(2):10-16.
[5]Jerome F.Law and modern mind[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9.
[6]刘星.法律是什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7]李琦.法的确定性及其相对性:从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J].法学研究,2002(5):24-41.
[8]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M].刘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9]姜峰.在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法理学问题随想[C]//谢晖,陈金钊.法律方法: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84-299.
[10]贾敬华.确定性的法向客观性的法的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planation to legal certainty and its uncertainty from the view of context situation
PANG Hai-xia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Chang'an University,Xi'an 710064,Shaanxi,China)
This pape,in view of the controversy about legal certainty,studi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eason and legal certainty.An in-depth analysis contends that the crisis in the field of law is an inevitable kind of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risis.Therefore,to secure the certainty of law,the endeavors should be made to imbue the legal certainty with new epoch connotations in the light of reflections upon the“human reason”,whereas there is a need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ntext for the legal certainty questioned and to hold on to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 rule of law in moderate measures.
legal certainty;legal uncertainty;human reason;context situation
D90
A
1671-6248(2012)03-0071-04
2012-04-09
庞海峡(1973-),女,河南洛阳人,讲师,法学硕士。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