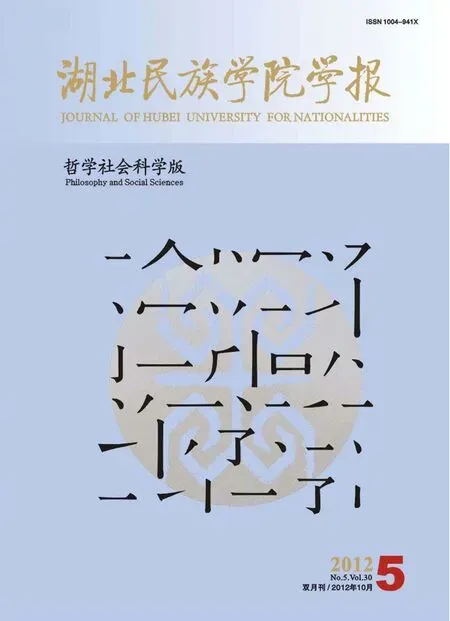论诗史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以唐代咏哥舒翰诗为例
马海龙
(1.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 710062;
2.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 810007)
论诗史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以唐代咏哥舒翰诗为例
马海龙1,2
(1.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 710062;
2.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 810007)
诗与史间既有互证性,又有差异性。以唐代咏哥舒翰诗为例,唐诗中的哥舒翰呈现出二种不同形象类型:一,骁勇善战,保国为民的沙场英雄;二,黩武穷荒,贪功好胜的军中败类。而唐史中的哥舒翰则是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民族英才。这种诗与史间差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背景及心理因素。它是诗人深受儒道两家“中和”与“不争”思想影响的产物,是唐玄宗后期社会历史背景在边塞诗中的折射,是诗人在不同境遇和心理下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可见,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诗史互证不等于对号入座。
唐代;诗;史;哥舒翰;差异;原因
“诗史互证”是目前学术界颇为推崇的一种治学方法。所谓“诗史互证”,汪荣祖先生说:“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批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1]但实际上,其中“诗”的内涵不仅限于诗,而是中国古代的词、小说、寓言、文论,乃至政论文章,均可包括在内。换言之,举凡古代文学作品均可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卞孝萱先生说:“文学作品是文人心声的反映,从一个人的诗词小说可以看见这个人的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造成了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的种种心态,这在史书中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得出来,何况史书中有粉饰,有隐晦,有曲笔,不可都信,有赖于利用史书以外的材料进行比较、判断。可见,文史互证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2]因此,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治学传统,加强文学与历史间的相互结合,以文学佐证历史、借历史审视文学,高度拓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阐释空间。但是,也应该看到文学与历史间的差异性,绝不能将文学作品简单地视为历史事件的图解,更不能在诗史互证中过于求深坐实,对号入座,而是力图挖掘诗史差异形成的原因,这是今后诗史互证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难点。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唐代咏哥舒翰诗为例,略论诗史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以期为中国文学研究者乃至历史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唐史中的哥舒翰
据《旧唐书》哥舒翰本传载:“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父是突厥,母是胡”,“倜傥任侠,好然诺,纵蒱酒”[3]可知哥舒翰是我国历史上名垂史册的少数民族将领之一,在草原文化影响下,他的身上具有粗犷豪爽、任侠仗义的民族性格特征。又据《新唐书》哥舒翰本传载:“翰能读左氏春秋、汉书,通大义。疏财,多施予,故士归心”[4]可知哥舒翰又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为人深明大义,重利轻义。因此,可以说哥舒翰是唐代社会多民族、多文化融合互通的典范。就文化修养而言,哥舒翰能读《左氏春秋》、《汉书》,可见其曾受很好的儒家文化教育。这一点,亦可从其文学作品《破阵乐》得到证明。其辞曰:
西戎最沐恩深,犬羊违背生心。
神将驱兵出塞,横行海畔生擒。
石堡岩高万丈,雕窠霞外千寻。
一唱尽属唐国,将知应合天心。
这首六律,《全唐诗》未见收录,仅见于敦煌伯3619唐诗写卷。盖当时仅流传于西部边塞,鲜为人知。[5]其艺术水平虽不堪与唐代著名边塞诗人之作品媲美,但笔力遒劲,语言朴实,音韵和谐,亦有称道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像哥舒翰这样热爱文学并留下作品的少数民族将领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当然,对于一个武将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运用其智慧和骁勇,抵御侵略,保国为民。哥舒翰生逢唐与吐蕃关系异常紧张的时代,参与和领导过多次唐蕃战争,其中最富盛名者乃天宝六载(747)“麦庄之役”,天宝八载(749)“石堡城之战”和天宝十二载(753)“九曲之战”。这三大战役的胜利在唐蕃关系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哥舒翰因此而进封西平郡王并名垂史册。可以说,这三大战争既成就了哥舒翰,又给他带来了非议。下面我们就根据史籍所载,试看这三次唐蕃战争及哥舒翰的军事才能与战斗形象。
首先看麦庄之战。据《旧唐书》哥舒翰本传载:“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天宝六载),翰使王难得、杨景晖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余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3]。《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亦载:“每岁积石军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呼为吐蕃麦庄。(哥舒)翰先伏兵于其侧,虏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复来”[6]可见,吐蕃统治者长期频繁地抢掠,给边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和巨大损失。哥舒翰运用其智慧和骁勇在麦庄之战中取得胜利,为保护边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
其次看石堡城之战。石堡城是隋唐时著名关隘,其地理位置在今青海省湟源县哈城东石城山。关于石堡城,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载:“石城山,西南去县治(今青海西宁)而百八十里,即石堡城。崖壁峭立,三面绝险,惟一径可上。隋史万岁诗曰:‘石城门峻谁开辟,更鼓误闻风落石’是也”[7]。《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胡三省引宋白注曰:“石堡城在龙支县西,四面悬崖数千仞,石路盘屈,长三四里,西至赤岭三十里”。[8]史籍虽记载不一,却均强调石堡城形势极为险峻,易守难攻,有“铁仞城”之称。这里曾是唐和吐谷浑边界,吐蕃侵占吐谷浑牧地后,成为唐朝防御吐蕃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唐蕃的交通要冲。开元天宝之前,吐蕃就攻陷了石堡城,留兵拒守,并以此为基地侵扰河右,给唐朝造成了极大威胁。天宝六载(747),玄宗欲派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石堡城,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若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釁,然后取之”[9]以婉言谏劝玄宗不宜强取,“玄宗因不快”。其后将军董延光奏请领兵攻打石堡城,玄宗命王忠嗣分兵协助,但久攻未克。天宝八载(749),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克吐蕃石堡城。这就是哥舒翰攻取石堡城的背景。诚然,这次战争使唐军“士卒死者数万,果如忠嗣所言”,时人和后人多议其牺牲太大,得不偿失。但牺牲和损失是任何一场战争所不可避免的,这并不能成为批判哥舒翰和判定战争性质的主要依据。可以说,石堡城之战的胜利,使唐朝在唐蕃长期对峙中不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也给河陇地区百姓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安定与和平。
最后看九曲之战。九曲,指今青海贵德县、化隆县一带的黄河地区,本属唐地,属廓州。睿宗景云元年(710),唐派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金城公主入蕃和亲,据《旧唐书·吐蕃传》载:“时杨矩为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厚遗之,因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11]。吐蕃诈取九曲地后,遂逾河筑城,置独山军(今青海同德南部),九曲军(今青海贵南西部置),架桥于黄河之上(今青海共和县曲沟附近),以此作为东进临洮、兰州、渭源等地的军事基地。开元二年(714)秋,即吐蕃得九曲的第三年“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余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渭等州,掠监牧羊马而去”[10]吐蕃占据九曲给唐王朝带了巨大威胁和损失。直至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率军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诸城,悉收九曲部落,终于才使其失而复得。哥舒翰收复九曲,不但彻底清除了吐蕃统治者的侵略和威胁,而且给边境人民带来了相对安定繁荣的局面。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载:时“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1]
由此可见,唐代史籍中的哥舒翰是个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少数民族英才。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骁勇在抵御吐蕃统治者掳掠战争中屡立战功,成就了一番丰功伟业,为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卫边境和平安宁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唐诗中的哥舒翰
在唐代诗坛上,不少诗人曾作诗咏及哥舒翰,如李白、杜甫、高适、储光羲、西鄙人等,但是歌颂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毁誉不一。为了说明问题,兹择其几首咏哥舒诗加以分析。其一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
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
奇兵邀转战,连孥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
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
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
威棱慑沙漠,忠义感乾坤。老将黯无色,儒生安敢论。
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唯有关河渺,苍茫空树墩。[12]
这首诗是诗人高适与李员外奉贺哥舒翰收复九曲而作。诗人不惜笔墨,热情颂扬了哥舒翰的威武神勇与赫赫战功,字里行间,充满着无比喜悦和钦慕之情。其二高适《九曲词》(三首):
一
许国从来彻庙堂,连年不为在疆场。
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上异姓王。
二
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驎。
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
三
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逤取封侯。
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12]
关于高适此组诗的具体创作时间,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一云:“天宝中,哥舒翰攻破吐蕃洪济、大莫等城,收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阳郡,(高)适由是作《九曲词》”[13]故有学者认为作于天宝十二年(753)秋。赵宗福先生以为当作于天宝十三年(754)春,创作地点在陇右节度使所在地西平郡(今西宁乐都)[14]。第一首诗颂扬哥舒翰以身许国,连年立功疆场的英雄形象和丰功伟绩。第二首诗描绘胜利给边境人民带来的欢乐与太平。第三首诗描写戍边将士保边卫国的飒爽英姿和收复九曲的重大历史意义。其三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
天纪启真命,君生臣亦生。乃知赤帝子,复有苍龙精。
神武建皇极,文昌开将星。超超渭滨器,落落山西名。
画阃入受脤,凿门出扞城。戎人昧正朔,我有轩辕兵。
陇路起丰镐,关云随旆旌。河湟训兵甲,义勇方横行。
韩魏多锐士,蹶张在幕庭。大非四决轧,石堡高峥嵘。
攻伐若振槁,孰云非神明。嘉谋即天意,骤胜由师贞。
枯草被西陆,烈风昏太清。戢戈旄头落,牧马昆仑平。
宾从俨冠盖,封山纪天声。来朝芙蓉阙,鸣玉飘华缨。
直道济时宪,天邦遂轻刑。抗书报知己,松柏亦以荣。
嘉命列上第,德辉照天京。在车持简墨,粲粲皆词英。
顾我抢榆者,莫能翔青冥。游燕非骐骥,踯躅思长鸣。[15]
此诗为时任监察御史的储光羲所作,把哥舒翰写得英明勇武,神奇非凡,尤其是对其石堡城之战给予了极高评价。其四西鄙人《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只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16]
此诗为西鄙人即当地百姓所作。关于此诗,《全唐诗》注云:“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此”(后两句《太平广记》作“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壕”)清沈德潜说此诗:“与《敕勒歌》同是天籁,不可以工拙求之”[17]。诚然,诗仅以寥寥数语描绘出哥舒翰的战斗形象和赫赫战功,语言简洁自然,有一种朴素美。可以说,此诗代表着当时普通百姓对哥舒翰的看法及态度。
但是,在唐代诗坛上,有另外一些诗人对哥舒翰的看法及态度与高适等诗人截然相反。最为典型者莫过于李白、杜甫两大诗人。试就其咏哥舒诗例举一二。其一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18]
此诗乃李白为哥舒翰拔石堡城而作。瞿蜕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引詹英注云:“王(琦)谱天宝八载附考云:是年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白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知为是时以后之作”[19]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对哥舒翰持强烈否定态度,赤裸地指斥其带刀横行,屠城邀功,行径丑恶如“狸膏斗鸡”之徒。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其二李白《古风·十四》: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
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
争锋徒死节,秉钺皆庸竖。
战士死蒿莱,将军获圭组。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20]
据元萧士赟考证,李白此诗“当是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盖当时上好边攻,诸将皆希旨开边隙,忠嗣独能持重安边不生事。……此诗盖以李牧叱忠嗣也”这首诗表现了李白对哥舒翰的极端鄙视和深恶痛绝,嘲讽其加官进爵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语出唐曹松《己亥岁二首》)的卑劣行径。其三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
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
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21]
此诗为杜甫规劝哥舒翰而作。清杨伦《杜诗镜诠》引朱鹤龄注云:哥舒翰“遂因麦庄一捷,而黩武穷荒,屡致败衂。今高之往,适当其时,公故戒其贪胜,欲适以之告翰也,此是送高本旨”[22]。清钱谦益《钱注杜诗》亦云:“哥舒翰大举兵伐石堡城,拔之,士卒死者数万。……此诗以穷荒为戒”[23]从诗的内容看,二诗论家所言为是。其四杜甫《喜闻盗贼番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二):
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
朝廷勿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24]
此诗为杜甫闻吐蕃退却而作。大历二年(767)十月,唐朔方节度使路嗣恭破吐蕃于灵州城(今宁夏灵武县)下,吐蕃王朝进攻唐王朝受阻,开始退却。诗意谓朝廷不要任用像哥舒翰那样的“边将好功之人”轻开边衅,并表明了诗人颂扬和亲,反对战争的政治态度。
从这二首诗,可以看出杜甫虽不似李白般直接严厉,但亦对哥舒翰持强烈批判态度。在他看来,哥舒翰黩武穷荒,轻开边衅,是破坏唐蕃友好关系的罪魁祸首。“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杜咏哥舒诗,历来颇为流行,影响很大。后来论者,多袭其议,对哥舒翰予以否定。
由此可见,唐代诗人对哥舒翰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及态度,从而使其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两种形象类型:一是高适等诗人笔下英明神武,保国卫民的英雄形象。二是李白、杜甫二大诗人笔下黩武穷荒,贪功好胜的枭雄形象。二者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三、诗史差异形成原因
显而易见,唐代诗与史中的哥舒翰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一致性容易理解,因为“不管作者如何虚构,一涉笔墨,往往不自觉地会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和社会的真相。”[25]那么,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只有挖掘出其中原因,才能正确处理文学与历史间的关系,才能找到诗歌与本事间的最佳契合点。究其原因,以笔者所见,大致有三:
(一)思想根源
唐代诗人对哥舒翰的否定,究其根源,则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儒道两家思想文化之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倡导“中和”思想,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故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关系上,主张和平与友好,反对暴政和战争。传统的道家文化亦同样倡导和平,反对斗争。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第八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儒、道两家这种“和为贵”的思想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历史地内化为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即厌战反战心理。所以,在中国古代边塞诗中,我们看到了不少颂扬和平,批判战争的诗篇。这些作品,无疑是深受这一传统民族心理影响的产物。众所周知,在文化开放、儒佛道三教并重的唐代,诗人中很少有单独受到或儒或佛或道一家影响的。以李白、杜甫二大诗人为例,李白出生于一个有儒家文化素养的家庭,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可知他曾受很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李白的少年时代,又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他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十五游神仙,仙友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道教的影响几乎终其一生。而伟大诗人杜甫则一生“奉儒守官”,“忠君恋阙,仁民爱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毋庸置疑,儒、道两家文化对李白、杜甫二大诗人的思想有巨大影响。李、杜诗中对哥舒翰的否定,显然是深受中华民族厌战反战心理的影响。
(二)社会背景
诚然,唐代诗人对哥舒翰的否定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唐玄宗后期,朝政大权先后落入权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手中,政治黑暗腐败。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载:天宝六载(747)“上(玄宗)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野无遗贤”[6]。又据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载:“唐玄宗自恃强盛,定要侵侮邻国来满足自己的骄侈心,边疆凭籍国家的威力,侵侮邻国来求富贵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朝廷能否控制。唐玄宗本人就有好战心节度便立功名往往入朝作宰相,实际上是鼓励边将生事邀功,唐与邻国当然不会相安无事”[26]从以上史实可知:其一当时国家奸佞当道,政治黑暗腐败,统治者好大喜功,边将贪功好胜,使得朝纲大乱,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其二当时知识分子受到奸相李林甫的压制与排挤,空有才华和抱负却得不到重用。而有些边将却凭藉国家威力,黩武穷荒,生事邀功,继而加官进爵。这种黑暗现实和不平待遇,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深感愤懑和不满,他们以笔为武器,写诗进行抨击。如杜甫云:“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李白云:“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秋歌》),“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关山月》),高适云:“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王昌龄云:“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等等,诗人们借对征戍士卒艰辛生活和忧怨思归情绪的描写,来表达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强烈不满和对无休止战争的深恶痛绝。哥舒翰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奉命出征吐蕃并取得胜利,继而加官进爵的,因此受到批判和否定是必然的,同时这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
(三)心理因素
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情绪的反映。我们联系诗人生平事迹,可以寻到诗人对哥舒翰持不同看法及态度的心理因素。如前所述,玄宗后期,朝政大权先后落入权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手中,政治黑暗腐败,杜甫、高适、元结等诗人均在当时应试中被奸相李林甫所黜落,成为那场骗局的受害者。落第后的杜甫客居长安,为了求得援引“朝扣富而门,暮随肥马尘”却一无所获,贫困无以为生,乃“卖药都市,不足则寄食友朋”。此时其处境之艰难,情绪之苦痛是可以想见的。而李白当时则为高力士所馋,得罪杨贵妃,被玄宗“由是斥去”,结束了其一生最光辉灿烂的一段生活,也就是他供奉翰林时期,而开始了长达十年左右的漫游。他“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看似逍遥快活,实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二人内心深处均充满因受统治阶级排斥、压抑而产生的强烈愤懑之情。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他们看待唐蕃战争时往往只注意到其“黩武”、“杀戮”的消极影响,而忽略了其积极意义。
再者,李、杜二人虽有不少边塞之作,但与唐代绝大多数边塞诗人一样,并未曾真正到过边塞,更未经历过边塞战争。他们二人关心时事,对边塞之事必有所知,但因并非战争的亲历者,故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战略全局,用兵部署均无法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他们只是根据传闻等间接信息,加以分析判断,形成对唐蕃战争及其哥舒翰的看法和态度。但是,诗人高适却与其不同。高适亦是个以经济自负的人,颇有用世之心,但是始终遭受统治阶级压抑而仕途坎坷,在梁宋间过了十余年“混迹渔樵”的流浪生活。据周勋初先生《高适年谱》言,天宝十二年“秋,(高适)受田良丘推荐,赴河西幕府谒哥舒翰,不遇;转至陇右,始为入幕之宾”[27]直至天宝十二年(753),五十三岁时,高适才因田良丘推荐,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下。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高适作为哥舒翰的掌书记,随军多次征战,熟悉边塞局势,与李、杜相比,感受自然要深刻得多。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高适正值否极泰来的人生转折时期,心情愉悦,思想积极,情绪高昂,所以当哥舒翰大破吐蕃,旗开得胜之时,诗人情不自禁地以诗尽情讴歌,表达心中的欣喜、兴奋之情,同时借哥舒之事,抒发自己“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的豪情壮志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可见,诗人境遇各异,情志有别,看待事物的角度自然不同,感受、结论也就不一样。
综上所述,诗歌与历史之间既有互证性,又有差异性。我们应该加强文学与历史间的相互结合,以文学佐证历史、借历史审视文学,高度拓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阐释空间。但是,也应该看到文学与历史间的差异性,“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但不是生活原型的翻版。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有意识地改变自然或社会的生活真实,并不是十分罕见的事情。文史互证,不等于对号入座。仅仅从局部着眼是很危险的”[5]因此,应该正确处理文学与历史、诗歌与本事之间的关系,力图寻找到二者间的最佳契合点。
[1]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M].台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5:128.[2] 卞孝萱.略谈文史互证[J].中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3] (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哥舒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5] 黄进德.说哥舒翰《破阵乐》[J].唐代文学研究,1998.
[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 1976:3212.
[7] (清)杨应琚.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131.
[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 1975:6784.
[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6878.
[10] (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吐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28.
[1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 1975:6918.
[12]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35.
[13]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833.
[14] 赵宗福.历代咏青诗选[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19.
[15] 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89-1390.
[16] 全唐诗卷七百八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8849-8850.
[17]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36.
[18]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1820.
[19]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1597.
[20]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1672-1673.
[21]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M].中华书局,1979:2252.
[22] (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1.
[23] (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3.
[24] 全唐诗卷二百三十[M].中华书局,1979:2520.
[25] 许倬云.历史分光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6]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61.
[27] 周勋初.高适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7-78.
责任编辑:毛正天
I206.2
A
1004-941(2012)05-0087-05
2012-08-16
马海龙(1979-),男,回族,青海西宁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