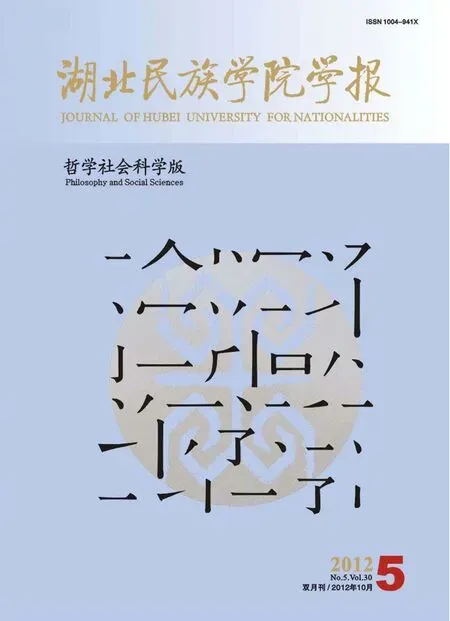论高启诗歌观念及诗歌风格的前后变化
贺雯婧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论高启诗歌观念及诗歌风格的前后变化
贺雯婧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高启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号称“诗淫”的天才诗人,身处元末明初,其诗歌创作与文学观念具有易代时期独有而鲜明的特色。他针对诗歌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的传统文艺观,提出并坚持文学主要的是诗人聊以自适和自得的特殊精神活动,是诗人用来抒发诗人内心情感的语言符号,他把诗歌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来追求,并通过诗歌创作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精神上的满足,使他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诗歌风格;“随所宜而赋”;“以诗存史”;“清新含蓄”;“放拓雄浑”
一、从“随所宜而赋”到“以诗存史”的变化
处于元末明初的高启,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号称“诗淫”的天才诗人。不管在诗歌创作还是文学思想上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具有易代时期所独有的特色。他认为诗歌不仅仅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而更主要的是诗人聊以自适和自得的特殊精神活动,也是诗人用来抒发内心情感的语言符号。一直以来,高启都把诗歌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来追求,并通过诗歌创作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精神上的满足。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始终把诗歌当作是政治教化的工具,早在先秦时,孔子就提出过“兴观群怨”说,认为诗除了抒发情志的作用外还要有“事父”、“事君”的功效。后来正统的文学批评中,主张明道、征圣、宗经,美刺等作用,也基本上都是延续了孔子“兴观群怨”的思想。但不管任何派别,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将文学看成为封建政治的附庸物。在这种理论影响下,文学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价值,逐渐堕落为政治的附庸。然而高启却不这样认为,在《击鸣集序》中,他表达出了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人自适、自娱;文学家,尤其是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应该是为自己而创作:
古人于诗,不专意而为之。《国风》之作发于性情之不能已。其以为务哉?后世始有名家者,一事补此而不他,疲弹心神,鬼利物象,以求工于言语之间,有所得意,则歌吟蹈舞,举事之可乐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笃好,虽以之取祸,身摧困逐而不忍废,谓之惑非一软?[1]
“国风”好诗,但非刻意写诗,而是诗人情感不得不发之产物。就是说,诗人写诗,是因为自身对社会有深刻的感触,内心产生了一种持久而不衰的激越情感势态,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借助诗歌艺术的创造,自然而然地显示这一心灵的特点。诗主情,非创见。汉《毛诗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晋代的陆机在《文赋》中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诗缘情而绮靡”,唐代白居易也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高启认为,历代论诗者都是以性情为诗的根本。唯一不同的是各家在性情内涵上有不同的理解。传统儒家强调的是大性情,排斥小性情。而高启认为诗歌中所体现的性情是一个人的全部情感,无所谓大小之分,“登高远望之情,怀贤吊古之意”,“草木之盛衰,鱼鸟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动目者,一发于诗。”由此可见,高启认为的性情涵义虽丰富繁杂,但却不缺少理性的思考。这样一来,他就将文学从政治附属物的地位中解救出来,恢复了文学的本来面貌,让它找到了属于自己应有的价值和地位。在《娄江吟稿序》中说:
天下无事时,士有豪迈奇崛之才,而无所用,往往放于山林草泽之间,与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闻于世也。[1]
高启不仅在理论上将文学地位提升,在平常的创作中他也将自己所提出的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践。如,“日与幽人逸士唱和于山巅水崖以遂其所好,虽其工未敢与古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乐,虽善辩者未能知其有异否也”,也就是在“自得之乐”中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及艺术价值。他说:“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犊,吟声唯呛不绝于口吻,或视为废事而丧志,即进不能有为于当时,退不能服勤于吠亩,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鹜于形势之途,顾独事此,岂不亦少愈哉?”他以自己全部的感受力,把自己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加以琢磨、变化、运用,在强烈的心灵震动中,写出自己的诗篇。这样的诗歌怎能不显示自己的个性呢?他在《娄江吟稿序》中还说道:“衡门茅屋之下,酒熟系肥,从田夫野老相饮而醉,扮击而歌之,亦足以适其适矣。”[1]在高启的一生中,他始终都将诗歌当作抒发诗人内心情感、聊以自适的工具。由于执着追求创作主体精神的自由,因此他在论诗的时候强调不拘一格,可以说高启早期的文学理想就是像他在《青丘子歌》中所说的那样成为一名自由的诗人:
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断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茹,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流淦,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车畴匕冻草萌。高攀天根深月窟,犀照牛诸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霞兹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江石相轰铿.江边茅草风雨情,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欲呼君山老父揩褚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焰忽波浪起,鸟兽骇叫山摇崩。天帝闻之怒,下遣白鹤还。不容在世作狡绘,复结飞佩遣瑶京。[1]
这是高启依外舅居吴淞江边的青丘时,作此诗以明志。诗中不仅抒写自己狂放不羁的独特个性,以颜回自喻,在元末的频繁战争中,自己隐居田园,沉溺于诗歌创作之中。也写出了高启创作冲动的内心自白和创作理念。他在终日苦吟中写此诗以言其志,“以解诗淫之嘲”,回答人们对自己沉溺于作诗的嘲笑。高启从大自然中吸取题材,把难以捉摸的大自然景象,通过诗歌的语言和构思给予形象化的表现。这是一位以性命情志作诗的诗人;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诗人;一位以自己心灵唱歌的诗人;一位追求自我精神独立的诗人;一位背叛传统价值观念的诗人,他绝不会人云亦云,拟古食古。也正是在对诗歌作用和地位深切认识的基础上,让他在《独庵集序》中表达出了如下看法:
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辫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变则入补邪陋,而师古之意乖;情不达则坠补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补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橄褥、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5]
高启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上要自由,“体不变则入补邪陋,而师古之意乖”。在他看来诗歌创作要不断地变化体裁,要有真情实感。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随所宜而赋焉”的诗歌最高境界。入明之后他提出了“以诗存史”的观点,与此观点不同。因此此论既是高启自我诗歌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参修《元史》受到激励的结果。胡翰《击鸣集序》中称赞高启诗歌“其事虽微,可以考得失,备史氏之所惩劝”。而高启本人也赞同胡翰的这种观点。
二、从“清新含蓄”到“放拓雄浑”
明初诗人的忧患意识,多哀时愤世之情;诗歌风格,有的沉郁,有的纯雅,有的清丽,有的朴健。这些诗歌从内容到风格,多学习唐宋诗的优良传统。方孝孺曾说:“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2]说出一代诗风之所宗,是李白与杜甫。《明三十家诗选》谓李晔:“草阁诗源砖杜陵,七古力劲神完,纵横如意,有骏马下坡之势。”[3]《静志居诗话》说程本立的诗“刻意杜陵”,《四库总目》说他的诗“颇似唐音”。而高启作诗狂放不羁,模仿李白,其他汉、魏、六朝、唐、宋诗他也学习。因此形成了如《击鸣集后序》中表述的多样性:
故季迪之诗,缘情随事,因物赋形,纵横百出,开合变化,而不构一体之长。其体制雅醇,则冠冕委蛇,佩玉而长裙也。其思致清远,则秋空素鹤,回翔欲下,而轻云雾月之连娟也。至其文采褥丽,如春花翘英,蜀锦心灌。其才气俊逸,如泰华秋华之孤赛,昆仑八骏追蹂风电而驰也。季迪于诗,可谓尽其心焉尔。[1]
尽管高启诗歌创作形式多样,既有五言、七言、五律、七律、也有古乐府、绝句、排律等。但从诗歌风格方面说,高启诗歌以清新含蓄和放拓雄浑这两方面为主。周南老云:“(季迪诗)古今诸体咸备。命意骋词,如健鹊横空,如快马历块。如春园桃李,如秋汀苹寥。超逸不群而俊丽可喜,深得诗人之妙。”[4]王世贞亦云:“太史弘博凌厉,殆馒侵正始。一时宿将选锋,莫敢横阵。快若迅鹊乘鹰,良骥镊景。”[5]在这段话中,指出了高启诗歌具有雄浑放拓之风格。而这类诗歌风格主要体现在纵论历史事件,评点古今人物为内容的诗篇中。高启也将自己诗歌风格总结为这两个方面。“国初,高启与袁凯皆以诗名,……高有赠景文诗曰:‘清新还似我,雄健不如他!’”[6]而之所以形成这种清晰含蓄的诗歌风格和他做诗时所选的民歌题材有着很大的关系。
首先,高启虽然生在元末明初的动乱年代。但是由于他在吴中地区处于战争犬牙交错的边缘。于是吴中也就成了惊涛骇浪上的一块和平小洲。因此,元末时期高启诗歌内容多以描绘江南水乡生活为主,诗歌题材也多半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如风云、花木等,所要表达的是诗人对家园的挚爱之情。在这类诗中,没有严肃的主题和深刻的内涵,有的只是一片清新明快之风。如《照田蚕词》、《养蚕词》等。这类诗风格均以清新自然的乡土气息为主。
东村西村作除夕,高炬千竿照田赤。老人笑小儿歌,愿得宜蚕又宜麦。明星影乱姜鸟惊,火光辟寒春已生。深夜燃罢归白屋,共说丰年真可卜。[7]
在这首诗中所谓的“高炬千竿照田赤”实际上说的就是吴中“照蚕”风俗。诗歌所描述的是村民在田间烧火驱逐灾异,以求得上天的保佑。小儿欢歌笑语,老人安详快乐。体现出了一片安宁祥和的田园景象。
其次,受到吴越地区民歌风格的影响。吴越地区人杰地灵,文风炽盛,“名士多于螂鱼,琵琶盛于饭甄。”吴越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或荆楚文化,《吴越春秋》载:“吴与越同音共律”。自古以来,吴越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因而也具有共同的特殊文化生活习俗和文化心态。由于地处长江中游,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们既保留了古老、淳朴、豪放、带有一些野性的文化特征,也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吴越民歌,历代都很盛行,如古代的越歌,风行一时。战国之后,吴越人好唱歌,《吴越春秋》中记载了多首越人唱的歌,如勾践夫人在勾践入吴为臣时所唱的哭歌,采葛妇唱的“苦之诗”,伐木人唱的“木客吟”,以及流传最广的越船夫吟唱的“榜泄越人歌”,淳朴、悠扬的民歌在吴越一带源远流长。加上江南方言柔美、委婉,民歌款款动听,清丽动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文人都喜欢写民歌,提倡向民歌学习。像刘基、贝琼等人都写过风格清丽的诗歌。当然高启也不例外。如《碧玉歌》、《打麦词》等。这些诗歌风格也以清新自然为主。
除此之外,才华横溢,胆识超群是高启诗歌所具有的另一面。为此,戴憬评价为:“为文雅澹,为诗雄健。”[8]而这类诗歌明显是受到了李白和杜甫的影响,主要出现在诗人纵论历史事件,评点人物为内容的诗篇中。如:
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暖高庙自藏弓。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岳王墓》)[7]
该诗作于诗人游吴越途中,游览杭州西湖栖霞岭下岳飞祠墓时所做。诗中讽刺宋高宗自毁长城、苟且偷安,感慨岳飞英雄失路。诗句成沉郁顿挫,风格雄壮。又如: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疹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阀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7]
这首诗歌表现出了大江东去的非凡气势和雄壮场面。情感慷慨激昂中也不乏苍凉悲壮,不愧是金陵之杰。
高启元末的作品以放拓雄浑、清新含蓄风格并存。但入明之诗却是以清新含蓄风格见长,这自然是易代变故的一种结果。高启诗风的这些变化,不仅与社会环境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易代之际诗人的独特心态也有很大的关系。
[1] 高启.高青丘集[M].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
[2]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586.
[3] 汪瑞.明三十家诗选:卷四册[M].同治癸酉十月蕴蘭吟馆刊本,982.
[4] 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2.
[5] 王士祯.明诗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489.
[6] 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M].山东:齐鲁书社,2008:1121.
[7] 李圣华选注.高启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M]江苏:凤凰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毛正天
I206.2
A
1004-941(2012)05-0092-03
2012-08-10
贺雯婧(1984-),女,藏族,青海西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