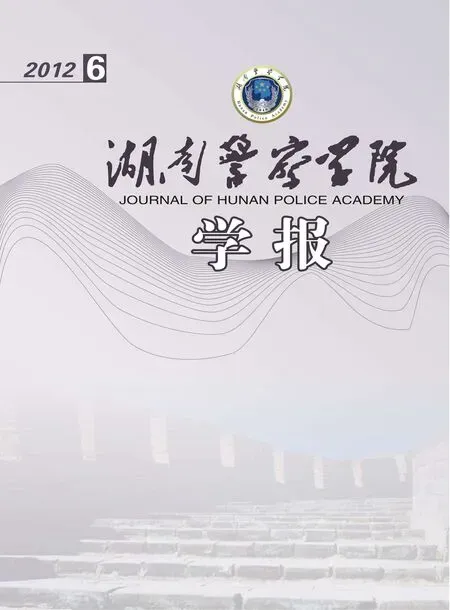法院附设人民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以青岛市A区设立交通事故争议案件人民调解室为视域
朱媛媛,李 璐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法院附设人民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以青岛市A区设立交通事故争议案件人民调解室为视域
朱媛媛,李 璐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依附于传统熟人社会土壤的人民调解制度正逐渐暴露出其致命缺陷,衍生出一系列体制化弱点。对在“息讼”理念下设立的处理交通事故争议案件的人民调解室我们应全面剖析,准确加以定位,并加强对人民调解制度的规范化建设。
人民调解制度;困境;出路
2011年,青岛市A区接报交通事故约14,000起,同时,青岛市A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侵权案件年审量约为800件,其中交通事故争议占到审判量的75%—80%。不可否认,交通事故的频发及其纠纷处理所需要的专业性,将青岛带入了交通事故争议“诉讼爆炸”的时代。当下,很多国家专门设立了处理交通事故程序简便、成本低廉的日常性的咨询和纠纷处理机关。例如,作为财团法人的日本的交通事故咨询所,根据与法院同样的规范和标准,应当事人的申请为其提供咨询、斡旋和裁定等有偿服务,每年受理各类业务近20万件[1]。这样既避免了当事人之间因对立情绪而无法协商的问题,也保证了处理过程的迅捷性和处理结果的精确性。青岛市A区针对现今交通事故引发纠纷逐年上升的社会管理新问题,在人民调解制度的理念支配下,探索出了类似的化解此种纠纷的新方法——成立A区交通事故争议案件人民调解室。
该人民调解室成立于2010年7月12日,由青岛市A区司法局、青岛市A区人民法院、青岛市A区交警大队联合设立,由A区人民法院以及A区司法局共同指导,本着“专业的角度,公平的立场”这一宗旨,为相关交通事故争议案件做免费的调解。2011年,共受理交通事故争议案件330起,成功调处261起,调解成功率为79.09%,涉案金额达384,752.88元,基本实现了人民调解与交通警察行政调解、法院司法调解的有效衔接,提高了交通事故处理效率,方便了群众,节省了警力,形成了将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多赢局面。
然而,人民调解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种种问题,隐藏在这些乐观的数字当中而鲜为人知,基于此,本文以青岛市A区交通事故争议案件人民调解室为例,旨在通过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剖析,为人民调解室突破困境寻求出路。
一、纠纷解决机制与人民调解制度
(一)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是与秩序相对应的范畴,纠纷的发生意味着一定范围内的协调状态或秩序被打破,纠纷的产生及其解决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纠纷解决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和程序解决纠纷和冲突,恢复社会平衡和秩序的活动和过程。
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2]:(1)自力救济,亦称“私力救济”,民间俗称“私了”,是指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纠纷,没有第三者的协助,主要包括避让与和解两种方式。(2)社会救济,是指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纠纷的方式,主要特征是基于纠纷主体的共同意愿,请求第三者协助或主持解决纠纷。这里的第三者是指除国家机关之外的个人或组织,不包括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依靠政权的力量解决纠纷属于国家的范畴。由社会力量介入解决民事纠纷的渠道主要有两个,即诉讼外调解和仲裁。(3)公力救济,是指利用国家的公权力来解决纠纷,即国家介入纠纷的解决。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来解决纠纷,表现形式是诉讼。
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国家司法权集中统和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到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面辅助、甚至替代法院审判模式的发展过程,非诉讼程序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时代性成果,其势已成。
非诉讼程序是对诉讼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制度的总称。目前世界各国一般采用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来表述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代替性(替代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ADR概念原来特指美国现代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劳动争议的解决,现在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由于非诉讼程序是一个总括性、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相对均难以准确界定。目前,国际上对ADR应包括哪些程序制度仍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其定义尚不十分严密和统一。其中,美国1998年《ADR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1998)的定义是:代替性纠纷解决方法包括任何审判法官的判决以外的程序和方法,在这种程序中,通过诸如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小型审判和仲裁等方式,中立第三方在论争中参与协助解决纠纷。
尽管表述和概念并不统一,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非诉讼程序(ADR)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用术语。一般而言,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与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判决)的区别与联系,对其界定通常根据如下几个因素:代替性,是指对法院审判或判决的代替;选择性,是指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以当事人的自主合意和选择为基础;解决纠纷,则是指ADR的基本功能[3]。
(二)立足国情:我国当代调解体系中的人民调解制度
在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下,调解是一种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所广泛采用的重要手段。所谓调解,是指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当事人双方自愿妥协,合意解决纠纷的活动。我国当代的调解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由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肇事造成的损害赔偿进行的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调解四部分组成。在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社会救济中的诉讼外调解即是指除法院调解之外的其他三个部分,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消费者协会、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及律师对纠纷的调解等。
在这一归类下对人民调解进行的定义,理论界主流观点如下:第一种,认为人民调解是民间调解的一种,民间调解是指官方调解之外的调解民间纠纷的各种方式。传统社会民间调解的类型有宗族调解、亲友调解、邻里调解、乡里调解和行会调解等,主要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简称人民调解)、乡镇法律服务所调解、律师事务所律师调解、家族调解、亲友调解和邻里调解等方式[4];第二种,认为人民调解实际上就是民间调解;第三种,认为民间调解是人民群众自发地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5]。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斡旋说服、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活动。
(三)国际视野:ADR中的人民调解制度
根据主持纠纷解决的主体或第三者,即ADR机关,可将ADR分为以下五种类型:法院附设非诉讼程序(court-annexed ADR)、国家的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非诉讼程序、由民间团体或组织进行的非诉讼程序、由律师主持的专业咨询或法律援助性质的非诉讼程序、国际组织所涉纠纷解决机构的非诉讼程序。根据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又可将ADR分为以下四种模式:谈判(和解)、调解、仲裁和美国的“混合型”(hybrid)纠纷解决程序(包括早期中立评价、中立专家和事实发现、建议陪审团审判、小型审判、聘请法官、调解—仲裁等多种形式)。
在以主持纠纷的第三者为标准划分的五种ADR类型中,每种类型所擅长和专注的纠纷解决方式各不相同。其中,由民间团体或组织进行的非诉讼程序(又称为“民间性ADR”)运用调解的手段化解纠纷,即包括本文旨在论述的人民调解制度。因此,人民调解制度实际上属于民间性ADR中的模式之一。
除此之外,既不属于正式的司法体系,也不属于国家行政建制的民间性ADR主体,还包括以财团法人或基金形式运作的专门机构,例如日本的交通事故纷争处理中心,也包括自发成立的民间团体或社会团体法人机构,例如美国的邻里司法中心(Neighborhood Justice Center),以及那些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民间社区的松散的纠纷解决组织,对此本文不做详细介绍。
二、法院附设人民调解制度的困境
可以说,法院与人民调解室是交通事故争议案件纠纷解决的两条殊途同归的道路,相较于诉讼,人民调解无立案、审判程序,直接进入调解程序,更加迅速、快捷,这对司法资源的盘活或有意义。然而,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在现实中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下文笔者将以青岛市A区交通事故争议案件人民调解室为例,全面剖析法院附设人民调解制度的缺陷及体制化弱点。
(一)赔偿风险不可避免,调解初衷难以实现
人民调解最大的特点是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因此其处理结果的效力和履行的保证始终是它的致命弱点,反映到A区交通事故争议案件的人民调解中即表现为赔偿风险无法化解。由于或涉及到伤残鉴定,或者当赔偿数额较大无法现场给付时,肇事方通常会出具还款凭证,以便受害方日后索要赔偿款。当肇事方逃逸或拒不履行赔偿义务时,由于缺少法院生效判决或调解的法律效力,当事人无法通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获得赔偿,因此,就该凭证引发的另一个法律关系,不免又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交通事故纠纷中调解的初衷难以实现。同时,该凭证系借条性质,受二年诉讼时效的约束,一旦两年期满,肇事方则可提出时效抗辩,如此对于受害方而言,难免另生枝节。
(二)调解过程存在“廉价正义”(Cheap Justice)
人民调解在追求低廉和迅速解决纠纷的同时,也由于其过程的随意性而导致当事人的程序利益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而程序的简略又可能导致解决结果的不公正,此即所谓“廉价正义”(Cheap Justice),人民调解因此面临着“向穷人出售廉价、低质、粗糙的正义”的指责[6]。例如,当事人的妥协使自己的权利不能全面实现;抹煞和淡化当事人的权利意识;不是以权利和义务作为处理纠纷的核心和标准;在运作中会出现违反当事人自主和合意原则的诱导和强制的可能性。
在A区交通事故争议案件的人民调解中,“廉价正义”最明显的表现即为保险公司的理赔较之法院审判存在差额。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在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投保交强险的车辆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然而,正是在保险公司理赔金额这一方面,人民调解与法院的认定存在较大差额。如在人民调解中,保险公司不承担间接损失责任,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就陪护费方面而言,法院认定的理赔标准为80元/天,而人民调解室认定的标准为50元/天;就误工费和误工时间而言,法院通常会根据个案情况或司法鉴定确定住院后的误工时间,但人民调解室对住院后提出的误工费主张不予认可;在治疗用药的认定方面,法院并无“甲类药、乙类药(即“医保药”)”和“自费药”之区分,均根据用药明细按照用药数量认定,而在人民调解中,保险公司对受害方的“自费药”部分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调解经费保障不足
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财政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财行〔2007〕179号),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的开支范围包括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补助经费、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包括人民调解工作宣传经费、培训经费、表彰奖励费等,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标准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标准,由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虽以上法规均对调解经费作了明确规定,但笔者通过调查采访发现,经费的缺乏确已限制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且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
(四)被削弱的调解权威
早在西周时期,大多数从事调解的人,都具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官府的“调人”,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乡绅。在一个“熟人社会”当中,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间人,成为调解得以成功最重要的实施者和保障人。而今,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变得越来越罕见。调解他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变成了双方都来相信一个陌生人。现实生活中,人民调解员有名无分,缺乏警察、法官等群体的威信,遭到质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上所述,人民调解制度最大的局限即在于其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在曾经的熟人社会中,依靠作为调解人的权威性人物的身份,人民调解结果的稳定性得以维系,而今,随着传统乡土社会的逐渐瓦解,这种维系不复存在,人民调解制度的天然缺陷直接演变为其致命弱点——其处理结果的效力和履行的保证。眼下,A区交通事故争议案件人民调解室的权威性往往来自交警大队的推荐,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多种宣传媒体百花齐放的时代,A区交通事故争议案件人民调解室的宣传却仅凭借一个尚未起步的网站,更缺乏表彰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员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社会影响力明显不足。
三、法院附设人民调解制度的出路
(一)明确法院附设人民调解的职权范围
首先,在理论界,“尽量不考虑法律进行调解,并且应本着门外汉的圆满主义常识来处理[7]”这种说法显然已不符合现代ADR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一种ADR形式越成熟和完善,其程序方面的规范化就会越严格。为使人民调解符合现代ADR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不仅要对自身提出法治化和规范化的要求,呈现出准司法或半司法的态势,更要在调解中充分贯彻合意原则,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避免诱导和强制的可能性。同时,在实务界,人民调解室不是万能的,对于纠纷的调解也只能量力而行。利益对抗才是纠纷的实质,也是纠纷发生的根本动因,更是纠纷解决的关键之所在。因此,人民调解室应明确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寻求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
根据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笔者认为,人民调解室基于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和利益对抗处理结果的维护,应更加着眼于赔偿的可行性。例如,在涉及伤残鉴定时,当只有一方当事人委托鉴定机构时,由于民事调解平等自愿的原则,保险公司可以对该伤残鉴定结果不予认可,基于此结果计算出的伤残赔偿金,当然也归于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只能放弃该部分的主张,或者在三方共同委托鉴定机构后进行二次鉴定,这不仅延长了调解时间,更无疑给受害者的身心带来第二次创伤。针对这种情况,现下人民调解应确保三方同时在场,在当事人第一次提起伤残鉴定时,就应由三方共同委托鉴定机构,以保证伤残鉴定结果的效力。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五年来,为增加销售额、提高市场占有率,我国企业应收账款数量逐年上涨。以我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为例,如表1所示。
简而言之,人民调解的能力和作用不能无限扩张,一旦其辅助性作用为侵蚀性的触手所替代,这一制度便不仅会侵害当事人的诉权、消除公民的权利意识,更会导致社会轻视审判的地位,直接对国家的司法权造成一定的蚕食。
(二)通过司法确认解决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
针对人民调解所固有的缺少强制执行力的弱点,各国采取了如下不同做法:(1)改变民间性ADR的属性,使其变成了司法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或司法性ADR,通过司法审查使民间ADR的调解等处理结果获得法律效力;(2)在法律上赋予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意(即所谓私法上的和解)以契约性效力,即将其视为当事人双方在第三方见证下签订的一种契约,对双方产生契约上的约束力;(3)当事人可以通过公证(审核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使调解协议产生法律效力,由此在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时,可据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我国目前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即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并通过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即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经过审核确认,审查调解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为当事人所自愿接受、是否侵害第三方利益等,赋予当事人无法现场给付赔偿款的案件以强制执行力,出案号为“(20XX)A民调确字第XXX号”的司法文书。该司法文书一经生效,便等同于赋予人民调解协议相当于判决书的法律效力,赔偿风险即可大大降低。为减少或避免“二次纠纷”的产生,人民调解员应在充分分析个案案情,了解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就不同情况给以不同意见,在肇事方多番推拒的情况下应及时提醒受害方司法确认这一途径,以实现人民调解的最终目的。
(三)严格依照部门规章落实调解经费
如前文所述,财政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已明确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标准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标准,由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展开,不应一味依靠党委政府的支持,行政法规是解决人民调解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匮乏的最好依据,若政府能够严格依照该规定落实人民调解经费,不仅能为人民调解工作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更能使人民调解工作逐步摆脱被动局面,增强调解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世殊时异,当下,人民调解的权威性不一定要依靠于传统的“德高望重”的调停人。一个对调解人来源的粗略的类型化描述也许可以从下列术语开始[8]:
1.按照血族、经济、政治关系的“上级”;
2.“所在”(beingthere):邻近的朋友,邻居或工作伙伴;
3.“外人”(the outsider):正是他们的疏离关系(distance)以及明显缺乏任何利益(stake)为其介入提供了合法性;
4.“专业”的调解人。
在这个流动人口日益增多的社会,人民调解员的“权威性”可以尝试从“专业的调解人”中另辟蹊径。因此,赔偿计算的规定越是具体明确,调解模式越是公正便捷,争议和交易的空间就越有限,在实际解决当事人困难的基础上,民众也就会对人民调解越有信心。
像A区交通事故争议案件人民调解室这种专门性的纠纷解决机构,根据专门经验和事先制定的面面俱到、细致入微的赔偿条款,很容易地便可计算出准确的赔偿数额。这种公式化的计算方法具有高度的平等性和确定性,也使当事人讨价还价的余地相对有限,从而可以大大节约协商的过程和时间,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认可度也会相对较高。现今,该人民调解室已成功实施了“小东公式”和“三步调解法”两种创新型调解模式。“小东公式”是调解室的人民调解员计算赔偿金的一种方法,即是把调解内容分为责任划分、保险情况和赔偿要求三部分,每部分都列出明细;并相应实施“三步调解法”,即先由当事双方根据公式列出各部分赔偿金额并累加出总金额,再由调解员按照损害情况和法律法规逐项修正,最后当事人双方在调解员列出的基准赔偿额度内达成一致的和解协议。A区交通事故争议案件人民调解室应通过创新推广“小东公式”和“三步调解法”,使大多数交通事故赔偿能够一次调处成功,复杂案件也能在一周内处结。相对于各种学习、例会、社区宣传,不断创新调解模式,切实为当事人解决交通事故纠纷,不啻为最好的树立权威的手段。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中国传统的“息诉”理念绵延了两千年。“应该鼓励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尝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范愉表示,“调解不但可以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社区建设和道德传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1][日]小岛武司,[日]伊藤真.诉讼外纠纷解决法[M].丁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23-128.
[2]李刚.人民调解概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3-32.
[3]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2.16-19.
[4]李存捧,刘广安.民间调解与权利保护[A].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修订本)[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50.
[5]常怡等.中国调解制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64.
[6]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日]川导武宜.现代化与法[M].王志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92-195.
[8][英]西蒙·罗伯茨,[英]彭文浩.纠纷的解决过程:ADR与形成决定的主要形式[M].刘哲玮,李佳佳,于春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7-158.
Dilemma and Outlet of the People's Mediation System Attached to the Court——on the basis of A district of Qingdao mediation room for traffic accident disputes
Zhu Yuanyuan,Li Lu
(Law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Sichuang,401120)
With speeding-up of our country's urbanization,the traditional people's mediation system dependent on the soil of acquaintances is gradually exposing its fatal defects and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ized weakness.under the idea of"stop litigation"the people's mediation room,is set up to deal with traffic accident dispute cases.So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nalyse and accurately locate those disputing traffic accident cases and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mediation system.
people’s mediation system;dilemma;outlet
D631.5
A
2095-1140(2012)06-0094-05
(责任编辑:王道春)
2012-05-18
朱媛媛(1990- ),女,山东青岛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学生;李璐(1991- ),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