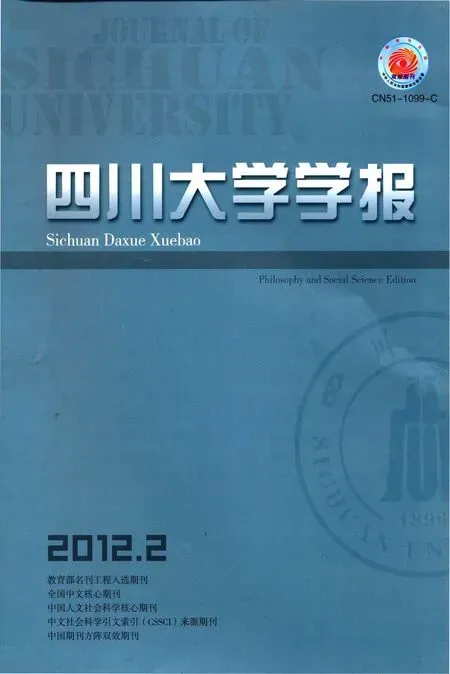“中国风”歌词的性别诉求:一个符号学分析
陆正兰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国风”歌曲在近年乐坛盛行不衰,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符号现象,是一种必然。在传播运作上,它成功实践了大众文化的流行法则,投合了当今中国社会相当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念以及对古典审美情趣诉求。这一现象,表面上只是个娱乐行为,背后却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倾向性问题,尤其在女性性别角色上,揭示出回归传统保守价值的隐秘心理。
在1990年代的《中华民谣》、《涛声依旧》等歌曲中,“中国风”已经初见端倪,大范围盛行并形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歌坛现象,始于词作家方文山和音乐人周杰伦合作的《娘子》和《东风破》等歌曲的流行,近几年许多歌曲沿袭此格调,随着郭敬明等一些文化人的纷纷投入,蔚为风气。对此,方文山的评价较为客观:“我和周杰伦不是中国风的发明者,却是制造它流行的人。”①《方文山:我和周杰伦掀起“中国风”热潮》,《南都周刊》2008年,第251期。
“中国风”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在音乐符号(曲调和配器)上使用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二是在歌词意象符号运用和意境创造上,向中国传统审美文化靠拢。两个层次的结合,通常会使一首歌显示出鲜明的复古风格。在这两个层次上,歌词作为歌曲情感和思想最直接的媒介,其符号表意也更为重要。本文旨在从符号学角度集中讨论中国风歌词特殊的编码方式,及其蕴含的性别伦理诉求。
“我对你唱”是歌曲最基本表意模式。歌的悠久历史,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基本模式。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②朱熹:《诗集传·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页。此种“我呼你应”的表意方式,也是歌词文本最基本的符形构造,它依赖于符号文本两种编码方式的偏重。一是现在、过去、未来三种时间意图编码混合,但偏重未来;二是在符号文本的功能中,主导功能为“意动性”, “诗性”为辅。班维尼斯特(Emile Benviniste)在讨论语言问题时,提出任何语言中,话语的意图方向都对应三种“语态”:过去向度着重记录,类似陈述句;现在向度着重演示,结果悬置,类似疑问句;未来向度着重说服,类似祈使句。三者的区别,在于叙述意图与期待回应之间的联系方式。③Emile Benvenist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Coral Gable: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p.10.从他的分析来看,歌词的表意模式“我对你唱”,决定了歌词话语的意图,是未来向度:因此,歌词的意图时间性朝向未来。雅克布森的文本六功能说中提出:任何文本都有功能偏重。①罗曼·雅克布森:《语言学与诗学》,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9-184页。当代诗更多地追求诗性,即“符号自指性”。而歌的主导功能却落在他说的意动性上,让发送者的情感引发接受者的反应,在两者之间构成动力性的交流。因为歌的意动目的非常明确:希望接受者做出反应(以歌回赠,或以情回赠),希望接受者有所行动 (把歌传唱下去)。歌词的这种对象目的,也使它和当代诗明显分途,因为诗的诉求对象“你”并不清晰,海伦·范德勒甚至认为诗的倾诉对象是“不可见”的。②Helen Vendler,Invisible Listeners Lyric Intimacy in Herbert,Whitman,and Ashbe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3.
由于歌词文本的这两种符号特征,歌能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种内在的时间意图性编织在一起:现在是歌曲表意的演出 (我此刻对你唱)所占的时间;将来是歌曲主导功能意动性 (我希望你回应)所期盼的时间;而过去,则是歌词叙述化后出现的“被叙述时间”。正因为横跨三个时间向度,歌词中被叙述的人物、情节、故事都可以在这三个语义场中自由转换:过去的事件是回溯,现在的事件是“歌唱的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未来的事件是抒情自我希望发生的,希望对方承诺的。时间符码在歌词中的转换,不仅自由而且自然。与小说、电影等记录过去事件的体裁,歌词在这一点上很不相同。在歌词“我对你唱”的基本模式中,时间意图性和人称代词的自由转换,使歌词文本成为一种灵活的符号表意方式。而中国风歌词与众多流行歌曲不同的地方,也正是它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将歌词中的意象、人物、空间,以“穿越”为编码方式,强化了其能指意义。
“穿越”一词来自于目前网络上流行的穿越小说,既指现代人穿越到历史中,也包括古人穿越到今天,今人穿越到未来。刘方说:“穿越小说情节通常是描述一个当代青年遭逢变故,机缘巧合下,进入古代,以在场的方式参与见证了种种众所周知又知之不详的历史事件……这类小说主要受到女学生和女白领的追捧,可以视为言情小说的一个变种。”③章红雨:《作家社12%版税拿下“四大穿越奇书”》,http://www.chinaxwcb.com/2007-07/18/content_ 62533.htm。穿越小说的主题主要是爱情幻想。最早的穿越小说,可以追述到马克·吐温1889年的《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中国公认的第一部穿越小说是台湾作家席绢创作于1993年的《交错时光的爱恋》。而真正引起“穿越”热潮的是近年黄易的历史穿越小说《寻秦记》,在此小说中,主人公项少龙穿越到古代,利用现代搏击打败了许多古代英雄好汉,并用诗词歌赋征服了很多古代公主小姐,成为人们仰慕的一个真正“雄霸”。2007年被网络文学界称为“穿越年”,这一年,《木槿花西月锦绣》、《鸾》、《迷涂》、《末世朱颜》等“四大穿越奇书”被作家出版社以“12%的版税,各10万册的首印量签下”。
当代网络文坛上穿越小说势头正劲,但“穿越”并不限于小说体裁,也不限定于言情主题。“穿越”作为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进入歌词,充分调动了歌词的时间意图和人称主体的符号意义,从而获得了独特的效果。“我对你唱”造成歌词的复杂人称代词关系编码。人称代词是歌词中突出的指示符号。而指示符号的最大特点是引起注意。④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2,p.299.人称问题关联到歌词的叙事主体。托多洛夫对“主体”有个有趣的例解。他说,在“我跑”这简短语句中有三个主体:叙事主体、被叙事主体和被叙事的叙事主体。“跑的我与说的我两者不同,一旦陈述出来,‘我’不是把两个‘我’压缩成一个我,而是把两个‘我’变成三个‘我’”。⑤托多罗夫:《诗学》,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181页。也就是说,歌词一旦唱出来,就出现三层主体“我”:最外层的叙事主体,即歌词先在的此时的叙述框架中的主体,第二层是歌词的言说主体;第三层歌词中人物的行动主体。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三层主体是可以“分裂”的,言说“我”的意识跨越时间三维,希望对方回应;①歌曲“我对你说”构筑模式中的“我”,有点类似于美国芝加哥学派学者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主体。“隐含作者”即隐含在文本中的拟人格形象,它不一定对应作者的真实身份,也就是不一定是词作者本人,也不一定依据某种真实情感事件。从歌曲接受角度来看,“隐含作者”是依托文本期盼被接受者构筑的拟人格作者形象。同一词作者写出的不同歌词作品,往往会有不同的隐含作者形象,就像歌词作者给不同的歌手写歌一样,其中隐含作者并不相同,甚至包含性别上的更换。歌唱主体始终在此刻,因为“我”在表演;而人物主体“我”则可以出现于任何时间,歌可以讲述“我”曾经有过的经历。正由于这三层主体分裂,文本“穿越”到过去才成为可能,在歌这种表演性符号文本中,此种分裂更为明显。在中国风歌词的语意穿越中,使用最多的是以下手法:
1.意象穿越编码。这是中国风歌词中最常见的一种。意象穿越编码,即将许多不同语境中的古典意象符号组合在一起,在保留古典意境的同时,重构成新的语义。比如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原唱的《东风破》:“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此歌词的中国古典风格,主要表现在其“历史意象”。当代学者张海鸥在研究宋词时,曾提出“意象叙事”概念。他认为,意象即为因象寓意,当一个意象隐喻某事时,它便具有叙事意味,尤其当意象的文化积累使之成为原型意象后,就更有某种类型化叙事的意味。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杨柳依依隐喻离别情事,孤鸿飘渺通常隐喻怀才不遇,秦楼月落隐喻深闺寂寞等等,②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这些意象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这种“意象叙事”,实际上是调动了意象符号的文本间性,促使读者在阅读中对文本进行附加解码,不只仅仅读出一段爱情故事。譬如,此歌题“东风破”,会令人与陆游《钗头凤》中的“东风恶”联系起来;“酒暖回忆思念瘦”让人联想起李清照《醉花阴》中的“人比黄花瘦”;“水向东流”当然来自李煜《虞美人》;“琴声幽幽”令人联想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意象能激发出歌众积累的与之相关联的各种文化印记,包括我们熟悉的文人生平故事等。但当它们一起涌出时,就会造成对现有歌词理解的混乱,破坏主题的集中性。然而,这首歌词正是通过意象符号在不同语义场中的穿越,故意制造一种编码的混淆,让我们在试图理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故事时,在历史文化维度上,产生了“回”与“不回”或“回不去”的矛盾心理。
意象穿越编码最密集的,要数郭敬明作词、刘佳和严丹丹作曲、李宇春原唱的《蜀绣》:“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缝韶华红尘千帐灯/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伊人倚门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此歌用了十一处不同时期的古典诗词意象,构成复杂的互文性:“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化用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羽毛扇遥指千军阵”化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羽扇纶巾”;“看铁马踏冰河”化用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铁马冰河入梦来”;“红尘千帐灯,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化用纳兰性德《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六月杏花村”化用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化用陆游《钗头凤》 “红酥手,黄籘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等残阳照孤影”化用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江河入海流”化用王之涣《登鹳雀楼》“黄河入海流”;“万物为谁春”化用纳兰性德《画堂春》 “相思想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化用晏殊《蝶恋花》“明月不谙离别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如此等等。这些意象符号分别来自唐诗、宋词、清诗词,让人觉得处处耳熟能详,却又支离破碎。如此大的时空跨度和复杂的语义场和意象,为什么编织到一起并没有损坏故事和情感的完整统一,依然让我们清晰地读出一个女子执著等待出征夫君归来的故事?原因正在于它将原文本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连接,获得艾科所说的新的“使用效果”:“有时候,使用文本意味着把它们从以前的阐释中解放出来,发现它们新的方面。”①Umberto Eco,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62.
2.人物穿越编码。人物穿越是中国风歌词中最明显的编码方式。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娘子》极为典型:“娘子却依旧每日折一枝杨柳/在小村外的溪边河口/默默的在等着我/家乡的爹娘早已苍老了轮廓/娘子我欠你太多/……娘子她人在江南等我/泪不休/语沉默”。这首歌与上面引用的《蜀绣》,同样是等待主题,但使用的更多是是人格分裂穿越,而不是意象移用,从而强调了人物主体:一个男子“我”的江湖闯荡漂泊,反衬“娘子”“在江南等我”的动人美德。一个现代的“我”和一个远古的“娘子”连接在一起,只有“穿越编码”式的叙事才能编织成如此文本。正如上文所说,在“我对你唱”歌词基本传达框架中,演唱者“我”作为言说主体,只能留在此刻,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到达未来。但歌词中被叙述的人物“我”可以通过穿越,跳过时间障碍,进入不同的语镜。穿越叙事制造的情景越特殊,编码的张力就越强烈,就越能达到歌曲的意动性的效果。此时,“我”就有可能变成所有人能感觉到的心中自我:听众及传唱者都加入了这个去会见“娘子”的“我”。
3.空间穿越编码。应该说,不管是人物穿越,还是意象穿越,都已蕴含了空间穿越。按巴赫金的观点,叙事文本中的任何时间,都是一个“时空体”(Chronotope)。②Mikhail Bakhtin,“Form of Time and Chronotope in the Novel,”In Michael Holquist(ed.),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pp.84-88.但中国风歌词中突出“携带历史意味”的空间符号,以此强调穿越的特殊意境效果。比如张超作词作曲、凤凰传奇演唱的《荷塘月色》:“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 /弹一首小荷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地望/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此歌题首先会令人想到1920年代朱自清的经典散文,歌词虽然没有直接化用中国古典诗词,但整首歌却建构了一个脱离现实的符号场:“淡淡荷香”、 “美丽琴音”、“姣白的月光”、“水中的鱼儿”等,营造的是一个远离红尘的纯净浪漫美好世界。而这些意象符号,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自然,清淡幽雅的审美风格契合,所以它依然是一首具有浓郁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歌曲进入的是一个时代并不明确,但这个世界显然超越于当今红尘万丈的现实之外,是个“虚拟古典世界”。
总结以上三种主要穿越编码方式,可以发现,符号表意远远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还贯穿着伦理精神。穿越编码实际上是将人类的情感经验重新组织,从而编织成一个暗含自己价值、情感及道德态度的符号意义文本。文本显示的情感,可以是静止的意象符号,可以是零碎片段缺少连接,接收者可以凭借他们的文本间性经验加以连接,以他们的再度叙述解读出情节。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风歌曲要用这种穿越编码?尤其在以情歌为多数的中国风歌曲中,这种编码策略又蕴藏着当代中国人怎样一种性别诉求?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当了解这种穿越编码的意义效果。
正如上文举出的“意象穿越”例子所示:歌词文本可以没有情节发展,其词句描写可以是静止的、片断的,但歌众的解码能力能把它扩展成为比较完成的故事,因为意象符号本身具有“扩张性”,即引发联想的能力。接受者对这些意象穿越进行再度叙述化,在想象中构筑一段浪漫情节。维特根斯坦在讨论语言符号意义时,观点尖锐却深刻:“别寻找意义,去寻找用法。”③转引自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符号意义正包含在符号的使用中,包含在语言的实现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中国风歌曲通过不同形式的穿越编码,凸显它们在当代的使用意义:当代人在现代生活对情感的压力下,通过现实和幻想交错,表现出对古典性别伦理的想象和诉求。
中国风歌曲文本中,不管是男唱文本,还是女唱文本,首先都通过不同的穿越编码方式寄托了男性对女性古典气质的诉求,突出女性古典气质的符号性别角色。比如屈塬作词、孟庆云作曲、曾静原唱的《一梦千年》,讲述的是一个“粉面含羞”的温柔典雅的“闺中少女”:“一样的绿肥红瘦一样的月如钩/声声慢的心事有谁猜得透/宛约的宋词是一杯线装的酒/一醉千年至今粉面含羞”;《蜀绣》中出现的是一个“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甚至“来世与君暮暮又朝朝”的贤妻形象;《娘子》则是“每日折一枝杨柳”,“在江南等我”的理想式忠贞化身。而周迪作词、王子鸣作曲并原唱的《我的林黛玉》,则更直接写出了男性对曹雪芹笔下女性古典气质的向往:“黛玉/牡丹/你的脸/这故事曾经感动着你和我/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十里山坡/后面有一汪清泉/云到这里/也缠绵/你含情脉脉的眼就像一朵牡丹/我看你千年万年也不会生厌”。
男女性别特质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中国古典女性气质,也是一种文化建构,或者说社会想象。但悖论是,为什么古典女性性别身份再次回流,并成为当代男性的性别诉求?通常歌曲中的男女形象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对峙和互塑关系,两个主体之间互映出的,不是对方的实际形象,而是男女不同的性别渴望,也就是心理符号特征。我们幻想对方,然后用对对方的幻想检验自身。与“古典女性”幻想同时产生的另一种“回归”,便是中国风歌曲中的男性气质符号的重新建构,这实际上也是当代文化想象对男性气质缺失的心理补偿。就像任贤齐作词作曲并原唱的《少年游》中所表达的:“翩翩一叶扁舟载不动许多愁/双肩扛起的是数不尽的忧/给我一杯酒喝尽人间仇/喝尽千古曾经的承诺/美人如此多娇英雄自古风流/纷纷扰扰只为红颜半点羞/给我一杯酒烽火几时休/喝完这杯一切再从头/江山仍在人难依旧”。从第一人称指示符号强化的演唱者立场,歌词一次次出发,将“我”的幻想送到“古代江山美人”的异样符号语义场中。似乎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男性阳刚气质,只是对着“红颜”而来,其余的“千古忧愁”只是助酒的空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直是中国传统男性文人志士的两种生存理想,但正如歌中最后一句所唱“喝完这杯一切再从头,江山仍在人难依旧”,这种“进而不得”的矛盾心理,充分展现的是当代男性面对现实情感的失落和无奈。
不管是对女性古典气质的符号诉求,还是对男性阳刚气质缺失的补偿,回归“古典意境”,似乎成为当代男性女性共用的一种性别“自我疗伤”方法,以此治疗现代化性别关系变异过程中留下的伤痕。符号学讨论意义时,特别强调符号的社会性使用:“不是符号给使用以意义,而是使用给符号以意义,使用本身就是意义。”①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尽管歌的流传,有着类似于时尚的同化机制,也就是常言说的“跟风”,但歌曲有其特殊的个人选择接受机制:歌曲必须与歌者的特殊体验关联,才会被歌众接过去开始社会性的流传。歌众不可能将意义权全部出让给商业法则,相反,因人而异的情感选择,会超越时尚的“分化同化”悖论,提出自己的主体诉求。如同克兰的分析,“如果一个文本的话语符合人们在特定的时间阐释他们社会体验的方式,这个文本就会流行起来”,这种“流行”还必须“产生于共识程度很高以至于这种共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话语领域中”。②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98页。“中国风”的流行,不仅是作为一种歌曲风格的取胜,还在于它包含了宋玉《风赋》中所含的社会象征意义:“夫风者,天地之气也”。自古以来“风”,总是和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及审美需求联系在一起。就如当代学者陶东风所说:“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与精神气候的写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因而也就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它表达了社会想表达又表达不出的真实情感。”③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在当代社会性别文化急剧变迁过程中,现实和想象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对称。中国风歌词正是通过它特殊的编码方式,在当代文化转型时期,表现着大众对具有古典审美倾向的性别伦理诉求。符号学的一条最基本的悖论是: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④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46页。正因为当代社会的女性,已经不可能再被囚禁于这些传统品德之中。温顺、贤淑、耐心、坚贞,这些女性特征在现在被认为已经过时,甚至被认为是传统道德对女性的压迫。而在相当多当今男性看来,这些已经缺席的品德非常值得怀念。
因此大量古典气质的女性性别符号进入了歌曲,被男性歌众有意识地呼唤,也被女性歌众不自觉地歌唱。中国古典风格的歌词,一方面回归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也在回归传统的道德价值,回归传统的女性角色。这点可能是赞美中国风歌曲的论者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中国人作为“文化的人”,几千年来性别关系中代代相承的意义方式,不可能彻底抛弃,文化中的集体潜意识,在每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中,总会曲折、但不可阻挡地表现出来。尤其在当代社会复杂的语境中,性别关系受到各种新的社会文化因素困扰,性别文化的走向,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歌曲这种艺术幻想领域,与现实的关系往往是相反方向地互动,歌曲的符号意义,会依从人们对缺失的感情需要,对当代性别文化作出补缺式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