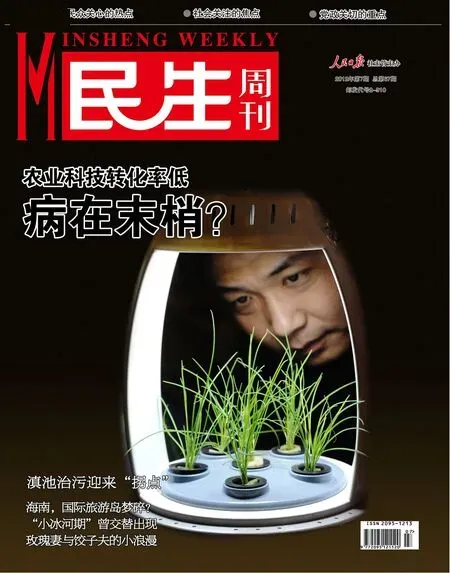“大义父亲”的背后
□ 张子琦
“大义父亲”的背后
□ 张子琦
六年间,胡文传经历了人生两次大的选择,在生死得失之间,困顿坚强背后,是一颗质朴有爱的灵魂。

2007年3月12日,胡文传吻别自己在世仅47天的小女儿。当晚,他刚刚夭折的女儿接受了眼角膜捐献手术。
在2012年的春节晚会上,主持人接连介绍了几位道德模范,其中对胡文传的介绍是这样的:“为了救落水的孩子们,痛失自己的孩子”。
在生命的天平上,倾向自己的血亲是人类最为本能的选择,放弃自己独子的生命,让很多人对胡文传不解甚至产生非议。
曾经采访过胡文传的央视主持人柴静事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不清楚原委,就不易明白这人(胡文传)站起时的艰难,脸上的意味,同情敬惜之心就不容易有。”
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公众很难了解事件的全貌,误解就显得不可避免。胡文传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他到底是一个“冷血”父亲,还是“大义”父亲?
“爸爸来世抱得你”
2002年6月8日,胡文传带着自己的独子胡凯明去家附近的池塘捉螃蟹。看见儿子头上沾满了泥,于是就让儿子去村里的大水塘洗洗。没过多久,正在做饭的胡文传听到“有人落水了”的呼救声。
听到呼救声,胡文传向一百米以外的水塘跑去,水面上有五个孩子在挣扎,儿子胡凯明在距离河岸最远的位置,他能看到儿子的头,儿子一声“爸爸”没喊完就沉下去了。
胡文传连鞋子都没来得及脱就跳下水,向儿子游去的时候,却被其它几个落水的孩子抓住。“这几个孩子有扯我肩膀的,有拉我衣襟的,还有一个孩子沉底了,我从水底下扯了一把把他捞上来。”
此时的胡文传也没有能力带着4个孩子游向自己的儿子。是掰开这些“阻碍”自己游向儿子的手,还是将这几个孩子送上岸,再救自己的孩子?
“儿子,坚持住,我能找到你。”胡文传向着儿子消失的方向大喊,转身带着四个孩子游向岸边,“我不是不想救我儿子,但孩子太多了。”
当胡文传再次跳下水时,池塘已经归于平静,什么也看不见了。当晚10点多,胡凯明的遗体才被闻讯赶来的村民们合力打捞上来。孩子抱住了一块石头,沉到了塘底,两只小手里死死地攥着两团塘泥。
对于胡文传来说,这是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细节,“他离岸边很近了,再向上爬一点,他就上来了。”
面对已经没有体温的儿子,胡文传“连站也站不住了”。那一刻,胡文传不是“勇救落水儿童”的英雄,而是一个痛失爱子的平凡父亲。
当夜,失去了唯一爱子的妻子精神失常,一度不能原谅丈夫。甚至很多村民也不能理解他,“先救自己的孩子”是很多村民们的第一选择。这个曾经幸福的小家庭顷刻间地覆天翻。
胡文传和妻子一个星期没有出家门,亲戚朋友,被救家庭的人守在门口,他谁也不让进门,亲手为儿子做了一个简易的棺材,把儿子读过的书,得过的奖状一并放在里面,葬在了池塘另一边的小树林里,与自己的家隔着池塘相望,下葬时,他把家里仅有的两床被子都盖在儿子的身上。“他死去时什么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觉得心里愧疚。”
夜里,他和妻子只能依靠旧棉絮取暖,安眠药成为他的必备品,愧疚和痛苦让他无法入眠,只能抓着床下的干草,“把草都抓起来”。
他卖了家里的一百五十斤稻子,给儿子刻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刻着“坟前流下千滴泪,悼念爱子寄九泉”。
胡凯明的遗照是儿子长大之后唯一的一张照片,是儿子自己到县里的照相馆拍的,相片中的小凯明很英气,眉眼之间透着少年特有的勃发朝气。相框边上,胡文传亲手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爸爸来世抱得你。安息吧?生存者不是幸存者。爸爸的生命与你紧紧联系。”
“当时我要有选择的话,把他救过来,自己去死都可以。活着的人内心承受的要……”他在“安息”的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是愧疚,这个问号是给我的。他得到安息了吗?”
接下来的日子里,胡文传先后被授予了“安徽见义勇为奖”、“安徽省道德模范”、“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每一次去领奖、做报告,他都会泪流满面,内心备受折磨,“如果我的孩子还活着,这份荣誉值得骄傲,我会高高兴兴的去演讲,可是我的孩子没有了,我亏欠他。”每一次说起,都不啻于一次对善行的煎熬,即便如此,胡文传仍愿意去演讲、作报告,因为对于他来说“可以痛哭一场,也是一种发泄。”
“当时我要有选择的话,把他救过来,自己去死都可以。活着的人内心承受的要……”他在“安息”的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是愧疚,这个问号是给我的。他得到安息了吗?”
“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时间不能抹去胡文传内心的悲痛,但2003年,女儿胡秋月的出生却多少挥散了弥漫在这个家庭里的哀伤。五年之后,他们的二女儿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再次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
这个小女儿和哥哥胡凯明一样出生在腊月,为了纪念哥哥,安慰妻子,胡文传给女儿起名李明娜。他还特意装修了自己简陋的家,“第一次,结婚时也没有装修。”
然而,命运却没有垂怜这个经历苦难的家庭,李明娜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患者,2007年除夕夜,他把小明娜搂在棉袄里,说:“你要坚持,爸爸带你回家过个年”。这个刚刚降临在人世间的生命以微笑回应了他。
“这是她第一次笑,也是唯一一次。”在漫天大雪中,他和妻子步行十几里路,去废品收购站买了张旧婴儿床给孩子。孩子难受的睡不着觉,他和妻子就用小被做成摇篮,拴在这个破旧的婴儿床上,摇她入睡。
大年初五,这个来到世界47天的生命终结,他和妻子再次痛失爱女。
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决心留住自己的孩子,以他能想到的方式。胡文传决定捐献孩子的眼角膜捐,捐献的时候,连接收的机构都找不到,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把她的命留下来”。“如果不捐献,我就会永远失去她。”
最终,女儿李明娜的眼角膜让两个人重见光明,在胡文传的心里,女儿的生命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这个世界上。
经历过女儿的眼角膜捐献过程,他知道中国每年有约150万患者等待接受器官移植,可惜只有1.3万人能有幸实施手术。全国十个试点城市中,南京被曝至今无一例自愿捐献,2011年,全国只有不足100人完成了器官捐献。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胡文传想自己创办一个慈善组织,给眼角膜等器官的捐受双方提供一个公益的平台。
他自己只是一个农民工,住在三十多平米的房子里,连张写字的桌子都没有。却承担了这样一项重大的社会责任。“是我的孩子让我走上了这条路。把这个愧疚的,愧疚儿子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吧。”胡文传哽咽着说道。
至今,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找到胡文传,希望得到器官捐助,也有很多无钱治病的人希望通过他得到捐款,胡文传经常因为他的“不忍心”去帮助这些人。在他工资只有七百元时,有时候甚至拿出两百块给更穷的做不起手术的人,“我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是我的孩子让我走上了这条路。把愧疚儿子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吧。”
“幸福的感觉”
在采访中,大女儿胡明月拿出一张画在胡文传用工合同背面的“全家福”,上面有他的爸爸、妈妈、自己、她无缘得见的哥哥和只相处了十几天的妹妹。妹妹的头上画着一顶王冠,还有一对小兔子的耳朵,“妹妹喜欢小兔子”。没有缘由,胡秋月觉得自己的妹妹喜欢小兔子。画面上是五个人手牵手,她说:“五个人在一起是幸福的感觉。”
童言无忌,年纪尚小的秋月也许还不能真正体会到死亡的意义。这个孩子是胡文传的唯一慰藉,再多的荣誉、奖励,都弥补不了他对于失去一双儿女的愧疚和痛苦,在孩子面前,胡文传不是英雄,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而已。
央视主持人柴静在采访完胡文传之后,在自己的博客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心的事,没有经受过的人,往往想不到,所以还是留些敬畏,如得其情,哀矜为宜。如果褒贬相激,都只依据简陋的事实轻易评判他人,流于武断,有了戾气,话象车轮子一样从人心上辗过去了。时间长了,把心都硬化了,碰上什么事都进不去,象在水泥地上一样流过去了。”
亲人的责怪,村民的不解,内心的愧疚,十年来,胡文传承受的苦,只源于他的“不忍心”。不忍心推开扒在他身上孩子,不忍心让女儿孤独离世,不忍心看着不幸的陌生人得不到救治。
依靠着这一份“不忍心”,胡文传开始了他的公益之路,也许前路漫漫,荆棘丛生,甚至他会遇到“此路不通”的牌子,但对于胡文传来说,有一天,他可以将儿子遗照上的“安息吧?”的问号去掉,他所有的努力便都是值得的。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于中央电视台《看见》栏目)
□编辑 张子琦 □美编 庞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