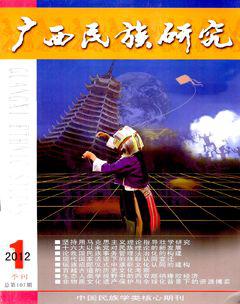瑶族招郎仪式中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
[摘要]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族群互动日益频繁的当今世界,生存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族群,既要维持族内的文化认同,又要接纳强势的外族文化,才能确保本族的正常生存与发展。如何抉择并保证两种甚至多种认同互不冲突,招郎仪式对此做出了明确回答。仪式中展示的建构族内、族际文化认同的方式方法,体现出瑶族群众充分利用各种场所和可能建構族群文化认同。它是瑶族在主动适应社会变迁的同时,又灵活保存本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键词]瑶族;招郎仪式;文化认同;认同建构
招郎,也称入赘、上门,是男子到女方家中成婚、居住的一种婚姻习俗。在我国的许多民族当中,历史上某个时期都曾经存在过,只是普遍与否的问题。即使现在,汉族中也偶尔会有入赘的事情发生,不过难得一见而已。然而,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居山族群中,入赘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存,并未因社会经济发展和与外族交往程度的加深而消失。吴秀芳的瑶族入赘婚初探(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第2期)、玉时阶的泰国瑶族的“招郎入赘”(世界民族,1998年第4期)等对瑶族入赘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侧重于形式和原因的分析。本文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高宅村委会的FMP瑶族自然村为例,通过对自然环境的考察,结合当地群众对入赘习俗的认知、理解,分析“招郎”仪式中的某些程序和展演过程,探讨仪式中建构族群文化认同的问题。认为在新的形式下,伴随着族际互动的频繁、加深,居山族群的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强大的外族文化的冲击,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业已存在的现实需要,仪式过程也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在认同主流文化的同时,始终重视强化对本族文化认同的建构,希望借此传承本族文化的精华。
一、瑶族的招郎习俗
瑶族自古就有招郎入赘的习俗。《评皇券牒》、《过山榜》、《过山文书》等瑶族的著名历史典籍,都有记载盘王子孙六男六女,“敇令六男娶外人之女为妻,以继其后;六女赘外人为夫,以继其宗”的材料;而且,通过皇帝的权威发布敇令,“准令民不许娶瑶女为妻,不许百姓土家为婚;盘王子女,不嫁五姓国汉土家”;但是,对于能否招外族男子入赘,则没有明确规定。所以,瑶族女子在招郎时原则上没有民族身份的限制,总体上有比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这也许是居山瑶族“招郎”婚能够长期保存的理由之一。加上瑶族招郎婚形式多样,并且得到族内成员的认同,使之得以长期存在。根据《富川瑶族自治县志》记载,居住高山的瑶族招郎婚有四种类型:一是卖断,男子上门后,一般要改同女方的姓氏,并规定要终身在女方的家中居住与劳动,不得回自己家中做事,所生子女随母姓;二是卖一半,男子到女家后,姓名可以改也可以不改,但要终身居住、劳动在女方家,婚后所生子女可以给一、二个随男方姓;三是两边走,婚后,男方先入居女家,在女家劳动、生活一段时间后又带着妻子儿女回男方家劳动、生活一段时间,并如此不断打循环下去,所生子女平均随父母姓,一般是第一个随母姓,第二个随父姓,依此类推;四是招郎转,男方到女方上门后,男方要在女家劳动、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带着妻子儿女回转男家定居,不再转回女家,婚后所生子女全部从父姓。[1]同时,为了确保婚姻家庭的稳定,每种类型都立有文书契约加以规范。这就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瑶族招郎婚制度。
考察点南岭走廊中段西岭山FMP瑶族村,是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高宅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村民居住在海拔800m~1 000m的鸟源山山腰上,北面1.5 km处有一座鸟源水库;西北与小源下自然村相距约2km;东南约1.8km与朝木林自然村相接,往西翻过一座约1 500m的高山后,可到达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牛塘村,东面与狗婆垒自然村接壤。全村26户163人,包括冯、俸、周、黄、李、赵、郑七姓,瑶族居民占95%,属瑶族盘瑶支系的过山瑶。村子周围,竹木茂盛,景色优美,山冲小溪清水长流,是鸟源水库的水源林地;山上林木葱葱,百年古树以及藤蔓遍地存在。村里的老人介绍:他们的祖先几百年来一直在都庞岭游走,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才在FMP定居下来。目前该自然村拥有2万多亩山林,人均林地约100亩,但没有任何农田,主要靠刀耕火种和林业维持生计。虽然环境如此险恶,但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开辟有林区公路与外界相接,现在则修建有一段混凝土道路,虽然没有全部完工,但可以通行农用车、摩托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与外界交往的程度已经较为密切,外来文化也深深渗入到本来极其单纯的瑶族文化之中。
调查发现,生活在这一区域的过山瑶族群,女子70%以上招郎上门,男子50%以上上门入赘。生存其中的上门女婿,与本地娶妻男儿在地位上已经平等,有财产继承权,生活中不存在明显差别,不需要改名换姓,孩子可随母姓,也可以跟父姓。被招郎的男子,有汉族、壮族,也有瑶族。从FMP村的情况看,入赘男子三族都有,地域上以附近的恭城县瑶族为多,也有江华、江永、钟山以及本县的壮、汉、瑶族群成员。由于入赘成员比较复杂,因而相关仪式也就显示出独特的风格。
2010年9月16日至18日,我们有幸参与了FMP村的一场招郎婚礼,三天的仪式隆重热烈,让人联想颇多。其中使我最为震惊的是仪式中族群文化认同建构的过程。原因是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瑶语,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讲汉语西南官话,并在对外交往时使用。可是在正式场合的婚礼上,主持者既使用瑶语,又使用汉语西南官话,两种语言在仪式中交叉使用。至于其它婚礼物品,如食品、用品、礼品以及相关仪式,无不体现出本族与外族相互兼容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族内、族际文化认同建构的特征。
二、招郎仪式中族内文化认同的建构
“招郎”婚俗是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着丰厚的历史、心理、情感等文化要素,具有相对的保守性和稳定性。但是,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运行模式、社会文化互动的变迁,又无法阻止新生的特别是外族政治、经济、文化对它的渗透,并使之发生相应变化。FMP村的招郎仪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的。虽然仪式中融入了众多的外族文化成份,但整个过程处处闪烁着女主人的果断、精明,恰如其分的指挥、安排,井井有条,体现出明显的通过婚礼仪式建构妇女主导地位及其对瑶族文化认同的特点。
从婚宴的食品看,保留着当地居山瑶族传统的不少特色。首先用“油茶”招待所有参加婚礼的宾客,但配食“油茶”的食品一定少不了山区传统的主食——炒玉米。它是通过“刀耕火种”方式生产的,粒小、香脆,必须是自产,不能到市场购买,充分显示出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认可。其次餐桌上的主菜不能缺少的是竹笋、香菇、木耳,体现出婚宴食品与山的联系;同时,猪肉也不需要到市场上购买,主家不足部分,可以向邻居、亲戚家借用,以后再还,期间不用支付利息,是一种互相帮助的瑶族传统美德。再次,饮用的大量米酒,由家主自己酿造,米可以到市场购买,但酒则不行,这与瑶族居住高寒山区必须继承酿酒技术有关。然而最有特色的是,该村酿酒的许多工序由妇女来操作完成。因此,餐桌上的传统食品充分体现出婚礼上瑶族建构对本族传统文化认同的特点。
从婚礼的饰品、礼品看,也保留着不少瑶族传统的风格。最为显眼的是服饰,仪式中家主、瑶族老人、瑶族客人以及已婚的瑶族男女,都尽可能穿戴本族衣装,以便外人分辨其族群身份。祖宗灵位的布局、装扮,一律按瑶族传统的风格实行;相关房屋的布置、安排、宴席装饰、门口饰物、新房的布局、床上用品都有瑶族传统的东西摆放。新娘的服饰虽然已经与汉族无异,但围裙却是瑶族的手工织物。仪式主持者身上穿戴着瑶族传统的装束,确保其瑶族成份的显著。派出去迎亲的姑娘小伙,穿戴着特色标识,使外人可以从中辨识出这是一场瑶族举办的“招郎”而不是娶妻的婚礼。对于参加婚礼者赠送的礼品,如果没有瑶族习俗标识的,待客者会给其加上带有瑶族习俗的标签,使其符合瑶族仪式的要求。而娶妻仪式中的礼品则不在乎是否标识瑶族族群的身份。这种从礼品开始标识族群成份象征物的做法,是当地瑶族建构族内文化认同不可缺少的步骤。
从仪式的过程看,也体现出建构对瑶族传统文化认同的格调。首先是拜堂,仪式主持者先用瑶语解说,然后进行跪拜,期间新娘必须向新郎敬酒三次,但不喝交杯酒,然后要新郎学着用瑶语讲话。对客人敬酒,较为重视再现瑶族传统的习惯。不会说瑶语的新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走到每一张餐桌前,主持人说一句瑶语,需要跟着说完,然后客人才会举杯喝酒,這是建构新郎对瑶族文化认同并使之融入集体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在当地的娶妻仪式中则没有建构语言认同的敬酒、拜堂之类的语言解说。对于仪式过程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晚上对歌,即新郎方的送亲队与“娶”新郎的女方家族及参加婚礼的男男女女进行的对歌。“歌”的主体内容是传统的瑶族情歌。然而,由于现在能够唱瑶族歌曲的人越来越少,但仪式中又必须用瑶语来唱。为此,年老且能够唱瑶族歌曲者只能带头领唱,一句一句地教会年轻人,或者先教唱,后对歌,通宵达旦。其目的在于建构年轻一代瑶族群众对瑶族传统文化的认同。
整体而言,从瑶族的角度思考,那些来自传统的规定、习惯,虽然受到了当代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但其生命力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招赘的男子,不分种姓,但求情投意合,便可成婚,使瑶族不仅延续了自身,而且极大地拓展了群体规模,增加了通婚的对象,对于瑶族人口体质、素质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整个招郎仪式还充分体现出妇女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果断性,仪式中的各个环节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出对瑶族传统文化的眷恋。无论是有形、有声和可视、可闻的物品、对歌,还是无声的食品、服饰、装饰,他们无时不在默默地塑造并期盼着建构对瑶族传统文化的认同。
三、招郎仪式中族际文化认同的建构
招郎仪式与娶妻仪式存在一定差别,其原因在于“郎”不一定是本族的,可能完全不懂瑶族习俗,“送嫁”者也可能是外族的,因此有必要建构对他们的文化认同。更何况,前来参加婚礼仪式的人,有不少是不同文化群体的,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展示瑶族与他们文化的近似性,可以为将来的“招郎”拓宽范围、创造条件。所以,招郎仪式中体现的是双重文化认同的建构。
从婚宴的食品看,在保留瑶族特色的同时,已经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成份,远远超越了瑶族传统的食品范围。首先是配喝“油茶”的小吃,增加了山外市场上出售的饼干、薯条、五香花生及各种油炸类食品,糖果、红瓜子、葵花子之类也搭配其中,明显地体现出与山外市场接轨的趋势。其次是婚宴上的食品,已经远远超出山区瑶族传统食物的范围,主菜至少增加了米粉丝、青蛙、海虾、鱿鱼、墨鱼之类;饮料食品也丰富了许多,除了传统的米酒以外,啤酒、橙汁、可乐之类都已登场。而且,宴席的丰盛程度绝对不亚于当地娶妻的花费,与传统招郎相比,其开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瑶族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后建构对山外族群文化认同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一个主动接纳的建构过程。
从婚礼的饰品、礼品看,也融入了大量外族文化的风格。首先是服饰、装饰:一眼望去,参加婚礼者的衣装多种多样,市场上的各类秋装几乎都能在此看到,除了一些刻意标识的民族服饰外,与其他民族已经没有明显区别,这是族群文化相互整合的重要标志。房屋里里外外的布局、装饰,大体上融入了周边族群文化的内涵。从布蓬、接待客人的桌椅装饰到门口对联,其用料、图案、放置位置、礼品登记乃至公榜,都充分体现出与周边族群文化互化的特征。其次是新郎服饰。新郎来自邻县的恭城瑶族自治县,瑶族成份;此时的穿着打扮是白衬衣、红白相间的丝绸领带、深色西装长裤、腰扎苹果牌皮带,完全是一个山外汉族时髦青年的打扮,没有任何一点象征瑶族身份的物品,是地地道道的汉族“新郎”装束。再次是“陪嫁”的物品,由于路途遥远,虽然数量不多,但有摩托车、常规家用电器以及来自市场的毛毯等,但没有打上任何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从中看不到任何瑶族的传统风格,已经完全与周边族群文化相融合了。所以,招郎仪式展示的各种物品,充分体现出当地瑶族主动认同主流文化、与周边族群文化认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是族群文化长期互动、吸纳、相融的结果。
仪式过程中,也体现出建构瑶族认同周边族群文化的格调。首先是迎新郎:新郎乘车到山脚后,由于道路不通,只能下车步行;迎亲队一拥而上,伴随鞭炮声,前面开路的是“鼓手队”,接着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撑着不锈钢架构的红色太阳伞为新郎遮“光”,紧随其后的是送亲宾客,最后是搬运礼品的帮工。这种形式与当地周边族群娶媳妇的仪式是一样的,没有明显差别。其次是拜堂:既然是“招”来的郎,那么需要先拜祭女方的祖宗,接着是女方的父母、宗亲,最后夫妻对拜,其形式与汉族娶妻拜堂相似;只是司仪在用瑶族传统语言主持的同时,又不厌其烦地用汉语方言进行解说,其表现出的礼节似乎也与当地周边族群相同,是山外族群娶妻仪式的翻版,体现出建构与周边族群文化认同的现实场景。再次是酒席,所用桌子方圆相兼,其摆设风格与山外族群基本相似,主客厅一律使用八仙方桌,八人一台,设四席,能座其中就餐的,是女方家庭的至亲和尊贵客人,是最重要的待客场所;周边厢房是普通客人的就餐场所,桌子有圆有方,客人有多有少,十人、八人、六人都有,主人也不介意;上菜吃饭也先主后次,从主厅开始,然后轮到旁边,从左到右。展示的是以汉为主、以瑶为辅的文化风格,体现出明显的对周边族群主流文化的认同。
整体而言,整个招郎仪式中,虽然瑶族的女方家庭想方设法保留一些传统的文化习俗,也在许多程序上进行标识与尝试,但毕竟要与时俱进,必须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吻合。所以对歌时往往瑶、汉双语都有表现,既有瑶族情感,也有汉族情调,甚至流行歌曲也被放置其中。因此,整个仪式从始至终都存在着建构对周边族群文化内容的认同。
四、招郎仪式建构族群文化认同的思考
仪式是一种文化表达,无论承认与否都会存在着有形与无形的目的,招郎仪式也是如此。尤其是历史上这一区域对招郎入赘婚姻的歧视性建构,使外人对“郎”始终存在着“贬低”的习惯性思维,“困难的方去上门,不困难那个愿去”?“来的总是受气的多”。[2]因而对于普遍招郎的过山瑶族群来说,仪式的办理既有展示财富的一面,更具有建构文化认同的现实意义。从FMP自然村的招郎仪式考察,其丰盛与热闹程度并不亚于山外族群的娶妻仪式,在传承过山瑶招郎传统习俗的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无形中激活了沉淀数百年来期盼民族平等的心态,也是过山瑶族群建构对山外主流文化认同的无声期盼与展示。
我们知道,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多族群杂居的区域,都需要建构区域性的共性文化认同,才能确保区域族群关系的和谐。如何达成文化认同,需要各个族群共同构建,并通过日常生活的行为、行动加以落实。招郎仪式中多元文化视角的展示、解读与陈述,既有建构族内文化认同的一面,又有建构族际文化认同的良苦用心。仪式中展演的内容,主要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项,既有规定程序,又可灵活调整;既充分反映过山瑶族群的文化变迁,特别是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基础以及与外族互动导致的变迁;反过来又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哪些通过主持人有操控性的展演,在快乐、欢笑的氛围里欣然接受不同族群文化的熏陶,使族内和族际文化认同的建构朝着可预见的、限定方向和有序的变革,既承传本族群的文化,又建构对新文化即对他族文化的认同,使之与周边族群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要求相适应。这是文化塑造仪式、仪式传承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具体体现。
当然,FMP自然村的过山瑶族群举办的“招郎”仪式,与传统的同类仪式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革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外族交往、交流加深、与认同并接受他族文化息息相关。当外来经济生活与思想文化在本族群成员中产生积极影响后,族群成员和族群精英就会想方设法打造在某种程度上与本族文化相吻合的新文化。仪式中的不少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频繁发生。如能说、讲和听懂瑶族语言的人口越来越少,在仪式上使用外族语言进行解说已经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仪式中瑶族语言的使用,最明显的目的就是告诉入赘者,以后必需学会讲瑶族语言。所以,到当地入赘的所有男子,一、二年后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这是建构对族内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仪式中的展演,也反映了瑶族文化消失过程中瑶族群众矛盾的心理,既要努力维持,又被迫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既是维持的需要,又是发展的需要。因此,仪式的多重表述是民间族群文化传承中自我调节与适应的表现形式之一。
整体而言,招郎仪式的展演过程,事实上也是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只是仪式中建构的族群文化认同,与历史上仅仅强调族内认同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仪式中展示的文化变迁与建构对他族的文化认同,是被当地人认可、接受并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不仅符合本族在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文化变化的需要,也适应了周边族群认同、了解该族群文化的各种诉求。同时,从过山瑶族群自身的角度思考,主动建构并认同周边族群的文化,可以减少与主流文化的差别,降低族群互动成本,具有与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某种合理性与适应性,是族群互动过程中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族群认同主流文化的表现之一。接受仪式熏陶的参与者,一方面可以感知建构对瑶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减少甚至弥补族际文化差异的鸿沟;另一方面又可以体会到瑶族主动接受并建构对周边族群及主流文化认同的的积极性、创造性。所以,招郎仪式具有建构族内、族际文化认同的双重功能。同理,无论家族、宗族、族群还是地方政府,在民族地区举办各种仪式,也具有建构族群文化认同的多重功能。
参考文献:
[1]盘承和主编: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88~489.
[2]廣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139.
Construction of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about Yao Door-law Ceremony
——An Example to the Xiling Mountain FMP Yao Village in the Middle of Nanling Corridor
Wei Haoming
(Humanity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Hezhou College ,Hezhou 5428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thnic groups interact increasingly frequent ,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normal famil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live in the same region ,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tribe's cultural identity, but also to accept a strong alien culture. How many choices and to ensure recognition of two or more do not conflict, we can find clear answer in Door-law Ceremon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ibe, inter-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of ways in the ceremony reflecting the Yao people may take advantage of a variety of sites to construct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It isone important means for Yao people in to initiative adapt to social change and conserve the ethnic culture of flexibility.
Key words: Yao; Door-law ceremony;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韦浩明,男,1965—,壮族,广西钟山县人,贺州学院人文与管理系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史、区域民族关系研究。联系电话:13307841639;电子邮箱:Weihm04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