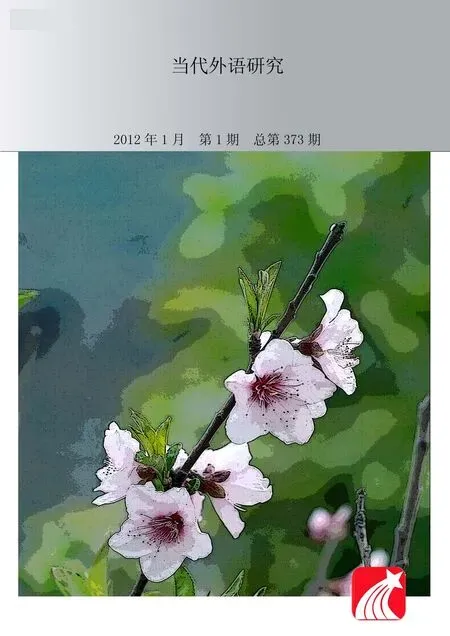自传叙事交流情景与自传身份隐喻
——源自《富兰克林自传》受述者背后的声音
刘 江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210009)
1. 前言
自传作者不同于小说家甚至传记作家,因为“自传作家往往从特定的身份出发来再现自我”,身份认同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原则”(赵白生2003:83)。无独有偶,法国自传研究鼻祖菲利普·勒热纳(Philippe Lejeune)也认为,究其本质,自传是传主的一种“身份契约”(Lejeune 1989:29)。也许,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传正是一种以身份建构为终极目标和叙事核心的文类。这种强烈的身份意识也就决定了自传作者会想方设法地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以实现其身份建构的“浩大工程”。遗憾的是,当我们热衷于分析纷繁复杂的自传叙事策略以期揭开自传作者神秘的身份面纱时,却忽略了自传叙事交流情景这一基本的叙事现象及其潜藏的深意。无论是在小说研究还是自传文本阐释中,学界往往倾向于分析某一叙事文本的叙事交流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即有关How的问题),而无视隐藏在这一叙事交流过程之后的意识形态(即关于Why的问题)。为此,本文将首先探讨小说和自传叙事交流情景之异同,对其现有模式加以必要之修正,并在此基础上以《富兰克林自传》为例,分析其叙事交流情景模式在叙述进程中的变化所蕴含的身份隐喻。
2. 叙事交流情景模式:小说vs.自传
叙事交流情景最早应用于小说文本的分析,旨在揭示叙事交流活动的过程及其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在小说研究中,虽然学界就叙事交流活动的参与者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却在小说叙事交流是否具有开放性这一议题上出现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对立。以塞缪尔·查特曼(Seymour Chatman)为代表的经典叙事学家们通常将小说文本视为一个孤立而封闭的世界(用实线框表示),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因而处在叙事交流情景之外,只有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是必不可少的,而叙述者和受述者则是可选择的(用圆括号表示)。据此,经典叙事学家们通常采用如下范式来说明小说中的叙事交流情景(Chatman 1978:151):

与经典叙事学家们仅关注小说的叙事语法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家们坚持认为小说文本具有不可置否的开放性,处于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在小说叙事交流过程中同样必不可少,因而主张去掉上述模式中的实线框。不过,这一做法却导致了小说叙事文本的相对独立性无法体现,从而招致经典叙事学家们的诟病。笔者以为,不妨将查特曼的模式修正如下,即用虚线框取代上图中的实线框,以调和两派之间的分歧:

虚线框一方面旨在标识小说叙事文本的“界线”,借此“暗喻”其相对独立性,从而表明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文本叙事诗学或叙事语法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虚线框也能“暗喻”小说叙事文本的开放性,表明其并非完全封闭和孤立,而是跟处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可以通过小说文本实现跨越时空的交流①。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小说文本的开放性和封闭性都是相对的,经典和后经典叙事学框架下的小说叙事交流情景模式所体现的仅仅是两种研究视角的差异。那么,上述小说叙事交流情景模式是否适用自传文本的阐释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基于自传文本所独具的叙事特点②,许德金教授曾在其《种族与形式》(RaceandForm2007)一书中将自传叙事交流情景模式建构如下(Xu 2007:31):
叙事文本
作者→叙述者→(受述者)→无意识/有意识读者
与小说叙事交流情景模式相比,上图表明自传叙事交流情景具有如下四个显著的特征:
首先,自传叙事交流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过程,读者可以通过叙述者(作者的“第二自我”)与“有血有肉的”的自传作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主要取决于小说文本是作者虚构的产品,而自传文本通常是作者对其一生之真实经历所作的回顾性叙述。虚构不是回顾,“只有对过去历史的记忆和重现才是回顾”,回顾“意味着真实”(杨正润2009:299)。因此,自传叙事与现实世界总是有着千丝万缕和不容置否的联系。一方面,自传中的叙述者“我”虽然并不完全就是真实作者的写照,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著名自传研究学者约翰·保罗·伊肯(John Paul Eakin)指出,自传本质上是一门“参照的艺术”(Eakin 1992:3)。自传作者与自传文本中的“我”互为参照,若即若离;自传身份与社会历史形象互为参照,或彼此印证、或相去甚远。另一方面,自传事实③与历史事实往往互为参照,遥相呼应。自传中涉及到的人物、事件也通常是真实地存在和发生过的。此外,大多数自传读者都不会将自传文本当成小说那样的虚构作品一笑置之,而总会或多或少地将其与现实世界中的作者及相应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
其次,参与小说叙事交流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叙事身份清晰可辨,而在自传研究中,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则合二为一了。因为,在自传文本中,“叙述者在讲述他(她)自身的故事时,既是文本内的叙述者,又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因而担任了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双重角色”(Xu 2007:32)。对此,多丽特·科恩(Dorrit Cohn)也曾指出,自传文本中的“叙述者就是作者,作者就是叙述者”(Cohn 2000:307)。不过,更准确地说,自传文本中的叙述者既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又是隐含作者的替身,他兼具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三位一体”的叙事身份。有趣的是,自传叙述者的这种特殊身份也无形中增强了自传叙事的“真实感”。因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合二为一导致了自传叙事表面上并不存在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所谓的不可靠叙述,即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隐含作者)规范不一致的情况(Booth 1983)。
再次,在小说叙事交流情景中,叙述者和受述者都是可以选择的,而在自传中则只有受述者是任选因素。因为在任何自传文本中总有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通常就是“我”④——自传作者的替身。尽管“受述者”是自传叙事交流情景中唯一的任选要素,但自传作者(叙述者)对受述者的直接讲话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功能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当同一自传文本中的“隐性受述者”和“显性受述者”之间有着明显的转化时,这种功能更为突出。
最后,正是由于自传中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重叠,导致了小说中“作者的读者”和“叙事读者”在自传中合二为一,成为许德金所谓的“无意识读者”⑤。这类读者“相信自传故事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意识不到自传文本的情节和它所指涉的真实个人经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对于那些“有能力,也有意识将(自传)文本世界与(自传)文本外世界加以比较”的读者,许称之为“有意识读者”,他们一方面沉浸于自传文本世界,另一方面则意识到文本世界可能与现实世界存在差距,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找到这样的差距(Xu 2007:33)。不过笔者以为,“无意识读者”本质上也具有“三位一体”性,他们不仅是自传叙事中的“叙事读者”和“作者的读者”,同时也是自传“理想的叙事读者”。因为,一位“无意识”的自传读者也会像小说“理想的叙事读者”那样完全相信自传叙述者的叙述,并分享自传叙述者的各种观点。因而对于“无意识读者”来说,自传文本就跟小说文本一样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此外,尽管自传文本有着独特的真实指涉性,但如果读者或评论者仅关注其文本内的叙事语法时,它便同小说文本一样具备了相对的独立性,只不过这种独立性没有小说叙事文本那样明显和强烈罢了。由此可见,我们同样应该用虚线框来标识自传叙事文本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并有必要将自传叙事交流情景模式修正如下:

3. 《富兰克林自传》的叙事交流情景与身份政治
《富兰克林自传》⑥(以下简称《自传》)素来被誉为美国道德完美工程的一座丰碑,一部成功之道的寓言,在全世界拥有最庞大的读者群。同时,它也是公认的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是世界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之一。《自传》不仅被视为美国梦的母版和最好的诠释,也通常被学界解读为“定义了主流美国人身份”(McKay 2005:27)的文本之一,富兰克林也因此顺理成章地被视为美国梦之父、主流美国人的身份之父。那么,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对个人身份又有着怎样的诉求?这种诉求又有何体现呢?为此,下文将聚焦《自传》中叙事交流情景的变化(尤其是受述者的转换),以期揭开富兰克林的自传身份之迷。
《自传》第一部分是富兰克林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写给儿子威廉的,在“Dear son”这样的称谓下,“you”是这部分的“显性受述者”。然而,自第二部分开始,也许是受到两位朋友来信的启发,不仅《自传》的叙事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其“受述者”也经历了明显的转换。笔者现将这一情况统计如下⑦:

受述者部分 you或your+x其他变体特 指非特指Dearsonmy+xyoung+xone第一部分2601203第二部分0140319第三部分060035第四部分000000
从上表不难发现,《自传》中受述者称谓的变化和分布情况呈现如下几个有趣的特征:
首先,受述者“you”虽然贯穿全文(第四部分除外),但却呈依次减少的趋势。其中,第一部分以“Dear son”开头,可见其中的“you”皆特指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然而,自第二部分开始,“you”不再特指具体的某个人,而是具有了普适的泛指意义。笔者发现,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出现受述者“you”的位置都相对集中。如第二部分中总共14个“you”中的10个都出现在富兰克林对十三点美德的阐释之中;第三部分中的“you”也同样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中第92-93页四处,第118页两处)。此外,第二和第三部分中的“you”也仅用于叙述评论之中。
其次,富兰克林在第一部分中先后有两次将受述者“Dear son”拓展为“我的子孙后代”(my posterity,见第3页和第55页)。在第二部分结尾处,富兰克林则相继使用“我的子孙后代”(my posterity)、“我的后代”(my descendants)和“我的同胞”(my fellow-citizens)这样的称谓对读者直接讲话。而到了第三部分,上述“我的某某”这种称谓则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诸如“青年们”(young men)、“青年女性”(young female)和“年轻的印刷商们”(young printers)等受述者。尽管“年轻的某某”这一显性受述者称谓仅出现了几次,但足以说明富兰克林的身份发生了相应的转换。
最后,《自传》中另一种显著的受述者称谓是指涉意义更为宽广的“one”。与非特指的“you”一样,所有的“one”都用于评论之中。其中,第二部分中最多,但都集中于开头(5个)和结尾(3个)之处。
从上述《自传》中受述者称谓变化及分布特征不难看出,《自传》的第一部分和其后的三个部分的叙事交流情景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也许是富兰克林自传叙事的一个独特之处。如前所述,《自传》第一部分是富兰克林写给儿子威廉的私人信件形式,故此部分中的显性受述者“you”绝大多数情况下特指其儿子威廉。如果此部分不公开发表,则其中的叙事交流主要是叙述者“我”(身兼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于一体的富兰克林)与受述者“you”(身兼叙事读者与作者的读者于一身的威廉)之间的父子对话(仅限于在密封的实线框内交流),其他读者则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一旦出版后,作为作者的富兰克林和无意识或有意识的读者之间便通过其自传文本有了交流。故《自传》第一部分的叙事交流情景可用如下范式表示:
叙事文本
作者→叙述者→受述者→无意识/有意识读者
然而,自第二部分以降,即使出现过非特指的“you”和其他称谓变体,也仅限于个别地方,并不存在任何一以贯之的、明显的受述者。此外,与第一部分非公开的初衷不同的是,第二至第四部分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公众的,因此不存在任何的仅限于文本内的叙事交流。可见,《自传》后三部分的叙事交流情景显然不同于第一部分,可用如下范式表示:
作者→叙述者→无意识/有意识读者
那么,《自传》为何要对叙事交流情景作上述那样的结构性安排和转换呢?其受述者称谓的不断变化之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目的呢?
由于第一部分是写给儿子威廉的家书,因此,无论富兰克林是用“you”还是“我的子孙后代”来称呼他们,都只是父与子,或隐喻化的“家族之父”与子孙后代的对话。因而,在叙事内容上,富兰克林侧重于展示其从“出身贫寒”到“家境富裕”和“小有名气”的有用“途径(means)”(3)。为了给儿子威廉或子孙后代树立一个可供模仿的榜样,富兰克林在《自传》第一部分主要讲述自己在职业上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印刷人,在精神追求上如何“成为一名说得过去的英语作家”(15)⑧。富兰克林希望他的这些成功之道能同样适用于子孙后代,并能为他们所“效仿”。此时,富兰克林着眼的仅是对儿子和自己个人子孙后代的教育。这种家庭教育的目的可谓贯穿《自传》的第一部分。例如,富兰克林在第一部分结尾处提到巴尔德博士(Dr. Baird)对其勤奋大加赞赏之后,发表了如下一段评论⑨:
我之所以这样毫无顾忌地强调自己的勤奋,尽管有自吹自擂之嫌,目的无非是让读过它的子孙后代们看到在这段叙述中勤奋产生的于我有利的效果时,就可以知道这种美德的用处了。(55,粗体为笔者自加,下同)
上述引文跟《自传》第一部分开头表述的写作目的毫无二致,即强调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作用。这种非公开的“父子”对话和家庭教育的取向在第一部分末尾的“备忘录”中也展露无遗:
到此为止是按本文开头所表达的意向写的。因而包含了一些与他人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以下是多年以后遵照下面两封信的劝告写成的,因此是面向公众的。(64)
上述这段文字的说明与前文的讨论表明,《自传》的第一部分除了成功地建构起了富兰克林作为印刷人的职业身份以及作为诗意作家的精神身份之外,其父型形象也初具雏形,只不过此时仅限于隐喻化的“家族之父”而已,远未上升至“隐喻国父”的文化身份层面⑩。因此,《自传》第一部分的叙事交流情景不过是父与子(们)之间的家族对话。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富兰克林在叙述中为何直呼其子或后代为“你”或“你们”了。作为受述者的威廉或富兰克林的子孙们也不会因此而觉得反感,相反会倍感一位“家族之父”的语重心长和用心良苦。
自第二部分以降,《自传》不仅在写作风格上有所变化,而且在叙事交流情景上也发生了相应转换。此部分及之后文本中,受述者的称谓有了丰富的变化,但总体上并不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显性的受述者。像“you”、“young+x”和“one”这样的受述者称谓也都失去了特指的对象,转而指涉普适的公众。此时,富兰克林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更为直接,因为交流的过程中间不再有一个受述者“you”,而仅有一个叙述者“我”。这种叙事情景的“突变”显然跟其后三个部分是“面向公众”的写作目的不无关系。而导致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就是第二部分之前全文引用的两封朋友的来信。富兰克林也似乎当仁不让地“遵照”朋友的劝告,肩负起了教育美国青少年的历史使命,而不再囿于家庭或家族的教育。
随着叙述或教育对象由个人的子孙后代转换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青少年,富兰克林在第一部分建构起来的隐喻化“家族之父”的形象也因此升华至“隐喻国父”的文化层面。因而,与第一部分不同的是,自第二部分开始,富兰克林开始有意识地避免直接对一个显性的受述者讲述其公益事业的故事,其受述者变得更为隐蔽,此举无形中扩大了其“布道”受众的范围。通过叙事交流情景的变化,富兰克林一方面不再对一个指涉面狭窄的、显性的受述者讲话;另一方面,则在叙述的过程中插入大量使用现在时的评论。这些穿插于后三个部分的现在时评论不仅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事件的教育意义或教化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是“读者破译自传文本信息的隐性线索”(Xu 2007:170)。同样可以作为破译作者潜藏叙事意图的还有散布于《自传》中非特指的受述者“you”及其变体。不难发现,最后三个部分中出现的“you”和“one”都用在评论之中。通过在这些评论中插入一个普适化的、非特指的受述者,富兰克林成功地将读者拽入其叙事之中,从而跟他分享这些事件的教化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至第四部分中的“you”和“one”甚至超越了指涉美国青少年的意义,而是具有了全球化的指涉性。换言之,通过受述者指涉对象的扩大化,富兰克林早已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定位成了美国之梦的文化之父。因为美国梦所强调的勤奋工作、诚信经营与个人成功的因果关系在富兰克林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找到最早和最完美的诠释与母版。
4. 结语
无论是在小说文本还是自传文本中,叙事交流情景,尤其是受述者或隐含读者在同一文本中的有意识转换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意识形态的变化,《富兰克林自传》则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叙事交流情景在《自传》第一部分和其后的三部分之间的变化,表面上是写作意图从个人向公众的转换,而实质上则是富兰克林“家族之父”的身份向“隐喻国父”的转换。若把《自传》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在《自传》开头“亲爱的儿子”的称谓之后,富兰克林成功地将自己的父型形象隐喻化成“家族之父”,并进而升华成美国之梦的文化之父。概言之,叙事交流情景在《自传》中被巧妙地运用于富兰克林身份的转换工程之中,尤其是其父型身份的隐喻化,从而在其《自传》文本内外的双重世界中建构起富兰克林式的身份政治神话。
附注:
① 以上主要观点已在刘江(2010a)中有所阐释。
② 详见Xu Dejin(2007)。
③ 赵白生(2003:14-26)认为,“自传事实是用来建构自我发展的事实,是经验化了的事实”。
④ 自传叙述者通常以“我”的身份进行叙述,但也有例外,如美籍华裔作家黄玉雪的自传《华女阿五》就是以第三人称“玉雪”作为叙述者,即便如此,第三人称的“玉雪”仍是真实作者本人。
⑤ 罗宾诺维兹在1977年首次提出了四维读者观:“理想的叙事读者”,即叙述者的理想读者,他们完全相信叙述者的叙述,并分享叙述者的各种观点;“叙事读者”,即叙述者叙述时的臆想读者,他们将小说文本中的虚拟世界假想为真实世界,而意识不到它的虚构性;“作者的读者”,即作者谋篇所假想的读者,他们能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深刻意识到文本的虚构性,从而能与作者一起评判叙述者和人物;“有血有肉的读者”,即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读者。详见Rabinowitz(1977:121-141)。
⑥ 本文所引富兰克林自传版本为Franklin(1982),中文为笔者自译,下引此文只注页码。
⑦ 学界通常按写作时间将《富兰克林自传》分为四个部分,本文亦采用此法。本统计表不包含对话、引用或其他场合中非显性受述者的称谓。统计数据或有疏漏,但足以说明问题。
⑧ 对此,赵白生(2004:87)也指出,富兰克林在写作中对《旁观者》亦步亦趋的模仿“无形中说明了他在精神上取法的层次”。
⑨ 巴尔德博士的赞扬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奋是他的同行们望尘莫及的:我离开俱乐部回家时,他还在干活呢;他的邻居还没有起床,他又在工作了。”(55)
⑩ 有关富兰克林的职业身份、精神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转换过程,详见刘江(2010b)。
Booth, Wayne C. 1983.TheRhetoricofFiction(2nd ed.)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Rprt. of 1961. Harmondsworth: Penguin.]
Chatman, Seymour. 1978.StoryandDiscours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hn, Dorrit. 2000. Discordant narration [J].Style34: 307-316.
Eakin, John Paul. 1992.TouchingtheWorld:ReferenceinAutobiograph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ranklin, Benjamin. 1982.TheAutobiography&OtherWritingsbyBenjaminFranklin[M]. (Peter Show ed.). New York: Bantam.
Lejeune, Philippe. 1989.OnAutobiography[M]. (Katherine Leary trans.). (Paul John Eakin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ckay, Nellie. 2005. Autobiography and the early novel [A]. In Emory Elliott (ed.).TheColumbiaHistoryoftheAmericanNovel[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6-45.
Rabinowitz, Peter. 1977. Truth in fiction: A reexamination of audience [J].CriticalInquiry(4): 121-141.
Xu, Dejin. 2007.RaceandForm:TowardsaContextualizedNarratologyofAfricanAmericanAutobiography[M]. Oxford: Peter Lang.
刘江.2010a.叙述、存在与成为——掀起圣经叙事交流情景的盖头来[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6):50-55.
刘江.2010b.语境、形式与神话——《富兰克林自传》的叙事时间与身份建构[J].当代外语研究(12):50-54.
杨正润.2009.现代传记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赵白生.2003.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白生.2004.身份的寓言——《富兰克林自传》的结构分析[J].外国文学(1):8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