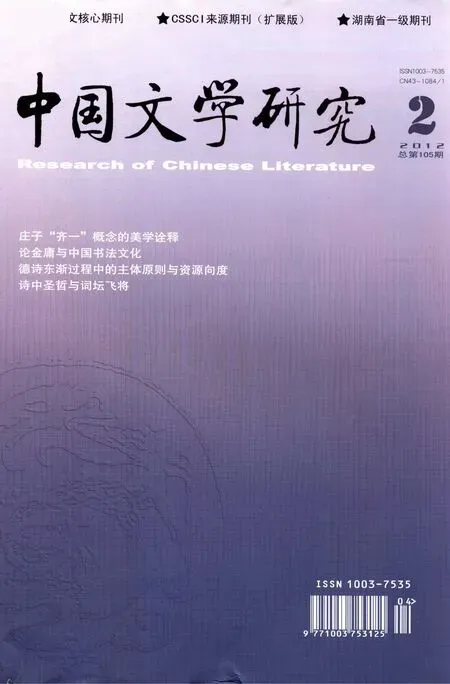王夫之诗情观论
袁愈宗 刘湘萍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情感是诗歌的生命,古今中外的诗人、批评家都对此有着共同的认识。魏晋时期,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1〕(P171)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于情,莫始于言,莫切于声,莫深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2〕(P96)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现代学者、诗人郭沫若说:“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3〕(P215)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4〕(P17)黑格尔说:“(抒情诗)是个别主体及其涉及的特殊的情境和对象,以及主体在面临这种内容时如何把所引起的他这一主体方面的情感和判断,喜悦,惊羡和苦痛之类内心活动认识清楚和表现出来的方式。”〔5〕(P190)王夫之非常重视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认为诗歌的基本特点就是表现情感,他说:“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古人于此,乍一寻之,如蝶无定宿,亦无定飞,乃往复百歧,总为情止,卷舒独立,情依以生。”〔6〕(P654-655)情感是诗歌特有的表现对象,因此诗歌与学术著作之间不能相互取代:“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6〕(P1440-1441)王夫之对诗情的重视也体现出了他对宋代“以理入诗”的批判。但王夫之身处明末清初之际,家国覆亡之痛,民族罹难之苦,再加上宋明理学的影响,时代思潮之激荡,使作为伟大哲学家和杰出文学批评家的王夫之关于诗歌情感的思想有着不同于一般的理解。
一、情的界定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情”总是与“性”联系在一起,而“性”又与“命”联系起来。王夫之是一个哲学家,他的诗学思想是其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里的贯彻,因此要探讨他的诗情观,首先必须清楚其哲学思想中关于“命”、“性”、“情”的看法。
什么是“命”呢?《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命”是一个动词,这是它的原始意义。“命”观念的来源非常久远,《尚书·商书·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后来“命”作为名词,被引申为一种外在的无可抗拒的力量,来源于瀚远深杳之“天”,所以称之为“天命”。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张载说:“天所自不能已者谓命。”〔7〕(P22)对于“命”的看法,王夫之接受了前人的一些观点,如他说:
董仲舒对策有云“天令之谓命”,朱子语本于此。以实求之,董语尤精。令者,天自行其政令,如月令、军令之谓,初不因命此人此物而设,然而人受之以为命矣。〔8〕(P454)
存亡者天也,死生者命也。〔9〕(P436)
命必有所受,有受于天者,有受于人者。知受于人者之莫非天也,可与观化也。……天之命也无心,人之命也有心。〔10〕(P313)
同时王夫之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创见,他认为天授命于人之后,人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只是“俟命”,而且能“造命”:“君相可以造命,邺侯之言大矣!进君相而与天争权,异乎古之言俟命者矣。乃惟能造命者,而后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推致其极,又岂徒君相为然哉!”〔11〕(P934)不仅君相可以“造命”,普通老百姓也可以“造命”,王夫之说:“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11〕(P935)
对于“性”的看法,王夫之也同样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观点。他说:
盖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则此与生俱有之理,未尝或异;故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为性。〔12〕(P128)
“性者,生之理”,这与宋明理学家的观点有着一致之处,如朱熹说:“生之理谓性。”〔13〕(P1376)但是他们认为只有仁义礼智之理才是性,而把人的物质生活欲望排除在外。王夫之认为仁义礼智之理是性,声色臭味之欲也是性。对于“性”的价值之源,王夫之归之于“天”,这亦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观点。他说:“性命于天,而才亦命于天,皆命也。”〔12〕(P227)又说:“知性者,知天道之成乎性;知天者,即性而知天之神理。知性知天,则性与天道通极于一。”〔12〕(P120)但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以“气”为本,“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8〕(P1109)“性”有人性、物性之分,“天命之人者为人之性,天命之物者为物之性。”〔8〕(P455)“天命”是“性”的价值来源,但归根到底是“气”,所以王夫之说:“人物同受太和之气以生,本一也。”〔12〕(P221)“气”为万物的资始,浩瀚的宇宙充满了气,“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12〕(P26)气处于永远不息的运动变化之中,王夫之说:
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14〕(P1044)
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8〕(P1074)万物的产生就是因为气的运动,王夫之称之为“气化”,他说:
气化者,气之化也。阴阳具于太虚絪緼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乗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12〕(P32)
太虚本体之气,是阴阳的统一体,“絪縕太和,合于一气,而阴阳之体具于中矣。”〔12〕(P46)阴阳二气摩之荡之,变化无穷,大千世界的种种活动由此而产生:
阴阳之撰具焉,絪縕不息,必无止机。故一物去而一物生,一事已而一事兴,一念息而一念起,以生生无穷,而尽天下之理,皆太虚之和气必动之几也。〔12〕(P364)
絪縕不息的太虚之“气”为“性”的最终价值之源,王夫之因此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观点:“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9〕(P299)“命”与“性”是降与受的关系,“命曰降,性曰受。性者生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性之日也。初生而受性之量,日生而受性之真。”〔12〕(P413)“降命受性”的过程,不是一次就完成,只要生命存在,就会处在一个不断“降”“受”的过程,
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岂非天哉?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9〕(P300)
王夫之还认为“命”与“性”有大、小之别,他说:“天道之本然是命,在人之天道是性。性者命也,命不仅性也。”〔8〕(P530)天道之命于万物,但是只有命于人之道才是“性”,“命”的范围要比“性”的范围宽,因此“命大,性小。在人者性也,在天者皆命也。既已为人,则能性而不能命矣。”〔15〕(P512)
“情”与“性”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王夫之认为,“情”和“性”都包函于“心”,“心者,函性、情、才而统言之也。”〔9〕(P366)“心”有“道心”、“人心”之分,《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明理学家以此十六字为心传密旨。情就是人心,性就是道心,王夫之说:“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道心也;喜、怒、哀、乐,人心也。”〔8〕(P964)道心与人心,性与情是互统互函的关系,“人心括于情,而情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统性。道心藏于性,性抑必有其情也,故曰道心统情。性不可闻,而情可验也。”〔9〕(P262)“性”与“情”的区别主要有:
1、性隐情显。“性”隐藏不可见,必须通过“情”才能显现出来,“惟性生情,情以显性,故人心原以资道心之用。”〔8〕(P473)
2、性善,情有善有恶。王夫之说:“惟一善者,性也;可以为善者,情也。”〔10〕(P313)又说:“性一于善,而情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也。”〔8〕(P1069)情可以为不善,但是王夫之不同意把情去掉“以塞其不善之原”,因为“人苟无情,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便只管堆塌去,如何尽得才,更如何尽得性!”〔8〕(P1070)如果去掉了情,虽然不可以为恶,但也不可以为善,无法尽才尽性。“情”包涵“欲”,人情、人欲都通极于天(理),“天理也,无非人情也。人情之通天下一理也,即天理也。非有绝己之意欲以徇天下,推理之清刚以制天下者也。”〔16〕(P120)
天——性——情——欲,这是王夫之性情观的逻辑结构,他用一段话总结为:
内生而外成者,性也,流于情而犹性也;外生而内受者,命也,性非有而莫非命也。尽其性,行乎情而贞,以性正情也;尽其性,安其命而不乱,以性顺命也。〔10〕(P429)
在《诗广传》中,王夫之对“情”作了如下的界定:
1、“情者,阴阳之几也。”〔10〕(P323)何谓“阴阳”? 《周易·系辞传下》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王夫之认为,天地中阴阳充塞无间,“凡两间之所有,为形为象,为精为气,为清为浊,自雷风水火山泽,以至蜎孓萌芽之小,自成形而上以至未有成形,相与絪縕以待用之初,皆此二者之充塞无间,而判然各为一物,其性情、才质、功效,皆不可强之而同。”〔14〕(P524)仁覆万物之天道,也就是阴阳之道。《系辞上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王夫之解释说:“‘道’,谓天道也。”〔14〕(P524)那么,“几”(通“机”)是什么意思呢? 《周易·系辞传下》云:“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微小征兆,不容易察觉,所以“知几其神”。王夫之说:
几者,变之微也。〔14〕(P555)
盖几者,形未著,物欲未杂,思虑未分,乃天德之良所发觉,唯神能见之,不倚于闻见也。〔17〕(P89)
天道不可闻,天无心而成化,天无心,以人之心为心,因此“天地之理因人以显,而以发越天地五行之光辉,使其全体大用之无不著也。心凝为性,性动为情;情行于气味声色之间而好恶分焉,则人之情于天之道相承始终而不二,其可知矣。”〔18〕(P564)那么“情者,阴阳之几也”的意思就是说微妙的“情”是体现不可闻见的天道的,人“情”之变化发展的征兆无一不体现天道,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人者,天之绪也。”〔10〕(P313)
2、“情上受性,下授欲。”〔10〕(P327)性无不善,情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因此要以性节情,不能“降其情以从欲”,“心统性情,而性为情节,自非圣人,不求尽于性,且或忧其荡,而况其尽情乎?”〔10〕(P308)如果不以性治情,那么情就有可能“荡”,致使“欲”超出正当的范围,而走向不善,王夫之说:“情之过者一发而不收,则闻见思虑者从之而流于妄。惟不能奉性以治情,而情奔于物欲之诱,则因以使才为恶用,而治教亦不能为之移。”〔16〕(P698)
3、“发乎情,止乎理。”〔10〕(P324)“理”就是天理、天道,天道与天理义近。〔19〕(P19)以性正情,“以性顺命”,情的最高价值依归最后在“天”,因此要“忧乐以理”。〔10〕(P385)王夫之说:“实则天理、人情,元无二致。”〔8〕(P896)
二、情的种类与评价
王夫之把情分为了不同的种类,并进行了评价。
1、白情与匿情。王夫之认为,情不可以无,也不可以“匿”,而必须“达”,诗就是用来“达”情的,他说:
君子与君子言,情无嫌於相示也;君子与小人言,非情而无以感之也。小人与君子言,不能自匿其情者也。将欲与之言,因其情而尽之,不得其情,不可尽也;将欲与之言,匡其情而正之,苟非其情,非所匡也。言之而欲其听,不以其情,嫌于不相知而置之也。言之而为可听,不自以其情,彼将谓我之有别情而相媢也。故曰“诗达情”。〔10〕(P353)
“匿”情就是不让情感表现出来,匿情产生的结果是“迁心移性”:“匿其哀,哀隐而结;匿其乐,乐幽而耽。耽乐结哀,势不能久,而必於旁流。旁流之哀,懰慄惨澹以终乎怨;怨之不恤,以旁流於乐,迁心移性而不自知。”〔10〕(P299)人正常的情感必须表达出来,如果把它们压抑在心里,得不到宣泄,时间长了,就会使人的本性改变。所以王夫之说:“是故文者,白也,圣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则将劝天下以匿情也。”〔10〕(P299)所谓“白情”,就是把内心的真实情感表现出来,王夫之批评佛教“四大皆空”的“窒情”思想,他说:“见情者,无匿情者也。是故情者,性之端也。循情而可以定性也。释氏窒情而天下贼恩,狺狺以果报怖天下,天下怖而不知善之乐,徒贼也,而奚救乎?”〔10〕(P353)“匿情”与“白情”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上不知下,下怨其上;下不知上,上怒其下。怒以报怨,怨以益怒,始於不相知,而上下之交绝矣。夫诗以言情也,胥天下之情于怨怒之中,而流不可反矣,奚其情哉!且唯其相知也,是以虽怨怒而当其情实。如其不相知也,则怨不知所怨,怒不知所怒,无已而被之以恶名。〔10〕(P341)
王夫之关于人的情感可以通过诗(文)得到表露,从而有益于人性的健康的观点是对文学的一个深刻认识。叶舒宪先生在《文学治疗的原理与实践》一文中从古今中外的实例中总结出,文学具有满足人的五个方面的高级需要,其中之一就是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如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荣格的原型说)。〔20〕(P12)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21〕(P3)王夫之的观点与此相似,不同的是王夫之是一个哲学家,他从哲学的高度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
2、贞情与淫情。王夫之说:“奖情者曰:‘以思士思妻之情,举而致之君父,亡忧其不忠孝矣’,君子甚恶其言。非恶其崇情以亢性,恶其迁性以就情也。情之贞淫,同行而异发久矣。”〔10〕(P327)又说:“贞亦情也,淫亦情也。情受于性,性其藏也,乃迨其为情,而情亦自为藏矣。藏者必性生而情乃生欲,故情上受性,下授欲。受有所依,授有所放,上下背行而各亲其生,东西流之势也。”〔10〕(P327)何谓“贞情”?贞者,正也,定也。“情上受性”,如果情以性为依归,就是“贞情”。“贞情”指的是一种以某种正确的价值指向为依归不会轻易改变的情感,王夫之说:
人之历今昔也,有异情乎?通贤不肖而情有所定,奚今昔之异也?其或异与?必其非情者矣。非其情,而乍动于彼于此,不肖之淫,而贤者惊之以为异矣。情同而或怨焉,或诽焉,或慕焉,或有所冀而无所复望,而情之致也殊,贤者以之称情,而不肖者惊之以为异矣。由不肖者之异,而知情之不可无贞。无贞者,不恒也。由贤者之异,而知贞于情者怨而不伤,慕而不暱,诽而不以其矜气,思而不以其私恩也。〔10〕(P320 -321)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情都应该“有所定”,或怨或慕,或诽或思,如果做到了“怨而不伤,慕而不暱,诽而不以其矜气,思而不以其私恩”,就是“贞情”。如果“不恒”,“乍动于彼于此”,那就是“非其情”,就是“无贞”。王夫之说:“情迫而有不迫,道有常而施受各如其分,是故命有所不徇,召有所不往,受禄而不诬,隆礼笃爱而不惊,,然乃终以可生可死而不可贰。”〔10〕(P328)
什么是“淫情”呢?“情下授欲”,“授有所放”,如果情听任欲的放肆,就是“淫”。在《说文广义》中,王夫之对“淫”解释说:
淫,本训浸淫也;一曰久雨为淫,久雨则水浸淫不已也。……乐音曼引而不止,谓之淫声,非谓其沉溺女色。乃以“郑声淫”之故,而谓《曼草》诸诗为婬奔之诗,正缘不辨六书耳。“婬色”、“婬奔”,从女从淫省,唯佛书犹存此字。〔22〕(P183-184)
所谓“淫情”就是情欲的不加节制,不以性为归依,王夫之说:“淫者,非谓其志於燕媟之私也,情极於一往,氾荡而不能自戢也。自戢云者,非欲其厓偨戌削以矜其孤高也,流意以自养,有所私而不自溺,托事之所可有,以开其菀结而平之也。能然,则情挚而不滞,气舒而有所忘,萧然行于忧哀之涂而自得。自得而不失,奚淫之有哉!”〔10〕(P433-434)“淫”并不是专指男女之间的私情,而是指所有情感不受节制流于过度的情况。“何以知情之淫也?其诸词不丰而音遽者乎!韩、柳、曾、王之文,噍削迫塞而无余,虽欲辞为千古之淫人,其将能乎?”〔10〕(P344)《采葛》是《诗经·王风》中的一首诗,全诗为: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王夫之评论说:
采葛之情,淫情也;以之思而淫于思,朱传云。以之惧而淫于惧,毛传云。天不能为之正其时,人不能为之副其望,耳荧而不聪,目瞀而不明,心眩而不戢,自非淫于情者,未有如是之亟亟也。此无所不庸其亟亟,终不能得彼之亟亟,彼不能与此偕亟亟焉,而此之情益迫矣。有望于人而不应,有畏于人而不知所裁,中区热迮而弗能自理,是故其词遽,其音促,其文不昌,其旨多所隐而不能详,情见乎辞矣。〔10〕(P344)
《采葛》中表现了一种深切的相思之情,王夫之认为表现得太迫切了,从“其词遽”,“其音促”就可以看出来。因此“采葛之情,淫情也”。王夫之所推赏的是那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和平之音,他说:
诵《采绿》之诗,其得之矣。幽而不閟,旁行而不迷,方哀而不丧其和,词轻而意至,心有系而不毁其容,可与怨也,可与思也,无所伤,故无所淫也。呜呼!知不伤之乃以不淫者,可以言情矣。孟郊、曹鄴之为淫人,谅矣。〔10〕(P434)
孟郊为中唐诗人,其诗多描写穷愁悲苦,诗风“清奇僻苦”(张为《诗人主客图》),与贾岛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曹鄴为晚唐诗人,其诗风与孟郊相似,清叶矫《龙性堂诗话初集》云:“晚唐之曹鄴,中唐之孟郊也。逸情促节,似无时代之别。”曹鄴有一首《四望楼》,其诗云:
背山见楼影,应合与山齐。
座上日已出,城中未鸣鸡。
无限燕赵女,吹笙上金梯。
风起洛阳东,香过洛阳西。
公子长夜醉,不闻子规啼。
这首诗音节较急促,王夫之评之曰:“讽刺如霜,为物薄而刑气已最。”〔6〕(P977)“刑气已最”就指的是气势的不舒缓。王夫之要求在诗文中表现的情感不能太过,而要有节制,以性为依,以这样的标准来评价作品时不可避免会带有一定的偏激性。但是王夫之这样来要求也有其时代意义,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讨论,此处不赘。
3、裕情与惉滞之情。“淫情”听任欲的放纵,其结果是局限在个人狭窄的情感中不能自拔,王夫之因此提倡情感之“裕”,他说:
不毗于忧乐者,可与通天下之忧乐矣。忧乐之不毗,非其忘忧乐也,然而通天下之志而无蔽。以是知忧乐之固无蔽而可为性用,故曰:情者,性之情也。惟毗于忧,则不通天下之乐;毗于其所忧,则不通天下之所忧。毗于忧,而所忧者乍释,则必毗于乐;毗于乐,亦将不通天下之忧;毗于其所乐,亦将不通天下之所乐。故曰:“一叶蔽目,不见泰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言毗也。圣人者,耳目启而性情贞,情挚而不滞,己与物交存而不忘,一无蔽焉,《东山》之所以通人之情也。周公之徂东山也,其忧也切矣;自东而归,其乐也大矣。忧之切则专以忧,乐之大则湛於乐。夫苟忧之专,乐之湛,所忧之外,举不见忧,而矧其见乐?所乐之外,举不见乐,而矧其见忧?独宿之悲,结缡之喜,夫何足以当公之忧乐,而为尔不忘邪?忧之切,乐之大,而不废天下不屑尔之忧乐,於以见公裕於忧乐而旁通无蔽也。〔10〕(P384)
所谓“裕情”就是不以己之忧废天下之乐,不以己之乐废天下之忧的情感,能够做到“忧乐以理”,广通天下诸情。《东山》为《诗经·豳风》中的一篇,《毛诗序》云:“《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悦)也。‘说(悦)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东山》乎?”〔23〕(P518)王夫之认为周公东征以及胜利而归,都是大忧大乐之事,但是周公能不以己之忧乐而废天下之忧乐,这种情感就是“裕”。王夫之说:
且圣人者,非独能裕于情者也,其裕于情者裕于理也。吾之所急,恶知天下之不见缓焉?吾之所缓,恶知天下之不见急焉?吾之所急,固非天下之所急者焉;吾之所缓,固非天下之所缓者焉。谓宗社大而行旅之劳细,谓君臣兄弟之故大而夫妇之情私,然则率天下以生死于君子之一情而尚不足厌也,则亦理之所固不可矣。故曰:不裕于理,未有能通天下之志者也。当忧而生死不易其心,然后能博以忧;忧释而功名不厌其志,然后能推以乐。其忧乐以理,斯不废天下之理。其释忧以即乐也,无凝滞之情,斯不废天下之情。诵《东山》之诗,若未尝有流言之惧、风雷之迎也,斯以为周公矣乎!〔10〕(P384-385)
王夫之还用“广”来形容“裕情”:“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至矣。不忘其所忘,慎之密也;忘其所不忘,心之广也。……忘其所不忘,非果忘也。示以不永怀,知其永怀矣。示以不永伤,知其永伤矣。情以盈而姑戢之以不损其度。故广之云者,非中枵而旁大之谓也,不舍此而通彼之谓也,方遽而能以暇之谓也,故曰广也。广则可以裕于生死之际矣。《葛屦》褊心于野,‘裳衣’颠倒于廷,意役于事,目荧足蹜,有万当前而不恤,政烦民菀,情沉性浮,其视此也,犹西崦之遽景视方升之旭日也,駤戾之情,迻乎风化,殆乎无中夏之气,而世变随之矣。”〔10〕(P302-303)
基于这种对情的看法,王夫之对《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释:
往戍,悲也;来归,愉也。往而咏杨柳之依依,来而叹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天物何其定哉!当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当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浅人以其褊衷而捷於相取也。当吾之悲,有未尝不可愉者焉;当吾之愉,有未尝不可悲者焉;目营於一方之所不见也。故吾以知不穷於情者之言矣: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虽然,不失悲也;其愉也,不失物之可悲者焉,虽然,不失愉也。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於一情之发,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穷,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言悲则悴以激,言愉则华以慆,元稹、白居易之一率天下於褊促,宜夫杜牧之欲施之以刑也。〔10〕(P392-393)
表现己之情悲,不一定非得强言外在景物也是凄惨的,表现己之情愉,不一定非得说外在景物也是喜气洋洋的。在《诗绎》中,王夫之以《采薇》中的这几句诗为例子,提出了“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24〕(P10)的诗学观,而这种特识的基础正是上面所讨论的王夫之关于情之“裕”的看法。
情之裕,才会有“余情”,就不会产生“惉滞之情”:
道生於余心,心生於余力,力生於余情。故於道而求有余,不如其有余情也。古之知道者,涵天下而余於己,乃以乐天下而不匮於道,奚事一束其心力,画於所事之中,敝敝以昕夕哉?画焉则无余情矣,无余者,惉滞之情也。〔10〕(P301)
“惉滞之情”是如何产生的呢?王夫之说:“惉滞之情,生夫愁苦;愁苦之情,生夫攰倦;攰倦者,不自理者也,生夫愒(按:“愒”疑为“惕”之形误,“惕”通“荡”,放也。)佚;乍愒佚而甘之,生夫傲侈。力趋以供傲侈之为,心注之,力营之,弗恤道矣。故安而行焉之谓圣,非必圣也,天下未有不安而能行者也。安于所事之中,则余于所事之外;余于所事之外,则益安于所事之中。见其有余,知其能安。人不必有圣人之材,而有圣人之情。惉滞以无余者,莫之能得焉耳。”〔10〕(P301)“惉滞之情”是一种与“裕情”完全相反的情感,王夫之用“遽”、“褊刻”、“悁急”、“瞿瞿”等词语来形容它:
遽而成,君子弗为,矧夫遽之未足有成也!所恶于遽者,恶其弗能待也,尤恶其弗能择也,至于弗择,而人道之不废鲜矣。〔10〕(P354)
元化无悁急之施,君子无迮切之求,……以悁急而尽天下之才,则天下之才疑以沮;以悁急而尽天下之情,则天下之情躁以薄。〔10〕(P388)
何谓“瞿瞿”?目方注之,心遽营之;心期成之,目数奔之;居素而若惊,未观而见察;忘远而亟攻其近,方为而辄用其疑:是之谓“瞿瞿”也。〔10〕(P355)
王夫之对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批评说:“韩退之何知,以其《车鄰》、《驷铁》之音,增之以浮促,倡天下於傲辟褊刻之守。”〔10〕(P370)内心情感的“遽”、“悁急”会在文章、语言上体现出来,王夫之因此要求:“勿极语以尽意,勿奔气以追语;勿趋气而枵其志,勿取安于度而惰归其气;即欲尽意,无宁均气以成其条理;即欲尚志,无宁饬度以舒其文章;疾言遽色,不知其亡也。”〔10〕(P502)
4、私情与道情。“淫情”和“惉滞之情”都是心注于一隅,目拘于一孔之情,这种情感局限在狭隘的个人情感之中,为一己之穷愁悲苦而哀叹,得而乍喜,失则立忧,用王夫之批评孟郊的话来说就是“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丧”。〔24〕(P10)这两类情都属于王夫之所说的“私情”,他说:“为《北山》之诗者,其音复以哀,甚节促以乱,其词诬,其情私矣。”〔10〕(P422)《北山》为《诗经·小雅》中一篇,其第二章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毛诗序》对此诗解释说:“《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23〕(P796)为什么《北山》之情为私情呢? 王夫之说:“为《北山》之诗者,知己之劳,而不恤人之情;知人之安而妒之,而不顾事之可,诬上行私而不可止。”〔10〕(P422)“私情”是一种只想到自己,而不体恤他人的情感,表现在诗中就是音复、节促、词诬。但是王夫之又认为如果私情在体现一己之私的同时又是为了一种更高的目的,那么这种私情也是被认可的,他说:“道在安身以卫主,身不安而怨,虽怨利禄之失可矣。道在固好以宜家,好不固而怼,虽怀床笫之欢可矣。”〔10〕(P319)
“贞情”和“裕情”能够以性为归,不流于欲,不毗于一己之忧乐,这两类情都属于“道情”。王夫之说:
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悉知之则辨用之,辨用之尤必裁成之,是以取天下之情而宅天下之正。故君子之用密矣。与天地同情者,化行于不自已,用其不自已而裁之以忧,故曰“天地不与圣人同忧”,圣人不与天地同不忧也。与禽鱼草木同情者,天下之莫不贵者,生也,贵其生尤不贱其死,是以贞其死而重用万物之死也。与女子小人同情者,均是人矣,情同而取,取斯好,好不即得斯忧;情异而攻,攻斯恶,所恶乍释斯乐;同异接于耳目,忧乐之应,如目击耳受之无须臾留也。用其须臾之不留者以为勇,而裁之以智;用耳目之旋相应者以不拒天下,而裁之以不訢。智以勇,君子之情以节;不拒而抑无訢焉,天下之情以止。君子非无情,而与道同情者,此之谓也。〔10〕(P310)
《周易·系辞传上》云:“(天地)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天地之道范围万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但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天地无心而成化,天地并没有刻意去对待世间一切,没有厚此薄彼,所以“天地不与圣人同忧”。但是圣人不可能也不应做到“不与天地同不忧”,必须关心天下之忧乐。而圣人忧乐之情如天地一样没有毗于一隅,宠辱不惊,没有刻意去要求,是“行于不自已”,所以君子之心要与天地同情,也就是“道情”。“女子小人”之情则不同,以耳目之应,得则喜,失即忧,而“耳目持权”,导致“心无恒”。〔10〕(P309)这种情无以性节之,无以天下之情止之,因此不是“道情”。
三、情的治理及王夫之诗情观的时代意义
不论是在诗学还是在哲学思想中,王夫之都非常重视情,他说:“情为至,文次之,法为下。”〔10〕(P307)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以自尽而专天下,法以自高而卑天下。卑天下而欲天下之尊己,贤者怼,不孝者靡矣,故下也。”而“情以亲天下者也,文以尊天下者也。尊之而人自贵,亲之而不必人之不自贱也。”〔10〕(P307-308)在王夫之看来,有情与无情是人与动物之间的一个区别,他说:
情在而礼亡,情未亡也。礼亡而情在,礼犹可存也。礼亡既久而情且亡,何禽之非人,而人之不可禽乎?……河北之割据也,百年之衣冠礼乐沦丧无余,而后燕云十六州戴契丹而不耻。故拂情蔑礼,人始见而惊之矣,继而不得已而因之,因之既久而顺以忘也。〔10〕(P377)
情在王夫之看来是如此重要,“周以情王,以情亡”,〔10〕(P342)所以“君子莫慎乎治情”。〔10〕(P342)
如何治情呢?王夫之认为,对情的治理既不能采取尽闭也不能采取尽启的态度,他说:
情欲,阴也;杀伐,亦阴也。阴之域,血气之所乐趋也,君子弗能绝,而况细人乎!善治民者,思其启闭而消息之,弗能尽闭也,犹其弗能尽启也。……故曰情欲,阴也;杀伐,亦阴也。阴弗能尽闭,而君子重用之。〔10〕(P369)
如果尽启之,情就会极于一往而流于妄;如果尽闭之,就会使正常的情感旁流,迁心移性而不自知。正确的措施是采取“达”、“舒”、“畅”的方法,王夫之说:“万有之情,不顺之则不动;百昌之气,不动之则不振;积习因循之染,不振之则不新。人情隐,而为达之;天道堙,而为疏之。”〔10〕(P489)“治不道之情,莫必其疾迁于道,能舒焉其几矣。”〔10〕(P415)对不道之情的治理,不能急着以“道”治之,首先必须“舒”,为什么呢?王夫之认为:
情附气,气成动,动而后善恶驰焉。驰而之善,日惠者也;驰而之不善,日逆者也。故待其动而不可挽。动不可挽,调之于早者,其唯气乎!气之动也,从血则狂,从神则理,故曰:‘君子有三戒’,戒从血之气也。六腑之气,剽疾之质,速化而成血,挟其至浊而未得清微者以乘化,而疾行于官窍之中。浊,故不能久居而疾;未能清微,故有力而剽。是故阴柔也,而其用常狠。狠非能刚也,迫而已矣。血者,六腑之躁化也。气无质,神无体,故不能与之争胜,挟持以行而受其躁化,则天地清微之用隐矣。清微之用隐,则不能以舒;重浊之发鸷,则触于物而攻取之也迫。其能舒也,则其喜也平,其怒也理,虽或不惠,末之狠矣;其不能舒而迫也,则其喜也盈,其怒也愤,狠于一发,未有能惠者也。末之能惠,而欲迁之以惠,清刚之不胜久矣。是故欲治不道之情者,莫若以舒也。舒者,所以沮其血之躁化,而俾气畅其清微,以与神相邂逅者也。〔10〕(P415-416)
不道之情是因为情附于重浊之血气,这种情的特点是迫、狠,以“道”治之,根本就不能与之争胜,只有先通过“舒”、“达”的方法平之、理之,才能使其复归于“道”,“与神邂逅”。
用什么来舒“情”呢?王夫之认为在天地万物中,受“江山云物之和”可以起到这种效果,他说:“是故古之王者,非遽致民也,畅民之郁,静民之躁,调其血气以善其心思,故民归之而不离。周衰道弛,风烦韵促,督天下于耕战,而人无以受江山云物之和,抱遐心者,宜其去朝市而若惊矣。”〔10〕(P434)《黍苗》为《小雅》中一篇,其第五章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朱熹《诗集传》解释说:“宣王封申伯于谢,命召穆公往营城邑,故将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25〕(P170)王夫之称赞召伯说: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之营谢,夫亦犹行古之道也。故其民肢体得安焉,耳目得旷焉,臭味得和焉,疾眚得远焉。治地以受天之和,迓天以集民之祉。其余者,犹使登高临远之士启其遐心,揫忧拘迮之夫平其悁志。鄙吝(袂)祛,怨恶忘,而人安其土。〔10〕(P434)
在审美中达到人性完善的目的,王夫之的观点与先秦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所谓“成于乐”就指的是在音乐的熏陶中完成人格修养的塑造。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说:“吾与点也。”所向往的也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另外,王夫之认为诗(文)也可以起到达、舒的效果,他说:“诗之教,导人於清贞而蠲其顽鄙,施及小人而廉隅未刓,其亦效矣。”〔10〕(P326)“诗者,所以荡涤惉滞而安天下于有余者也。”〔10〕(P302)王夫之把“情”的最终价值取向归于天,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说:“用俄顷之性情,而古今宙合、四时百物,赅而存焉,非拟诸天,其何以俟之哉!”〔10〕(P481)他对诗情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6〕(P681)人的情(怀)是通天的,诗人就是要把这种情怀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是诗家第一义。
王夫之的诗情观是对儒家“温柔敦厚”诗学思想在理论上的一次全面总结。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对“温柔敦厚”解释说:“温柔敦厚诗教者也: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26〕(P1368)《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这些都是对“温柔敦厚”诗学思想的具体阐述。王夫之的诗情观以其哲学思想作为基础,在深刻阐述、全面总结儒家“温柔敦厚”诗学思想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和满族铁骑的冲击下覆亡,王夫之亲眼目睹了这场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亲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在回天无望之后,归隐深山,潜心著述。王夫之的上辈从十世祖王仲一开始,便追随朱明,〔27〕(P78)因此王家对朱明王朝的感情是非常深刻的。在寒灯破室下,怀着“刘越石之孤愤”的王夫之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家国覆亡的原因。这种思考不仅表现在他的哲学、历史著作中,而且体现在他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他对诗情的看法中就体现出这一点。王夫之从明王朝的覆亡中看到了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他一方面同情老百姓的悲苦生活,揭露贪官污吏对他们的残酷剥削,他说:
今夫农夫泞耕,红女寒织,渔凌曾波,猎犯鸷兽,行旅履霜,酸悲乡土,淘金、采珠、罗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年皓发以获赢余者,岂不顾父母,拊妻子,慰终天之思,邀须臾之乐哉!而刷玄鬓,长指爪,宴安谐笑于其上者,密布毕网,巧为射弋,甚或鞭楚斩杀以继其后。乃使悬罄在堂,肤肌剟削,含声陨涕,郁闷宛转于老母弱子之侧,此亦可寒心而栗体矣。〔12〕(P528)
王夫之认为上层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是激起民怨,导致起义的重要原因,“货积于上,而怨流于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王仙芝、黄巢一呼而天下鼎沸,有司之败人国家,不已酷乎!”〔11〕(P1023)另一方面,王夫之则认为要防止老百姓造反,要及早采取措施调节他们的性情,化解“民岩”,他说:
古之称民者曰“民岩”。上与民相依以立,同气同伦而共此区夏者也,乃畏之如岩也哉?言此者,以责上之善调其情而平其险阻也。唐至懿宗之世,民果岩矣。裘甫方馘,而怀州之民攘袂张拳以逐其刺史;陕州继起,逐观察使崔荛;……夫民既如此矣,欲执民而治其逐上之罪,是不矜其穷迫而激之乱也;欲诛观察刺史以抚民,而民之不道又恶可长哉?小失豪民之意,狺狺而起,胁天子以为之快志,抑不大乱不已。然则反此而欲靖之也无术,则抑追诘其所由来,而知畏民之岩者,调制其性情于早,不可唯意以乱法也。〔11〕(P1025 -1026)
“岩”是积石高峻的意思,“民岩”指民众的难于治理。怎样来调节民众的性情、“平民岩”呢?王夫之说:“夫粟所以饱,帛所以暖,礼所以履,乐所以乐,政所以正,刑所以侀,民岩之可畏实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诚有其事。”〔9〕(P378)除了政治清明,法律公正之外,王夫之认为还要满足老百姓的物质需求,同时还要用礼乐等文化来对其性情进行调节。诗文作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用来使民众之性情趋于平缓的,因此王夫之激烈反对在诗文中表达太“过”的情感,认为这样会激起民众的戾气,从而引起天下动荡,他说:
翘然自好者,以诋讦为直,以歌谣讽刺为文章之乐事。言出而递相流传,蛊斯民之忿怼,以诅咒其君父。于是乎乖戾之气充塞乎两间,以干天和而奖叛逆。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伦攸斁,横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必然乎!〔11〕(P1048)
对于《诗经》中的《相鼠》一诗,因为其中表现的情感太过激烈,王夫之批评说:“褒而无度,溢为淫赏;刺而无余,滥为酷刑。淫赏、酷刑,礼之大禁。然则视人如鼠而诅其死,无礼之尤者也,而何足以刺人?赵壹之褊,息夫躬之忿,孟郊、张籍之傲率,王廷陈、丰坊之狂讦,学诗不择而取《相鼠》者乎!”〔10〕(P334)王夫之的观点带有一定的偏激性,但这种偏激性中有着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沉之思。
王夫之的诗情观也是建立在对明代文坛的批评之上的。王夫之倡导在诗中表达真诚的情感,因此对任何桎梏性情的作法都持批判态度。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诗歌所取得的成绩甚少为人所称道,但其派系之多,标榜之风之烈却为历代所罕见,郭绍虞先生评价说:“标榜之风,固然古已有之,然而于明为烈。明代文人只须稍有一些表现,就可以加以品题,而且树立门户。”〔28〕(P518)这种风气严重影响到了明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各门派各自标榜,都树立自己的“创作法则”,与己不合的就加以排斥。一些有着真才实学的要么遭到排挤,要么就只能依附于某一门派,最后沦为平庸之辈。而一些本无才情的靠着拼凑文字、典故,俨然“大家”。王夫之对明代诗坛上的这种风气深恶痛绝,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说:
所以门庭一立,举世称为“才子”、为“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即无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则更不须尔;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之”“于”“其”“以”“静”“澹”“归”“怀”,熟活字句,凑泊将去,即已居然词客。如源休一收图籍,即自谓酂侯,何得不向白华殿拥戴朱泚邪?为朱泚者,遂褎然自以为天子矣。举世悠悠,才不敏,学不充,思不精,情不属者,十姓百家而皆是,有此开方便门大功德主,谁能舍之而去?又其下,更有皎然《诗式》一派下游,印纸门神待填朱绿者,亦号为诗。庄子曰:“人莫悲于心死。”心死矣,何不可图度予雄邪?〔24〕(P112-113)
王夫之认为,那些立门庭的都是没有真才实学的,进行创作时,他们就从《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等之类的类书里查找词语、故实,如果与题有些相关,就把它们拼凑起来。这样写出来的诗当然没有真情实感,只是无病呻吟。这些门派所谓的“法则”只能桎梏人的性情,王夫之对在明代文坛很出名的一些诗人都进行了辛辣的批评和讽刺,他说:
一解弈者,以诲人弈为游资。后遇一高手,与对弈至十数子,辄揶揄之曰:“此教师棋耳。”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廷,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24〕(98-99)
立门庭或者依傍门庭者所创作的诗文千篇一律,程式化,完全没有一点创作个性。王夫之对能够不依傍门庭,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些诗人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若刘伯温之思理,高季迪之韵度,刘彦昺之高华,贝廷琚之俊逸,汤义仍之灵警,绝壁孤骞,无可攀蹑,人固望洋而返;而后以其亭亭岳岳之风神,与古人相辉映。次则孙仲衍之畅适,周履道之萧清,徐昌谷之密瞻,高子业之戌削,李宝之之流丽,徐文长之豪迈,各擅胜场,沈酣自得。正以不悬牌开肆,充风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掩抑,岂与碌碌余子争市易之场哉?〔24〕(P99)
明末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反对复古主义,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创作宗旨,也得到了王夫之的称誉,他说:“王、李笼罩天下,无一好手敢于立异,中郎以天姿迥出,不受其弹压,一时俗目骇所未见,遂推为廓清之主。”〔6〕(P1529)但是王夫之所提倡的“情”是能广通天下的“性”之情,“道”之情,而对于诗中过狭、过于激烈的情感,他是非常反对的。他说:“关情是雅俗鸿沟,不关情者貌雅必俗。然关情亦大不易,钟、谭亦未尝不以关情自赏,乃以措大攒眉、市井附耳之情为情,则插入酸俗中为甚。”〔6〕(P1510)明末“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其诗风“幽深孤峭”,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中评价说:
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擿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以一二辁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胜叹悼哉!〔29〕(P221)
钱谦益认为钟、谭的诗风体现了明王朝国运衰败的气象,王夫之也斥“竟陵派”为祸国之原,他说:
《子夜》、《读曲》等篇,……晋宋以还,传者几至百篇,历代艺林莫之或采。自竟陵乘闰位以登坛,奖之使厕于风雅。乃其可读者一二篇而已。其他媟者如青楼哑谜,黠者如市井局话,蹇者如闽夷鸟语,恶者如酒肆拇声,涩陋秽恶,稍有须眉人见欲哕。而竟陵唱之,文士之无行者相与斅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竟陵灭裂风雅,登进淫靡之罪,诚为戎首。而生心害政,则上结兽行之宣城,以毒清流;下传卖国之贵阳,以殄宗社。凡民罔不譈,非竟陵之归而谁归邪? 推本祸原,为之眥裂。〔6〕(P617)
王夫之孤心苦诣,推究历代兴亡之原,撰成《读通鉴论》三十余卷,最后总结说:“卑污之说进焉,以其纤曲之小慧,乐与跳荡游移、阴匿钩距之术而相取;以其躁动之客气,迫与轻挑忮忿、武健驰突之能而相依;以其妇姑之小慈,易与狐媚猫驯、淟涊柔巽之情而相昵。闻其说者,震其奇诡,歆其纤利,惊其决裂,利其呴呕;而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斁,廉耻以堕。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患。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11〕(P1178)王夫之对李贽的批评虽然过于严厉,但李贽对于“情”不加限制的推崇,由此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这也是事实。
民众之“情”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这是王夫之总结历史得出的教训,也是他反对匿情、私情、惉滞之情、淫情,倡导白情、道情、裕情、贞情的诗情观的根本原因。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郭沫若.论诗三札〔A〕.文艺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引自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7〕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9〕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三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1〕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3〕朱熹.朱子语类(四·卷五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八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7〕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四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9〕此借鉴张立文先生观点.见其《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0〕详见叶舒宪主编.文学与治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1〕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九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3〕毛诗正义(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4〕戴鸿森.薑斋诗话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5〕朱熹.诗集传(卷十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6〕礼记正义(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7〕王敔.薑斋公行述.船山全书(第十六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8〕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9〕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