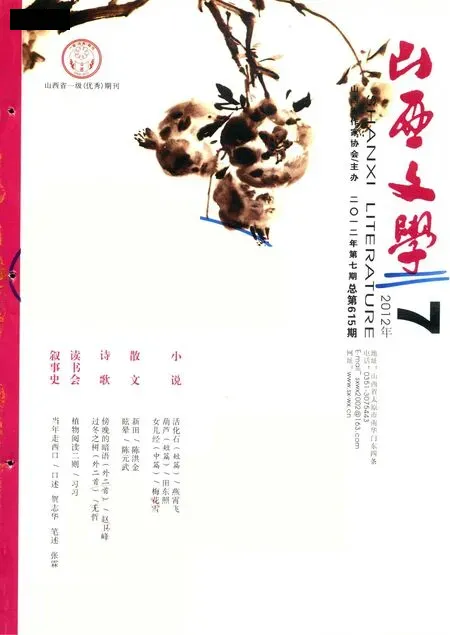活化石
燕霄飞
终于赶在日落前到了。政府办干事皱着眉,很礼貌地将两位专家从风尘仆仆的小车里扶出来。三人在斜阳里伸伸腰踢踢腿,感叹沧海桑田人生苦短。
一架自行车丁零当啷地从黄土坡上冲下来,他们挥手喊住了。
专家们急于知道有关槐树的一切事情。
“你看到那棵老槐了吗?它怎样,多高?多粗?传说中的老头儿还在吗?我是说……神木有没有遭到看守人的破坏?”专家焦急地问。
骑车人自称是位出名的古董商,谙熟方圆百里的行情和规矩。他吸着外路人递上的高级香烟,看了几次牌子说: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了,我帮了不少人的忙,当然,价钱不很贵……当然,也不很低……”
“老乡,”政府干事忍不住打断他的话,“听说那槐树院光剩一个苶老汉了,是不是?听说那是个苶老汉,是不是?”
收古董的小贩乍听到本地土话后,很气恼,忽然冲那两个外路人发起脾气来:“甚树精日怪?妈逼问俺,俺知道个毬……”
自行车气鼓鼓绝尘而去。三人纳闷儿。相慰几句后他们向坡顶的槐树院进发了。
槐树院内,老头儿斜倚槐树笑对夕阳,眯眼回味今去来兮的桩桩件件。
早晨,他曾为头晚剩了一碗米汤心疼,端碗愣怔片刻,还是跟往常一样泼到了树底。然后又跟往常一样,把小炕桌搬到窑外,把高凳低凳马扎儿通统搬到窑外。桌凳污渍斑驳,依稀映着一些陈年旧痕。老头儿把碗碗碟碟、油盐罐罐收罗全,也抱出来摊炕桌上。凳子团团圆圆围一圈儿,早饭开始了。老头儿坐主人位置,用两颗大牙四颗臼齿,坚持啃完了一只萝卜。“老汉的牙口还不赖。”他大声喊,以便让自个儿听见。上午,老头儿照例坐檐下石阶上愣神儿,每天早饭后他就这样,坐着,偶尔捏起一颗石子。不管何时,他手边准有一小摊石子。石子磨了棱角,一天比一天圆滑。他听惯了石头摩摩擦擦的声音。晌午时分,他的视线里,灰色鸽群又落回树底,翅翎扑扑扇腾,次第收拢。碎屑和烟尘翻卷而起。“跟昨儿一个数,十九圈。”他捡起一颗石子,掂了掂。十九颗石子,代表鸽群在很远的地方兜了十九圈儿。
很远的地方,就是院子以外的地方。
这群野鸽子一律灰羽红喙,都有名字。当然,它们自己不知道。它们对一辈子不洗澡、常年光膀子、麻绳系棉裤腰的老汉不感兴趣。它们只管享受树荫,散步,啄一口泥土中的米粒,看看左近亲属。
“灰猴,”老头儿忽然扬了一下胳膊,白腋毛和全身的褶子都使着劲儿,“嘟哨……”
跃上石桌的鸽子没在意老头儿的动静,轻松地完成了排泄。老头儿肿着眼泡,从灰影的动作猜到了它做的事,“你个灰猴。”
“真该你落单。”他喊。
石桌上的鸽子蹦下来,混迹于鸽群,老头儿找不到它了。他抹掉眦糊,开始疑惑一向称做“灰猴”的鸽子是不是同一只。老头儿又点了一遍鸽子数目,还是单数。再以前他点的是双;再以前,是单。看来它们的生活也很无常。“可是,老汉的身子骨还行!”他大声喊,重新乐呵起来,拍着肚皮决定把昨天剩下的酒喝完。
起身时,他朝院外望了一眼。
他的槐树院曾有过土墙。
老头儿将破席片、草垫子,拎到了石桌两边,没有忘记带他的搪瓷茶缸,还有能装十斤的塑料酒桶。他到东南角的菜畦拔蒜苗时,鸽子全飞走了。“走吧,走吧,吃饱了灰去吧。”他冲那些啪啪扇动的翅膀喊着,望着。它们相追相随,离他越来越远。拐到树下,他伸手抹掉石桌上的鸽粪,蹭在鞋底上,手在棉裤上搓搓。棉裤是一年四季的裤子,油光黑亮;布鞋缺了后帮,前边有两个窟窿,两根黑垢趾露在外面。他趿着鞋片,坐到树荫下,光着黑脊背,靠着树干,准备将酒全部干掉。看起来,塑料酒桶只浅浅地铺着底儿。倒了半茶缸,他举起桶,放眼前晃晃,塑料酒桶依然只铺着底儿。不能很快喝完,他朝原来大门的位置瞅了一眼,把蒜苗分成了三份儿。抿了一小口酒,觉得不够劲儿,他怀疑地看了看茶缸。茶缸上印有“将……进行到底”的红字,中间掉了瓷的部分颜色很深。
他又拎起酒桶晃了晃。没有不妥,跟昨个儿没啥两样。他冲石桌对面举了举茶缸,开始认真喝酒。茶缸在他唇间吱儿吱儿地响。蒜苗一拃来长,没有长全。那叶儿,该是对儿生呢。他在心里数算着,应该用它们炒个鸡蛋的,他抿一口酒,巴咂巴咂唇舌。蒜苗炒鸡蛋,够味儿!
“再炒一个蒜苗鸡蛋来……”他冲窑洞大喊。
老头儿一口酒一口蒜苗,茶缸与石桌不停磕出清脆的声响。第一份蒜苗结束时,树荫悄悄东挪了一尺。老汉没有察觉。鸽子在远处又转了刚好十圈。这一点,老汉很清楚。隔一阵子,他就会从棉裤兜里,摸出一颗小石子,扔桌上。“跟昨儿个一样呵。”他喊着,咂着唇舌,茶缸吱儿吱儿地响。生下来就为个转呵。灰猴们。
老头儿的眼睛红了,又糊了一层垢糊。这酒还不赖,够辣。今天一定干掉它。他搓把脸,摸着白胡茬,觉得脸上没有一点酒的影子呢。第二份蒜苗也完了,他又晃了几回酒桶,酒依然只浅浅地铺着底儿。茶缸里的酒,又添到了原来的位置。他的脸红了,皱褶里的汗也是红的。后来他踢掉了鞋片儿,光脚板着地,一口酒一口蒜苗,茶缸吱儿吱儿地响。
一只蚂蚁从他脚面上爬了过去。他盯着它,盯了很久。蚂蚁没头绪地忙碌,最后在石桌底下的青苔里,发现了一粒米。他灌一口酒,觉得世道是公平的。
树荫悄悄移动。
有几片叶子飘落桌上,窑洞上的窗户纸啪啪作响。他眯着眼泡,看见远处一片苍茫的白光,两孔窑洞在风里晃荡着。镶着三块玻璃的那间,檐下吊着的一排锄耙摇来摆去,后面褪色的窗花曾让他欣喜;不住人的那间,没糊麻纸,黑洞洞的,窗格子折了多处,几根窗棂还没有完全掉下来。他想了想,想不起里面放着什么。
他远远地打量那把硕大的黑色铸铁锁。
院子里静极了。一声猫叫也没有,一声狗叫也没有。
真应该养群鸡崽呢,东北角呢,可以卧头肥猪。他记不清动过多少回这样的念头了。
东北角的荒草中,斜撑着一架扇车,木料已然腐烂,铁质摇柄掉在草丛里,锈迹暗黄。扇车前是一口裂缝的碌碡,上面布满褐绿色斑点。他盯着碌碡前的一堆黄土,走了神儿。那里曾是间牲口棚,如今,石料槽和栏杆埋在土堆下面。西边的黄土堆是两间厢房,住过不少客人。现在上面是半人高的蒿草。
嗨,草比人长呵……他灌了一大口酒。
看到蒿草中间鹤立一株向阳葵,黄花灿烂,他脸上又溢出了笑容,甚至闪过一丝羞赧。他想起了年轻时候的一件事。他陶醉着,手在裤裆里挠着痒痒。
“对畔畔那个圪梁梁上……”
老头儿突然吼了一嗓。一口猛酒呛得他咳嗽起来。一通咳嗽震出两行浊泪。他呵呵大笑。两排肋条骨好一阵蹿跳。靠着树,听着自己呼哧不止的喘息,他刻意歇了歇劲儿,而后,猛然吼道:
“那是一个谁——”
伴着回音,他朝原来院门的位置瞥了一眼。现在那里是踩实的两堆黄土,中间凹下去的部分是出路,白光光的,连着一路缓坡的村道。村道上杳无人烟。鸽子们不知飞哪里去了。远处青山默然,白云也好似凝滞不动。静极了,真是静极了。他斜依树干,眼神干干的,耳朵里空空的。地气蒸腾上来了,眼前白蒙蒙的。
老头儿少年时,也做过一些浮浪营生。这些事流走后,他开始相信父亲的话:人活一辈子,苦不过几十年;守苦几十年,活人几辈辈。
酒劲儿汹涌澎湃,老头儿解开麻绳,蹬掉泛光的掩裆棉裤。
远山依然静默,白云仍旧沉滞。
老汉喝着酒,木然地摩挲光脚板,摩挲赤腚。糙手擦过去又擦过来,皱褶平了又皱了。光线绿了黄了,黑了又白了。
古董贩子就是这时候进村的。
连只狗也没有呀!连只猫也没有呀!失望的古董贩子蹬着自行车,丁零当啷地在村里转了一圈儿。几年前,他在这里收过一只青花碗,正经好东西。挥手跟十几户人告别时,他激动地喊:我认识一个大款,你们的戏台会有的,小学校会有的,啥啥都会有的……反正,他觉得这种憨人有的是耐性。后来他去了很多地方,也遇见过很多憨人,却再没那样激动过。那只碗卖了多少钱,他不记得了。
原来做新房的窑洞破旧了,原来破旧的倒塌了,到处是断垣残壁,到处是腐烂气息,小贩摇着车铃铛,在村里没看到一个人影,没撞见一个活物。他的铃铛声显得多余而生硬。见鬼,他嘟哝着。
青石板路面生满苔藓,石缝里的荒草划破了脚面。他沮丧极了,蹲在一口积满雨水的对臼上,抠了一片黄泥敷着脚背,打算抽棵烟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妈的,如果不是那棵绿森森的槐树,傻逼才会来这里呢。
那棵槐树覆盖了半个村庄,远远望去,给了他繁茂昌盛的假象。
骂了一会儿,抽了一棵烟,蹲在那口曾经舂米舂烟叶的对臼上,屙了泡屎,他觉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做法还不解恨,觉得还可以做点什么。妈的,真应该毁掉那棵树!他骂道。
古董贩子带着鼓囊囊的怨气,丁零当啷地冲向那棵树。至少要剥光它的皮,挖断它的根,要不,干脆放把火。他看看四周,反正鬼才会晓得。
可是,一冲进院子,他就泄了气。
他傻子似的大张着嘴:
好……大!好……可怕!
大得没边沿的槐树冠,势若虬龙,墨如重铅。矮在树面前,他觉得喘不过气来。这他妈哪是树,是他妈集束炸弹!
轰!他感觉自己窒息死掉了。
说真的,那一刻,他眼前极快地闪过一只青花碗。不干了!再也不干了!古董贩子嚷嚷着,啥也不想干了,只想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可是他的腿哆嗦,手哆嗦,自行车跟着哆嗦。他垂下头,失望地打量两只走南闯北的脚。他妈的,青花碗。他嘟哝着。
地气弥散,槐树离他越来越远,小贩恍惚看到挥手告别的场面。小贩的时空感有点错乱。事实上他没有走。——半扇石磨盘后面,他看见一个赤裸的老头儿。
他支好车,小心地走近去。那人该两百岁了吧,形容滑稽,涎水长流,靠着树打盹呢。他好笑地瞧着他,渐渐平静下来。总算是个活物吧。
这种憨货他见多了,不过,正经好东西也是这种人守住的,怎样从他们手里弄出宝贝来,小贩很在行。
小贩开始职业地端详老汉,打量没有围墙的院子。树叶在头顶簌簌作响。
这是一户破落的五口之家。小贩数了数团圆在炕桌周围的板凳马扎,作出判断。小贩笑着挺了挺腰杆,作好了开场的准备。
可是老汉忽然动弹了。
“儿——”老汉在梦中召唤着,声音浑浊。
儿你个鸡巴,小贩笑着,完全放松了,冲老头儿吐了口痰,山汉!
小贩的脚在石磨盘上划了一下,搪瓷缸哐啷摔到地上。
他看着老汉抽搐一下,挤开眼泡,惺忪又警觉地瞅他。
“老人家还记得我吗?”小贩歪着脑袋,心存揶揄。
老汉一脸疑惑,朝他递过一只耳朵。
小贩拾起茶缸,在石磨上认真摆正。
“我一眼就认出你了老人家,你比上次年轻了许多哦老人家。”小贩提高嗓门,将石磨上的几片树叶捻掉。
看得出,老汉激动起来,唇上皱褶抽动着。
小贩半天方才听清,老汉说的是“戚人”。小贩笑着,老山汉!
老汉晃了晃酒桶,倒满茶缸,向他推过来。老汉的动作笨拙,神色夸张,小贩脸上保持着笑容。有一群野鸽子在远处盘旋,自由自在,没人打它们的主意。小贩矜持地弹了弹席片上的灰,坐下来。
“你是个好人,”小贩说,“可是我不好,我早该来看你。”小贩敬给老汉一棵烟,点烟的时候,抚了抚老汉颤抖的手。老汉一直激动着。
小贩觉得轻松一些才好,捧起缸抿了一口:“真是好酒哦。”
老汉咝咝地吸烟,皱纹缓缓舒展,觉出了在戚人面前的难堪,在石桌这边,夹紧腿。
“本来,俺早该来,”小贩紧盯着老汉,思谋着,忽地冒出一句,“还记得吗?我跟你儿子……”
……
“记得……记得。”
老汉混沌的声音真难听。老汉开了口,小贩很高兴,看着老汉悄悄勾起脚,将棉裤拖过去,盖住裆,小贩几乎笑出声,又抿了一口酒。
老汉也笑了:“三儿是个灰娃。”
他们一起笑着,好像想起了某件淘气事。
“很好,是吧,”看样子,开场很好。小贩开始打算谈谈童年、友谊,以及自己的考古专业。小贩为“考古”这个词好笑,“他是个好孩子,不是吗?”
“是的是的。”老汉喝了一大口酒,眼睛里溢满慈爱:
“你们都是老汉的好娃。”
“我们很相好的,你晓得吧?”
“晓得晓得。”
“他聪明、孝顺,是把好手呢。”
“是的是的。”老汉望着不远处的桌凳,惋惜地说,“就是命苦一些。”
“都一样,生在苦里谁不一样呢。”
老汉喝着酒,脊背在树上蹭着痒痒。
有悠长的嘶声传过来,不远处的窑洞门打开,又合上。风吹得几孔玻璃明明暗暗,窑顶芨草起起伏伏,锄钯摇摇摆摆。小贩望着坍塌的院墙、两间破窑、围一圈的旧桌凳,想象这家人往昔的悲欢日月,小院里曾经的鸡飞狗叫。他把握着谈话气氛,觉得不宜过多询问老头儿的家事。
“真好老人家,都搬迁了,奔向新生活了是吧。”
“在下边盖了新村。可惜,山是好山,村是好村哦。”
“山还是那个山,村还是那个村,只是人挪活了呀。”
“连戚人都不来了哦,没头吃草的牛,没只撒蹄儿的羊,没个蹦欢儿的娃……”老汉穆然望着远山,一山烟绿,天色时黄时黑,近处的杨树叶摇着白光。
老家伙并不很糊涂,小贩有点着急,担心地瞅着来时的村路。
“好哦,好哦,好久没好好说话啦!”老汉忽然大声傻笑起来,而后端起茶缸一气猛灌。
树影渐渐挪移。小贩说了不少话,费了不少心机。看看天色,小贩决定快刀抽水:
“这些年,我去过不少地方,学到不少东西。考古你懂不懂,考古?我是个考古工作者。”小贩抽出一棵烟,自己点上。“啥宝贝我都认得,谁有啥宝贝都找我瞧。好多人傍我挣了钱,你懂不懂,钱!”小贩做着数钱的动作,“有了钱可以做很多事,盖屋修院,给儿子做生意,改换门庭。你懂不懂?”
小贩一口气说了这些话,有点气喘,他觉得耽搁的时间不短了。
“你有没有宝贝,老汉?”
……
“你儿子说你有,老汉。”
……
“别光顾喝酒,老汉,快说!有没有?”
老头儿期期艾艾:“有。”
“真有?”
“有。”
小贩笑了,吁了口气,拿过茶缸大喝一口:“阿爷,我跟你儿子好哦。我盼你们好哦。”
“老汉知道,可惜没好茶饭上待戚人……”
“会有的,很快就会有的阿爷。”
“可惜呵……”老头儿的声音忽然凄怆起来。
“……都过去了,阿爷,不用想啦,想也没用哦。活命谁不苦呢,阿爷,家家一样,不用讲啦阿爷。”
“噢……呵呵,”老头儿又换上笑脸,“老汉不嫌日子苦,不怕命苦,儿啊,就怕你们守不住苦哦。懂吗俺儿?”
“不用讲了不用讲了,阿爷,快拿出来吧。”
小贩伸出一只手,“快!”
凉风拂面,槐叶簌簌鼓噪,老汉轻呷浅酒。
老山精!小贩咽着唾沫,不停擦汗。日头已向西滑去。小贩觉得须尽快结束生意。
“阿爷,我有的是时间听你访古,可是……你知道,有很多很多乡亲在受苦煎熬哪,阿爷!”小贩说,“他们没钱给妈妈治病,没钱给娃娃上学,他们的锅都揭不开了,阿爷!他们眼巴巴苦熬苦盼苦等着我呢,阿爷!他们都指望我挣钱呢,阿爷!可怜可怜他们的命吧阿爷!发发善心吧阿爷!”
小贩抽泣着,伏在磨盘上抹泪。
他发现老头儿也激动了。老头儿怆然举目,遥望远山,又环顾一圈小院,最后下了决心,扶着石桌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窑洞走去。
小贩窥着老汉佝偻的背影,踉跄的步履,心里承认,他愿意给这个半醉的瘸腿老头儿一个好价钱。
老头儿在窑洞前停下,俯身从炕桌上拿起盐罐,又摇摆回树下。那丑陋的裸体又坐在了他对面。盐罐是王致和腐乳罐改成的,一文不值。老头儿一言不发,从磨盘上捡起一粒小石头,扔进盐罐,又捡起一粒,扔进去,小贩怀着好奇,耐心地等老头儿把十几粒小石头都扔进了盐罐。老头儿抱着罐子晃荡着,然后从罐里捏出一颗石子,嘬着,放嘴里巴咂巴咂,放桌上,端茶缸抿一口酒。
小贩耐着性子等着老头儿开口。老汉顾自嘬石头抿酒。小贩窝着火,揉着脚面,怀疑老头儿真他妈喝醉了。
“拿出来吧阿爷,我等着呢,快!”
小贩看着老汉把石子一粒一粒,又丢盐罐里,然后把罐子往他这边推了推,小贩摆手拒绝。
“太阳都要下山了,老汉,你说过有宝的是不是?你不能白耽搁俺不是?”
老头儿却半天没话,只管喝酒,嘬石子,靠树上挠痒痒。
小贩拭拭眼角,劝老汉不要喝了。
老汉不紧不慢地晃盐罐,嘬石子,抿酒,咂嘴。
小贩真等不及了,站起来呵斥:“别喝了苶老汉,俺大老远来,是为你好,你懂不懂?你有宝没宝关俺屁事啊苶老汉,受死受活谁管谁啊苶老汉,俺老远远地来,不是想看你受苦,谁他妈不苦,想不苦就得挣钱,钱!你懂不懂苶老汉?钱!”
小贩真是气坏了,真想把苶老头儿的盐罐踹掉。
老头儿说话了:“儿哦,你去过很多地方,老汉没有。受苦人一辈子,黄土黑窑,经见得孤陋,受受活活罢了。”
“废话别说了老汉!把宝交出来老汉!”
“儿哦,你见过了哦,”老汉继续嘬石子抿酒,“儿哦,你跟老汉说了一后晌话,受苦人不诓你,你见过宝了哦。”
小贩一脚踹过去。
日薄风轻,一群鸽子盘旋于山村上空。觅食转天,生来如此。
下山路上,小贩将诓了他一下午时间的老山汉骂得狗血淋头,老憨货,活该受苦。踹了老山汉的罐子茶缸不算,暴揍一顿苶老汉不算,真妈逼应该放把火,烧了那棵树。他骂着,在村口碰上三个弃车而行的外路人。
他想,他们跟他一样,被那见鬼的大槐树给骗了。
小贩走后,鼻青脸肿的老头儿爬起来,拾起茶缸,摸了摸新添伤疤的搪瓷,将酒倒进去,控尽最后一滴。山还是好山,村还是好村,来的都是戚人。老头儿背靠槐树沉默着,抿酒,受活。
远山在暮霭中浮动着,一座山头呈现出黄牛哞叫的侧影,在它身后,群羊咩咩撒欢。槐树荫蔽下的村庄静谧祥和,斜阳透过枝缕晕染在两间窑洞上,依稀能辨一些“喜”字窗花的印痕。老头儿抿酒笑着。老头儿眼中,窑顶炊烟袅袅,院里扇车轰响,禽畜归圈忙。
两位专家和政府干事气喘吁吁,终于赶在日落前进了小院。
他们同样被槐树震慑住了。天!天!这哪还是树,这他妈的,这真他妈的……
政府干事小心措辞,他小心提醒专家:
“您确定吗?这棵沉默在我们这儿的名不见传的丑陋槐树,就是你们誓死要找的神木?价值连城的活化石?”
“必是无疑!”
两位专家异口同声,激动拥抱,涕泪齐下。
为表达喜悦,政府干事也流出了泪水。
在他们激情阐述人与自然、发现与存在的时候,谁也没有在意、没有愿意多瞅一眼树根那儿,那个一直傻笑的活物。
在确定古槐没有受到太大破坏之后,两位专家迅速而仔细地梳理着平生所学,政府干事就专家们的话,在笔记本上迅速作了记录。谈到对神木的保护,两位专家本着科学的态度,一致认为:
“此乃人类文化遗产及自然科学之活化石,或当移植到适宜其生存之绝佳妙地,由专业人士而非傻瓜来保护它。”
政府干事记录着专家们的话,不由瞟了一眼窝在树根那儿的活物。
“再炒一个蒜苗鸡蛋来……”活物大叫。
天色倏暗,灰色鸽群又落回了树底,翅翎扑扑扇腾,次第收拢。碎屑和烟尘翻卷而起。
槐树院的三位戚人惊讶地看过来,只见活物向他们举着茶缸,呵呵傻笑。最后一抹夕阳透过枝叶,打在他跳动的褐色阳物上。
野鸽子们无视一切,蹿上蹦下,有一只落在那活物身上。
“你个灰猴。”活物快活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