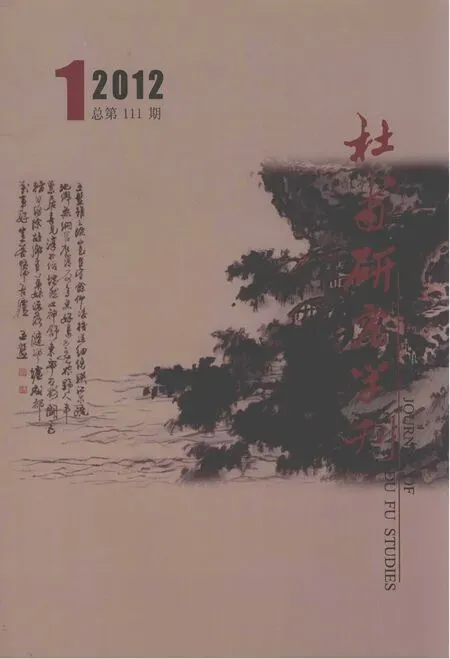邵祖平论杜甫与杜诗辑佚
熊飞宇
作者:熊飞宇(1974-),男,重庆图书馆馆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重庆抗战文化,400037。
因人废言,是学界无可奈何的积弊。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邵祖平因曾遭受鲁迅先生批评,在建国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其成就与贡献,长期以来鲜有论及。现将其履历简述如下。邵祖平(1898-1969),江西南昌人。字潭秋,别号中陵老隐、培风老人,室名无尽藏斋、培风楼。早年肄业于江西高等学堂,为章太炎高足。1922年后历任《学衡》杂志编辑,东南、之江、浙江大学教授,章氏国学会讲席,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秘书,朝阳法学院、四川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大学、西北大学、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建国后,又任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青海民族学院教授。由此观之,邵祖平与四川结缘甚深,也曾游历杜甫草堂。
对于杜甫及杜诗,邵祖平有精到的见解。其相关论述,主要见诸《唐诗通论》、《读杜劄记》和《杜甫诗法十讲》。1922年,邵祖平在《学衡》第12期发表《唐诗通论》。文章前半部分,后以《全唐诗说》为名,重刊于《东方杂志》1947年第43卷17期。另一部分,则以《全唐诗评》为题,载《东方杂志》1948年第44卷第2期。邵祖平曾为《学衡》杂志撰《无尽藏斋诗话》,成读杜数十则,但未尽印布于世。后以课余,于1932年立冬日,约成二十条,题为《读杜劄记》,刊《学艺》1933年第12卷第2期。1945年,《文史杂志》第5卷第1、2期合集刊其《杜甫诗法十讲》,勒为审体裁、明兴寄、探义蕴、究声律、参事实、讨警策、辨沿依、寻派衍、较同异、论善学十端。同年,又在《东方杂志》第41卷第1期发表《杜诗精义》,则仅有述抱负、明兴寄、探义蕴、究声律、参事实、讨警策六目。现就其主要内容,重新疏列排比于后。
杜甫其人。颂其诗,必先知其人。欲读杜诗,必先明杜甫,这是开宗明义第一事。《读杜劄记》将此列为头条。《旧唐书·文苑传》谓:“甫性褊躁,无器度”,《新唐书》谓:“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浇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事君、交友二端,实杜甫一生的大节。在邵祖平看来,杜甫为人尚有二端足可称述,一是“情真”。“情真”者,诚爱充盈,遇物固着,忽悲忽喜不知为累,故于其君,于其国,于其友,于其弟,于其妻,于其子,无不一往情深。二是“气豪”。“气豪”者,天姿英迈,不屑软贴,睨傲狎荡,遇事便发①(247)。《杜诗精义》之“述抱负”,针对《唐书》的讥病,认为杜甫实有大抱负,不过“所如不偶”而已②(63)。“劄记”二十进而指出,杜甫初有用世之志,许身稷契,兴忧黎元,是其本色。然自《三大礼赋》一动人主之后,即遇乱离,遭播徙,辛苦拜左拾遗,而终以救房琯之故,不蒙肃宗省录,自是阶进之望绝无,前后依严武,得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卒,欲往依高适,适又亡。于是终为漂泊之人而竟客死耒阳。考其诗篇,有可悲感者。“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虚名但蒙寒温问,泛爱不救沟壑辱”;“独鹤不知何事舞,饥鸟似欲向人啼”;“北归冲雨雪,谁悯敝貂裘”,皆兴悲于不可悲之地。杜甫的遭遇,只能指证肃、代二主的刻薄少恩①(256)。
“诗史”与“诗圣”。老杜之诗,推服至极者,如秦少游以为孔子集大成,郑尚明以为周公制作,黄鲁直以为诗中之史,罗景纶以为诗中之经,杨诚斋以为诗中之圣,王元美以为诗中之神,各衷一是。对“诗史”一说,邵祖平颇不以为然。《全唐诗评》的“盛唐诗评”指出,人以其善叙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号为“诗史”,实则晚唐文宗时,始有“诗史”之目。盖因“江头宫殿锁千门”记宫室,当时为人主者,欲借诗人成句以兴复土木;为人臣者,则欲拈诗人成句以捷给塞问,并非真正要尊为“诗史”。而宋仁宗问近臣唐时酒价,近臣则告以“急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制铜钱”。《新唐书》于是掎摭细说,尊杜为“诗史”,却不知“诗史”距“诗圣”尊号甚远。诗惟称圣,温柔敦厚,兴观群怨,始有意义与其价值。若只纪事纪言,又何足言贵。至于杨万里《江西宗派图序》尊杜甫为有诗以来第一大诗阀,则更为可笑③(41)。在《杜诗精义》和《杜甫诗法十讲》的“参事实”一项中,邵祖平明确指出,杜甫部分诗篇,确有诗史意味,但有主观判断与文学组织,所以今日尊杜甫,当尊其为“诗圣”,不当尊其为“诗史”。不过,其诗中所叙述的时事,即所谓诗之本事,也可以事实目之。②(67)④(16)正是在此意义上,“十讲”之“较同异”强调说:《杜工部诗集》,不但为唐玄、肃、代三朝的诗史,也是杜甫一生的起居生活史④(25)。
虽不赞同“诗史”这一名号,但邵祖平仍认为杜诗绝似《史记》,读者当具一副眼目对观。《唐诗通论》引叶梦得之语,谓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初不以叙事倾尽为工,至老杜《北征》、《述怀》诸篇,穷极笔力,乃如太史公纪传者⑤(11)。“劄记”十一对此多有分剖。《北征》、《奉先》诸诗似《高祖项羽本纪》;《八哀》、《诸将》诗似《萧曹世家》、《淮阴黥布列传》;《丽人行》、《哀江头》诸诗,似外戚世家;《马》、《鹰》、《义鶻》诸诗似刺客列传及游侠列传;《堕马》、《赠友》诸俳谐体,似滑稽列传。其他尚多相类,不能一一比合。而老杜的好“奇”,尤与史公相似。其诗喜用“苍兕角鹰”,“骐骥凤麟”,“赤霄玄圃”,“死树鬼妾”等,亦如史公好述“白昼杀人”、“刎首谢客”、“悲歌慷慨”、“箕踞骂坐”诸事,此虽仅就其纤小处推言,然就其一生而言,固无所而不遇①(252)。
李杜优劣论。严羽论诗,认为诗有九品,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惋。其大致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著痛快;极致有一,曰入神,惟李杜得之。对此,邵祖平提出异议,认为严羽虽知之,却言之不详,且以李白对举,易惹起文学中的李杜优劣论,故不足取。但邵祖平论杜,自身并未逃出这一窠臼。《唐诗通论》秉承旧说,认为唐诗分自然、工力两大派。至李杜,天才学力,两臻绝境。李白为“自然派之神而圣者”,杜甫则是“工力派神而圣者”⑤(6)。“盛唐诗评”即展开二者之间的比较,其间自有高下显见。首先是五古。杜甫不似射洪(陈子昂)、曲江(张九龄),仅有冲劲清夷之致,而是更加恢宏广丽,其抉情指事、顿挫拗宕处,读者莫不得尽其情,虽李白不能望其藩篱。此体自杜甫开唐调,而李白仍停留在摹古的层面,未能自开生面。其次是歌行。杜甫多以古文笔法为之,故其气骨苍劲,造语横绝,同时除太白外,无敢近之者。再则是五七言律诗。此为杜甫绝技,悲壮雄浑,千古一人。即论其绝句,亦惟一独具之面目。他人则悉多平调,此独戛戛独造。惜其源不从乐府出,以此逊太白一筹③(41)。“十讲”之九,则有更详尽的分析。不过此番比较,更着眼于异同而非优劣。太白与杜公有相同处者:一,太白抗心希古,志在述作,以垂辉千春自任。杜公气劘屈贾,目短曹刘,以垂名万年自居。二,两公俱怀壮志,欲扶社稷。杜公稷契自任,李以太公望、管仲、诸葛亮自比;好谈兵,《唐书》并称其高而不切。三,两公胸次宏阔,洒落不群,俱欲突破天网思出宇宙。四,李杜挺起开元间,七言歌行一以古文笔法出之,格势高老,雄跨百代。相异处者:太白诗从国风、离骚、汉魏乐府、鲍谢诸风人出,多得风人之旨。子美诗从二雅、苏武、李陵、十九首、曹氏父子、陶渊明诸人出,多合于诗家之轨。李云:“借问以何日?春风语流莺”。杜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其趣致不同。此其一。太白旷代仙才,人中奇逸,作诗不耐拘束,豪而见率,故其七言、五言律诗均极少。惟五绝七绝,太白为之,飞行绝迹,极合其纵恣之性。子美则受才雄博,侈情铺陈,精言律理,于诗体除五、七言绝句自开一派不为当行外,他体殆无不雄浑,无不精绝。而五言排体,七言律诗,无不超轶绝伦,非太白所可望。此其二。太白长于学,为人颇近战国时的纵横家,又稍有道家神仙黄白之意,故其诗随处可见乘云翔凤、飘风骤雨之致。谈笑却秦,指麾楚汉,是其心志所在,故于安史犯阙之际,不思勤王,不奔行走,反欲事逆王以取功名,殆有琴瑟不调甚者得为更张之意。其弊在于学未沉着,识未稳定,不及子美“麻鞋万里,远趋行在,嫉恶如仇,事主尽年”那般可敬。这并非因为杜甫之才优胜李白,而是子美好义心切,法自儒家得来,诗的修养远过太白,所以子美述古数章,沉博绝丽处,辄凌驾于太白古风五十首之上。子美识力深邃,寓感重大,不像太白惝恍无定,忽说辩士,忽说剑客,忽说神仙,忽说妇人,不知其宗旨所在。此其三。子美诗格所得者古重高老,拙大雄浑;太白诗格所得者,飘逸高旷,清新秀伟。太白不生于唐,则与鲍明远、谢玄晖诸人当并驱于六朝间;子美不生于唐,则有唐诗格,无以产生。此其四④(24-25)。
杜诗源流。所谓“源”,或言“渊源”与“沿依”。《唐诗通论》之五,即“唐诗作者师法渊源之概测”,曾引秦观的说法:杜子美于诗,实积众流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长于豪逸,陶潜、阮籍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长于峻洁,徐陵、庾信长于藻丽,于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趋,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若非博采众长,杜甫也断不能独至于斯⑤(7)。《杜甫诗法十讲》之七“辨沿依”,称赞秦观灼见杜诗之集大成,最为通识。又胡应麟有言:“王杨之繁富,陈杜之孤高,沈宋之精工,储孟之闲旷,高岑之浑厚,王李之风华,昌龄之神秀,常建之幽玄,云卿之古苍,任华之拙朴,皆所专也。兼之者,杜甫也”。邵祖平认为此语甚是,但惜无诗例证明,故在《读杜劄记》之九剔取杜诗中足可掩盖诸家者,疏列其后。至于方回虚谷《瀛奎律髓》沈佺期诗评云:“学古诗必本苏武、李陵,学律诗必本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此数人者,老杜诗所自出也。”则觉其见稍僻④(20)。
吴沆《环溪诗话》云:“杜甫诗中有风有雅”。此论与山谷称杜诗表里风雅颂者相同。溯源探本,以杜诗分列风雅颂,深得古人意。陈柱撰《十万卷楼说诗文丛》,认为自《三百篇》至唐,诗体不外乎风雅颂三类,而以杜甫入于雅。对此,邵祖平则有所质疑。《读杜劄记》之三认为,杜诗初看本似雅,及加虚心讽咏,则觉雅者其外,风者其内,即令虽为雅诗,亦不能少风诗之描写。如《北征》前幅叙朝野多故,雅矣;后幅叙至尊蒙尘,亦雅矣。惟在中幅,则必叙“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诸语,以膏泽之,足见风雅之相须,如跫跫驱虚之不可或离。杜诗除风雅颂外,犹有骚之一体。诗骚以外,次当更求汉魏乐府六朝诸家诗①(248)。再则是《文选》。唐人重《文选》,杜诗中即有“续儿诵文选,熟精文选理”一语。“劄记”之四对此有所寻绎,举其学选诗者如次:《历下亭》云“修筑不受暑,交流空涌波”,似刘公幹;《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云“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似大谢;《夏日李公见访》云“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似陶公;《园官送菜》云“志士采紫芝,放歌避戎轩”,似鲍明远。其他如“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清晖迴群鸥,暝色带远客”,并可乱陶谢集。而《同谷七歌》脱胎于张衡《四愁》,《八哀》祖述于沈约《怀旧》,并不稍爽①(249)。合观上述各例,足知杜诗渊源有自,波澜不二。但杜诗颇多创造性的转化。“劄记”十五云:古诗“荣名以为宝”,老杜反之曰“荣名忽中人,世乱如虮虱”;曹子建诗“俯身散马蹄”,老杜因之曰“归马散霜蹄”;阴铿诗“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老杜即之曰“月明垂叶露,云逐下山风”;何逊诗“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老杜继之曰“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谢灵运诗“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老杜改之曰“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宋之问诗“水一曲兮肠一曲,山一重兮愁一重”,老杜约之曰“一重一掩吾肺腑”;骆宾王诗“诸葛才雄已号龙,公孙跃马轻称帝”,老杜综之曰“卧龙跃马终黄土”①(253-254)。其间虽有工拙不同,而一经点化,便是杜甫自己的作品。
所谓“流”,或言“派衍”。杜诗开派论,初见于孙僅《赠杜工部诗集序》,以为杜甫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虽得其奇偏,尚轩轩然自号一家。《唐诗通论》之五已略有论列⑤(8)。但邵祖平却认为,晚唐诗家学杜者,尚有李商隐其人,孙僅略而未言,故在《杜甫诗法十讲》之八“寻派衍”中加以补叙。义山摹杜,气貌逼真,其集中有《杜工部蜀中离席》七律一首,置于杜集中,可乱楮叶。唐诗开启宋派者,多为白体、昆体、晚唐体,而最著者则是杜甫。其生涩瘦硬,即为宋贤所师。西昆体是杜诗的支裔流派。江西诗派也是。方回有“一祖三宗”之说。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其间山谷得杜之高妙,后山得杜之精炼,简斋得杜之宏放。盖杜诗如长江大河,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一变而为郊岛,则无寒潭止水,清澈而无洪浪。再变而为义山、西昆,则如清涟縠纹,绮美而少实用。三变而为江西,则如盘涡急湍,能者操舟,仅无倾覆而已④(23)。“劄记”之十,更有细绎。如《戏简郑广文》云“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即骑马归,颇遭官长骂”,山谷诗即每挹此风趣。《万丈潭》云“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后山亦每喜此句法。《水阁朝霁》云“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范石湖平丽处似之。《岳阳楼》云“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剑南感愤国事诸作,大抵类此。《送辛员外》云“细草流连侵坐软,残花怅望近人开”,半山“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取此而更为工致,惟句中之“因”字、“得”字,终是宋人语,不及杜甫气象之浑融无迹①(251-252)。唐宋之判,也可由此见出。
杜诗残膏剩馥,沾溉百代,学者敝精殚神,心摹手追,不乏其人。然如东坡句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学之不善者,多袭其皮毛,遗其神髓。仇沧柱云:杜诗句法,后人用之而工拙不同。统观工部全集,学之无病者,十得七八;学之不善徒增疵纇者,亦十得一二。子美诗朴而近俚,故欧阳修不喜其“老夫清晨梳白头”,“垢腻脚不袜”。王士祯则直讥为村夫子。若无惊才劲气、丽思翰藻以副,不过徒见其粗拙可笑。因此,《杜甫诗法十讲》又别列“论善学”一节④(27-28)。其得失,则见诸《读杜劄记》十九。学杜者,得其雄浑固难,得其简丽亦不易;得其拙厚固难,得其新秀亦不易。而世俗之学杜者,往往于其悲天悯人忧叹内热者求之,而不知老杜逸情野趣,深自媚悦者,固亦有在。读《奉先》、《咏怀》诸诗,苍莽郁结,想见其为人,及其濡笔作《游何将军山林十五首》,又复赤舄几几,雍容闲豫,退食自公,纡徐委蛇,其名贵气象,非盛时人物莫辨。而近世学杜如吴陋轩者,则寒窘逼仄,满纸酸鼻,盖不仅有草野气,亦更兼酸饀气。推究起来,境遇的不同是其一,更主要的还是胸襟学问的差别。正因为如此,古今诗人学杜甫者虽多,而卓然可自成一家者,邵祖平以为仅李义山、黄山谷、元遗山三人而已!李学杜得其深,黄学杜得其奇,元学杜得其大(元遗山《论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皆若似杜而非杜,非杜而似杜,既不甘为古人臣仆,亦不忘其初祖,此真善学杜甫者。其他如张籍之古淡,姚合之海切,贾岛之僻涩,嗛嗛之德,不足有。后山、简斋与山谷并学杜,虽号为“三宗”,实则后山学杜失之隘(后山句如“飞萤元失照”、“寒花只自香”等于硬黄褟帖矣),简斋学杜失之晦(简斋诗典实太多,佛乘道藏,尤贪用),非山谷之比。陆放翁受诗法于曾茶山,然曾诗局宇不敞,绌于才气,至放翁则声势壮弈,才思烂漫,不仅青蓝寒冰,突过乃师,且遥与浣花异代相视如两雄。盖陆放翁得杜之心气,虽貌不为杜,然较之终日矻矻师杜者,其成就已不可同日而语①(255-256)。
杜诗体裁。诗经立诗教之本,楚骚为词赋之祖,垂为体裁。至后世所谓古今诗,依时期演变,可示为三体,即汉魏体、唐体、宋体。其中唐体为诗中脊干。杜甫为审言之孙,生睿宗末叶,承其家学渊源。诗体灿备后,无须别创新体以骋其才情。然不变之中,有矫变,有恢廓,如五言古诗,穷极笔力,扩张境界,不觉自十韵展为五十韵《自京赴奉先咏怀》,又展为七十韵《北征》巨制。五言排律,更务铺陈终始,排比声韵,故《秋日夔府书怀》,则已展至一百韵。七言古诗歌行体,气格苍老,雄跨百代。如:“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李潮八分小篆歌》),以古文笔法出之,大矫初唐绮靡纤巧之习。“劄记”之八,以为老杜七言歌行,其雄悍处不可及,其拙厚处亦不可及,关键在其于换韵紧前一联,惯用对语,以厚其势。宋人学老杜七古者,固不乏人,但只学得声势流转,峭拔廉悍,于此处似尚未窥见①(250-251)。五言律诗则有扇对格、四句一气格、八句一气格。七言律诗,则变体尤多,有自第三句起失粘落平仄格,有自第五句起失粘落平仄之折腰体,有颈联腹联均失粘落平仄格,有第五句起不粘第七句后复不粘之落平仄格,有拗体,有吴体。杜诗七律泼辣悲壮,字字威棱逼人,考其谋篇之法,惟在得势。“劄记”十二认为一篇重心,尤在颔联。颔联得势,则后半幅不患无腾坡走阪之致。《有客》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野望》云“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登楼》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秋兴》云“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等,皆各律颔联,而为一篇警策①(252-253)。七言绝句,有律体之绝句格,有拗体之绝句格,有第三句呼应第一句、第四句呼应第二句之口号体。杨仲弘《诗法家数》云:“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若以此说绳少陵绝句,则其所作,几全无主句,不过是对列二联而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究竟有何关涉?此杜甫于绝句本无所解之证(胡应麟语),无怪人以半律讥之。那么,工部集中难道就没有绝句可诵?曰:五绝得《归雁》,七绝得《赠花卿》。“肠断江城雁,高高正北飞”;“此曲只应天上,人间难得几回闻”,神味既不在王龙标、李青莲之下,也与杨仲弘的矩镬相符。乐府方面,不袭旧制,大创有唐新乐府,如“三吏”、“三别”、《哀江头》、《哀王孙》、《兵车行》、《洗兵马》皆是。更有《曲江三章章五句》学诗经格,《桃竹杖引》学骚体格,《杜鹃》学乐府诗江南曲格,再加上写琐事、纪风土的俳谐体,无不是杜甫炉锤自具、方寸独运的新体变体诗,所以,究杜诗者,对此当首先审认清楚④(7-9)。
杜诗声律。杜甫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其精稳惬律处,常得力于改诗,故曰:“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又曰:“新诗改罢自长吟”。杜诗声调,可以“悲壮沉浑”四字概括,却又不能尽赅其能事,也有奇创险急之作,如七绝,子美就曾自创一种拗体,崒嵂不平,错落排奡,最为特殊,不容他人仿效②(66)。杜诗声律,不唯近体中具之。《容斋随笔》载张文潜暮年常喜哦《玉华宫》五言古诗,至三日不绝口,何大圭请问其故?回答说:“此章乃风雅鼓吹,未易为子言!”盖好其音响节奏至深。对杜之五古,邵祖平最喜《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第三首,每诵之,觉其清幽激越,如闻九溪十八涧之泉声活活,又疑环佩璆然。考其声律,则此诗凡双句第三字悉用平声,其所押为平声韵①(249)。又杜诗七古中最工丽而善焉喜情者,当推《洗兵马》第一,其音节亦极谐美,有丝竹之音,嘹喨悦耳。此外七古如《同谷七歌》,飒沓飘忽,悲凄哀诉,音节几疑神化。《哀王孙》、《哀江头》音悲而肃,《晚晴》音颓而放,《角鹰》音峭而急,读者熟讽,可得其妙。又七律诗中之拗体者,则首推《白帝城最高楼》,音节奇姿,令人不可捉摸,惟有叹此老伎俩之狡狯①(250)。
“神来说”。杜甫有文章通神之论,尝自状其诗,除“吾人诗家秀”、“诗接谢宣城”、“诗名惟我共”、“诗是我家事”、“语不惊人死不休”诸自负语外,其他如“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即自喻其成就之到;“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即自誉其思力之至;“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即自绳其气势之浮;“律比昆仑竹,音知燥湿弦”,即自譬其格律之细。舍“成就”、“思力”、“气势”、“格律”之外,尤有一必具之物,维何?《读杜劄记》之二认为是“神来”,故复补以数语:“诗兴不无神”,“下笔如有神”,“诗应有神助”,“诗成觉有神”,“文章有神交有道”①(248)。《杜诗精义》和《杜甫诗法十讲》有“探义蕴”一条,指出:这正是诗道的极诣,离去畦町踪迹,猝不可求。其中,神即理,理即义蕴。关于杜诗的义蕴,从其《写怀》诗,可略见一斑。“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非关故安排,曾是顺幽独”。此儒家之哲理。又云:“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我不知,负暄候樵牧”。盖已深得印度哲学之髓,法执我执皆已尽忘。再云:“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这则是老庄绝学无忧、为道日损与不益生而达生的情怀。杜甫取精用宏,以儒家哲理,建立民胞物与的兼善思想;同时出入二氏之学,破除妄执,齐同得丧,从而铸成其思想与义理。正是在积学富理的基础上,诗方有神,神完而义蕴自足。在邵祖平看来,杜甫于三家思想之外,又有一种不夷不惠、非周非礼、亦儒亦侠的诗人思想,超然独存于天地之间。这种思想或精神,慈祥恺悌,通于 人 物,洒 落 飞 腾,绝 无凝滞②(65)④(11-12)。
杜诗抉微。自宋人“巩溪”、“岁寒堂”以来,杜诗诗话甚多,惟皆包论大体,鲜及纤细。邵祖平则从小处着眼,发现杜诗精绝处有二。其一,《李崆峒集》曾云:叠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得律诗三昧,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幛泰碑在,荒城鲁殿余”,前景寓目,后景感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诏从三殿去,碑刻百蛮开”,前半阔大,后半工细①(249)。古往今来,诗人虽众,然未有及杜子美者,以工致者少悲壮,排奡者寡妥帖。其中奥秘,在于杜诗阴阳之美毕具而极胜。子美有“马”、“鹰”、“画松”诸诗,后有“风雨落花”之什;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浑脱行》,后有“黄四娘家花满蹊”之作;有“子章髑髅”、“王郎莫哀”之词,复有“牙樯锦缆”、“香雾云鬟”之句,莫不阴阳并美,配置惬当。就其《北征》一篇来看,浑雄庄阔;而“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诸句,则又细熨妥帖,香泽动人。一篇之中,阴阳之配置尚如是,况与他篇相互乎?此杜诗之所以独绝①(254)。其二,少陵各篇起结必争,皆有奇采起句,如《天育骠骑歌》、《慈恩寺塔》、《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简薛华醉歌》、《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短歌行》、《王兵马使二角鹰》等篇,捉笔直写,奇横无匹。用比兴起者虽多,却是各诗家常用的手法,故无需标榜。结句如《章赠韦左丞丈》、《北征》、《洗兵马》、《忆昔》诸巨篇,足握全篇之奇,固不必论。他篇悉用一种开拓法,而常喜用一“何”字,如“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大雨》);“自古有羁旅,我何苦衷伤?”(《成都府》);“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藜?”(《无家别》);“若道巫山女麤醜,何为有此昭君村?”(《负薪行》);“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等等,余不尽书。反观宋之问“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司空图“味外味”,姜夔“有余不尽”,则难及此老后路宽宏①(253)。
“草堂”。草堂祠紧邻浣花夫人祠,杜甫卜筑幽栖之处。对此,邵祖平也有所质疑和考辨。其一,入祠门向左趋入,亭院洒落,有堂一所,中祀诗圣杜甫,左右陆游、黄庭坚配飨。放翁来蜀依范石湖,身世略同杜子美,但世代在山谷后。曾茶山私淑山谷诗,学而传授于放翁,放翁诗名虽在茶山上,但师承次第,不容凌躐,何以配飨诗圣,陆翁反在山谷之上?此邵之所未解。其二,考“草堂”一名,未至成都者,皆以万里桥西一草堂,即杜诗《堂成》一首之“堂”,纯为杜公自筑以幽栖者,而不知浣花溪先已有草堂。杨慎引《文选》注云:“萧齐周颙,昔经为成都令在蜀,至金陵时,以蜀草堂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寺。”可知蜀之草堂,原为一寺,子美不过依其地曲折而卜筑。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杜少陵在成都有两草堂,一在万里桥之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万里桥故迹,湮没不可见,或云房季可园是也”。综观各家记载,草堂寺最古,闻名于齐梁时。草堂自草堂,浣花夫人祠自浣花夫人祠,各不相涉⑥(31-32)。
对邵祖平的《唐诗通论》,杜晓勤认为,此著是20世纪对唐诗较早进行的系统研究,虽未能够完全跳出明清以来唐诗研究界“天分”、“学力”之争的框架,但对唐诗艺术特质的把握和唐诗优缺点的评述,深刻而中肯。其精彩新警的剖析,对当时文坛重宋轻唐的风气,引导学界重视研究唐诗,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⑦(71)。这是总体评价。其实,就其中论杜部分,又何尝不是如此!邵祖平论杜,显然仍未蜕去传统的点评形式,其遣词造句,也多采用古代文论话语,但所论对象与内容,如其所言,已无关乎杜甫本传、世系、年谱和史迹①(103)。就其系统性而言,则初具现代学术品格。遗憾的是,这些论述和批评,迄今为止,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笔者谨以此文,聊作引玉之砖。
注释:
①邵祖平.读杜劄记〔J〕.学艺,1933(2).
②邵祖平.杜诗精义〔J〕.东方杂志,1945(1).
③邵祖平.全唐诗评〔J〕.东方杂志,1948(2).
④邵祖平.杜甫诗法十讲〔J〕.文史杂志,1945(1/2).
⑤邵祖平.唐诗通论〔J〕.学衡,1922(12).
⑥邵祖平.成都名胜访问记〔J〕.旅行杂志,1930(1).
⑦杜晓勤.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