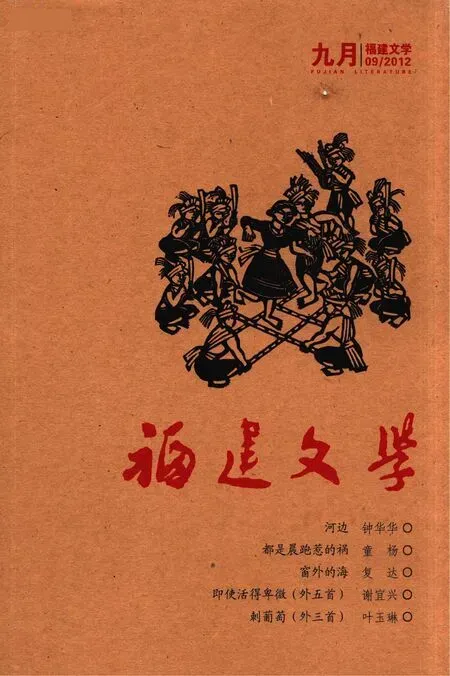苜蓿进士
缪 华
第一和前茅,虽然指的都是名次靠前,但前茅还只是靠近头里,而第一则是站在头里。号称第一,这让后来者望其项背的荣耀,无疑是让人既羡慕又嫉妒的。不论是靠巧合还是凭实力,只要站在第一的位置上,就意味着无人超越且有开先河之态。
很多人都处心积虑在力争第一。世上也因为有人争来夺去,才变得扑朔迷离、世事难料。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文坛、无论在武场还是在赛场,个个都憋足了劲,拼得是你死我活。在武侠小说中,很多武林高手都为天下第一的名号而使出浑身解数,什么“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打得是天昏地暗。看来,这第一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实力说话呀。
不过,薛令之拿了第一,凭的是运气,没费太大的劲,就轻轻松松拿了个开闽第一进士的称号,成为了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这绝不是实力的比较,而是时间的早晚。之后福建的状元榜眼探花也不乏其人,薛令之的故乡——宁德就曾在宋朝出过状元余复、缪蟾,后来居上。但薛令之却先拔头筹。也许他不如你文采出众,也许他不如你才华横溢,但他比你早中进士,这可是铁板钉钉的不争事实,你不得不认了。
薛令之是在唐神龙二年(706年)一举登科的,那年他24岁,是一个青年才俊,这么年轻就为福建争了光,也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科举从隋朝大业二年(606年)开科取士,到唐中宗的神龙年间,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之前的福建竟然没有人能够登科,这不能不令福建的后人感到汗颜。我们这有一个村名叫登科地,虽不清楚和科考有什么联系,但取这个名,肯定蕴涵着某种期望。福建地偏东南,离西北的长安相距甚远,属蛮荒之地。过去是以中原地区为汉民族的中心,对四邻地区素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福建没有多少人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再加上远离政治中心,信息不灵,无人中举也无可厚非。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南北的交融,蛮荒的福建迟早会有人中举的。这个“第一”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捡到的人无疑是撞了个好运,它竟落在了福安人薛令之的头上。薛进士之所以中举,得益于家庭的影响。他的先世居于河南高阳郡,先祖薛贺曾被南朝梁武帝授予“光禄大夫”之衔,虽然这属于现在的“顾问”之类的散官,但也算是江南士族人家了。为避战乱,薛贺离开梁都城建康(今南京),举家南迁,来到了当时温麻县西北的乡村——石津矶(今宁德市福安境内),过着自食其力、宁静平和的生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开创了家业,成为了薛氏入闽的第一世祖,这又赚了个第一。
到了薛令之出生时,已经是李唐的天下了。此时的唐朝已经走过了63年,经过太宗的“贞观之治”和高宗的“永徽之治”,轻徭薄赋、国富民强。在选人方面,开科取士作为由门第特殊阶层开放政权的一条途径,给很多寒门庶族的读书人带来了希望。求取功名之风日盛,薛令之勤读经史、饱览诗书。他在入仕前写的《灵岩寺》一诗,就表现了志存高远的政治抱负,以苏秦和韩信自比,期望得到明君的赏识。
在春光明媚、春花浪漫的季节,已经通过了在福州“解试”的薛令之踌躇满志地离开家乡,远赴长安,开始了他的苜蓿生涯。唐科举考试主要以诗赋取人,进士所考的科目主要有诗赋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诗赋为薛令之的强项,否则《全唐诗》也不会收录其诗的。经过省试、殿试,到了冬日放榜之时,温暖的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睁开眼时又被红榜刺得合上了眼。“薛令之”三个大字名列进士榜内。昨日白衣,今日朱紫。唐诗人刘禹锡写过一首放榜的诗:“礼闱新榜动长安,九陌人人走马看。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描绘出了唐社会艳羡及第进士的盛况。
更让薛令之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成了前无古人的福建第一进士。这对福建来说是件破天荒的事,值得大书特书。就像今天的许海峰在奥运会上为中国拿下第一枚金牌一样地载入了史册。薛令之当然也很高兴,因为这已经超越了他个人和家族的功名,成为了福建的骄傲,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这功名还让宁德人感到骄傲无比。
薛令之确实风光,这个中秋节出生、自号“明月”的进士终于有机会和皇室帝胄近距离接触了,也有了步入仕途的资格。我们现在很多的作品不了解历史,写状元、写进士,总写一中举就当了官,其实不然,至少在唐朝不是这样的。考上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按照唐朝的“辟署制”,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才能做官。薛令之后来当了官,于“开元中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册太子”是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所以,薛令之任这个“太子侍讲”肯定是在太子册封之后,那时的他已过了不惑之年。此前他究竟在干什么,没有史料,我们不敢妄猜,但他肯定经历甚至目睹了“神龙之后,后族干政”。太子重俊政变、唐中宗被毒死、韦皇后临朝称制、李隆基诛灭韦氏、唐睿宗重新登位,太平公主政变未遂被灭,唐玄宗登基……一系列的权力争夺,让众多的官员和举子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只好下赌注般地押宝选主子。
薛令之站到了李隆基的一边,这一站就站对了。投桃报李,李隆基继位后,不仅把具有重要作用的“左补阙”授予了薛进士,还另外给他增加了“太子侍讲”一职,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和储君在一起,这是一种信任、一种关照。
“左补阙”属于谏官。唐制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掌供奉谏诤,凡朝政阙失,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说白了就是规谏皇帝、纠正朝政,另有弹劾百官的权力。这个职务的作用,取决于皇帝纳谏的态度。唐太宗借鉴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开了“从谏如顺流”的先河。他的曾孙唐玄宗登基伊始,效仿先祖,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薛令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奉皇命写《唐明皇命吟屈轶草》一诗,说的就是这事。诗云:“托荫生枫庭,曾惊破胆人。头昂朝圣主,心正效忠臣。节义归城下,奸雄遁海滨。纶言为草芥,臣谓国家珍。”屈轶草是古代传说的一种草名,据说能指出佞人,又名“指佞草”,在此喻为谏官的象征。而皇帝命题,说明了皇帝在倡导敢于谏诤、放胆进言的政治氛围。
在这样宽松、和谐的氛围里,皇帝纳谏如流,谏官言无不尽,君臣齐心打造出了一个辉煌的“开元盛世”。虽然没有史料记载薛令之在这个过程中都谏了哪些言做了哪些事,但一定是谏了言做了事的。否则,依唐玄宗用人的原则,无所事事、滥竽充数的人肯定会被免职的。
开元中期,“因时极盛,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已经被膨胀的个人魅力所左右,对谏诤的官员开始应付和罢免,曾担任过左补阙的名相张九龄被撤去了宰相一职。这个信号让口蜜腹剑、见风使舵的李林甫捕捉住了,上任伊始就拿谏官开刀。被剥夺了发言权的薛令之和众多谏官只能噤若寒蝉,只好专心致志干他的“太子侍讲”。
太子是储君、是未来的皇帝。伴君如伴虎,之前发生的太子之争,让与世无争的薛令之卷入了后来的政治斗争之中,最终阴郁离京,终老故乡。
在唐玄宗五十四岁那年,他“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终于意识到确定储君的事。高力士拥三子忠王李亨,李林甫拥十八子寿王李瑁,双方相持不下。玄宗最终接受了“推长而立”的原则,立李亨为太子。李林甫压错了赌注,如临深渊,总想找机会颠覆太子的地位。动不了太子,就动太子府的人。因此,东宫官员生活十分清苦,薛令之为此感叹而写下了《自悼》一诗:“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保岁寒?”苜蓿是一种马吃的草料,连这个都上了桌,足见东宫生活之清苦。吃多了山珍海味的唐玄宗看了很不是滋味,心想都太平盛世了,你还发什么牢骚!在薛令之的诗边判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这下子把薛令之逼到了绝路上。这不是下个跪磕个头能够挽回的事,让你知趣离去已经是很宽容了,要不然投入牢狱判个斩立决也不是不可能的。
薛令之只好走人了。他肯定后悔写了那首诗,我也觉得薛进士写的这首诗放在自己的“博客”里就算了,实在没有必要到处张扬而且让皇帝看到。事情闹大了,太子也救你不得。
薛令之走的时候很凄凉,没有车辆,没有随从,自己徒步行走,走了多长时间不清楚。远离了繁华的皇城,告别了京畿的生活,薛令之转了个圈又回到了石津矶这个小山村,中秋之夜遥望圆月,心有不甘地等待着。这一次等来的会是什么,不知道。年龄不饶人,年近七十的他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东山再起。不过,他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唐玄宗还念叨着他,下了一道“令有司资其岁赋”的圣旨。对于来自朝廷的天恩,以清廉自诩的薛令之采取了“酌量受之”的谨慎态度。
几年后,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出逃。天宝十五年(756年),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城继位,是为唐肃宗。八年平叛,收拾金瓯。在百废待兴之际,新君急召旧人,欲兴昔日繁荣。“肃宗乾元初以雅旧赠(贺知章)礼部尚书……令之长溪人,肃宗亦发旧恩召,而令之已前卒。”(《新唐书》)薛令之的死,让肃宗十分惋惜,“嘉叹其廉”,于是,“敕其乡为廉村,水曰廉溪。”这个封号,在当今强调廉政建设的环境中更加寓意深长。
平心而论,薛令之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也许和他的职位、文采等因素有关。不过,他在福建还是有影响的,毕竟他是开闽第一进士。另外,还有一个也和他有关的第一,那就是“苜蓿”一词的使用和词义的延伸。从此,苜蓿竟成为了形容学官清贫和廉洁的熟典,为历代的诗文家频频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