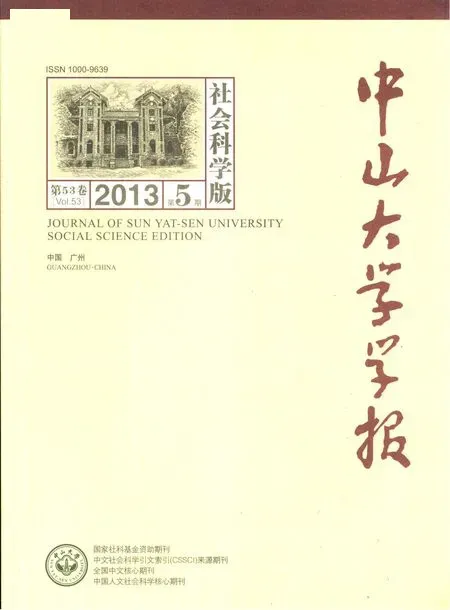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鲍曼的后现代性思想研究*
穆宝清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1925— ),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文化理论家,也是20 世纪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鲍曼1925 年11 月19 日出生于波兰波兹南的一个贫困犹太家庭,他的出身对他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中鲍曼参加了波兰红军,后来由于坚持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受到反犹主义的影响离开波兰,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求职,并定居英国,曾任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解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二难》(1991)和“后现代性”三部曲《后现代的伦理学》(1993)、《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1995)、《后现代性及其缺憾》(2002),其他如《全球化:人类的后果》、《流动的现代性》、《个体化社会》、《流动的时代》等也广为人知。
鲍曼学识渊博,其著作影响深远,触及后现代社会的诸多思想领域,但他始终阐释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的层面,而不是沉湎于理论文本的解读。鲍曼从不渴求建立详尽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他是一个现代生活的阐释者,而不是一个寻求立法和规定的知识分子。鲍曼自始至终的关注对象是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的生存境况,后现代栖息地的居民如何尝试着为自己创造有意义的生活。鲍曼遵循这一信条:“知识是粗糙的,而生活是微妙的。”①Tony Blackshaw,Zygmunt Bauman,London:Routledge,2005,p.3.他把日常生活的节奏转变成为批评的实践,并将其融入社会学的想像,因此,我们可以说:“鲍曼的社会学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活动,他最终主要致力于理解构建的过程(the structured process)而不是某一特殊的结构或学派本身。”②[美]泰勒、文奎斯特编著,章燕、李自修等译:《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36页。鲍曼认为,线性的脚本无法传达思想的逻辑,人类的经验要比任何对它的解释丰富得多:“那些想与人类经验展开对话的人,最好放弃轻易到达旅途终点的梦想。这一旅程没有幸福的结局——一切幸福都在旅途中。”①Zygmunt Bauman,Postscript: Bauman on Bauman-Pro Domo Sua,in The Sociology of Zygmunt Bauman: Challenges and Critique,edited by Michael Hviid Jacobsen and Poul Poder,Burlington,VT:Ashgate,2008,p.240,238,239.在有关后现代性愈加喧嚣的激烈争论中,鲍曼的声音非常独特。他的著作为我们了解当代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可以完全作为“困惑者的向导(guide to the perplexed)”②Stuart Sim,edite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ostmodernism,London:Routledge,2001,p.195.。
一
按照鲍曼的语义学,“后现代性”指的是一种“社会”(society),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人类状况(human condition);而“后现代主义”代表一种“世界视野—和—认知策略”(worldview-cum-cognitive strategy)③Zygmunt Bauman,Postscript: Bauman on Bauman-Pro Domo Sua,in The Sociology of Zygmunt Bauman: Challenges and Critique,edited by Michael Hviid Jacobsen and Poul Poder,Burlington,VT:Ashgate,2008,p.240,238,239.。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始于固体的现代性开始反思自身的时刻。在个人的、“生活—政治”的层面上我们仍然处在现代时期,社会身份不再是“给予”或“归于”我们的。然而,我们也是属于后现代的,我们不再奢望享有一生的任何获得的或设想的身份,社会认可的各种身份随着时间而改变了其数量和成分,因而“在身份构建中最大关注不是如何‘看到这个生命—工程进行到最后’,而是如何保持许多工程作为选择的可能性。可变性而不是固定性是一个‘良好—构建’的身份标志”④Zygmunt Bauman,Postscript: Bauman on Bauman-Pro Domo Sua,in The Sociology of Zygmunt Bauman: Challenges and Critique,edited by Michael Hviid Jacobsen and Poul Poder,Burlington,VT:Ashgate,2008,p.240,238,239.。鲍曼认为,后现代状况的一系列典型的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他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合适描述它的术语。因为,所有液体的根本属性就是“流动”(flow),液体所拥有的特征可以作为一个对我们时代的恰当隐喻:像液体一样,我们的这种状态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其形状。“液体”作为一个指向现代性当前阶段的隐喻就使脆弱性、易破碎性,尤其是人类之间关联的形态表现得特别显著。因此,他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难道现代性不是一个从起点就已开始的‘液化’(liquefaction)的进程吗?难道‘溶解液体中的固形物’(melting the solids),不一直是它的主要的消遣方式和首要的成就吗?换言之,从现代性的萌芽时期起,难道它不一直是‘流动性的’吗?”⑤[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前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第3—4 页。
作为后现代主义著名的理论家,鲍曼核心的思想就是他对“流动性”的论述。鲍曼在著述中使用了“稳固”和“流动”来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从某种程度来说,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这一隐喻并没有完全与后现代性分离,因为隐含于后现代中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的观念相关联。雷蒙德认为,鲍曼使用“流动的现代性”这个新的话语,“或许出于对后现代主义不能面对在西方世界以及整个世界范围正在出现的不平等境况的不满。鲍曼早期关于不平等的论著主要涉及西方社会的问题,但是由于现代性的全球化的影响,他关注的视野延伸到了世界范围。由于这个原因,流动性的观念对于概括现代性的流动及其在全球的后果是恰当的”⑥Raymond L. M. Lee,Bauman,Liquid Modernity and Dilemmas of Development,Thesis Eleven,Number 83,November 2005,p.62.。在鲍曼看来,确定性代表了现代性,而不确定性则代表了后现代性,不确定性就是流动性,没有固定的规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未来——现实主义的未来和理想的未来只能在一系列的‘当下’(nows)中捕捉到。”⑦Zygmunt Bauman,Consuming Life,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 1(1) : p.22.。鲍曼在他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中针对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阐述了现代化与后现代的基本区别,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永远变动的世界里,焦虑凝聚成为惧怕陌生者,它充斥在全部日常生活中,充斥在人类现状的每一个方面和角落。”⑧[英]齐格蒙·鲍曼著,郇建立等译:《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年,第9 页。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不再有稳定的基础,每个个体都时刻处于流动之中,非中心的社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无法找到自我的流散的存在,再也没有传统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结构性,也没有结构自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压倒一切的就是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不管是关于人自身,还是关于社会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标准都是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差异性、变动性成为后现代的根本标志。所以有人把当今社会称为晚现代,有人称为后现代,有人称为超现代,也有人称为第二现代性,但鲍曼则称为“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流动的现代性》。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的变化都是草率的。系统性结构的遥不可及,伴随着生活政治非结构化的、流动的状态这一直接背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在对人类状况进行宏大叙事时起构架作用的旧概念。”①[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第12,12—13,194—195 页。因此,《流动的现代性》可以看作鲍曼竭力去证明和理解进步的异化而作出的不断的努力。
在鲍曼看来,如果现代性由于追求固定的结构和以稳定性为标志而被称为固体的话,那么后现代则可称为流体。因为后现代的基本特点就是流动和不稳定性,没有可以用来一劳永逸地指称的性质与特点,到处充满了矛盾、断裂、出其不意的更新,生活在差异之中没有什么再是新的,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差异,并被强迫接受差异的永久性。只有新奇是后现代惟一审美的标志,传统僵死的结构及停滞的步伐都在后现代不断更新的英勇无畏的洪流中清扫净尽。所谓严密的道德体系与死气沉沉的生活秩序都在自由灵活的后现代熔炉中溶解为一种可变的液体,再也没有清晰的界限与固定的风格,沉重的现代性就被更加轻灵的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的意义非常丰富,借助许多不同的标识,我们可以追踪它的实现和随后的进展。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时代:“现代生活和现代背景……突出特点也许是‘差异产生差异’(difference makes difference);也许是它们的所有其他的特性都源于它的关键特性。这一关键特性是空间和时间之间的变动关系。”②[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第12,12—13,194—195 页。因此,传统的越大越好,追求体积、数量、笨重的重型机器时代被一种没有体积、无法计算、更加空灵的信息时代所代替。代表权力与财富的不再是看得见的矿山、难以移动的厂房、笨重的机械,而是无法看见的股票、随身携带的信息、无处不在的品牌符号。这样,现代性的沉重就与后现代的流动形成了对比,正如福特主义的工厂和比尔·盖茨的软件形成的对比。福特主义的工厂是以数量和重量为标志的传统工业,它意味着规模的扩大、空间的扩张及时间的紧凑;而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软件资本主义则是以所谓轻快的风格为代表的,多元、快速、富于变化就成为其根本特征。时空不再像传统现代主义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空间的移动性和时间的闪瞬性使后现代的软件资本主义呈现出与传统钢铁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风格。正如鲍曼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探讨达沃斯会议观察员塞纳特研究比尔·盖茨的个性时所说的:“塞纳特说,比尔·盖茨‘看来不会对某些东西深深地着迷。他的产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推出,然后同样迅速地消失,然而洛克菲勒却想着要长期地拥有油井、建筑物、机械或是铁路。’盖茨一再重申,他宁可‘将自己置于可能性的网络中,而不愿让自己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工作中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失去勇气’。看来,盖茨最为打动塞纳特的,是他的从容大方、坦率直言,甚至是让他感到自豪的‘毁灭自己创造的东西,只满足目前片刻的需要’决断力。盖茨看起来是一个‘在位置的变换之中取得成功’的选手。他非常谨慎,不会对任何事物产生情感(尤其是情感上的依附),或是不会持续地参与任何事情,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创造。既然没有任何一次转变会让他长期地向同一个方向走下去,而且既然离开原定途径或是重新回头,依然是长期直接可行的选择,那么他就根本不会担心自己作出了错误的改变。我们可以那样说,除了可得到的机会范围的扩大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会积聚成或形成他的生活轨迹:机车刚刚向前移动几步,铁路就被摧毁了,脚印就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东西刚刚堆放到一起,它们就土崩瓦解了——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忘记。”③[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第12,12—13,194—195 页。
塞纳特对比尔·盖茨个性特征、人生信念所呈现的后现代特性的深刻见解令人赞叹,这充分说明后现代精神的无处不在。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日常生活,无论是宏观的哲学政治还是微观的精神内心,到处都充满了后现代的流动性。正如人们常说,无论是谁,只要事业的起点是微软公司,他就无法知道自己事业生涯的终点在何处。对此,鲍曼也说:“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移动,不管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不管是目前的还是未来的,也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我们都不能确定,他/她获得了永远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利,而且,没有谁认为,他/她在某地永远的停留是一个可能的前景;无论我们何时停下来,我们不是部分地被取代,就是处在了不合适的位置上。在此,我们境况的共同性终结了,差异开始了。”①[英]齐格蒙·鲍曼著,郇建立等译:《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第109 页。因此,在鲍曼看来,完美的观光者与不可救药的流浪者就成为后现代人的两种基本生活模式,他们都在移动中生活,只不过由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不同而真正享有自由的程度不同而已。如奥威尔小说《1984》描写的集权主义所极力追求的系统性、稳定性、完美性已被偶然性、变化性、模糊性代替,没有什么是事先决定的、永恒的,也没有什么不可能,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只有流动和变化是永恒而惟一的权威。当代社会的问题不再是保持传统和维护其稳定性,而是不断创造出他者:“当代社会其特征表现为突出新奇,贬低陈腐(marks its newness by relegating the old)。”②Zygmunt Bauman,Consuming Life.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 1(1) : p.23,12.流动的现代性生活意味着忍受这一事实:不仅“他者”不是“他者”了,而且你本人也不一定就是你过去理解的“你”了。这是因为“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变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围绕着意想不到的、充满着常常被顿时‘感觉’到的偶然事件,并且通向其他领域的世界”③Tony Blackshaw,Zygmunt Bauman,London:Routledge,2005,p.98.。换言之,当代人所面临的窘境,不是如何寻找一个属于某一社会阶级或范畴的身份并得到身边人的认可,而是保持对身份流动性的警觉,因为刚刚获得的身份将很快被充满着“喧嚣与骚动”的不断流动的社会撕裂或融化。因此,流动的现代社会中自身认同没有稳定性和参照点,由此而来的紧张、焦虑、冲突和痛苦将始终纠缠困扰后现代的人们。
二
自从1968 年波德里亚发表《消费社会》以来,“当代西方学者纷纷把消费社会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通过消费社会考察后现代主义或通过后现代主义考察消费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最具价值的理论视角”④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399 页。。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中说:“我们的社会在根本上是一个‘消费者社会’。”⑤[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77 页。当然,鲍曼所说的消费社会并不是指任何人都消费——那是自古就有的一种生活状态——而是指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消费为标志的社会,它更多需要的不是生产而是消费。鲍曼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时期,人们的自由依赖于其消费能力。消费主义对解释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控制模式有重要的意义,由物品消费到符号消费的转换是社会消费行为的一个根本性变化。鲍曼在《消费生活》一书中对比分析了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的“流动性”社会中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的不同。他指出:“在过去需要满足消费者的‘消费品’的总量都是固定的:有其最低和最高限制。限制是由所期望完成的任务所决定的。生存是消费的目的,而一旦目的得以实现,需求得以满足,消费更多便毫无意义。沉溺于肉体、贪食和不节制的生活一直遭到社会的反感与唾弃,人们把夸耀式消费看作是虚荣与自负。”⑥Zygmunt Bauman,Consuming Life.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 1(1): p.23,12然而,在消费社会,福利国家旧有的原则受到了挑战,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影响了身份构建,而且也影响了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消费社会和消费者文化明显的特征不是提升或快速增长的消费量;消费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之处是,消费从过去作为确定限度的生存工具解放出来,这就使得消费免于功能性的约束,免除了消费作为满足舒适性的需求。在消费社会,消费就是其自身的目的,是自行推进的。消费社会宣告满足的不可能性,并通过不断增长的需求衡量其进步。“满足的延迟”(delay of gratification)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再也不是高尚美德的标志,“立即满足”是一个诱人的合理选择。正如人们所常说的,假如你心情低落,那就吃,就去购物,去消费!后现代社会的信条就是:“我买,故我在(I shop therefore I am)。”①Nigel Watson,Postmodernism and Lifestyles (or: You Are What You Buy),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ostmodernism,edited by Stuart Sim,London:Routledge,2001,p.63.
对鲍曼而言,消费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基本模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以广告及意识形态创造出来的诱惑性消费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说:“今天,使个人联结成社会的力量,是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活动,是他们的由消费而构成的生活。”②[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223—224 页。在今天,商品以绝对的优势决定了人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商品的生产、流通、倾销与更替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改变着社会,商品的经久耐用不再具有吸引力,商品的新奇与光鲜驱使着更多的人愈来愈躲避持久性而追逐短暂性。虽然传统的人们会认为在他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之后,他就会感到幸福,失去了继续努力的动力,但后现代消费社会却告知人们根本就不存在满足,一切所谓的满足都会转瞬即逝,都会随着新的商品的推出产生新的欲望,从而产生新的焦虑和努力。正如丹尼斯·史密斯所分析的,鲍曼“看见一个正在成形的世界,在其中,一些人总是享受着消费市场的单向自由,并且,他们作为市民的行为能力已经凋谢、死亡。与此同时,穷人被拒绝在所有自由之外。政府的主要任务将是压制那些没能加入消费者狂欢节的穷人”③[英]丹尼斯·史密斯著,萧韶译:《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9 页。。在消费社会只有成功的消费者和失败的消费者,他们是以金钱满足欲望的可能性来衡量的。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已不是传统的那种以追求生活必需品为标志的消费,而是一种符号属性的消费。符号消费作为消费社会的特点,需要制造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神话来获取合法性。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传播方式的巨大革命都使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不是在购买产品,而是在购买幸福、尊严、权力、自由、快乐、健康、地位、品味、爱情等等精神层面的价值,它们更多地体现在商品所呈现的符号中,而这些多是由电视、广告与媒体所激发诱惑而产生的。人们由物的有用性消费过渡到了物的符号性消费,符号价值替代了使用价值,精神需求代替了生理需求,购物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志。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指出:“如果消费是人生成功、幸福甚至尊严的度量器,那么人类欲求的盖子就被打开了;无论多少占有和激动人心都无法‘与标注同步’所许诺的那样带来满足——因为不存在可以达到同步的标准。”④[英]齐格蒙特·鲍曼著,仇子明、李兰译:《工作、消费、新穷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148 页。鲍曼作出了恰当的总结:“人们不停地完成一件事,而又重新从头开始另一件事,这已经不是荒谬的象征,而是所有人可得到的共有的生活方式。”⑤Zygmunt Bauman,Consuming Life,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 1(1) :p.12,25.可见,在消费社会中,只有消费的快乐是真实的,欲望的流动性和变易性成为消费的基本动机,欲望把消费者、市场、商品与服务联系在一起,就像网上购物所呈现的那样,没有商店,没有服务,看不到商品,只有购物欲望的展示,这是纯粹的“精神经济”(psychic economy),购物者仅仅生活在短暂的、看似快乐的审美经验之中,视觉与想象性的触觉与嗅觉代替了一切。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喜欢的是“骚动与忙碌”,寻求的快乐不在于明显的回报和收获,而是在于对它们的欲望和追逐中:“人们所说的幸福不是捕获到兔子,而是在捕猎它的过程中。”⑥Zygmunt Bauman,Consuming Life,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 1(1) :p.12,25.
鲍曼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大众传媒对当代集体或者个体的想象力所产生的可怕的影响力:“屏幕上无所不在的、强有力的、‘比现实更加现实’的图像,除了为使活生生的现实更加如意而制定激励标准外,它还定下了现实的标准和现实评价的标准。人们渴求的生活往往就是‘和在电视上看到的生活’一样的生活。”⑦[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第130 页。在鲍曼看来,消费社会的人们生活在由媒体与广告制造的各种虚幻的景象之中,人们常常身不由己地聚集在各种各样由媒体制造的消费场所:商业大街、旅游胜地、运动场所、展览馆、咖啡馆、餐馆等,是共同的欲望与幻觉促使他们奔赴同样的目的地。购物天堂里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商品不过是各种各样感觉的代替品,立即满足与推迟满足都不过是各种消费策略的天罗地网,“我们都不一样”的初衷与“我们都一样”的结果混杂在一起。欲望是一切流动的根本原因,也是消费万象的根本原因,由此,无聊、倦怠和失眠也必然是贪求诱惑进而腻烦诱惑的必然结果。
三
生活在后现代时期的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却失去了安全感,处在一种充满焦虑和困惑的不确定状态。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差异失去了框架,一切都变得混淆不清,变化不定,人们无法找到清晰的生存目标,始终面临着一系列无法确定或实现的选择。这既是自由的代价,也是后现代的缺憾。鲍曼指出:“与其说后现代在总体上产生了大量的个体自由,不如说它以日益极化的方式对之进行了重新分配:它在大量增加被诱惑者自由的同时,也把被压迫者与全方位被监视者的自由缩减到了近乎不存在的程度。”①[英]齐格蒙·鲍曼著,郇建立等译:《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第36 页。传统的权力结构,正如福柯及边沁的全景式监狱,就是为了维护一种稳定的社会及精神结构,它的目的就是封闭监狱,隔离监狱与外部的联系,加强内外的区别,从而成为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基本象征。稳定性和确定性通常是现代“结构”的标志,后现代生活的情景却不是这样,压倒一切的情感是新型的不确定性感,个体生活筹划不再有稳定的基础,个体认同建构的努力并不能纠正“抽离化”的后果,并不能抓住不断流动的自我。在鲍曼看来,“流动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对有序生活的一种快乐拆解:永久的脱域和再嵌入。因此,流动的现代性生活总是会成为偶然性的产物。”②Tony Blackshaw,Zygmunt Bauman,London: Routledge,2005,p.93,93.鲍曼发现,后现代的流动性打开了传统社会的各种壁垒和障碍,人们能够自由地流动,就像草原上随意流动的民族。约翰·多恩(John Donne)那首诗歌中的“孤岛”已不复存在,在流动的当代社会谁也不能“躲开踏出来的道路”,或“远离尘嚣”。他断言:“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完整无缺;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没有人能够依靠在纯朴和贫穷时代可以安全避难的岛屿。在大陆上,所有的道路都被交错纵横的铁路和高速公路连接起来——没有藏身之处。”③Zygmunt Bauman,in an interview with Milena Yakimova,‘A Postmodern Grid on the Worldmap’,in Eurozine (2002)at http: //www.eurozine.com/article/2002 -11 -08 -bauman-en.htmtl.鲍曼善于使用隐喻,这使得他著作中抽象的理论分析读起来津津有味。“根茎”(rhizome)总是处在不断成形状态,而“根茎”一词具有“多样性和多向性的制度、组织、思想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喻意。鲍曼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流动的现代性生活具有根茎的特征:“它好像没有优先方向感,而是向侧面、向上部和下部扩展,没有相同的频率,也没有能够预测下一次运动的可发现的规律,新茎生于不可能提前预测的地方。”④Zygmunt 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London: Routledge,1992,p.27.
鲍曼分析指出,在流动的后现代性中,根据社会阶级、地域和社团确定身份的传统形式已不再盛行,因而流动的现代性可以通过根茎的隐喻得以显示,因为“它的构建就像是一幅展开的地图——而不像是社会阶级或者其他的根系或生命结构形式的合上的书本——它的特征包括对涉及到流动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身份和多种社会网络不断修正”。显然,流动的现代性中的身份没有深层结构,并且是“这样建构起来的,每一路径与另外一个相连接……(它)没有中心,没有边缘,没有出口,因为它可能是无限的、不确定的”⑤Tony Blackshaw,Zygmunt Bauman,London: Routledge,2005,p.93,93.。
但后现代所呈现,甚至是鼓励与追求的这种自由其最终的趋向到底如何?它最终能给人类文明带来什么呢?这是后现代必须面对的困惑。鲍曼在谈到当前的不确定性时说:“当前生活的许多特征都导致了无法抵抗的不确定性感:导致了把未来的世界和‘力所能及的世界’视为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无法控制的和令人危险的。借用马库塞·多尔和戴维·克拉克发明的恰当的术语来说,我们今天生活在充满恐惧的氛围中。”①[英]齐格蒙·鲍曼著,郇建立等译:《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第22 页。显然,追求幸福与消费的后现代并没有消除传统的社会文化祸根,新世界的无序、各种各样的瘟疫战火、国家间与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对立、资本的无所不能、社会安全网络的巨大缺陷、经济理性之外的理性原则的荡然无存等等,无不彰显了后现代的困惑与无奈。人们在奋力摆脱传统的束缚,但最终发现,他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魔咒,只是与自己的起点近在咫尺,而与自己的目标却谬以千里。他们在消解传统暴力原则的同时,又以一种新的暴力原则给暴力再分配,那就是差异原则的无处不在,在总体原则与个体行为之间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制衡,在手段和目的裂谷之间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桥梁,富裕的欧洲大量的穷人和失业者就是证明,更不要说那些非发达国家穷人的苦难了。
显然,“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虽然熟悉与陌生、自我与他者的差距在逐渐消失,但自我形象的认同与自我身份的确认仍然是后现代的一个基本问题。鲍曼指出:“在我们这个猖獗的‘个体化’世界里,身份是忧喜参半的事。它们摇摆在梦想和噩梦之间,难以预料它们会在何时向对方转换。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即使处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这两种身份的现代形态共存。在生活的流动的现代场景,身份或许是一种矛盾心态的最为普遍,最为敏锐和最为深刻的体现。”②Zygmunt Bauman,Identity:Conversations with Benedetto Vecchi,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4,p.32,in Tony Blackshaw,Zygmunt Bauman London:Routledge,2005,p.97.因此,新秩序建构的平常与怪异、叛逆与顺服、自我与非我、自我与他者的各种身份建构中权力的运作并没有根本消失,规则的缺失或含混使人的行为在面对混乱的世界时更加无能为力,剩下的只有不确定性带来的怀疑和恐惧。在流动的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依靠的,过去、现在、未来都一样,都是由不相连贯的碎片组成,终极的秩序和解放的目标都已不存在。那些脚步匆匆的行人无法找到可以依靠的目标,而惟一可以作为标准的内心也是只有流动的感觉而已,再也没有人告诉你如何行动,再也没有参考的行为让你作为自己的依据。因此,鲍曼认为:“陌生人不是现代的发明——但是造成那些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永远处在陌生人的状态却是现代的发明。”③Zygmunt Bauman,City of Fears,City of Hopes,London: Goldsmiths College,2003,P.6,5.所谓集体主义、自我认定、共同体、自我的满足、理性等都在流动中烟消云散,在城市中“陌生人相遇,彼此相邻,而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彼此之间仍然是素不相识”④Zygmunt Bauman,City of Fears,City of Hopes,London: Goldsmiths College,2003P.65。在充满陌生人的世界里,人只有像《等待戈多》中的米斯特拉尔和埃斯特拉冈一样,除了自言自语和互相说着谁也不懂的话以外什么都不能做。既然不能和陌生人讲话,那和谁讲话呢?——你的周围都是陌生人。
这样,留给后现代人的惟一真实的感觉就是现在,正如鲍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多变的世界中,在一个严重的、没有希望的、不稳定的危险的状况下,这一不稳定渗透进了个体生活的所有方面。”⑤[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第212 页。的确,传统的集体主义在以个体为主导的后现代里荡然无存,那碌碌无为所带来的虚无与快感也只有个体才能体会到。集体的联合、团结、商定都被个体的恐惧、焦虑、孤独所承担,传统社会的忠诚和顺服被流动社会的自我和自由所代替,但传统社会所特有的安全与幸福也被个体社会的自主与对立所代替。在鲍曼看来,安全与自由的矛盾性在后现代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丹尼斯·史密斯指出,鲍曼在1990 年代所写的著作中探究了这些问题,对鲍曼而言,“自由变成了一种负担。面对选择,人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是实际上的‘应该’——我应该做什么才能保证我能得到最大的利润,同时无需承受太多的耗费?第二是伦理上的‘应该’——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和好的行为方式?正如鲍曼反复指出的,根本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安全不会在同一邮包中投寄出来。高水平的自由通常意味着低水平的安全,高水平的安全意味着低水平的自由”⑥[英]丹尼斯·史密斯著,萧韶译:《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第26—27 页。。
人类自古就生存在二难的选择里,善恶总是相伴而行,从来也没有得到完美的解决。鲍曼认为,在后现代这样一个无根的陌生人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们企图生存下来,并通过消耗他们偶然获得的个人资源去创造意义。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们不具有由较高的权力强加的绝对的道德准则的鼓励性的指导”①[英]丹尼斯·史密斯著,萧韶译:《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第21 页。。人类在不断追求自我与自由的同时又何尝摆脱过那些烦恼不已的孤独与苦恼呢?道德自由主义与感官享乐主义在无限追求的强烈体验与感官满足时,随之而来的不就是空虚与厌倦吗?但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确实告诉了我们,失败者并不是一败涂地,无可挽回,获胜者也不是一劳永逸,永远坐享其成,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劳埃德·斯宾塞认为:“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包括这一理念,即我们绝不试图消除模糊性,而是必须学会面对它,并忍受它。鲍曼一本又一本的著作传达出的一个信息就是,道德冲动(moral impulse)能够而且必须存在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景观中。”②Lloyd Spencer,Postmodernism,Modernity,and the Tradition of Dissent,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ostmodernism,edited by Stuart Sim,London:Routledge,2001,p.164.后现代告诉人们:他们是自由的,即使是掉入陷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