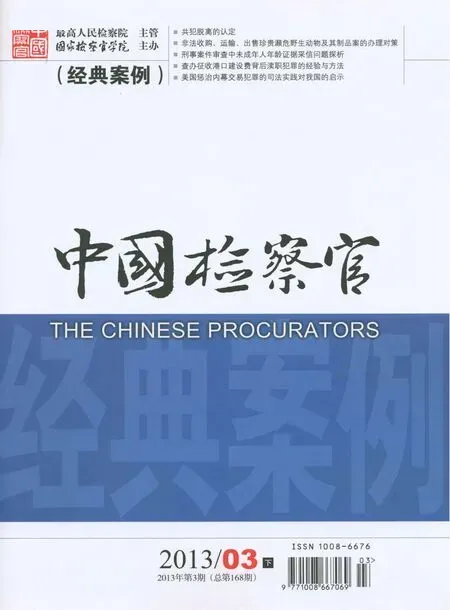抢劫案中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的把握——以左某抢劫案为例
文◎王宪峰 吴 晓
抢劫案中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的把握
——以左某抢劫案为例
文◎王宪峰*吴 晓**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321300]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321300]
[基本案情]2012年某日凌晨1时许,犯罪嫌疑人左某驾驶马自达轿车至某市东城街道巴黎王府第宾馆的小巷中,见被害人涂某独自一人行至该处时,犯罪嫌疑人左某对被害人涂某实施言语威胁、殴打等暴力行为,被害人涂某在与犯罪嫌疑人左某拉扯中逃跑后左某拾起疑似手机物品离开。
一、本案的相关证据
根据案卷,证明左某犯罪的主要证据有:(1)犯罪嫌疑人左某供认实施暴力行为,但辩解称其目的是为教训被害人涂某且实施暴力行为后并没有拿走被害人手机和现金;(2)被害人涂某被抢手机和现金的陈述部分反复,但被抢手机的陈述前后一致明确;(3)监控录像和路人郎某证实犯罪嫌疑人左某对被害人涂某实施暴力行为并在被害人逃跑后捡起疑似手机物品的作案经过;(4)被害人涂某(案发两天后)补卡记录及报案记录、轿车租赁合同、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据。
二、办案分歧
本案审查起诉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左某抢劫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存在如下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左某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明确,虽然实施威胁、殴打受害人涂某的暴力行为后捡起疑似手机物品离开案发现场,但没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左某捡起的物品是被害人的手机,且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是出于报复而实施暴力的犯罪故意,因此,本案犯罪事实不清,缺乏定罪证据,是无罪案件,宜作绝对不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左某对被害人施加暴力并在被害人逃脱之后捡起疑似手机物品离开案发现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现有证据无法排除犯罪嫌疑人是出于报复的主观故意,也无法排除捡起香烟离开案发现场的合理怀疑,因此,本案定抢劫罪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宜作存疑不起诉。
第三种意见认为,虽然犯罪嫌疑人左某始终否认是为占有他人财物而实施暴力行为的主观犯意,但有监控录像、被害人陈述及案发两天后补换手机卡的证据、证人郎某的证言,充分证实了左某实施暴力并劫得财物的犯罪经过。因此,本案证据已经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应当依法认定左某构成抢劫罪。
三、对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
办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现有证据是否达到了案件起诉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即认定犯罪嫌疑人左某抢劫的事实是否能够 “排除合理怀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第2款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件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由此可见,我国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以法律的形式融合了普通法系国家带有较强主观性色彩的“排除合理怀疑”要素。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合理怀疑”?如何把握“排除合理怀疑”的度?诠释以上两个疑问是正确应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第3项本质要求,也是评析本案的关键。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换句话说,对案件的事实的怀疑应当是合理的即符合常理的怀疑,应当是有根据的而非妄想的怀疑。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常理性。常理性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朴实的法律观和逻辑判断犯罪事实后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根据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合理怀疑要求有怀疑的事实和依据,而不能吹毛求疵地推测。
对“排除合理怀疑”度的把握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目前,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刑事审判中尚无统一规定,即使在其发源地英美法系国家中对该程度的要求也没有明确、清晰的界定。但对其有两点共识:第一,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客观真实”不同于“法律真实”,案件事实作为历史性事实,具有“回溯性”,这就使得对案件的把控不可能完全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还原”的客观真实都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证据对过去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这种证明属于一种典型的“回溯性认识”,而基于回溯性认识的自身特点,无论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及关联性多么充分,所认定的事实都不可能必然正确,而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执法人员应做到就是使“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无限趋近。第二,排除合理怀疑并非排除一切怀疑而是要求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排除合理怀疑”发源并盛行于遵循判例法的国家,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体现出证明标准的经验主义。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并非排除一切怀疑,而是排除否认指控犯罪事实存在的怀疑,反之,对于不影响定罪的事实则允许存在怀疑。
四、本案结论
结合本案,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已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犯罪嫌疑人左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首先,阻碍本案定罪的最大合理怀疑是犯罪嫌疑人左某实施暴力行为的目的是出于“教训”而非占有他人财物。但左某为何要无缘无故“教训”被害人涂某?左某称被害人涂某赶走了其在A-KTV带领的三个唱歌服务员。根据左某的辩解,这三个唱歌服务员却都没有具体身份信息、家庭住址信息以及联系方式。按照常理,既然这三个唱歌服务员是犯罪嫌疑人带领,为何会没有身份信息、详细住址,甚至在通讯如此普及的今天都没有其联系方式?这就对左某辩解的真实性产生巨大怀疑。另外,被害人涂某的笔录和路人郎某的证言也能削弱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路人郎某证实案发当时,被害人涂某被犯罪嫌疑人左某拉扯时曾大声呼喊 “抢劫”、“救命”,后被害人逃跑。被害人涂某的笔录明确提到案发之前其上班地点并非犯罪嫌疑人所讲的AKTV,而是第一天去案发地点附近的B-KTV上班。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监控录像,录像清晰显示犯罪嫌疑人左某停下车是凌晨1点05分28秒,下车立马上前接触到被害人涂某(背了只包,一只手拿手机,另一只手有无拿钱包无法看清)至被害人逃跑,后左某捡起疑似手机物品坐上轿车离开是凌晨1点06分15秒,整个过程持续时间仅仅只有47秒,但其暴力行为之明显,动作之迅速也足以印证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劫取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综上,可以充分排除犯罪嫌疑人是出于“教训”而实施暴力行为的合理华裔,基本可以确信其作案具有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其次,被害人笔录反复,两次笔录存在矛盾使得对该证据的有效性产生合理怀疑 (被害人前后两次笔录时间间隔近三个月,现无法联系被害人)。第一次笔录被害人的陈述是犯罪嫌疑人左某抢走其钱包和一只白色苹果手机,钱包里有2000元左右的现金和卡若干,后逃跑;第二次笔录被害人的陈述是犯罪嫌疑人先拿其背包里的1000元左右现金,后再抢其手上的白色苹果手机,后逃跑。虽然抢钱包的行为发生在车内,监控录像无法证实被害人关于被抢钱包及现金的事实,被害人前后两次关于被抢现金的陈述也有所矛盾,但被抢手机的陈述较为稳定,对手机如外观、内存等信息的描述前后基本一致,这就与被害人在案发两天后进行手机补换卡的事实形成有效证据链,手机已脱离被害人实际占有,可以形成内心确信其真实性。据此,关于被害人前后两次被抢现金不一致部分并不完全不影响定罪,其证明标准并非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较高程度,允许对该事实的真实性存在怀疑。被害人其余陈述足以采信。
最后,对犯罪嫌疑人左某捡起的疑似香烟物品的合理怀疑。犯罪嫌疑人左某辩解称捡起的是自己掉在地上的香烟而非被害人的手机。案发后,被害人迅速报抢劫案的笔录,被害人案发两天后补换卡的记录,审查起诉阶段审讯时犯罪嫌疑人左某对疑似香烟物品相关问题的回避态度足以否定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因而可以排除拾拣物品为香烟的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