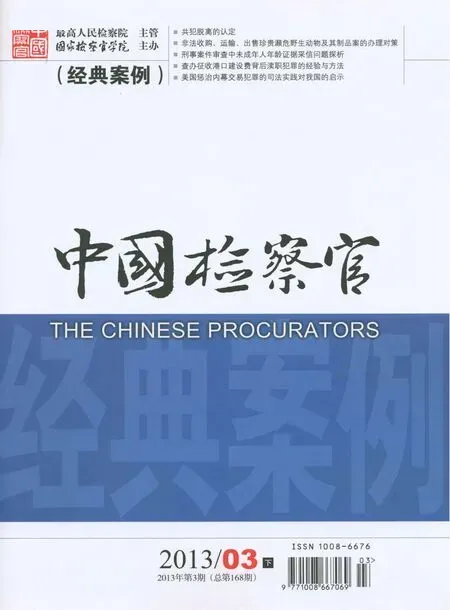美国惩治内幕交易犯罪的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文◎俞 燕
美国惩治内幕交易犯罪的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文◎俞 燕*
20 12年是美国联邦政府打击华尔街内幕交易的第四个年头。继2011年广为关注的对冲基金帆船集团(Galleon Group)经理、亿万富翁拉贾·那纳姆(Raj Rajaratnam)因内幕交易被判入狱11年后,美国政府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仍在不断加强。
一、SAC资本内幕交易犯罪
2012年 11月,美国检方逮捕 SAC资本(SAC Capital)的一位前基金经理马修·马拓玛(Mathew Martoma)。SAC资本是华尔街最具实力的对冲基金之一。而马拓玛是该对冲基金旗下第五个因涉嫌内幕交易犯罪被捕的基金经理。检方指控其利用从负责监督某种老年痴呆症药物试验的西德尼·吉尔曼(Sidney Gilman)医生处得到的内幕信息,买卖艾兰和惠氏两家医药公司的股票并获利2.76亿美元。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涉案金额最高的一起内幕交易案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分别对马拓玛、吉尔曼医生以及马拓玛所在的SAC旗下基金CR Intrinsic提起了民事诉讼。
据媒体报导,马拓玛是通过一家名为GLG的人脉网络公司与吉尔曼医生取得联系的,而GLG的主要业务是帮助基金经理寻找行业专家。检方指控,2007年底至2008年上半年,随着某种老年痴呆症药物的保密试验快得出结果,马拓玛向SAC的所有者史蒂文·科恩(Steven A.Cohen)建议,药物试验将得出积极结果,SAC应进一步买入艾兰和惠氏的股票。截至2008年6月,SAC将对艾兰和惠氏的持仓规模分别扩大至3.28亿美元和3.63亿美元。2008年7月17日,吉尔曼告知马拓玛,药物试验的结果不如人意。三天后,马拓玛和科恩交谈了20分钟,并建议卖出艾兰和惠氏的股票。次日,马拓玛和科恩指示科恩手下的高级交易员出清SAC持有的艾兰和惠氏股票,并要求采用“不会使SAC内外的任何人产生警觉”的交易方式。SAC还建立了能从这两只股票的下跌中获利的看跌头寸。后来,药物试验的负面结果公布,艾兰和惠氏的股价受其影响分别下跌了42%和12%。SAC从中获利2.76亿美元,并避免了相关交易损失,马拓玛也因此得到了930万美元奖金。[1]
二、美国内幕交易罪的界定
内幕交易是指证券交易的知情人员或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的人员,在涉及证券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或泄露该信息的行为。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立法禁止内幕交易,将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处罚力度也在加强。
美国在1929年10月发生股票恐慌之后,分别制定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这是美国对内幕交易的最早规制。内幕交易行为适用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的“反欺诈条款”等规定,但这些条款中并没有使用“内幕交易”一词。[2]
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利用州际商业方式或工具,或利用邮政或国家证券交易所的设施进行下列行为,皆为违法:……违反了委员会制定的对公众利益或投资者保护为必要或适当的规制和条例,对在国家证券交易所已注册或未注册之任何证券,使用任何操纵手段、欺诈手段或阴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该款制定了10b-5规则。根据证券交易法第10节(b)款以及1984年、1988年的证券法修正案,内幕交易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为:(1)行为主体必须使用了州际贸易、邮政或国内证券交易所的某些设备,这属于管辖权方面的要件;(2)行为主体必须掌握内幕信息;(3)行为主体进行了与证券买卖有关的欺诈活动或实施了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主要包括买卖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泄露内幕信息给从事证券买卖的第三人,或为买卖该证券提供内幕信息给第三人);(4)行为主体所掌握或知道的内幕信息是重要的;(5)行为主体所知道或获悉的重要内幕信息尚未公开;(6)行为主体主观上具有故意。[3]
美国成文法中没有对“内幕信息”作明确定义。根据判例法,“内幕信息”包括“重要性”和“秘密性”两个核心要素。“重要性”指消息公布后会对股价产生影响。“秘密性”是相对于有效公开的信息而言,指该信息尚未被普通投资者所知悉。在上述SAC资本案中,如果检方指控的事实成立,马拓玛从吉尔曼医生处获得药物负面试验结果时,该试验结果尚未公布,且其一旦公布,必将造成股价下跌。显然,这一药物试验结果具备“重要性”和“秘密性”,属于内幕信息。马拓玛掌握这种内幕信息,并买卖了与之相关的艾兰和惠氏两家医药公司的股票,符合内幕交易罪的构成要件。
三、我国的“老鼠仓”犯罪
2008年4月,证监会对上投摩根基金的原基金经理助理唐建没收违法所得152.72万元,并处50万元罚款,同时认定为永久市场禁入。这是基金法实施以来,证监会对基金“老鼠仓”开出的第一单处罚[4]。根据证监会调查结果,2006年3月,唐建利用担任上投摩根研究员兼阿尔法基金经理助理之便,在建议基金买入新疆众和股票时,使用自己控制的“唐金龙”证券账户先于基金买入,后又借基金连续买入新疆众和,趁该股股价不断上升之机卖出,非法获利约153万元。唐建辩称,自己对“唐金龙”账户没有控制权。但调查发现,唐建办理了“唐金龙”资金账户的开立手续。其证券账户网络交易IP地址、上投摩根出差记录等也证明,唐建曾通过网络交易方式在香港、新疆、云南等地以“唐金龙”账户交易过新疆众和。
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第一百八十条中增加一款,将“老鼠仓”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2009年10月,《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该罪名确定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2012年11月,上海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刚由公募转私募的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1800万元人民币。同时,对其违法所得人民币1071.57万元予以追缴。李旭利是继基金经理韩刚、许春茂后,我国因“老鼠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三人,也是迄今为止涉案金额最大、量刑最重的一起。李旭利于2009年2月28日至5月25日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指令他人在其控制的证券账户内,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基金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两只,两个月内,该两只股票的累计买入金额约5226.4万元,获利总额约为1071.6万元。[5]
与美国法律不同,我国刑法对内幕信息的范围界定较窄,所以当需要规制“老鼠仓”这种新情况时,刑法便采用了另行制定新罪名的方法进行修正,但实际上都属于广义的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在犯罪构成方面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对象不同,前者为“内幕信息”,后者为“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即 “老鼠仓”信息)。关于“内幕信息”,我国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界定。[6]但何谓“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立法中并没有明确界定。
笔者认为,直接进行正面界定存在难度,且易导致内容和逻辑方面的不严密,故宜采用个案认定的方法,给执法留下一定的操作空间。可以从与“内幕信息”同异的角度,采用以下几个标准进行综合判断:(1)两者都具有“秘密性”。例如唐建一案中的基金投资信息属于基金公司掌握的核心商业秘密,对此,基金公司从保护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角度出发,会对该类信息的使用、传播使用监控手段加以限制。(2)两者都具有“重要性”。唐建一案中新疆众和股票在短短数周内其股价大幅度飙升了40%,充分说明了基金投资信息对二级市场股价走势会产生重要影响。(3)在信息源头、信息性质和影响范围上,两者存在重大差异。股票投资价值本质上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运营质量、发展前景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故我国相关法律主要是从对上市公司运营状况可能产生实质影响的信息入手,规定内幕信息的范围。“老鼠仓”信息会影响股票价格,但它并不是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本质因素。(4)内幕交易一定跟内幕信息公开有关,换言之内幕信息具有当然的公开性这一重大特征,即其将会公开。但是“老鼠仓”信息,例如基金经理投资决策会意见、基金持仓变动等信息都具有非公开的特点,而上述信息也只有在符合规定时才可以对外公开。
四、美国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在今年6月正式实施,必将推动证券投资基金业,特别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随着对基金从业人员个人证券投资的解禁,基金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参与内幕交易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立法虽有威慑作用,但由于这类案件大多发生在网络交易平台,取证难度较大;如果是工作时间之外传递信息,取证更无可能,客观上将影响到法律的实施效果。内幕交易的调查取证难,也是至今股市里内幕交易普遍,但被查处的案件不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为加强对我国内幕交易等金融犯罪的惩处,首先,可以借鉴辩诉交易制度。内幕交易行为的复杂性导致其发现难、查处难,并给公诉机关的调查取证和法庭举证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处理一起内幕交易案件必定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诉讼的无效率必然带来诉讼的不经济。要解决查证难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司法机关与行政监管部门间的联系协作,提高侦查破案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在审查起诉环节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接近90%的案件都是通过辩诉交易或者辩诉协议解决的。辩诉交易的好处就在于它对公诉人和被指控者均有利,就公诉人而言,辩诉交易产生了无需增加有限公诉资源的定罪;就被告而言,风险被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确定性所代替。[7]我国不一定全盘照抄美国的诉辩交易机制,但是可以借鉴其中的合理因素。在审查起诉时,公诉机关一方面可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查清其非法获利数额时可以以内幕交易行为被害人的身份与之进行协商、和解,达成赔偿数额。这样刑事案件及其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可以极大提高诉讼效率,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得到及时救济。
其次,要明确秘密监听所获证据规则。内幕交易是一种难以打击的犯罪。在对冲基金里,专业人士不断交易着大量证券,并且通常都有大量研究和分析文件来支持每一项决策,因此调查尤其困难。美国联邦检察官用于指控马拓玛的证据是基于交易记录。但之前包括帆船集团创始人拉贾·拉贾那纳姆在内的一系列对冲基金内幕交易案中,FBI和SEC能够窃听移动电话和电话会议,因此可以追踪用于非正式传递内幕信息的准确术语。[8]法庭对这些备受争议的窃听证据予以采信。
从形式而言,秘密监听证据资料是以录音资料的形式体现的,属于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的视听资料范畴。我国 1993年《国家安全法》、1995年《人民警察法》均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但是,采用技侦手段具体应遵守哪些法定程序、对技侦所获证据资料的使用必须符合哪些条件、如何认定该类证据资料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积累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规定,从而平衡好执行法律和保护私权之间的关系。
最后,要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内幕交易犯罪存在被害人数量众多、主体难以确定等特点。一方面,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在被害人认定方面,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应包括单位。可建立被害人限期申报制度,即在刑事案件立案后有被害人向法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时就向全国发出申报通告,将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在通告中明确,并规定一定的申报期间,以便做好资格认定,进入民事审判程序。另一方面,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除非为了防止刑事案件的过分迟延,否则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但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几乎不可能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一审判决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不影响刑事判决的生效、执行。但二审法院应当对全案进行全面审查,审查后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出终审裁决。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该类犯罪中的附带民事诉讼是对立法本意的的扩大解释和运用,或许用准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更为确切。[9]
注释:
[1]参见《SAC前交易员涉内幕交易被捕》,载于FT 中文网, 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 001047623,2013年2月17日访问。
[2]顾肖荣、张国炎著:《证券期货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57页。
[3]同注[2],第276页。
[4]参见《上投摩根唐建“老鼠仓”事件》,载于新浪财经网,网址: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tangjianinsiderdealing/,2013年2月23日访问。
[5]参见:《李旭利内幕交易罪名成立 获刑4年罚款1800万》,载于网易财经网,网址:http://money.163. com/12/1123/14/8H0IV50O00251LIE.html,2013 年 2月23日访问。目前该案已进入二审。
[6]主要为我国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六十七第二款以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五条第(十一)项中的相关规定。
[7]郑顺炎:《证券市场不当行为的法律实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8]参见《必须对内幕交易动真格》,载于FT中文网,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489/? print=y,2013年2月23日访问。
[9]同注[2],第409页。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20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