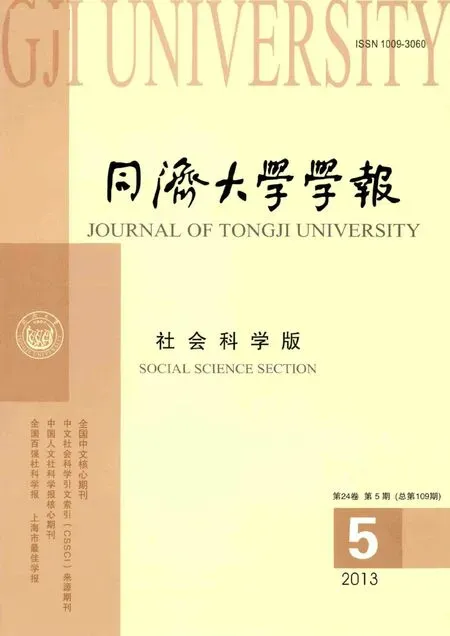民族性·世界性·人类性:莫言小说的核心质素与诗学启示
白 杨, 刘红英
(吉林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格局中呈现民族特性及其世界意义,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莫言作为当下汉语文学写作的佼佼者,同时也是东方文化以及民族性传播的集中代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前后期创作的转型能够呈现出何种向度的主体自觉?这种主体性的自觉对于莫言乃至于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又有着怎样的启示意义?这些问题在当下的文化时空中都有深入思考的必要。
一、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集:人类性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场域中,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力非同寻常,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百年孤独》不仅震撼了拉丁美洲,也深深引发了中国作家的群体性焦虑。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中国现代文化的弱势境况被再次反衬出来,这种心灵阵痛对中国作家而言既是暂时的,也是深远的。一时间,民族性写作异军突起,莫言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创作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及纠葛成为一代中国作家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也成为他们文学写作的内在动力和无法克服的软肋。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这种心智能量尖锐冲突的一次集体性爆发。张扬民族性的群体无意识被彰显出来,既然“凡是世界的,必然是民族的”,那么反之亦然:“凡是民族的,也必然是世界的。”在寻根文学运动的热潮中产生了一大批耐人寻味的优秀作品,阿城、郑义、韩少功、王安忆、莫言等人的探索性写作,将当代文学从之前的过于关注现实和当下社会问题的格局中,带入了更为深远的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回望及反思中。尽管在文学意识、美学风格和价值诉求等方面,寻根文学表现出内部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对民族性的重审是为了探索走向世界之路。近代以来,被迫“开眼看世界”的中华民族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历经政治历史的沧桑巨变,寻根文学作家们尝试解决这个历史留下的难题。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旦“富有民族特色的表达被符号化”*参见王德威在复旦大学召开的“莫言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傅小平:《众声评说“浪得虚名三十年”——“莫言创作研讨会”侧记》,载《文学报》,2010年7月15日。之后,难免会成为当代文学的包袱和负担,甚至会将文学引向偏执、狭隘的歧途,那么,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是平行关系,还是具有相交的可能?如果存在交集,这二者之间的重叠处究竟何在?
事实上,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无国界的。“国界”意味着地理上的祖国以及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无国界”则意味着作家对人类性困境和精神难题的思考,是超越家国意识和种族范畴的价值认同。“在人类文化观之下,没有异己文化,都属于自己的文化,文化的时间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空间性(民族与地域),都具有新的意义。”*张福贵:《“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0页。因此,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重合交集之处应该是人类性。“人类性”指的是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它兼具人道、人文、人性等多重内涵。伟大的作家应该用凌云健笔去描绘关于自己的时代、关于人类心灵复杂历程的真实状况,在他们的笔下,我们不仅看到了有关生命存在的本质,而且能够共同体验人性的需要、痛苦和希望,去面对人类性的难题。一部作品,不管他如何伟大,如果他的思想性以及对人物性格的揭示不具有人类性的思想感情,那么肯定不会有吸引力。历史早已证明,民族性的文化元素不一定具有世界性的内涵,而世界性的文化心灵则必然深深植根于民族性的土壤之中。鲁迅曾在这方面有过经典的譬喻,不能说“国粹”就好,关键要看其内容的构成是精华还是糟粕。同样,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找到开启自己人物心灵的钥匙,在波谲云诡的世事变迁中去书写生存的多重样态,唯有人性及人类命运才是其文学真正的创作主题。
莫言作为当代文坛的重量级作家,将民族性和世界性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他赞赏艾略特的这段话:“任何一位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应具备这两种特性——突发地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和作品的自在的普遍意义……”*[英]艾略特:《批评批评家》,见《美国文学和美国语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57页。,他也认同福克纳的写作艺术,试图“在当前的时代中寻找某种联系过去的东西,一种连绵不断的人类价值的纽带”*转引自莫言:《会唱歌的墙》,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诺贝尔文学奖的收获是对其文学成就的巨大肯定,某种程度上而言,莫言已经成为当下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如前所述,既然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交集是人类性,那么在莫言的作品中是如何得以体现的?其前后期的小说创作存在着诗学上的转型,这种“撤退”显然具有深层的涵义,深入思考其艺术创新力与民族性的关系,对当代中国文学确立自身的文学品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莫言小说的核心质素及诗学转型
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出版后,得到文艺界的好评。主人公黑孩那难以言表的压抑和怅惘,反映了弱小者心灵的深切苦痛,隐喻了潜意识中不可遏止的人性欲望。《红高粱》进一步彰显出莫言创作的个性与雄心,他尝试以恣肆磅礴的艺术想象力去重新形塑中国民间的文化精神,“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见《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0-21页。主人公戴凤莲临死前的那段告白,堪称是那个无个性时代中最有灵魂冲击力的声音:“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56页。这种对人性自由和生命活力的大胆追求,使莫言的小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批判,达到了“人性”书写的高度。同时,他也为“五四”以来新文学叙事中的“乡土世界”增加了新的美学内涵——乡土世界中虽然不乏灾难与痛苦、奴役与不幸,但那里也同时涌动着野性气质和狂欢精神!张新颖认为:“齐东野语的传统在这些年是被压抑的,但在民间没有中断过,而莫言是重新唤起了这样一种民间叙事。”*傅小平:《众声评说“浪得虚名三十年”——“莫言创作研讨会”侧记》,载《文学报》,2010年7月15日。故乡大地上那些质朴、自在的生命如何在强大的历史风云中流徙、遗存,成为莫言最关注并依赖的创作之源,对这种文学探索,他有自己的坚持与自信,在一次同王尧的对谈中,莫言这样定位自己的创作状态:“我能不断地写作,没有枯竭之感,农村生活二十年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当兵入伍,到了北京,上了军艺、鲁迅文学院,接触了西方的小说和理论,它起到了发现自我的作用。前面你说过要我给自己定位,我大言不惭地说: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如果列举前十五名,我应该榜上有名。”*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第19-20、20页。事实也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莫言的确是个性非常突出的作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民间经验的创造性书写为莫言赢得了世界声誉,他也一度被称为是“中国的马尔克斯”,但在巨人的阴影下亦步亦趋显然并不是莫言希望达到的文学境界,他并不讳言自己对这种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赞誉之词的抗拒心态,甚至直言“为了摆脱马尔克斯的影响”,“我和马尔克斯搏斗二十年”*穆肃:《莫言:我和马尔克斯搏斗二十年》,载《东莞日报》,2011年6月27日。。在普遍的意义上看,80年代的中国作家大多都曾受到西方文学的滋养,但莫言对“影响之弊”有清醒的思考,他呼吁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两座炽热的高峰”,因为“这两位风格化的作家,就像鸦片一样,一旦吸到之后,很容易上瘾。他们会产生极大的磁性,吸引你去模仿”,“我们就像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就很容易被迫融化。”*穆肃:《莫言:我和马尔克斯搏斗二十年》,载《东莞日报》,2011年6月27日。而真正内心强大的作家都渴望建造具有独一性和自我性的文学王国,从《天堂蒜薹之歌》开始,莫言已经有意识地进行文字表达上的“突围”,他忍痛割舍了一些曾经令他着迷的细节,尝试运用现实主义的写法去表现“故乡”。到写作《檀香刑》时,他还曾毅然割舍了已经写好的五万字内容,因为“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有魔幻气,也就舍弃不用……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莫言:《〈檀香刑〉后记》,见《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517页。。这是一次主动的文学调整,他的作品逐渐摆脱了马尔克斯的艺术笔法,在对本土经验的重审中日渐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四十一炮》等力作,一次次冲击着读者的阅读经验,他由此“和时代的流行色告别了,也和旧我告别了”*孙郁:《莫言:一个时代的文学突围》,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第28页。。
摆脱了影响的焦虑,莫言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与作家的自我生长有关,他在创作谈中多次提到“超越故乡”这个概念。“一个作家能不能走得更远,能不能源源不断地写出富有新意的作品来,就看他这种‘超越故乡’的能力。‘超越故乡’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同化生活的能力。”*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第19-20、20页。一个只能模仿生活的作者注定无法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优秀的作家懂得如何从朴素的民间文化经验中提取写作素材,以惊世骇俗的艺术想象能力将那些匍匐在乡野大地上的生存命题,提升为具有跨文化沟通意义的“人类经验”。张清华评价莫言小说的意义,敏锐地指出:“民间世界也只有在人类学思想的烛照下,才能成为和大地、酒神、历史和生命本体论的美学相联通的东西,而不只是习俗和风情,才能具有形而上学的诗意,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园诗。”*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第62页。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塑造了一个20世纪中华大地和人民苦难的象征性形象——上官鲁氏,她全家的悲苦遭遇成为我们透视过去历史的形象佐证。她的痛苦处境和凄惨身世,寓言了作家对生活在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上的人民的深深悲悯之情。她是苦难的化身,同时也是正义、勇气、韧性、力量、和平和博大人性的象征。上官鲁氏说:“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她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者,也是人类性精神的承担者。莫言说:“丰乳与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她产生于大地,又象征着大地。”*莫言:《〈丰乳肥臀〉解》,载《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他是将故乡的记忆放在世界版图里进行重构,乡村世界中生死歌哭的故事所承载的寓言,因此具有了世界意义。
莫言从来没有把艺术人物漫画化,他既表现人性的美好与质朴的情愫,也关注被生活、暴力和不公正的环境所扭曲的普通人。他犀利地揭露专制政体给人性造成的戕害,仇视贪婪与伪善,也不回避生活中荒谬的现实。《酒国》通过丁钩儿波澜起伏的“破案”经历,揭示了一幅“酒国”的群像图。不管作者如何书写荒诞与疯狂,但是对人性弱点的揭示,充满了对污浊不堪世态的批判性反思,其“食婴”主题传达出作家忧愤深广的现实主义精神。真正伟大的作家必然具有“道德洁癖”,见不得人性肮脏,不能接受没有温情的人间。许多批评家质疑莫言“丑化”人类的笔法,殊不知这种视角正体现了他心目中难以挥去的人性意识和现实关怀。《檀香刑》在残酷中发现人性的美好,在刑罚中透视历史的荒谬性。《蛙》展示了人性被异化的丑陋与自我救赎的真实,把人情伦理与国家意志的冲突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些作品中,他以形态各异的文学叙事引领读者进入历史时空,去反思物欲世界中人性的扭曲。
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莫言这样解释自己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也许,这部小说更合适在广场上由一个嗓子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莫言:《〈檀香刑〉后记》,见《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517-518页。勿论这种“撤退”是否到位,但是这种转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道路的重新调整和修正,是在传统的艺术形式中寻找全新的突破,是文化自信心的重新建构。“撤退”显然是以退为进,采用更符合自己民族文化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世界性和人类性的主题。莫言艺术创新的可贵性与这种“撤退”及转型有直接关系,而且对于当代文学写作来说具有启示的价值。
三、 当下语境中民族性转向的价值启示
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莫言的创作转型和艺术探索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从客观角度来看,这种向“本土性”、“民族性”大踏步的“撤退”,反映了作家主体性的深度觉醒和文化重构的自觉意识。应该看到,莫言后期创作的价值诉求不仅仅是作家的个案选择,而且具有文化整体意义上的启示价值。他的“撤退”昭示了建构在理性思考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心的彰显,同时也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某种借鉴的意义。为了更好地阐释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本文的逻辑起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浑融以及文化如何实现创新的可能这个问题上来。
在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今天,民族性的文化元素如何得以保存乃至不被时代冲击,成为全球性难题。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造成了文化的同质性和单一性格局。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昭示着文化一体化的尴尬与困境。尽管多元文化并存理应是人类文明的常态格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族性在与世界一体化的对峙中越来越失去了竞争力。那么,如何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保持自己鲜活的民族特色,已经成为思想界、文学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莫言的成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价值参考和示范意味。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莫言前后期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核心质素便是人类性意识。他书写历史,重要的不是人物事件,而是书写涌动其中的人性与人心。他是民间心灵史和情感史的记录者。民间大地上的人性活力和舒展精神,成为莫言创作的不竭源泉,他对美的洞察,他的巨大才华和纯艺术禀赋,于此获得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融合。他知道什么是无知和偏执,什么是粗俗陋风、迷信和黑暗,他的民族性诉求建立在深沉的爱与痛切的悲的美学建构中。莫言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驰骋于艺术天地中,但是他的作品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即便在幻想时也停留于故乡的大地上。张清华认为:“正是人类学的‘生命诗学’发酵了他的那些乡村生活经验,使他越出了当代作家一直难以胀破的乡村叙述中的风俗趣味、伦理情调、道德冲突,而构建出了一个全然在道德世界之外的‘生命的大地’,一部由人性和欲望而不是道德和伦理书写的民间生存的历史。”*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第61页。建立在人类性基础上的民族性,必然具有深远宽广的艺术生命力,这也正是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折服诺奖评委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概言之,以人类性作为价值底蕴的艺术创作,自然而然就具有了“世界性”的因子,正如《丰乳肥臀》尽管是书写高密东北乡的百年变迁史,但却凸显了人类性的孤独与终极困境;《酒国》虽然是表达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却艺术地揭示出经济时代的巨大隐患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民族性与人类性的浑然统一使莫言成为东方文化的传承者和全新表述者,在文化重建的资源取向上,他深谙“民族性”“本土化”的重要性。有人曾经问司汤达在哪里出生,他回答说:“我是世界种。你们可以把我认做是‘世界主义者’。”*转引自[苏]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孟广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但是,他的文化之根毕竟扎在法兰西文化的土壤深处。莫言的创作之根也深深地扎在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之中,他的转向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和重构的雄心,反映了当下艺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和重构民族文化谱系的重要性。
艺术创新是艺术生命力的基石,也是作家独特个性的标识。如果说莫言的艺术世界像一只在高空翱翔的鲲鹏,那么构成其强劲双翼的要素便是人类性和民族性,他的“飞翔”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