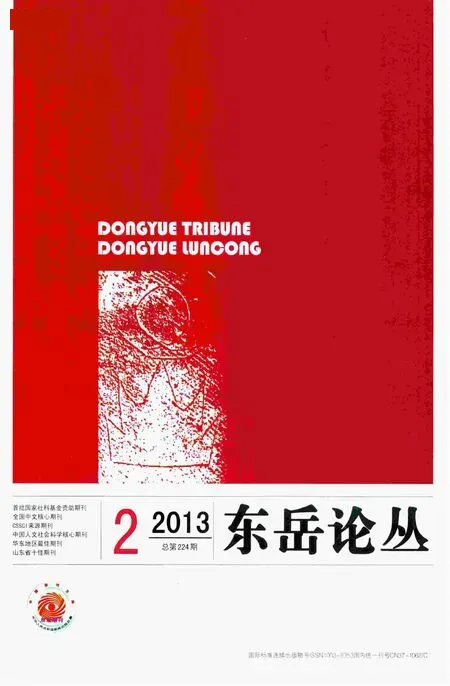嫦娥神话演变及其主题
蔡先金,李佩瑶
(济南大学,山东济南250022)
“嫦娥奔月”是我国古代著名神话之一,在坊间流传甚广,在学界倍受关注,对其研究也不乏卓有影响的成果。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将其作为“整个羿的神话的一部分”进行探讨①袁珂:《嫦娥奔月神话初探》,《神话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并且对嫦娥形象也颇多微词,认为嫦娥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背叛丈夫的无德女子,变形蟾蜍、终生栖身于冰冷寂寥的月宫乃是对其一种惩罚。其实,嫦娥神话原本远非如此,只是我们对其文本“生产过程”缺乏完整的了解而已,最终导致对于文本理解的偏差甚或误读。1993年王家台秦简《归藏·归妹》的出土②1993年,荆州博物馆在湖北江陵荆州镇邱北村王家台发掘了秦汉墓葬共十六座,其中的十五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共计813枚。简文内容有《归藏》、《效律》、《政事之常》、《日书》和《灾异占》(参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王家台“《归藏》编号者164支,未编号的残简230支,共计394支,总字数约4千余字。由于残缺过甚,至今尚未拼出一支整简,顺序也难以排定。”(朱渊清:《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周易研究》,2002年第6期)整理者认为《归藏》“文字形体最古,接近楚简文字,应为战国末年的抄本。”(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刑文编:《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既证明了嫦娥神话存在的相对独立性(而非完全依附于羿的神话),又颠覆了我们对于该神话的一些惯有认识(该神话主题并非是对恶的惩罚,反而是对吉美乐生的向往)。现将新出土的《归藏·归妹》与相关传世文献进行比勘,尽可能地还原嫦娥神话的文本生产过程,并在对这则神话的诸要素进行分析基础上较为深入地挖掘其永生不死的主题观念。
一、嫦娥神话文本梳理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嫦娥神话文献记载始见于西汉时成书的《淮南子》,而秦简《归藏》的出土面世将嫦娥神话的文献记录年代提前至战国时期③戴霖,蔡运章:《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现在我们就从《归藏·归妹》卦辞记载的嫦娥神话文本雏形开始,梳理一下嫦娥神话的文献记录情况。
(一)秦简《归藏·归妹》文本
秦简《归藏》出土时严重残缺,整理者将《归妹》编为307和201两支,虽仅存两支残简,但却是至今发现最早记载嫦娥神话的第一手文献,弥足珍贵,至于后期引用《归藏·归妹》的传世文献则属于二次文献范畴。秦简《归藏·归妹》整理出的简文④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刑文编:《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307号简文是:
《归妹》曰:昔者恒我窃毋死之□。
201号简文是:
□□奔月,而攴(枚)占□□□。
从残简文可得到有关嫦娥神话的信息有:1、嫦娥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2、神话的主角是恒我;3、恒我窃取了不死药;4、恒我奔月。简文记载简略,倘若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只有借助于传世文献了。
(二)传世文献引用《归藏·归妹》文本
传世文献中最早注明引用《归藏·归妹》的是《文选》的“李善注”,之后再注明引用者没有超出“李善注”内容范围的,因此“李善注”作为《归藏·归妹》的佚文就显得弥足珍贵:
《归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药奔月。”(《文选》谢希逸《月赋》,李善注)①(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80页。
《归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文选》王僧达《祭颜光禄文》,李善注)②(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840页。
从传世《归藏·归妹》佚文来看,我们得到的有关嫦娥神话的信息又有所增加:1、恒我变为了常娥,显然是汉以后的称呼;2、神话的角色增加了一位西王母;3、不死药来自于西王母;4、常娥奔月后变为月精。但是,也丢掉了一个内容,即恒我窃药的行为。到此为止,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嫦娥神话文献源于《归藏》,其实,这一事实早有人提出,明陈耀文撰《正杨》云:“《归藏》云常娥奔月是为月精,非始《淮南》也。”③(明)陈耀文:《正杨》(卷四),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可能是由于《归藏》遭受疑伪的影响,故此说法并没有受到他人多少重视罢了。
(三)两汉时期嫦娥神话传世文本
在传世文献中,西汉《淮南子·览冥训》可谓是最早记载嫦娥神话的文本: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④(汉)高诱:《淮南子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8页。
东汉高诱为之作注曰:“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⑤(汉)高诱:《淮南子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8页。《初学记》卷一引古本《淮南子》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⑥(唐)徐坚等:《初学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期。略异于高诱作注本。
东汉张衡《灵宪》记载了“嫦娥奔月”神话,可能直接取源于《归藏·归妹》。张衡《灵宪》载: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⑦( 晋)司马彪撰,(唐)刘昭注补:《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16页;(清)严可均辑,徐振生审定:《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66页。
袁珂认为:“张衡《灵宪》记叙的嫦娥在奔月以前‘枚占于有黄’一节,可能仍是《归藏》的旧文,增加的内容不多。”⑧袁珂:《古神话选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1页。至此可知,无论张衡《灵宪》记载嫦娥神话文本是否来源于《归藏》,嫦娥神话文本在两汉时期也已基本定型。这种基本定型的文本较《归藏》出土及传世标明引用文本增添的内容有:1、姮娥称谓第一次出现;2、神话中的角色又增加了两位:一为羿,一为巫师有黄;3、嫦娥成为了羿之妻;4、嫦娥在奔月之前进行了一次占卜,且占卜结果为“吉”;5、嫦娥变形为蟾蜍,元代白珽对此不解,在《湛渊静语》卷一中云:“后汉张衡……云常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尤可笑也。”⑨(元)白珽:《湛渊静语》(卷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至此,我们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进行了详细的比勘与梳理,嫦娥神话文本的“层累”过程已经清楚无疑。由于《归藏》原文的缺失,我们还不能完全从传世文献中剥离出汉人增饰的成分,然而,细审王家台秦简及《文选》李善注引《归妹》文本,都没有发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和“嫦娥,羿妻也”等内容,可见,嫦娥与羿之夫妻关系当系两汉人撮合的结果①戴霖,蔡运章:《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即完成这一“婚配”叙事的文本形成时间断定是在“汉代”。这一结论也可从羿神话中得到反证。在羿神话系统中,无论是淫佚无度、任用歹人、祸国殃民的残暴君主羿,还是上射十日、下除百害、为民造福的英雄羿,都与嫦娥丝毫无涉。由此可见,在“嫦娥奔月”的早期神话里,嫦娥与羿并没有什么瓜葛。
(四)两汉以后嫦娥神话的流传文本
两汉时期嫦娥神话内容框架已基本构设完毕,之后流传的传世文献文本基本没有增加新的“生产”内容。清马骕《绎史》卷十三记载的可谓一较为“标准”的流行文本:
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药,服之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②(清)马驌:《绎史》,刘晓东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47页。
这种文本完全是建立在汉代传世文献基础之上,只是对于汉代文献起到“缀合”的作用,可谓是较为齐全的“全汉本”。也就是说,自魏晋以来,嫦娥神话就几乎没有进行“再生产”,但这对于该神话的价值与传播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嫦娥神话文本既短小精悍又十分生动感人,完全符合一个神话文本必须有主角、有行动、包含一个或是一个以上的故事的要素③张 光直在《商周神话之分类》一文中提出神话材料的三个标准:第一,我们的神话材料必须要包含一件或一件以上的“故事”。故事中必定有个主角,主角必定要有行动。第二,神话的材料必须要牵涉“非常”的人物或事件或世界——所谓超自然的,神圣的,或者是神秘的。第三,神话从说述故事的人或他的同一个文化社会的人来看却决然不是谎。他们不但坚信这些“假”的神话为“真”的史实——至少就社会行为的标准而言——而且以神话为其日常生活社会行动仪式行为的基础(张光直:《商周神话之分类》,载《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62-363页)。。该神话中角色既有主角嫦娥,还有重要配角羿、西王母、有黄,而西王母与羿又有各自独立的神话系统,这三个神话系统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神话谱系。中国神话历来不需要宏大叙事的手法,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产生像宏大叙事一样的效果;嫦娥神话的文献记载虽然很简短,但这也并不影响其叙述的完整性以及诸神谱系的塑造。在完整的感觉上,嫦娥神话可以与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神话故事相媲美。
二、嫦娥的数次“变形”
在西方神话学术语境中,“变形”一词意思大概是说借助巫术、幻术、魔法等外界力量以达到形体改变的目的。从世界神话生产过程来看,变形的思维是神话生产的突出特征,它并非基于逻辑的一贯性,而是情感的统一性。神话人物“变形”也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神话“生产手段”,而且“变形”的神话人物让人感觉到捉摸不定,难以把握,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中国神话生产也不例外,但却有其独特性。在中国话语体系中,《说文》云“变,更也”,“形,像也”④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8、184页。,所谓“变形”,即是变更了原始形象,从一种形象变更为另一种不同的形象。《礼记·月令》孔疏:“按易云‘乾道变化,谓先有旧形,渐渐改者谓之变;虽有旧形,忽改者谓之化;及本无旧形,非类而改亦谓之化。’”⑤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4页。乐蘅军认为“这一个‘变’和‘化’的定义恰好可以用作神话中‘变形’的完整注脚。”⑥乐蘅军:《中国原始变形神话试探》,温儒敏编:《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一)嫦娥性别“变形”:女性神
许多神话人物原本可能是不分性别的,属于“超人”系列。据出土文献《归藏·归妹》可知,嫦娥神话的原型主角“恒我”,是一个中性词,其蕴含的内容意义应该是“使我永恒”,即期望长生不老之意。因此,这个“恒我”可以作为人的泛指,不需要有性别之分的⑦即使需要分出性别,在父权制社会中这个“恒我”也许应该是男性形象,就像夸父一样,只不过一个为逐日,一个为奔月而已。。
西汉时,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淮南子·览冥训》及东汉张衡《灵宪》皆改“恒”为“姮”了。这一改显然就发出了一个信号,“恒我”与“女”有关联了,从此偏向了阴性化,同时也改变了“恒我”中蕴含的“永恒”的意义。这种避讳所用之法为改字法,此仅改了字形没有改音,还有将避讳字的形、音全改仅留义的①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说文》云:“恒,常也。”②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6页。故“恒”可用“常”作替代,如《诗·小雅·小明》云“无恒安息”,《汉书·董仲舒传》就写作“毋常安息”③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4页。。据此可知“恒我”就变成了“常我”。汉时的“雅言”肯定是以长安为中心的语系,而“我”至今在陕西地方话中发音仍旧近似为“娥”,既然恒我已经女性化,那么语言及文字讹变为“常娥”或是“嫦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自此一个不明性别的“恒我”就演变成为一位美丽的女神形象。是故,秦简中的“恒我”与传世文献中的“恒娥”、“姮娥”、“常娥”、“嫦娥”实为一人。清吴玉搢撰《别雅》云:“恒、姮,皆常也。古人因避讳,……又有羿妻之说,故遂作娥。今则确然以为女子矣,其可笑孰甚焉。”④(清)吴玉搢:《别雅》(卷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嫦娥既然成为了女性神,那么神话生产者就开始来丰富“嫦娥”的身世,着意为如此之神女配上如意之郎君——同样是伟大的神话传说人物——羿。这样,本来与嫦娥并没有任何关系的羿,就成为了嫦娥的夫君。
“恒我”华丽变身为女性神“嫦娥”当为西汉文帝之后,嫦娥这一美妙的女神称谓也当在汉之后形成,因为这次变形主要源于语言及文字的讹变,所以这种讹变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神话人物变形形式。
(二)嫦娥变形神:蟾蜍
奔月的嫦娥最终结局是“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蟾蜍就成为了嫦娥的变形神。如果单从今人眼光来看,美女神变成了奇丑无比的癞蛤蟆,怎么看都是一种悲剧和嘲讽,但在其深层意义上,却是嫦娥通过变形蟾蜍来实现其不死之愿望。
动植物从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在自然界中当是难事,但是在先民看来,却是真实存在且极为普遍的,这主要源于图腾崇拜和灵魂观念:一者氏族成员变化为图腾物的形貌可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者人们灵魂出窍之后可以安置在任何动植物或无生命物上,这就成了变形神话的基本逻辑基础。故嫦娥变形为蟾蜍,是因为灵魂既可以寄存在嫦娥体内,也可以寄存在变形后的蟾蜍身上。在初民看来,这两者并无实质区别,正如卡西尔所说:“神话和原始宗教决不是完全无条理性的,它们并不是没有道理或没有原因的。”⑤[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中国的变形神话主要是基于对生命永恒的坚定信仰以及对于不死的执着追求。传世文献中的变形神话如: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蒂蘨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山海经·中山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山海经·大荒西经》)⑥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92、142、238、389 页。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楚辞·天问》)⑦(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0页。
在这些变形神话中,人可以变形为动物、植物,其他物种之间也可以互相变化,但这并不说明神话具有偶然性或随意性。若要理解嫦娥为什么会变形蟾蜍而非其他,就必须从当时人赋予变形对象的特征中,发现变形前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王孝廉认为“溺而不返”的女娃、“帝女死焉”的女尸,通过改变自己的形象而变形为精卫鸟、蘨草,都是取得了一种“同质异形”的生命延续⑧王孝廉:《中原民族的神话与信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153页。,故嫦娥变形蟾蜍同样如此。蟾蜍能够具有月亮的同位神格,这主要是以蟾蜍的生物学属性为基础的:1、蟾蜍由于皮肤易丧失水分,故白天多潜伏隐蔽,夜晚及黄昏出来活动。而在人类的眼中,月亮也是昼伏夜出的。2、蟾蜍的发育过程属变态发育,从幼体发育到成体,在外形上会有较大改变。而月亮有月相的变化,这无疑也是二者之间的一个相似点。3、蟾蜍鸣叫时肚皮会由消而鼓,这与月亮的消长也极为雷同。4、蟾蜍属两栖类动物,能够生活在水中。原始人相信蟾蜍与水关系密切,在殷代晚期盛放水浆的器皿上就发现有蟾蜍纹图案。初民还相信蟾蜍能够影响水气的多寡,由于蟾蜍的叫声随着天气的改变(水气的多寡)而不同,因此,蟾蜍便如同“雨水的使者”一般①杨堃:《女媧考——论中国古代的母性崇拜与图腾》,《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而月亮恰是水气的掌控者,《淮南子·天文训》云“水气之精者为月”②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7页。;《太平御览》卷四引《抱朴子》亦云“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涛大”③(宋)李昉编纂,夏剑钦等校点:《太平御览》(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另外,在中国古老的占星术中,月亮是主管水旱之神,故可根据月形占验气象④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由于蟾蜍与月亮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故古人常视蟾蜍为月亮之象征。变形神话中的人物,大都是死后变形,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一种生命的延续。但是,嫦娥却并未经历死亡的过程,可以说她是生而变形。究其原因,就在于嫦娥在奔月之前曾经服食了得自于西王母处的不死之药,因为不死药的神奇力量,使得嫦娥免除了死亡的痛苦而得以直接变形蟾蜍,成为月精。实际上,无论是死后变形还是生前变形,其目的皆是为了获得永生。从这个角度来讲,变形神话是具有消解死亡恐惧的积极意义的。
嫦娥变形蟾蜍,完全不存在惩罚之意。事实上,自先秦直至魏晋,蟾蜍一直被人们视为神物,就连殷商青铜器上也有以蟾蜍纹为饰的。《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引《文子》曰:“蟾蜍辟兵。”⑤(宋)李昉编纂,夏剑钦等校点:《太平御览》(第八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页。东晋葛洪《抱朴子》曰:“肉芝者,谓万岁蟾蜍。”⑥(宋)李昉编纂,夏剑钦等校点:《太平御览》(第八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页。可见,古人确实相信蟾蜍是辟邪气、助长生的吉祥之物。因而,古人对于嫦娥的变形蟾蜍非但丝毫没有嫌恶之意,反而充满溢美之词。
(三)嫦娥变形为月母神常羲
嫦娥既然成为了月精,也就具有了月神神格,因此,在嫦娥神话传播过程中,嫦娥又变形为月母神——常羲。《山海经》中有关于日神、月神的记载: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山海经·大荒西经》)⑦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81,402-404页。
从《山海经》来看,羲和与常羲原为神话中的日月之母,但到了《吕氏春秋》里却变成了占日与占月之官。《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载:“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⑧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8页。《史记·历书》唐司马贞索隐:“《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⑨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6页。在这里,“尚仪”就成了“常仪”。《说文·巾部》云:“常,从巾尚声,市羊切”[10]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9页。,“尚”与“常”可通用,例如《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所附《卫绾列传》载“剑尚盛”[1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69页。,《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则记作“剑常盛”[1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01页。。《山海经》中的月母常羲虽不同于占月的常仪、尚仪,但《山海经》中的日母羲和却与占日之羲和别无二致,根据类比原则,则常羲也应该就是常仪、尚仪。事实上也是如此,“仪、羲并从我得声,并属歌部,故得通用。”[13]贾雯鹤:《月神源流考》,《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生日、生月之羲和、常羲变成黄帝时占日、占月之羲和、常仪自然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那么,生月、占月之常羲、常仪与奔月之嫦娥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为在后世嫦娥神话传播过程之中嫦娥与常仪是一体的。明代杨慎《丹铅总录》云:“月中嫦娥,其说始于《淮南》及张衡《灵宪》,其实因常仪占月而误也。古者羲和占日,常仪占月,皆官名也,见于《吕氏春秋》。……后讹为常娥,以‘仪’、‘娥’音同耳!周礼注‘仪’、‘羲’二字古皆音娥。”①(明)杨慎:《丹铅总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杨慎言嫦娥之说始于《淮南子》及《灵宪》,鉴于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自然是不对的;同时他认为嫦娥衍生于常羲,鉴于前文对于恒我演变为嫦娥的文本梳理,当然也是不确切的,清毕沅具有同样的判断性失误:“尚仪即常仪(羲),古音读仪为何,后世遂有‘嫦娥’之鄙言。”②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3页。但他们指明常娥与常仪、常羲乃一脉相承,音同演化则是颇有见地的。清代吴玉搢撰《别雅》亦云:“尚仪,常娥也。《呂氏春秋·勿躬篇》:尚仪作占月。……尚、常形、声相近故得通用;仪亦有娥音也。”③(清)吴玉搢:《别雅》(卷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由于嫦娥在嫦娥神话传播过程中变形为常羲,或者说常羲变形为嫦娥,神格二位一体,导致产生嫦娥源于常羲之误说,以至于袁珂亦曾作过这样的误判:常羲生月“这还是原始时代的神话,而嫦娥奔月神话便是从这个神话演变而来。”④袁珂:《嫦娥奔月神话初探》,《神话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这种长期的误判反而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于嫦娥变形为常羲的可信度。无论是由于语言之讹变还是缘于人们之“误判”,嫦娥变形为常羲已经成为了神话中的事实了。
总之,嫦娥月神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归妹》卦辞对嫦娥的奔月行为充满溢美之词:“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故其奔月就含有一种回归的意味,而“归妹”之隐意为“女之嫁也”,如《诗·周南·桃夭》云“之子于归,宜其家室”,那么嫦娥也就可以当然取得了月母神的地位。由此看来,嫦娥(月神)、蟾蜍(月精)、常羲(月母神)具有三位一体的神格。
三、嫦娥神话主题:“恒我”
当嫦娥神话传说初期,嫦娥的名字“恒我”就点出了神话的主题:“恒我”即“使我永恒”,期望长生不老,蕴含不死之观念,即表明人们对于现世的积极依恋,而非悲观厌世的消极颓废。这一文化主题影响中国几千年,既表明中国人当下的达观,又表现出中国人对于未来的期待。中国古人十分现实地面对死亡问题,希望延长现实的生命,而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再造一个虚幻的“天国”,以追求虚无缥缈的天堂作为人生的目标。“嫦娥奔月”神话所表达的就是对于生命的执着,整个神话也可以说就是依循着不死观念而构设的。
(一)西王母与不死药
如何能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呢?西王母手中的不死药就是灵验的妙方,服食则可。西王母的不死药就成为了该神话成立的关键元素。倘若没有这种特殊的不死药,嫦娥奔月化为蟾蜍月精的神话也就难以存在了。掌有不死药的西王母是何许神人?
西王母的神格之一就是月神。西王母的月神身份在汉代已得到确认,既体现在将东王公与西王母配对出现的汉画像石上,又有汉人铜镜铭文“明如日月不已,寿如东王公、西王母”为证⑤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4页。。其实,西王母月神身份的来源是颇为古老的,殷墟卜辞中常见祭祀东母、西母之辞,陈梦家认为“东母、西母大约指日月之神”⑥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4页。,丁山认为西母即是西王母⑦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第71-72页。,而张光直也不否认这一点,尽管他说得相当谨慎:“卜辞中的‘西母’,或许就是东周载集中所称的‘西王母’,为居于西方昆仑山的一个有力的女王。”⑧张光直:《商周文化分类》,《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65页。由此也可以看出西王母与嫦娥一样,也是具有月神神格的。
嫦娥是服食了从西王母处窃取的不死之药才得以奔月不死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是西王母操有不死之药?这与西王母的居处——昆仑山有关。文献记载: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西山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山海经·海内北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山海经·大荒西经》)①袁 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0、306、407页。
西王母在流沙之濒。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淮南子·墬形训》)②何 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1页。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死,与天相保。(《焦氏易林注·颂之》)③( 西汉)焦延寿著,(民国)尚秉和注,(民国)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玉山与昆仑山乃为同一山脉,《穆天子传》载群玉之山与西王母之邦相连:“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④郭 璞注:《穆天子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杜而未则认为昆仑山与玉山皆为月山,西王母为月神,故可以居住在所有的月山上⑤杜 而未:《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61-64页。。既然西王母居住在昆仑山,那么不死药就很可能生长于昆仑山上了。为何作此推测呢?现看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山万物尽有。(《山海经·大荒西经》)⑥袁 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07页。
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尔雅·释地》)⑦(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淮南子·墬形训》)⑧何 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2-329页。从这些记载来看,昆仑山上万物尽有、诸美齐备,且还有与珠树、玉树等一起出现的不死树、“饮之不死”的丹水和“登之不死”的凉风之山。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昆仑山俨然就是一个不死的乐园,而西王母的不死之药也只有在这样的乐园中才能产生。昆仑山不死的遐想与“嫦娥奔月”神话不死的追寻,若合符契。昆仑山上群神聚集,为何单单西王母掌管不死药呢?因为西王母除了具有月神那种不死神性外,还具有另一种冥神的神格,而这种神格与不死之药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山海经·西山经》言西王母的职司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也就是说西王母是掌管瘟疫、疾病、死亡和刑杀的神,即冥神,而瘟神、疫神可以对立转化为医药之神,故西王母掌管有不死之药最为合适⑨萧 兵:《西王母以猿猴为图腾考》,《楚辞与神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西王母不管是月神还是冥神,二者皆与生死密切相关,因而也只有像西王母这样的具有月神的不死神性及冥神的主生又主死超级能力的大神,方可操有不死药。
嫦娥神话的内在结构是以“不死”为主题展开的,而神话中的西王母亦是定格在“不死”的深层意涵上,这就是两个神话可以相互渗入之内在原因。既然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之自然法则,那么嫦娥神话就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而已,但嫦娥奔月之飘逸将留给人们以无尽的遐想与审美。
(二)月亮崇拜与期望永生
“嫦娥奔月”神话是在远古月亮崇拜的基础上产生的。《管子·形势解》云:“日月,昭察万物者也。”[10]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88页。《淮南子·天文训》云:“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蠃蛖膲。……日月者,天之使也……。”①何 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1-178页。《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云:“月也者,群阴之本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②陈 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人类对月亮的崇拜可谓由来已久,考古发现河南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都常见日月纹图案③戴 霖,蔡运章:《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史学月刊》,2005年版,第9期。,正如严文明所言:“可能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崇拜在彩陶花纹上的体现”④严 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载王仁湘主编:《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到了商周时期,祭祀太阳神和月亮神的习俗就已经普遍流行了。月神崇拜为何能成为嫦娥神话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呢?这主要是因为隐藏于崇拜背后的不死观念。《楚辞·天问》云:“夜光何德,死则又育?”⑤(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太平御览》卷四引皇甫谧《年历》曰:“月者,群阴之宗,月以宵耀,名曰夜光。”⑥( 宋)李昉编纂:《太平御览》(第一册),夏剑钦等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可见,“夜光”就是“月光”,东汉王逸注解该句为:“言月何德与天,死而复生也?”⑦(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近人一般认为“德”通“得”,是说月光来自何处。戴震言:“死,即所谓死霸也。育,生也,所谓生霸也。”⑧( 清)戴震:《屈原赋注》,载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647页。月光以十五天为一个周期,一明一暗。明,古人称作“生霸”或“生魄”;暗,古人称作“死霸”或“死魄”。“霸”、“魄”古音皆与“白”相通,月体银白色,故称“白”。不见月光,即称“死白”,月光死而复生,即称“生白”⑨何 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故《孙子兵法·虚实》云:“日有短长,月有死生。”[10]骈宇骞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期。古人不理解月圆月亏、周而复始的月相变化,故认为月亮具有不死与再生的能力,也就具有了“永恒与不死”的抽象意义。在“嫦娥奔月”神话中,嫦娥服下不死药后,飞奔进月宫,这就象征着嫦娥跨越了生死界,最终达到永恒与不死的境地。因此,“嫦娥奔月”神话在其内在结构上表达着坚定的不死信仰,而其神话诸要素——月亮、嫦娥、西王母、蟾蜍,都具有不死的强烈诉求。归纳嫦娥奔月的历程,实际上有三重不死意象:月神身份——不死的象征;服食不死药——不死能力的获得;飞奔进月宫——不死与永恒境地的回归。无论嫦娥是基于月神身份而得不死,还是服食不死药抑或是飞奔进月宫而得不死,都表明该神话正昭示了关于生命与死亡的人类古老文化的主题。
综上所述,王家台秦简《归妹》的出土,将嫦娥神话的文献记录时间提前到了战国时期,且打破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嫦娥神话从属于羿神话的看法,基本洗刷了嫦娥背夫无德的千年罪名,开启了嫦娥神话独立研究的新时代。嫦娥神话文本经历了一个“层累”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嫦娥之数次“变形”;嫦娥神话的不死主题,是在先民月亮崇拜和不死信仰的观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组成该神话的每一个要素都可能被深深地打上了月亮崇拜和不死信仰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