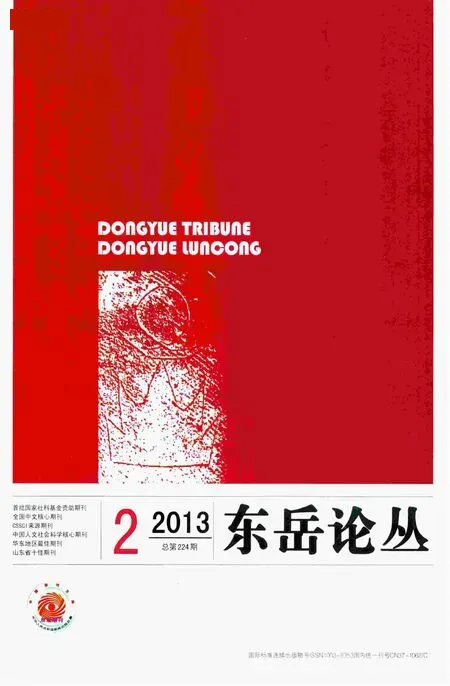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
曹金合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老舍是满族正红旗人,童年时代受到的底层满族文化的熏陶,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人之初’是人的性情的根本所在,童年的人生教育和生命体验是带有原生性的,它包含一个作家的审美选择,存在着永志难忘的精神维系的潜在力量”①。对老舍而言,魂牵梦绕的是小时候来自母亲的生命教育,和满族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艺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满族文化情结。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就是老舍不论采取何种书写方式,这种文化情结都贯穿始终。
满族文化情结的压抑性抒写
在解放前的小说创作中,老舍有意压制对满族文化的抒写。无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都采取了与汉民族文学同化的叙事策略。这样的书写方式,由于老舍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其在外在的风格表现上,与汉族作家创作的小说相比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如果不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就很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满族文化成分。因此舒乙先生曾提出“隐式满族文学”的概念,“认为按照籍贯、职业、生活变迁、气质、外在线索等标准,可以剥离出老舍作品中许多人物形象的满族身份。”②确实,在老舍的小说中,在不引人注意的细枝末节里,包含着满族文化独有的成分。
首先,满族尚武文化的潜隐性展示。满洲八旗制度崇尚的是全族皆兵的尚武文化,以战死沙场为国尽忠为荣,以贪生怕死老死户牖为耻,成为满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尽管满族上层统治者腐朽无能,给整个民族背上了割地赔款的卖国罪名,但尚武的血性气质和民族文化精神并没有丢失,还是在底层民间的八旗子弟的血液中滚滚流淌。即使当时的八旗士兵们家徒四壁,生活处境异常艰难,他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儿,也还是那么一句令人感奋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老舍对满族的尚武文化的精神和血脉倍加珍惜,在许多小说中,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份难舍的感情。如在他的处女作《小铃儿》中,精心叙写了“一只虎”、“花孔雀”、“卷毛狮子”、“金钱豹”这四个小学生为民族大义,苦练武功,透露出作者对满族尚武文化精神的向往之情。此后,老舍从满族文化中不断提取出侠义文化的丝线,织成一件件血脉贲张的艺术珍品,塑造了一系列侠士形象:洋车夫赵四(《老张的哲学》)、书生李景纯(《赵子曰》)、弱国子民小马(《二马》)、猫民大鹰(《猫城记》)、知识分子白李和黑李(《黑白李》),他们侠肝义胆、正气凛然、不畏强暴、扶危济困的尚武侠义行为,典型地体现了满族人尚武文化的精神特质,尽管老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描摹时,有意隐瞒了他们的民族身份。这样,小说中的侠士形象,老舍实际上是把他们当做了民族文化的化身来刻画的,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系列,说明了老舍难以割舍的侠义之情,那份尚武的文化情结的深厚。
其次,满族贞节文化的无意间表露。发源于白山黑水的满族文化主要是游牧和狩猎文化,它不同于中原的农耕文化,没有严格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职责和等级划分,也就形成了不同于儒家文化的贞节观念。特别是未出阁的姑娘借助相沿成习的“当家姑娘”③的权威,在家庭中享有至高的地位,而且与男子的交往中也没有把贞操观念看得多么重要。这种满族贞节文化更多地遵从人的天性,在老舍的小说中无意间得到了表露。如小说《月牙儿》中两代烟花女子所信奉的生活价值观念,核心就是如何看待贞节问题。母亲从坎坷的生活经历中所得出的结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意味着可以通过卖身求得生存;女儿接受现代启蒙教育,认同“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潮观念,二者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从冲突的结果来看,是母亲战胜了女儿。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女儿的贞节观发成了彻底的转变,认同了原初的民族文化观念,认为“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都是笑话,都是吃饱了没事时的玩艺。”因此才有结婚是“卖给一个男人”,卖淫是“卖给大家”的念头,二者形异而质同,并真得付诸实践。这种行为方式和生活观念显然与汉族人有很大的差别,汉族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贞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妨拿丁玲的小说《梦珂》中的主人公略作比较:梦珂在看到表嫂婚后的凄惨生活后,也曾产生结婚与卖淫事实上都一样,都是女性成为男性欲望的发泄对象的念头,但一丝闪念与具体实践之间的遥远距离,注定这只是一个羞于启齿的荒唐的梦。而这在严峻的生活逼迫下的满族女性来说,牺牲贞操换取日常生活的消费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没有汉族女性那么多的顾虑。因此《月牙儿》的女主人公喊出的“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也只有放到满族文化的特定语境中,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理解。正因如此,“她”(《微神》)、小福子(《骆驼祥子》)、谭玉娥(《赵子曰》)等底层女子为生活所迫而操起了皮肉生意。即使是衣食无忧的中层或上层女子,对婚前的性行为或者婚后的性观念等方面也是迥异于汉族女子的,尽管老舍采取隐性书写的方式,没有标明女性的民族身份。比如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的老姑娘虎妞,不但在婚前勾引祥子,与他发生性关系,而且祥子得到的也不是处女,这一细节说明虎妞在婚前至少与两个男人发生了性爱关系。这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中上层汉族女子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满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女子来说,决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虎妞在婚后性爱中的主动性,使祥子发出了悲叹:“那个红袄虎牙的东西;吸人精血的东西;她已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还有小说《阳光》中上层阔人家的女儿,在日常的谈话中“也低声报告着在家中各人所看到的事,关于男女的事。”这些一再出现于老舍小说中的情节和细节,都体现了不欲言明的满族贞节文化:一方面,未出阁的女儿因沾选秀女制度的光,有可能成为贵族夫人,而在满族家庭中占有尊贵的地位和身份,从而很小就培养了她们比较开放的性观念;另一方面,满族贞节观念的淡漠,也导致对性爱关系采取祛除神秘和禁忌的自然化的态度。
最后,满族风俗文化的含蓄性描摹。风俗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生活积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习俗,作为从洪荒年代流传下来的文化信息,它沉潜于每一个成员的内心深处,并左右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老舍的一生中最触动他的灵魂的,就是满族独特的风俗文化。即使他成年之后,这种土著文化遭受了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也仍然念念不忘。“在老舍踏上人生漫漫行程的开始阶段,他的早期文化归位,带着清晰的满族文化属性”④。因此,在老舍的前期小说创作中,带有浓郁的满族色彩的风俗文化,就非常含蓄地流露了出来。老舍展示的满族特有的文化风俗,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类:一是娶长妇的风俗(不同于汉族的童养媳),为保证兵员和繁衍生息的目的,八旗制度要求男子在入伍作战前,一般要完成结婚生子的任务,这就形成了满族的娶长妇的风俗。如《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比祥子大十四五岁,《老张的哲学》中,“赵姑母比赵姑父永远大十来岁”,王德娶的妻比他大八岁,这绝不是“老驴吃嫩草”的汉文化的价值观念所能解释的。在老妻少夫组成的婚姻生活中,妻子对丈夫充当着保护人的角色,并在家庭中享有支配丈夫和其他成员的权威地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对祥子,“像老嫂子疼小叔那样”;《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心疼冠晓荷,“好像一个老姐姐心疼小弟弟那样”;管教他时,“像继母打儿子那么下狠手”。这些生活情景只能在少受中原文化熏染的满族风习中,才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二是婚丧礼俗:满族婚丧要比汉族更讲究场面和排场,程序、规矩和礼节有许多是汉族所没有的。老舍在小说中通过《二马》中马夫人的丧事“接三、放焰口、出殡”,《四世同堂》中小崔的后事,《骆驼祥子》中虎妞死后出殡场面的细致描摹,展示了满族不同于汉族的立幡、停床、烧活、放焰口、供饽饽席等丧葬风俗,形象地说明了满族人“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文化心理。此外,小说《抱孙》中提到的洗三的产育风俗、《二马》中提到的吃“饽饽”、《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过大寿吃的火锅,这些都充分地展示了满族人的饮食风俗。由此可见,尽管老舍采取了压抑性的抒写策略,对满族的风俗文化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但独特的满族风情还是无法掩饰,它们为老舍小说的艺术风格增添了满族风俗文化的色彩。
满族文化情结的张扬性回望
建国后,老舍不再采取遮掩的方式,对满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观念进行压抑性抒写,而是采取回望和留恋的姿态,将包孕着民族文化的内容予以张扬性表现。老舍这种创作心理的变化,首先是新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满族是社会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把满族历史上遗留下的问题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扫除了满族卖国的世俗偏见,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确实提高了满族的社会地位。这对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备受压抑的老舍来说,怎能不欢欣鼓舞呢?其次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让满族等少数民族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国家事务的协商表决,如老舍本人就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和作协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副主席,并作为满族的代表为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献计献策。这样老舍就对自己作为满族作家身份的认定感到骄傲和自豪,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老舍提到“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为人和为文的统一、人品和文品的一致,自然让老舍在文学中尽情地展示满族文化的艺术魅力。最后,正反两方面的艺术对比使老舍清醒地认识到,从小最熟识的满族文化才是自己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艺术资源,也是自己的艺术风格最鲜明的地方。这样,老舍的满族文化情结在比较宽松的时代氛围下,就会在饱含深情的少时生活的回忆中得到凸显,张扬民族文化的艺术魅力和独特风味。
这在未完成的长篇自传式小说《正红旗下》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满载着满族文化信息的风俗习惯,通过三教九流的言行举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因此被称为“清末旗族社会的百科全书”。老舍在对满族风俗文化的精细描摹中,展示出一幅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满族文化画卷。
第一,生活文化的精致化刻画。生活文化包括饮食文化、休闲文化、起居文化、器具文化、服饰文化、娱乐文化等方面,它是一个民族热爱生活、感悟生活和创造生活、享受生活的见证标本。在这方面,满族可以说是将生活文化的内涵和层次进行了巨大提升的优秀民族。老舍在小说中将满族的生活文化作了动情的描写:首先是饮食文化,豆多枣甜的盆糕、麻辣豆腐、干炸丸子、炸鹿尾、酱肘子、腌螃蟹、木樨肉、杏仁茶、豆汁儿、“赛梨耶,辣来换”的水萝卜、“半空儿”的花生等,这些都是满族人怀着对生活讲究的目的,创造出的带有浓郁的满族风味的食品。其次是起居文化,如写福海二哥优美的请安姿势:“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生活礼节带给人的是艺术的享受,作为旗人,老舍对满族文化的精致化和生活的艺术化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又对本民族的文化耳熟能详,因此才放开手脚进行了张扬性的抒写。不过,对这种使“鸽铃,风筝,鼻烟壶,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等日常生活的花鸟虫鱼,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的泛文化现象,对“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的不正常的文化心态,老舍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对于满族文化,老舍怀着既眷念又批判的双重情感态度,才将它的优长和缺陷如此逼真地刻画了出来。
第二,风俗文化的铺张性描摹。白山黑水的地域文化,形成了满族不同于中原文化的风俗习惯,对这些成为自己的艺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文化特质,老舍在小说中进行了铺张性的描写。正如学者赵园所评价的:“《正红旗下》写旗人文化很满,大可补有关民俗学材料之不足。在老舍本人,这作品较之前此诸作也更有明确的‘展示文化’的意向和为此所需的从容心境。甚至不妨认为这小说的主人公即‘风习’。”⑤佐领、骁骑校、旗兵等官兵的称谓,辫子、旗袍等服饰习俗的外在表征,都典型地体现了满族作为狩猎民族的骑射习俗。此外,对祭灶守岁、画鸡爪赊欠的满族习俗也作了详细描述。不过,重点描绘的还是满族独特的“洗三”的风俗,那是在小孩出生后第三天,在亲戚朋友前来祝贺的祥和氛围中,由德高望重的“姥姥”完成的庄重仪式。老舍用工笔细描的手法,有条不紊地层层渲染“洗三”的过程:白姥姥边洗边说祝词,洗完用“姜片艾团灸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最后“用一根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
为了使满族文化的本真面目得到客观化的呈现,老舍在小说《正红旗下》中还采用了儿童视角。这样不谙世事的“我”作为小说的人物兼叙事者的双重角色,体现了老舍希望采取童稚的眼光观察满族社会的风俗文化,以达到尽量还原满族文化原生态的叙事目的。通过自传性、第一人称“我”、儿童视角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个很好地审视民族文化的角度。在淡化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民间的日常生活造成的遮蔽的情况下,老舍的生花妙笔实现了对满族风情文化的诗意描绘。“对于旗人社会的诸种制度、礼俗、家族关系,以及旗人与汉、回民族的关系,无不写及,几近于‘旗人风习大全’。”⑥这种效果的产生,其实正是老舍解不开的满族文化情结,采取张扬性回顾的方式化身为艺术的必然结果。
满族文化情结的创伤性记忆
老舍前后期的小说创作,无论采取压抑性还是张扬性的抒写策略,都与他的文化情结的创伤性记忆有关。压抑性抒写与创伤性记忆的关系显而易见,就是老舍解放后的张扬性抒写,也打上了创伤性记忆的底色。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长期地对创伤性记忆的压制,就不会有张力反弹,形成张扬性抒写的局面,那是老舍念念不忘的满族文化的艺术展露;二是小说的选材上,选取满族底层的困苦生活作为表现的对象,显然与儿时的痛苦记忆有密切的关系。其实,“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他的精神世界,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种种旗人文化和旗人社会的烙印”⑦。这种烙印的创伤性记忆,是由社会反满的大环境和困苦生活的小环境造成的,在老舍的精神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瘢痕,会对他的创作产生重大的作用。从老舍的书信、日记、散文等更能表露作者心迹的文体形式中,可以寻绎出满族底层生活的困苦及受到的歧视,对他的精神造成的伤害。在《老舍自述》中,他写道:“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⑧原本念书无望的老舍被善人刘大叔资助去学堂的路上,幼小的心灵在产生极度兴奋的同时,也有明显地被别人施舍的自卑心理。他日后回忆道“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⑨可以说,幼年时代难以磨灭的创伤性记忆,使老舍在展示满族文化的生命质感时,往往聚焦于贫苦市民的精神创伤和悲剧性的命运遭际。
老舍的满族文化情结的创伤性记忆,对小说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创伤性的满族文化情结,首先在小说的幽默艺术中得到了缓释。幽默在老舍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宣泄与抚慰的作用,将“本无法满足的被来自各方力量压抑着的心理欲力得到了一个释放的可能”⑩。因此老舍才在故意停止幽默之后又念念不忘幽默,经过积极的艺术探索,终于形成了既不故意搞笑又不陷入油滑的幽默风格。幽默的氛围中蕴藏的苦涩和凄凉,与老舍的创伤性记忆是分不开的。在《骆驼祥子》中以幽默的笔墨,描述祥子三次买车又三次丢车的人生经历,实际上是用饱含血与泪的文字“寓沉痛于幽默”(茅盾语)。描绘出要强、自尊、自爱的祥子被毁灭的悲剧,正是在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后,下层满族人的性格写照和命运的隐喻。因为浸透着老舍对贫穷的满族人惯常的拉车生涯充满悲悼性的回忆,所以才写得那么情绪饱满荡气回肠。在《正红旗下》里,对母亲从衙门里领出每月的三两饷银,如何在还债和谋生之间左右为难的心理状态的描摹也充满了幽默的色彩,这幽默是小时候自己艰辛困苦的生活记忆的复活,也是悲中含酸的。《牛天赐传》中的主人公对牛氏家族的人瓜分财产的强盗行径,心中怨恨但强装笑脸的无可奈何的处境,老舍用“含泪的笑”的诙谐幽默予以表现:“不老实怎么办呢?肋条上有刀!”。没有作为弱小民族的一员被强势民族欺压和凌辱,又不得不忍气吞声的创伤性记忆,老舍是不会这样感同身受到牛天赐遭人欺侮还赔笑脸的尴尬处境的。如果说对于底层的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任人宰割的凄苦命运,老舍的幽默中包蕴着深深的同情的话,那么对满汉同化的过熟过烂的文化造成的人性伤害、夜郎自大的精神优越心理、自私自利没有民族和国家是非观念的败类,这些文化劣根及其表现者给满族造成的伤害,则采取了幽默中包含犀利的讽刺方式,强烈地表达着自己的爱憎。如《二马》中对熟烂的文化戕害人性的严重后果作了痛彻的反思:“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赵子曰》中对满族统治者与洋人打仗的战略战术的嘲讽:“不磨快了刀而想去杀野兽,与‘武大郎捉奸’大概差不了多少。”这些都是老舍以满族文化映射整个民族文化的泣血之笔,也是他对满族的政治和文化的颓败给自己造成的心灵创伤采取的压抑性抒写。正因为有这样刻骨铭心的创伤性体验,他才对满族的败类采取不留情面的辛辣讽刺,剖析其丑恶的灵魂。最突出的是信奉“钱本位三位一体”的老张(《老张的哲学》),他的宗教、职业、语言、哲学甚至是洗澡的“三种经”,确实引人捧腹大笑。但笑过之后,不禁让人对老舍解剖本民族的官僚主义和流氓文化的犀利性而拍案叫绝。再细读小说写老张第一次洗澡的情节:“他生下来的第三天,由收生婆把那时候无知无识的他,象小老鼠似的在铜盆里洗的”,在这里,老舍用描述性的语言,而不是用满族独特的婴儿“洗三”的文化风俗的术语,点明老张的民族身份,目的就是为了淡化老张的满族标志。在这背后,不难发现老舍的一颗饱经创伤和忧患的心。由此可见,老舍以幽默作为最主要的掩饰物,对“抑郁寡欢”的个人情感采取压抑性的抒写。看不到老舍幽默背后所隐藏的创伤性的满族文化情结,就不算真正读懂老舍。
其次,纵观老舍的小说创作历程,在幽默达观的背后蕴含的含泪的笑的悲剧,始终是老舍小说创作的动人旋律。悲剧性的结局取代传统小说惯用的大团圆结局,与老舍民族文化的创伤性情结是分不开的。当老舍采取“头朝下”的观察视角,看待满族底层市民凄苦的生活时,他更多地怀着悲悯之情,选取底层社会被侮辱被损害者的不幸遭遇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小说《兔》中小陈坎坷曲折的从艺经历;《离婚》中张大哥无端飞来的横祸;《二马》中老马日常生活中的尴尬处境;《月牙儿》中被逼为娼的母女两代的生活悲剧;《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和祥子的悲惨结局……这一曲曲由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引发的生命悲歌,确实是老舍各种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月牙儿》中的女儿决定在“自由浪漫地挣饭吃”,还是嫁人做贤妻良母之间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贫穷的生活和操皮肉生意毕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何一定要让她选择卖淫这条不归路,那是老舍的民族命运的创伤性情结起的作用。因为在满清政权被推翻之后,满族政治、社会和生活地位的一落千丈,导致许多的满族女儿走上了娼妓的生活之路,因此才触动了老舍的痛苦记忆,写下了以妓女为题材的《微神》、《月牙儿》和《骆驼祥子》。对《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小时候的心理体验,正是老舍儿时创伤性情愫的真切流露。如常被人称道的刻画女儿情感波动的一段:“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是被臭袜子熏的常不吃饭。”正是老舍儿时对母亲为人洗衣的劳动场景的观察感受,也因为是刻骨铭心的切身记忆,所以才会展现得如此生动传神。再比如对祥子和小福子爱情悲剧的描写,两个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只因为一点小事就放弃了,小福子要照顾父亲和年幼的弟弟,这会拖累祥子以后的生活。这样的分手理由确实是有违常情的:因为一是两人的感情比较深厚,能够生活在一起的机会不容错失;二是满族特别尊老爱幼,侍奉老人、抚育幼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如果采取互文本的方式,对照老舍对美国改编本的《骆驼祥子》中,二人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大团圆结局的极度反感,不难发现他内心深处隐藏极深的创伤性的民族文化情结。此外,对底层市民文化痼疾的批判和都市文明病的揭露,对人性弱点的犀利解剖和对主客观环境的强调性描绘,对悲剧的复杂性的艺术展露和人物悲剧命运的多维透视,对老大帝国的乌托邦幻灭和民族文化的悲剧性探析,老舍在小说中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宏观扫描与微观探寻,无疑受到了创伤性的民族文化情结的制约。
老舍曾深情地回忆说:“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11]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口传满族文化传统,以及对书写的满族文化的学习和探究,底层民间浓郁的满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熏陶和浸染,这一切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老舍浓郁的满族文化情结。虽然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老舍在前后期的小说创作中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策略,但二者都深深地扎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满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满族文化的色调。因此,老舍用“包含了满族素质与旗人文化的内容”[12]的小说,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无人撼动的大师级地位。
[注释]
①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②舒乙:《再谈老舍先生和满族文学》,《满族研究》,1985年第1期,第62-63页。
③张佳生:《满族文化史》,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534页。
④关纪新:《论旗人作家老舍》,《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87页。
⑤⑥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第30页。
⑦路地,关纪新:《当代满族作家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⑧老舍:《老舍自述》,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⑨老舍:《宗月大师》,《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⑩杨敏:《分裂者的微笑——对幽默的心理机制的探讨》,《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9页。
[11]老舍:《老舍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12]樊骏:《认识老舍》(上),《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