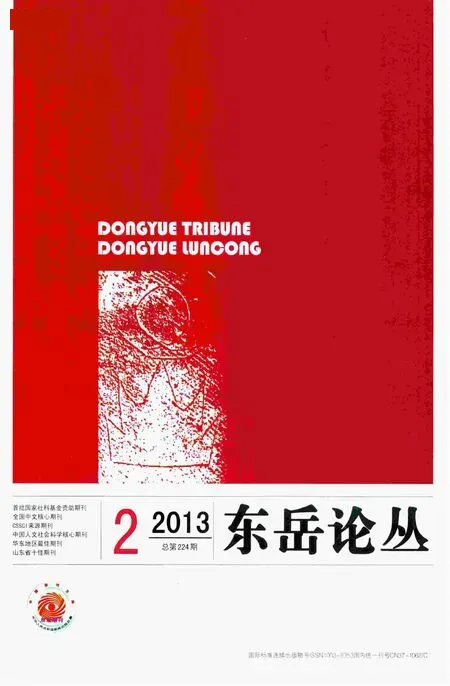后殖民批评“三剑客”的理论内涵及在文本解读中的运用——以《印度之行》为例
于 丹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系,山东烟台264006)
“后殖民主义”出现并流行于二十世纪晚期,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文化思潮,它是对后殖民地社会依然无法摆脱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控制和影响的反映。后殖民主义理论直接针对后殖民主义的现状,呼吁人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学看作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应该看到文学也参与了对现实社会的建构。帝国主义的霸权以前是通过军事冲突、民族迁移和财富掠夺等暴力得以形成,如今是通过隐性的殖民文化继续侵略,是一个文化表征的过程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第432页。。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在于:颠覆西方文化的传统优势性地位,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为全球性语境中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一批任职于欧美高等学府、同时具有第三世界文化背景的学者崛起于西方学术界,其中最负盛名、被称为后殖民批评“三剑客”的是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和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他们站在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独特位置上,以跨文化的国际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欧洲中心论和霸权主义进行了批评,在西方学术界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②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第432页。。萨义德开创了后殖民文化的批评领域,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声望虽然不及萨义德,但同样也为丰富后殖民主义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爱·摩·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在世界文学史中亦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的代表作《印度之行》是其获得最高声望的作品,许多评论家都把它看成是一部政治小说。这部小说颇具政治与文化冲突意味的是,其主角分别来自两个对立的世界:殖民宗主国英国和被殖民地印度,故事以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为参照,批评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种族偏见,表达了作者福斯特对印度人民的同情。《印度之行》的出版对印度独立起到了客观上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也是英国人第一次从本国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自己那副傲慢冷酷的嘴脸,同时也看到了身处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民渴望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强烈愿望。但是,《印度之行》中除了表现历史视角中的印度之外,还存在非常隐晦的东方学意义上的印度,这是因为福斯特始终无法摆脱其固有的西方立场,无法完全超越他的年代,因此,《印度之行》里也就隐藏了诸多后殖民主义的痕迹。本文分别对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并通过解读小说《印度之行》来深入剖析他们各自主要的批评思想。我们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应从更宽广的视野、更多元的角度进行探讨,在运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采用全面综合的视角,深入理解此种理论的意义内涵。
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
众所周知,萨义德有关东方主义的阐述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石。无论何时,当论及后殖民理论的时候,我们都不能绕开萨义德,因为他的《东方主义》正是后殖民批评兴起的显著标志。东方主义是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核心,要深入了解它的实质,首先必须清楚“东方”在萨义德观点中的根本内涵。我们通常所说的东方和西方是一个地理概念,二者的差别是自然的、空间上的差别,但在萨义德的理论中“东方”是被人为建立起来的一种话语模式和符号,“将欧洲之东的地域空间命名为‘东方的’这一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做法部分地是政治性的,部分地是宗教性的,部分地是想象性的;它并不表明在东方的实际经验与有关东方的知识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①[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8页。萨义德指出,西方作家描绘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东方的真实体现,而是在东、西方的对立模式下,以西方为中心映射出来的产物,这些关于东方的描述使西方人民产生了虚妄的文化优越感,更使殖民者的侵略得以合法化。由此可见,东方主义并不是描述、研究真正的东方,而是西方文化霸权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所虚构的东方,是为了控制和压迫东方的一种话语系统②许晓琴:《东方·东方学·东方主义:赛义德后殖民批评与东方学批判》,《语文学刊》,2010年第2期。。从根本上说,萨义德运用东方主义表述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后殖民关系,并揭示了隐含在其内部的文化霸权以及从西方如何看东方的视角,批判西方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东方主义审美观。萨义德研究的是西方帝国主义文本中的东方,注重边缘阅读,旨在挖掘文本中未提到的、故意隐藏起来的真实的东方。“我反对我所说的东方主义,原因不在于它只是对东方语言、社会、民族进行文物式的研究,而是因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东方主义从未经批判的本质主义立场出发,来研究一个异质的、动态的、复杂的人类现实;这意味着既存在一个永恒的东方现实,也存在一个相反的,但同样永恒的西方本质……我寄希望于这样的人文研究:努力超越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局限,追求一种非独断和非本质主义的知识类型。”③[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唐建清,张建民译,《文化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他并不赞成用被美化过的西方来侵蚀东方,也不赞成用民族式的东方去抵抗西方,他力求超越二元对立的东、西方冲突模式,构建平等对话、融合共生的新型关系。从萨义德的后殖民视角出发,小说《印度之行》中有很多细节都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立场,尤其体现在景物描写、人物塑造和宗教信仰方面。
从风景描述方面来看,昌德拉普尔小镇“那么卑微而败落,那么单调而无生气”④[英]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第137页,第74页,第43页,第37页,第73页。;马拉巴山洞的“样式单调,缺乏变化……真是难以一一分辨清楚”⑤[英]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第137页,第74页,第43页,第37页,第73页。;阿齐兹的家是通过他自己的话语进行描述的:“那是一座令人厌恶的简陋房子,在一个低洼的市场附近。实际上里面只有一个房间,房间里面有许多小黑苍蝇乱飞。”⑥[英]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第137页,第74页,第43页,第37页,第73页。从人物塑造方面来看,阿齐兹的热情好客被描写得过分殷勤,奴性十足;他对伊斯兰教的崇敬被看作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的行为;他还时不时地认同殖民的外来文化,流露出自卑羞愧感。参加鹊桥会的印度女士,“她们的姿态有些古怪,变化无常,好像在寻求东方和西方都没有的一种新的方式……一会儿畏缩着,一会儿又有了精神…表露出赎罪或者失望的情绪。”⑦[英]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第137页,第74页,第43页,第37页,第73页。没被邀请的印度人,“他们赤身露体,只束着一块腰布,有些人甚至连腰布也没有……他们的人品行为低下多变,超过了有知识者的想象,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受到邀请。”⑧[英]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第137页,第74页,第43页,第37页,第73页。从宗教信仰方面看,当摩尔太太在白人罕至的清真寺里,遵守伊斯兰的风俗脱鞋膜拜时,竟使阿齐兹对她刮目相看,可以想象英国人平时是多么霸道,印度文化处于多么卑微的地位;通过阿齐兹的口,他对印度教徒是这样评价的:“散懒的印度教徒——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交往……他们没有卫生设备,家里脏得很。”⑨[英]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第137页,第74页,第43页,第37页,第73页。这些明显无法摆脱帝国意识的东方主义话语,处处体现着萨义德东方主义揭示出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印度风景与欧洲风景相对立,印度人与欧洲人相对立,印度宗教与欧洲宗教相对立。总之,前者都是落后的、低下的、消极的,而后者则是先进的、高尚的、积极的。这些对比性的描述都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暗示着落后的东方印度需要先进的西方文明来拯救。在殖民主义背景下,由于欧洲种族文化的优越感早已深深嵌入以福斯特为代表的殖民地国家作家的脑海,因此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意识,必然传承历代殖民主义学者对被殖民地的书写套路。所谓的印度及其他东方国家的肮脏落后表现,实际上是由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侵略造成的,而这些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只看到了东方国家消极的一面,他们无法明白,也根本不愿意深究东方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小说《印度之行》中,英国指派专人到印度担任总督,管理印度,在政治上实行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为了制造殖民统治合理化的假象,英国殖民者还对印度人民实施文化侵略。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迄今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印度的语言①刘 晓霞:《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印度之行〉:论福斯特的反殖民主义意识与殖民主义意识》,《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可见,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传统文化的压迫之深重。萨义德作为一个东方人对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进行批判,认为西方殖民者从自身的立场,怀揣着对东方的偏见和歧视的态度,因而他们无法看到东方国家的灿烂文化和东方人民的勤劳热情。某种意义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折射出“东方”突破西方压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崛起。
二、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理论
作为当代重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家之一,斯皮瓦克最突出的特点是其鲜明的女性主义理论。她出身第三世界,跻身于第一世界学术阵营,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她对第三世界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有着格外敏锐的深切感受。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中,列举并分析了印度寡妇登上已故丈夫的火葬堆以身殉夫的陪葬制度,英国殖民者进入印度后,废除了这个习俗,宣称他们解放了印度妇女,给她们带来了文明,“白人正在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②[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通过解救妇女,把她们作为自身种族的保护对象,帝国主义冠冕堂皇地建构起社会建设者的良好形象,从而为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殖民入侵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土著保护主义者的论点:“妇女实际上想要那样死”③[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认为她们是自愿陪葬的。斯皮瓦克指出,在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观点背后,真正属于印度妇女自己的声音消失了。她更深一步揭示出,这些印度妇女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土著保护主义者用以证明各自理论合法性的工具,两者实质上都是在压迫妇女,印度妇女遭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她们的声音受到双重遮蔽④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构成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⑤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在斯皮瓦克看来,女性群体内部也并不统一,在批判男权主义的同时,还要批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西方第一世界的白人女性忽视第三世界妇女存在的因不同阶级、种族、地区和文化背景造成的差异,把自己的利益和观点强加于第三世界的妇女,并以优等文化代表者自居,把第三世界妇女看成是一个邋遢落后、毫无反抗精神的低等群体⑥李小林:《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1期。。可见,将后殖民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融为一炉,是斯皮瓦克显著的批评特色。《印度之行》中西方白人女性与印度女性之间的对话,以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视角进行解读,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女性的声音被湮没在西方优势话语权之下,甚至被完全剥夺。
特顿夫人,昌德拉普尔市的市长太太,在鹊桥会上假惺惺地用乌尔都语讲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她学了几句乌尔都语,但她只对她的佣人讲,所以她只知道动词的命令式,却根本不知道还有比较客气的说法。”⑦[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3页。当她听到一位印度女士说“你们的语言我们可能会说几句”⑧[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3页。,特顿夫人很惊讶,“什么!奇怪!她懂英语!”⑨[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3页。当另外一位印度女士提到巴黎,特顿夫人肯定地说:“她们只是路过巴黎,这是无疑的。”⑩[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3页。特顿夫人的话“好像是在描述候鸟的活动……她发现这群印度女士中有的已经西洋化,也会用自己的尺度来对待她这位市长夫人,所以她的态度便更加冷漠了。”[11][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3页。可见,在特顿夫人与印度女士进行交流的时候,故作热情地与她们攀谈,其真正目的是显示自己的本国语言,展示自己的身份优势,她幻想着对那些听不懂或者不会说英语的印度女士加以蔑视和耻笑;但事实恰恰相反,当其中一些印度女士能够讲她的语言的时候,她变得失落,继而冷淡,也为失去语言的优势感到愤慨,因为她得知有些印度人已经西化,也会用她的社交礼节同她打交道,显然这触及到了她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动摇了英语的霸权地位。特顿夫人,作为西方白人女性的代表,她只关注西方白人世界的女性,东方的、黑人的或是第三世界的女性根本不在她的视野范围内,正如她向摩尔夫人介绍参加聚会的那些印度女士一样,“不管怎么说,你比她们都高贵。不要忘记,在印度,除一两个女帮主之外,所有的女人都在你之下。她们都是一类人。”①[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2页。这便是西方白人女性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作为第三世界女性形象的代表,这些参加鹊桥会的印度妇女是处于被压迫国家的被压迫群体的位置,她们一方面在国内受到传统男权文化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到英国殖民主义的压迫,双重的压迫使第三世界的女性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利,正如一位印度女士不肯定地表述,“你们的语言我们‘可能’会说几句”,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就被特顿夫人一连串的惊讶、奇怪打断了,她没有了继续说话的机会,更被剥夺了继续说话的权利,因为她的身份是第三世界的女性。面对西方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第三世界的妇女遭受到最为沉重的文化压抑,同在女性群体内部,第一世界的白人女性人为地设定了对第三世界女性的认知标准,将她们自己主观的标准设定为全世界女性共同的、唯一的参照②巴微:《多重的身份,自由的视角:斯皮瓦克理论综述》,《新西部》,2008年第14期。,不接受也不允许其他不同形式的女性存在方式,视不同于她们的女性就是落后、未开化的低等群体。同时拥有双重身份即第三世界有色人种身份和女性身份的斯皮瓦克,其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第三世界的女性是最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群体,尤其提倡恢复她们的话语权。与以往的女性主义不同的是,她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不仅包括对男权主义的反击,还包括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抵抗。简言之,就是反对“统治与服从”的现存状态,旨在颠覆“宗主与臣属”的二元对立结构。伴随后殖民主义文化兴起而产生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斯皮瓦克正在努力使人们认识到:第三世界女性遭受到更深的权利制约和压迫,要把种族、阶级等内容融入到性别理论的批评中,恢复和实现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权。
三、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
前殖民时代的传统文化被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文化所摧毁,新的文化正在建立之中,面对这种过渡的局面,如何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是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社会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后殖民理论批评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出生于印度,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霍米·巴巴对此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文化的混杂性理论,即不同民族的文化无论优劣、大小,总是呈现出一种混杂的形态,特别是在全球市场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文化交流日渐迅速和频繁,民族文化之间的混杂及其由此引起的变化广泛而深刻,民族文化要想保持自己鲜明独特的民族性已经成为不可能③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那些作为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石的东西,比如同质化的、自愿的、邻近的历史性传统的传播,或者有机的种族社区,正面临着重新定义的深刻过程。……我倾向认为,精神的爱国热情这方面有着压倒一切的例证,说明了想象社区的混杂特点的跨国性和译转性。”④Bhabha,H.K.,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5.巴巴认为对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社会的人们来说,要解决文化身份的问题,首先要承认文化的混杂性,必须把这种理论工作的指涉和制度要求重新定位在文化差异(不是文化多样性)领域。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即文化是经验知识的对象,而文化差异则是这样一个过程:宣布文化是可知的、权威的,可以充分构建文化认同系统⑤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6页。。文化多样性把文化视为一个客观的、静止的、没有发展变化的、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文化差异则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与外界、与异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只要这个过程存在一天,文化就始终是混杂的。霍米·巴巴认为,一种文化是在与不同文化的交往过程中,在寻找差异的过程中肯定自己和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动态的过程中不断混杂的结果。霍米·巴巴试图通过混杂理论颠覆殖民话语的权威,揭示殖民化过程中被殖民文化与殖民权力的种种矛盾。殖民者想要树立权威,使殖民话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就势必要和当地的语言、文化互动接触,以达到“同化”的目的,并声称“拯救”被殖民者落后、野蛮的本土文化。在权威本土化的过程中,异质的两种文化发生碰撞、交流,同时由于他者语言的吸收,殖民话语变得具有混杂性,失去本真,殖民话语本身从内部遭遇到挑战。在霍米·巴巴看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势必要发生碰撞,进一步沟通和转化,弱势的被殖民文化不一定非要被强势的殖民文化完全吞没,可以通过双方互相对话、协调,达到一种均衡的文化认同;反之,如果双方的文化权利不均衡,势必要产生矛盾,弱势的被殖民文化就要挑战强势的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对《印度之行》中的菲尔丁这个人物,可以从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视角进行解读,透视殖民霸权从内部发生的瓦解。
菲尔丁,一个英国派驻印度的文化官员,他温和理智,没有狭隘的种族观念,在整个昌德拉普尔市,菲尔丁无疑是和当地印度人保持友好关系最成功的英国人的正面形象,“他不像其他英国官员那样对印度人冷嘲热讽,菲尔丁是个健壮又快乐的人,他喜欢嬉戏逗乐。他做过很多错事,可他学生的父母却设法为他掩盖,因为他深得他们的爱戴。聚会上招待人员端来茶点的时候,菲尔丁没有回到英国人那一边去,而是同印度人一起吃辣味鹰嘴豆去了。他与什么人都谈得来,什么东西都能吃。许多印度人都接近他……”①[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6页,第73页,第366页,第368页。可是他骨子里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必须从西方的视角审视东方,“神秘只是脏乱的一种动听的说法,不管是神秘还是脏乱,两种说法分不出优劣……”他眼里的印度“的确是一个脏乱的国家。”②[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6页,第73页,第366页,第368页。他眼里的印度人也是愚昧低俗的:阿齐兹是个愤世嫉俗、无能的家伙;拯救阿齐兹的各派印度人民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印度人民的游行示威在他看来都是无理混乱的荒唐之举;甚至是戈德博尔教授也只是个贪吃鬼的形象。阿齐兹蒙冤被拘禁,菲尔丁却劝他放弃赔偿,这些都是因为菲尔丁是一个来自殖民地国家的英国人,从西方殖民主义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一方面,他是文化使者,在印度各地开办学校,和印度人友好相处,接触的是印度文化;另一方面,他又是英国殖民者,他推行的一系列教育都是为了间接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当他经受两种不同文化碰撞的时候,他失去了均衡,倾向于英国的殖民霸权地位,他与阿齐兹交往的前提是坚持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他嘲笑阿齐兹建立独立印度的愿望,“大英帝国真的不能废除,因为它还不成熟……要是离开了我们,印度人会马上衰败下来。”③[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6页,第73页,第366页,第368页。在这种前提条件下,菲尔丁的愿望“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成为朋友呢?”④[英]福斯特:《印度之行》,第46页,第73页,第366页,第368页。注定要失败,他的静悄悄的殖民之路注定会瓦解。事实上,菲尔丁混杂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在印度找不到真正的友谊,在英国也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他注定找不到自己的归属,英国人和印度人都容不下他。在后殖民话语范围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始终处于对立的位置,欧洲殖民者认为自身是文明进步的,而东方被殖民者是野蛮冲动的;西方殖民者把东方被殖民者构建为他者,用殖民文化去影响或同化被殖民国家的民族文化,嘲笑贬低他们;但同时又迫使被殖民的人们远离白人文化中心,在各个方面压迫他们。所以,按照霍米·巴巴的观点,殖民者是处于一个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混杂世界里,在冲突的生活现实中试图寻求他们的身份认同。事实上,霍米·巴巴自身也始终处于一种身份认同上的两难境界,即活跃于西方学术界,却出身于第三世界,因此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也是不确定的(既有对自己民族的怀旧,又有对宗主国的肯定)。毫无疑问,霍米·巴巴的混杂身份对他的混杂性理论是有影响的。作为一个来自印度、来自后殖民地国家的学者,霍米·巴巴的使命是从内部摧毁西方欧洲中心主义,他的策略就是让殖民内部混杂化,消解其固有的权威性。他从被殖民者的视角对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提出质疑,因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西方话语对东方的表述,表露出强烈的矛盾状态——被殖民地既是西方帝国主义欲望的目标,又是被他们嘲笑的目标⑤王波:《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述评》,《史教资料》,2007年第11期(上旬刊)。——殖民侵略的后果让西方帝国主义自身产生了复杂的混杂状态,使殖民者矛盾不安,从而达到从内部瓦解殖民霸权的目的。
结 语
如今,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西方世界试图对话所借鉴的文化策略,而且也是边缘文化寻求重新认识自己民族文化光辉前景的一种有效途径。后殖民主义理论让我们认识到,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发展过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绝对尺度,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利,也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面对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当中,因此,我们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和方法也应该不断变化、更新,我们要灵活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不能片面关注某个评论家的某个理论,要全面系统地加以研究学习,并深入发掘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