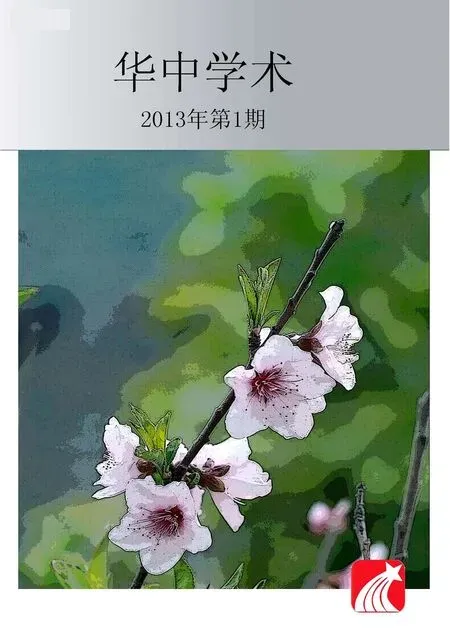忆先师石声淮先生
佘斯大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学缘漫忆
忆先师石声淮先生
佘斯大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我是1979年考取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是石声淮先生。上课的地方就在石先生的书房。当时先生住在城内华中村一栋古老的两层居室楼上,书房不大,木地板,窗外是几株高大的朴树。时值九月,外面炎热非常,可室内一派清幽,时不时传来知了悠长的鸣声,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先生坐在书桌前,用地道的长沙话给我们讲着那些历经沧桑的古代文献,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目前,可先生竟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
记得先生给我们讲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周易》。三年,先生每周至少都要给我们讲一次课,每次都是一上午,最后总要留半小时左右让我们提问。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先生就和我们闲聊,我们丝毫不感到拘束。在闲聊中,我们得知先生是191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人家,父亲是晚清翰林。先生字仲丁,1938年就读于湖南省国立蓝田师范学院国文系,那时在这所学校任教的有著名的国学大师黄侃、钱基博、钟泰诸位先生。后来先生毕业留校,再后来就随钱基博先生受聘于华中大学,又随钱先生一起留在了华师。先生说在现在这栋房子里已经住了半个世纪,楼下就是先生岳父钱基博先生的故居。
有一次,我出于好奇,翻看先生书桌上讲课用的一部线装的《十三经注疏》,因为我手上也是一部线装的。先生说“我一生‘吃’了两部《十三经》”。见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解释说,当时家里困难,读书无法维持,只好把一部《十三经》卖掉,这是第一部;后来买了一部,因为治病,不得不又卖掉,现在是第三部。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读书时,学校特别批准先生以学生的身份兼助教,以补贴生活。接着他又说,我这部《十三经》过录的是黄侃先生的句读。我见书上有工整的红色圈点,便体会到先生曾下过怎样的功夫。还有一次,讲课时先生引用了《韩非子》,他从书架上拿下书来,也是线装的,将引用的那一段翻给我们抄,而先生自己却不是看着书,而是背诵,那熟悉的程度让我们吃惊!有时见我们不太清楚,便开玩笑地说:“你们呀,真是‘书生’,书是生的,不熟!这不行。‘熟’是首要的,书要多读。”我见这部书上不仅用朱笔认真地打上了圈点,天头之上还用毛笔整整齐齐地写上了批注,书末还盖有一方图章,“石声淮仲丁校读”。因为图章刻的是金文,“仲丁”二字只占一个字的位置,我没有认出来,便向先生请教。先生说:“那是仲丁两个字。我在家行二,又是个男孩子,所以字仲丁。不过我很少用这个名字。”最近看到一些资料,才知道先生还字均如。还有一次,我不懂什么是“黄杨题凑”,就提了出来。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回去查查《汉书·霍光传》的注解,不懂,再来。”我明白了,学问不能靠老师喂,书要自己读,不然就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而先生连《汉书》的注解也如此熟悉,这又是使我们大吃一惊的!
先生无论是教学,还是回答学生的问题都特别认真,有一种循循善诱、雍容和雅的长者风范,每每使人如沐春风。先生对于经书的熟悉程度是惊人的,然而我们没想到的是,每次上课,先生都做了极为认真的准备,一张张卡片,都整整齐齐写着讲课的内容。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看到一副清吴昌硕写的集石鼓文的对联,上面写着“用猎碣字集蘤经句”,我不知道《蘤经》是部什么书,便问先生。先生说:“蘤即葩,即《葩经》,就是《诗经》。”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先生就托人带封信给我,这里不妨抄录出来,以见先生的教学态度之认真:
斯大:
《蘤经》即《葩经》,韩愈《进学解》“《诗》正而葩”,后人遂以《诗》为《葩经》。《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思玄赋》,“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蘤’”。《文选》卷十五《思玄赋》作“天地烟煴,百卉含葩”。我以前疏忽,以为“葩”“蘤”同字,实在是《后汉书》与《文选》不同,“蘤”音huā,“葩”音pā。几十年我一直未弄清,你一问,我逞口而答。方才翻了《后汉书》和《文选》,才悟到我几十年的迷误。“葩”和“蘤”都是花,义同形异,音也不同,是两个不同的字。特为纠正。吴昌硕改“葩”为“蘤”,大约和我犯的错误相同。
声淮 七日
回答一个学生的问题,偶有失误,亦是常事,竟如此郑重地予以纠正。看罢信,我内心好久不能平静,我想到很多。在考研之前,我曾在中学任教十五年,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对待过学生的提问。从此我感觉到,作为一个教师的责任之重大,深深感到先生这才是大家风范!一个教师绝对不会因纠正偶然的失误而失去学生的尊重,相反,学生会对他更加崇敬。先生对学生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我的讲稿,先生对每一章、每一节都作了仔细的修改。我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时,请先生去听课指导,先生说:“我住校外,不太方便,就不去了。你大胆讲,没关系。”记得那天课是早上一、二节,地点是老三号楼二楼西边的阶梯教室,那天天气晴朗。当我讲完第一节课休息时,发现先生竟然坐在门外走廊里!我大吃一惊,先生笑着对我说:“我若是在课堂里,你会紧张,讲课放不开的。讲得不错,放开讲。”我坚决要先生进课堂,先生想了一下,笑着说:“好吧,不过你不要把我看成是来发现你毛病的,看成是你的援军,是帮你的,就不紧张了。”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眼眶里潮润了。
先生曾担任中国屈原学会、湖北屈原研究会、中国孔子学会的副会长、顾问等职,通英语、德语,日语也能作一般会话。
先生治学异常严谨,常常对我们说:“古代文学需要深厚的文史根基,因此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学识积累过程,不要仅仅是外国的理论框架,填补一些中国的例子就算研究,以中国的例子去证明外国某些理论的正确。”先生走的是乾嘉一路,从考证入手,先占有有关文献资料,从文本中抽出观点。先生致力于《周易》研究多年,发表了《说〈彖传〉》(上中下)、《说〈杂卦传〉》、《说〈损〉〈益〉》等论文多篇(有一部分文稿,可惜出版社要先生自费而未能出版)。以《说〈彖传〉》为例,为给《彖传》一文断代,论文中征引《史记》、《汉书》等多种文献以说明司马迁时代、汉宣帝时代还没有《彖传》,结论令人信服。一次到武大周大璞先生家听课,讲到《周易》,周先生说:“石先生的文章我仔细读了,考证细密。”先生的《说〈损〉〈益〉》一文,为了说明儒家的“损”“益”(如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与道家的异同(如《老子》中“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从《荀子》、《淮南子》、《孔子家语》、《说苑》,以及《周易》的汉代各家之注,一一考证而对其异同加以说明,将问题论述得清清楚楚。
先生治学是既继承古道,又益之以新法。他非常关心出土的新的资料,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之中。有一次我看一部文字学方面的书,书中说到郭沫若反对《说文》的将“易”释为“蜴”,认为是由甲骨文中一个“一只器皿向另一器皿倒水”的字形演变而来。由此我想到《周易》的书名,便提出来问先生。先生说:“郭沫若有道理。《德鼎》出土后由上海博物馆移交给了故宫,其铭文中‘王益之贝二十朋’之‘益’写作‘易’下加个‘皿’字,那么古‘易’‘益’为一,所以‘王益之’可读为‘王易(锡、赐……)之’。《周易》本是讲变化的。”并说:“你可以参考《讼》上九和《损》六五。”先生如此熟悉出土文物,确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先生为我们讲解《周易》,曾要我给他找长沙马王堆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等出土时的有关图片,他说每卦应该有个中心事件,如《师》卦是关于战争,《旅》卦是关于商旅等,他怀疑《大过》卦与殉葬有关,卦辞中的“栋桡(挠)”中的“栋”即墓穴上方的横木。我找了包括这两处的许多古墓开掘时的图片,过了许久,我问及此事,先生说:“还没有成文,觉得证据还不足。”
以经学为本,旁涉诗文子史,是先生治学的又一特点。《如何自学〈离骚〉》、《说〈招魂〉》等一些论文以及《苏轼文选》、《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合作)等是先生的又一批研究成果,大都用的是乾嘉考据之法。如《说〈招魂〉》一文通过五个方面的论辩和多方引证,证明了《招魂》是屈原被楚襄王于公元前299年放逐汉北时所作,乃招怀王之魂,并寄托了屈原的哀思。有关苏轼的著作则是在传统注笺之法的基础上有所增益,特别是《注笺》的附录,给予读者关于该词的相关资料,免却了读者翻寻之苦。因注笺细密,故而钱钟书先生欣然为此书题写了书名。
先生还有许多成稿,如关于《尚书》、《周易》的专著以及《元结诗文注》等,我曾见先生认真誊抄、定稿,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来商谈数次,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现在先生已离我们而去,这已成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我毕业之后,每逢疑难,常常到先生那里请教,先生总是细细讲解。平时也常去看望先生,先生记忆力依然如故,令人十分欣慰。先生有什么事情,如要查找资料,或解答我的疑难,常常是托人带信给我。这些信件至今我仍然珍藏着。大约是1996年11月8日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过八十岁了,已入老境,夜间足冷,被子上必加厚毯子等压得重重的,两足仍是冰冷。眠食如常……”万没想到,过了不久,先生竟一病不起!虽然先生已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的长者风范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主持人语】“学缘漫忆”栏目所谈“学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转益多师”,所写学缘不限于一位老师或一所学校,如第三辑王先霈老师的文章,第六辑刘守华、黄健中老师的文章;另一类则是某一位老师的“专辑”,本刊第五辑“学缘漫忆”刊发的三篇文章,都是记述率真浪漫的黄曼君先生的。本辑我们刊发的四篇文章,怀念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另一位学识渊博、有长者之风的前辈石声淮先生。四位作者均为石先生的学生,佘、何、傅三位是石先生的研究生,戴建业则是在本科生阶段听过石先生的课。四篇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勾画出石先生治学为人的优雅风姿,不约而同地谈到石先生的博闻强记、经典倒背如流、外语能力强、教学认真、著述严谨、对学生关爱有加等惊人才华和传统师德。石先生就是一位能体现华中师范大学校训“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代表人物!
四篇文章还不约而同地谈到石先生的“述而不作”,四位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与理解,试图回答为什么学问这么好的石先生发表的著述这么少的疑问。他们或指出受制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有一部分文稿,可惜出版社要先生自费而未能出版。”(佘斯大)或指出是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学术传统:“先生治学严谨,又秉持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述而不作’(或许应该是‘厚积薄发’)的学术传统,反对轻率立言和华而不实的文风。他不轻易著书立说,论文也写得不多,可谓是惜墨如金。”“在先生心目中,著书为文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非有真才实学且具真知灼见者不能为。因此,他不轻率立言,不赞成研究生忙着发表论文,也从不催促我们写文章,反而还告诫大家不要学某些人没有什么心得却喜欢‘干喊干叫’,所谓胸无点墨,却好自矜夸。”(何新文)或指出是出于“敬惜字纸”的学术敬畏和学术操守:“珍重文字,不率意为文,不强作解人,则是先生对文字对学术的尊重。这或许可以解释先生留存文字不多的原因,而这恰恰体现了先生的一种学术敬畏,一种学术操守,一种学术神圣。总体来说先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先生的世界中,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保住一点守住一点什么似乎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任务。在古典文化传统消失殆尽的时代里,传承比发明更为急切,讲述比创新更有力量。”(傅道彬)或指出有两种原因:“一是他走进学术界后国家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学者的言论空间越来越逼窄,天天见到因言获罪和因书招辱的恐怖场面,特别是岳父钱基博先生打成‘右派’以后,石老师不仅自己不敢著述,也把钱先生未付梓的著述付之一炬,这样,他自然就从治学的严谨变成了处世的拘谨;二是石老师对学问、人生和著述可能有自己独特的体认。”“在我所见到的老一辈学者中,只有石老师谨守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遗训。石老师求学以为己,其旨在因心以会道,今人求学以为人,其意多在借学以求利,写书以邀名。到底何者为得?又何者为失呢?”(戴建业)这些回答,各自自圆其说,对于我们加深认识石先生的学术人品不无裨益。尤其是在今天学术成果量化评价机制下盛产“印刷垃圾”的现实中,石先生的“述而不作”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反而成为我们反省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丧失学术敬畏和操守的学术流弊的参照。什么叫做真有学问?什么人能够传承中国优良文化传统?什么样的老师对学生有正面影响并被学生永远怀念?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位于昙华林的华中村14号那栋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是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及其女婿石声淮先生的故居,也是石先生给研究生上课的课堂。佘、何、傅三位对这座小楼的深厚情感溢于言表。“书房不大,木地板,窗外是几株高大的朴树。时值九月,外面炎热非常,可室内一派清幽,时不时传来知了悠长的鸣声,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佘斯大)“门前有几棵枝叶繁茂的高大朴树,顿时便觉有一阵清凉袭来。”“毕业之后,没有机会再聚集在昙华林先生的书房里听课了。但华中村那座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仍然是我们师兄弟和先生团聚的圣地。……门前的朴树依然茂盛,先生也还是那样的温和博雅,嘘寒问暖,记忆犹新。”(何新文)“小楼原是先生岳丈钱基博先生的旧居,房前屋后,梧桐掩映,绿荫如盖。”“先生有歌唱的习惯,我们去昙华林拜访先生,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哼唱着一首首古诗,曲调悠扬,意味深长,环绕于梁间树上。听到先生歌声的人,都被诗的音乐所感染。”(傅道彬)今天华师校园内高楼林立,但是再也找不到一处“昙华林华中村14号”了!我曾经随何新文去这座小楼拜访过一次石先生,书房茶几上摆放着先生刚刚翻阅的英文报刊,那次拜访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可惜后来没有机缘继续向石先生请教。好在读了四位教授情真意切的怀念文字,使我们对石先生仰之弥高,同时又使我们懂得何谓中国传统的优雅的学术境界。(张三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