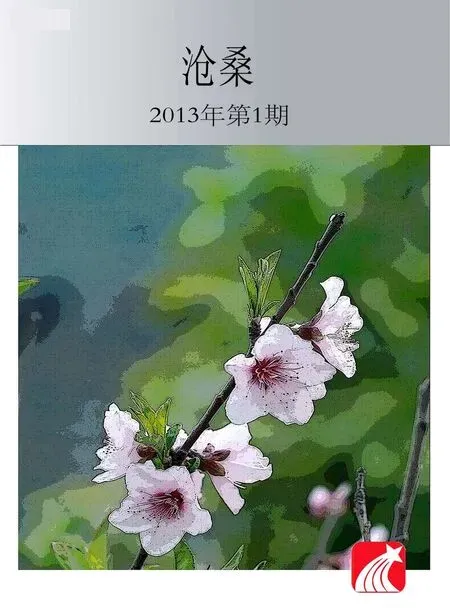试论口述史学在当代中国农田水利史研究中的应用
李安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学界对建国以来农田水利史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但一些著作文章大多停留在依靠档案资料或者纯粹从自然技术史的角度论述水利史,对口述方法的应用或因著作本身的需要或因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完全展开。本文试图从现代口述史学的价值和把其引入到当代中国农田水利史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其在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略作论述。
一
传统口述史学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没有文字之前,人们用口述方法来传授知识、传播经验、记忆历史,这是最古老的传承人类活动的方式。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是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成为新兴的一种历史研究学科的分支。一般认为,现代口述史学的开端是以1948年美国学者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口述历史研究室为标志。随着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发展,口述史学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对弥补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盲区、盲点,对研究近代以来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口述史料,展现给我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过,对现代口述史学的理解并不是很统一,很多学者都是从自身的研究角度来给出定义的,如张广智先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的口述证据,然后再经过筛选与比照,进行历史研究。”[1](P331)他认为口述史学运用现代的录音技术等,以谈话录音为依据获取资料,同时也要注意访谈资料的鉴别和筛选。而杨立文教授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义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2](P120)杨先生是侧重于传统的口述方法而进行搜集史料,对现代录音等技术的运用并不是很重视。虽然内涵定义不一样,但这并不妨碍现代人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等学者对口述史学的重视和运用。目前,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口述方法已被普遍运用。在近现代历史学领域中,现代口述史学的操作性、技术性和实用性比较强,这为研究者找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但能够更深入发掘历史的新方法。
现代口述史学的发展是对传统史学方法和理论的重大革新,是伴随着科技进步所发明的音像技术而产生的,为我们当代史学无论在资料搜集还是研究视野等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推动了近现代重要人物领袖和底层群众及相关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档案史料的不足,方档案来治史的传统方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异常丰富,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因为政治运动或者其他方面的影响,一些重大事件或焦点人物的档案资料不完善,存在错误疏漏之处或者记录相对简单,在研究中缺乏丰富、有力的档案史料支撑。口述史学方法运用到当代史研究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一些官方文献资料的不足,补正空白或修正错误的史料,其价值显而易见。现代口述史方法,操作灵活,视野开阔,运用性强,应用性广,在现代史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可使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论证更有力、更充实、更有趣味性,分析也更具有客观真实性。因此,口述史学特有的地位使我们认为应该加强它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重大事件,参与其中的不同阶层的当事人现在基本还健在,他们对这些事件的口述是补充和互证档案资料的宝贵财富,广泛地挖掘和利用这些“活的史料”,可以更全面清晰地分析当时的历史,也为后人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史料。
二
水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何充分合理科学地利用水资源是数千年来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且不断进行探索解决的问题。传统的农业中国有着治水用水和管水的优良习惯,统治者和民间群体都很重视水利设施的修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始终把水利建设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在建国初期、十年建设时期、“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表现在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加快了工业发展的步伐,为城乡居民饮用水提供了水源,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学界对建国以来农田水利建设的分析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著作、地方志和论文都是在原始档案史料的支撑之上完成,笔者认为这是不完全客观的,档案本身因历史原因有其复杂性,甚至掺杂了政治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现在的研究应该在现有的条件下不断扩展视野,在充分利用音像等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发挥口述方法的作用,不断深挖整理不同阶层群体的口述史料。总之,把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农田水利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更加有力地推动建国以来农田水利建设史的研究,更充分地全面深入客观地把握这段历史。
第一,通过访谈、笔录、录音等方式整理形成的口述史料可以为建国以来农田水利史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填补一些文献记载的空白,弥补档案史料的不足,为一些有疑问的档案文献提供口述史料的支撑。不可否认,原始的正统档案是研究农田水利史的基础,但档案在形成的过程中往往会带有主观性的政治色彩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出现记录的遗漏及空白。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政治运动一直不断,档案里面的某些内容难免会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农田水利建设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群众运动,尤其是1957年冬季开始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被认为是“大跃进”运动的先声,当时的档案文献记载中难免会留下一些政治色彩较强的内容,这些内容很多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笔者针对查阅的档案和走访而形成的口述史料进行过一定的对比,发现在一些相对敏感的问题上如民工伤亡如何处理,其抚恤金是否到位等,官方档案和民间口述史料就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建国以来农田水利史的研究仅仅依靠档案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通过其他途径挖掘史料成为水利史学研究中的新任务。而现代口述史学的兴起,口述历史方法的运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口述史料的挖掘实质上就是生活在现在的当代人整理保存当代史料的过程。在史学中存在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传统,但我们当代人更应该注意当代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为以后开展当代史研究提供便利。现在这一惯例已被打破,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农田水利建设史是当代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同阶层的人大部分还健在,从他们身上可以捕捉到很多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史料,通过采访、记录、整理形成口述史料,可以更充分地研究把握在建国以来农田水利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群众的意愿和思想状态、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当时是如何处理的等等。因此,作为中国当代史研究者,我们应该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加快当代中国水利史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最大可能地抢救濒临失去的“活史料”,为以后的史学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第二,在当代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史的研究中,引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可以直接接触到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他们的身份差异反映到当时的水利建设过程中就是意愿、态度、行为和思想的差异。人民创造了历史,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最不能忽视的就是人,通过接触不同阶层的群众,尤其是底层的工农群众,获取他们对事件或人物的朴实看法,可以使农田水利建设史的研究更全面、更深入、更客观。过去“历史学家的眼光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而集中在决策者身上,集中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杰出人物身上。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没有历史价值,惟独意识领域才值得史学家去关注”[3](P5)。历史发展是人民群众参与推动的,深入群众才能记录真实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田水利建设是成千上万普通群众参与的,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和亲身感受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真实想法,可以更好地透析历史本来的面貌。把口述历史方法引用到当代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研究中,“使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4]。作为当代水利史工作者,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水利史研究中的宏观叙事或者只用正统档案的层面上,应该放宽我们的研究视野,关注底层劳苦大众,了解并记述他们不同时期在水利修建中的思想意愿和生活、工作状况等。因为普通百姓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历史前进的持久动力,他们具有真正的历史发言权。底层群众“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下,不能直接把它写出来,如果没有口述历史,许多文化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就难以提供他们所见所闻的重要历史情节,这些历史情节只能湮没不彰。口述历史可以如实记录他们的谈话,保存原始的记录,使广大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历史的撰述,极大地扩充了历史信息的来源”[5](P4)。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在参与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他们的意愿、态度、想法等才是真实的历史写照。因为知识水平的差异性,如何真实地记录保存这些普通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意愿和生产生活中的境遇正是我们口述史工作者的任务。
第三,口述史学和当代中国农田水利史的研究的有机结合有助于该领域研究运用新方法,找到新领域,发现新问题,使该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我们在与历史见证者面对面的采访过程中,思维的火花往往因双方思想的交流而产生;在整理分析口述史料的过程中,新问题的发现,研究视野的扩展也会在无形之中产生。口述史学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突破了以往史学所固有的范式,它具有叙述性、大众性、社会性等特点,作为主要特征之一的社会性,“不仅决定了口述史学所闻广泛性和完整性,也对其客观性和叙述性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口述史学的社会性使该学科成为名副其实的面向大众的历史学,体现了重返人文的传统,与整个历史学科的研究方向是完全一致的”[6]。作为研究当代农田水利的历史工作者,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现代技术手段在搜集整理史料中的作用,在新史学方法不断革新的过程中,既保留传统史学对政治史、领袖人物史等的关注,又要关注不断变化的底层社会群众的历史,了解把握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水利建设过程中的思想动态和心理意愿。通过访谈交流,收集整理反映历史见证者的口述史料,可以让我们发现研究中的盲点、空白点,为研究当代中国农田水利史提供新的领域和多元视角。
三
真实、客观和可信是史学的生命,也是史学工作者一直努力的方向。一些学者对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叙述过程中会存在着个人的好恶、怀旧的情感、短时的失忆、回避自身的错误、政治的压力、年代的久远、记忆的模糊等现象,以此形成的口述史料肯定会有一部分失真,这就要求口述史学工作者要加强对口述史料真伪性的辨别,尽最大的可能采访记录并保存历史见证者在当时最真实的想法和最客观的历史记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通过访谈等形成的关于当代农田水利史的相关口述史料要与文献档案互证,这是确保该口述史料真实可靠的主要途径。杨雁斌指出:“口述史料必须同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和补充,才能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7]由此可见,通过相关文献的补充和互证对农田水利史口述史料真实客观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在当代中国农田水利史研究的过程中,注重相关资料档案等文献的收集保存是必不可少的,但原始的档案史料也有疏忽错误之处,单靠这些资料不可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历史,而充分挖掘不同阶层的群众口述史料,以期与档案资料相互补充证明,寻找两者的契合点,最大程度地使口述史料具有真实可靠性,也使我们的水利史研究更具真实客观性和趣味性。如果档案之中缺乏记载,难以与口述史料互证,而被采访者恰好参与了当时的历史活动,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做呢?笔者认为,一方面尽可能地寻找档案文献或者报刊、杂志等,寻找记录;另一方面,如果相关文献确实找不到记录,应多采访几位历史的见证者,以口述和口述之间相互印证。
其次,口述史工作者应积极与被采访者互动,取得被采访者的信任,在访前充分准备,采访中共同参与,密切配合,并注意访谈方法的规范性以尽可能地获得口述的翔实资料。采访之前充分地准备,包括语言是否有沟通障碍,如有可以找向导或者翻译;问题设问是否合乎情理,某些涉及个人伤痛之处的问题尽可能避免或者委婉提出。采访过程中亲密地配合,开场白如何设定,一些历史敏感问题如何婉转地提出等等,这个过程是决定访谈是否成功的关键,也是决定口述史料是否真实可靠的重要因素,因为,在采访的过程中也是在和被采访者进行情感思想的交流。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大跃进”期间的农田水利建设,既是群众运动也是政治运动,一些人可能在这期间做了一些有违道德的事,或受到了心理生理上的伤害,或感情的不允许,他们有可能不愿坦诚相告。如笔者在贵州某地采访一位老人时,让他回忆当年在水利建设中可有干部贪污腐化问题,老人沉思了半天说干部腐化不知道但是在男女问题上影响不好。因此,作为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者,我们应制定周密的采访计划,运用成熟的采访技巧,对被采访人加以引导提醒,调动积极因素,规避不利的主观因素,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在保护被采访者个人隐私的基础上以求口述者最大程度地口吐真言,实事求是,最后才能形成相对真实可靠的口述史料。
最后,尊重受访者的个人尊严是口述史工作者必备的基本道德准则。充分尊重是口述史学学科发展的支撑点,如果不懂得尊重人,对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漠视,就不会获得真实的口述史料,更谈不上口述史学的发展进步。口述访问要想成功,就必须在充分尊重受访者个人尊严的基础上,去主动关心对方生活和工作等,对对方的观点表示同情和理解,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最大程度地获得对方的真实口述资料。总之,将珍贵的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等有机结合,会比较全面客观地推动当代中国农田水利史的研究,进而也会带动口述史学的发展。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杨立文.论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功用和地位.北大史学(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朱佳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
[5]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杨雁斌.面向大众的历史学:口述史学的社会主义辨析[J].国外社会科学,1998,(5).
[7]杨雁斌.浅论口述史学的发展与特点[J].国外社会科学,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