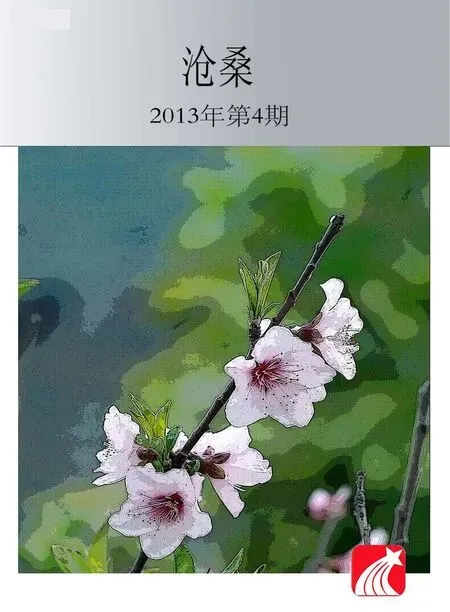清代治河名臣靳辅
陈 健
陈 健 辽阳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靳辅(1623—1692),字紫垣,辽阳( 今属辽宁)人,隶汉军镶黄旗。顺治九年(1652),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顺治十五年(1658)改内阁中书,旋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元年( 1662),迁郎中。康熙七年( 1668),晋通政使司右通政。康熙八年(1669),擢国史院学士,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副总裁官。康熙九年(1670),改内阁学士。康熙十年(1671),授安徽巡抚。康熙十五年(1676),因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康熙十六年(1677),授河道总督。康熙二十七年(1688),被参劾革职。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复为河道总督,十一月卒于任,年六十,赐祭葬,谥文襄。康熙四十六年(1707),追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雍正五年(1727),复加工部尚书。雍正八年(1730),入祀京师贤良祠。著有《靳文襄公奏疏》《治河奏绩书》和《治河方略》。
三百年来,靳辅的“本事”史不绝书。譬如,《清史稿》辟有4800字的篇幅为靳辅立传;《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更是洋洋近9万言;《辽阳乡土志》之《耆旧录》和《辽阳县志》卷八《勋旧志》,对靳辅也均有简略的记载。文献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学术的附丽。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上述一“ 稿”、一“ 传”、两“ 志”所提供的史料为依据,概括性地介绍靳辅这位清朝治河名臣世代传颂的生平事迹[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治理从来都是关乎安民兴邦的大事。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因素和历史原因,自古以来黄河流域就经常泛滥成灾。在元朝初期最终建成的纵贯南北,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既依赖黄河的水量补助,又惧怕黄河的泛滥和淤积,特别是运河与黄河的交汇,更加剧了黄河的泛滥。此外,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而高含沙量致其善淤,淤积的泥沙致其善决,决堤又致其善徙。明末清初,战乱频仍,河道年久失修,至康熙初年,黄河为害更甚,使得运堤崩溃、漕运阻塞。康熙帝亲政之初,即“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后来因“廑念河防”,曾“屡行亲阅”。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康熙帝命工部会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共同商酌对黄、淮、运河汇合部清口的治理,以防水患。翌年十月,批准工部议复河道总督王光裕的奏疏,于清口筑坝,“以遏浊流”,后因爆发了吴三桂叛乱而无暇他顾,清口筑坝之事才被搁置下来。总体而言,自顺治初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尽管治河修运未辍,但始终成效甚微。
康熙十五年(1676),黄河、淮河泛滥更甚,促使康熙帝在对黄河、淮河的全面治理上痛下决心,并确定“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治河总方针。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河道总督王光裕因“全无治河之才”,实难再继续担此重任,遂被康熙帝解职。在吏部尚书明珠的推荐下,靳辅由安徽巡抚擢授河道总督,从此开始了其长达十六年之久的治河生涯。据此看来,靳辅出任河道总督,也的确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2]。靳辅果然不负所望,上任伊始,就施展和显示出高超的治水才能。
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靳辅在进京受命途经邯郸时,于吕祖祠看到“负才久不遇”的陈潢所作的一首雄奇豪迈的题壁诗,惊异之余,“踪迹得之,引为幕客”。四月,靳辅即与陈潢日夜兼程地走马上任,接着是马不停蹄地视察河道。两个月间,靳辅在得力僚属陈潢的协助下,经过“周度形势,博采舆论”的踏勘和考察,既领会了康熙帝“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谕旨之意,又分析了历代治水的利弊得失,同时继承了明代著名河臣潘季驯“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治河理念,从而形成了他“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3]的治理方略和治河、导淮、保运的治理模式。同年七月,靳辅胸有成竹地向康熙帝提出《经理河工八疏》,随即得到康熙帝的赞同和支持,因此,即使经仪政王王大臣廷议,“以军务未竣,大修募夫甚多”为由被“暂停”时,蔼然待之的康熙帝仍然对靳辅下了“熟筹”之令,即吩咐待其进行一番深入的谋划后,再予考虑。靳辅在作了一些诸如以“车运”取代“用夫”,即可解决“募夫甚多”问题之类的修改后,于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又“复申前奏”,经议政王大臣等议复,康熙帝给予批准,接着“发帑兴工”,限三年告竣。自此,在靳辅的主持下,一项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全面展开,并逐步取得成效。
治河之初,靳辅为执行“河、运宜为一体”的治理方针,根据“黄水四溃,不复归海,清口运道尽塞”的实际,重点实施了两项举措:一是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起,对运河自清口至清水潭长约二百三十里的河段进行挑浚,一年内完工;二是筑江都漕堤和塞清水潭等处决口,第二年告竣。而仅筑江都漕堤这一项工程,就比原计划节省了六分之五以上的费用,为此受到康熙帝的表彰。后经奏请,新挑河更名为“永安河”,新河堤更名为“永安堤”。在靳辅的督治下,治河工程仍在继续进行,但是一边修治,一边仍有水患,给治河工程带来了极大困难,由此为人垢病,进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不断、日益升级的激烈争论。康熙二十年(1681)三月,靳辅“以大修已满三年,黄河未尽故道,自请议处”。虽然“部议革职”,但康熙帝念其勤勉,遂从宽留任,以戴罪督修。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康熙帝应靳辅的请求,派遣户部尚书伊桑阿等人前往江南勘察河工。此时,正值“不端之人”崔维雅以候补布政使身份奏呈所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两书及条议二十四事,诽谤和否定靳辅“所行诸法”。康熙帝谕令崔维雅与伊桑阿等随行,到现场同靳辅商议。伊桑阿等以挑剔的目光“遍勘诸工”,回到徐州后,以崔维雅条陈的二十四款质问靳辅。靳辅无所畏惧,慷慨陈辞,认为:“河道全局已成十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辟,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同时再三强调“断不宜有所更张,隳成功,酿后患”。同年十月,在廷议会上,工部尚书萨穆哈等提出萧家渡决口应责令靳辅赔修。康熙帝出于对靳辅的垂青和厚爱,更出于对靳辅的信任和呵护,以靳辅赔修不起和赔修万一贻误漕运的委婉托辞,予以拒绝,并且表示“崔维雅所奏诚无可行者”。十一月,靳辅应召来京,清廷在靳辅本人的参加之下,再次商议他的治河事宜。靳辅的陈述和应答,特别是对崔维雅意见的否定和反驳,当场得到康熙帝的首肯和支持。崔维雅条奏的“似有可取”、“诚无可行”的二十四款被彻底否决后,康熙帝对靳辅“特旨宽免赔修,决口仍给帑堵筑”。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靳辅疏报“萧家渡工成,河归故道”,同时因七里沟险汛日加,提出请修“天妃坝、王公堤等闸座”。另外,又“请增开封、归德堤工,以防上流壅滞”。对此,康熙帝在欣喜之余,一一准奏,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河道问题上提出“以后益宜严毖,勿致疏防”的谆谆告诫。同年十二月,靳辅也得以官复原职。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率众从京都出发,第一次南巡河务。十月十七日,康熙帝到达山东郯城县红花铺。靳辅赴康熙帝驻跸之地朝见后,就扈从康熙帝详视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势、灾情和各项重要工程的进展情况。在巡视途中,康熙帝语重心长地跟靳辅谈及对“水流浸灌,多坏民田”的切身感受和对“运道之患在黄河”的深重忧虑,并向靳辅明确提出“筹划精详,措置得当”的治河要求和“水行沙刷,永无壅决”,进而“一劳永逸,可以告河工之成”的治河目标。临别时,康熙帝把自己有感而发、亲洒翰墨的《阅河堤诗》赠给靳辅,且以“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相勉,再次体现出对河道总督靳辅的极大信任和殷切希望。
在治河初见成效之后,靳辅谨记康熙帝“减水淹民”的嘱托,踌躇满志地进一步提出“于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新河谓之中河”的奏请。中河工程动工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竣工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有论者说,“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4]此是后话。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提及在开中河事件上,从奏请到议决,从启动到完成,靳辅所受到的诸多磨难。
康熙二十四年(1685)九月,力持“减水闸益河工无益百姓”和“分水不致多损民田”主张的康熙帝,“念高邮、宝应诸州县湖水泛滥,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经理海口及下河事宜,仍听辅节制。”为解决河南地处上游,如有失误江南必将淤淀的现实问题,靳辅提出“自高邮城东车逻镇筑长堤二,历兴化白驹场至海口,束所泄之水入海。堤内涸出田亩,丈量还民;其余田招民屯垦,以抵经费”的疏请,因“取田价恐累民”,康熙帝“未即许”。同年十月,靳辅为挑浚下河、筑高长堤和修河两堤等事,又连奏三本。由于靳辅所持观点与自己相左,且与众人也多有不同,加之事关重大、非同小可,康熙帝决定召靳辅和于成龙进京会同九卿详加讨论。在修治海口及下河问题上,于成龙和靳辅之间发生了各执一词的意见分歧,前者力主疏浚海口以泄积水,后者仍旧坚持筑高长堤束水以敌海潮,并因此形成了以于成龙和靳辅为各自代表的两大阵营。自此,一场新的治河之争又不可避免地迅即展开,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但使靳辅处于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而且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难境地。康熙二十五年(1686),工部疏劾靳辅治河已经九年,迄未成功,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康熙帝依然坚持说:“若遽议处,后任者益难为力,今姑宽之,仍责令督修。”虽然康熙帝口头上一再为靳辅开脱,但我们对其“河务甚难,而辅易视之”的含蓄言辞细加品味,会不难发现,个中未始没有对靳辅言语浮夸的责备之意。可见,反对派的攻讦此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康熙帝对靳辅的绝对信任。
康熙二十六年(1687)七月,靳辅矢志未改,仍认为与其杜患于流,不如杜患于源,于是又一次疏请“筑重堤”,并具体阐述了他与幕属陈潢沿河勘察后拟定的设计方案,同时还称扬陈潢十年来的“佐治勤劳”。此疏随后产生的两个结果却喜忧参半:一是廷议同意了靳辅的意见,并赐陈潢佥事道衔;二是当时已担任直隶巡抚的于成龙仍然固执地坚持“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筑”。由于彼此完全对立,因此议而不决。康熙帝本欲举行廷议,后来因太皇太后之薨而中止。
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辅进入了他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的人生晚年,以至于在时运多舛和举步维艰中度过了他生命时光的最后四年,也从而走完了他60年生为逆旅、死为永归的人生旅途。
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向朝廷呈递《参河臣疏》,偏听偏信地发表了对靳辅进行诋毁和攻击的言论,更将陈潢斥之为“忌功之念重,图利之心坚,真国之蠹民之讐”的“一介小人”。二月,给事中刘楷又疏劾靳辅用人不当,“任事漫无寸功,惟见每岁报冲决而已”。而山东道御史陆祖修的疏劾足以致人于死地,认为:“河臣积恶已盈……今兼有屯田害民之事,去一靳辅,天下万世仰赖圣明,无逾此矣。”一时之间,靳辅成为众矢之的,参劾之声,甚嚣尘上。三月,尽管靳辅当廷进行陈辩,但由于康熙帝就靳辅与于成龙之间的河工之争再次作出了“屯田害民,靳辅纵有百口亦不能辩,开海口乃必然应行之事”和“海水倒灌,无有是理”的明确裁决[5],群臣“ 恐议为靳辅之党,谁复敢言”[6],所以靳辅最终难逃劫难。随后,康熙帝“允九卿议停筑重堤,革辅职,以福建浙江巡抚王新命代之”,陈潢同时被革去佥事道衔,工部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和赵吉士也相继被革职。
此后,靳辅在连续四年的赋闲期间,曾多次应诏承担临时性的任务,但劳而无怨、苦而不悔,实心任事、竭尽全力。康熙二十七年(1687)十一月,靳辅奉命同工部尚书苏赫等往阅通州运河,为有利于漕运,提出了“沙河建闸蓄水”和“通州下流筑堤束水”两条建议,均被采纳。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康熙帝就漕运总督董讷请尽泄南旺湖之水北流和仓场侍郎凯音布请挑浚北运河之事召靳辅咨询,靳辅提出两全其美之策,认为从北运河两旁下埽,束水则水深,自可济运。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靳辅因谙练河务,奉命与户部侍郎博霁、兵部侍郎李光地等阅黄河险工。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靳辅随从康熙帝南巡阅视河工。从沿途的所见到百姓的叨念,从治河的论询到从实的回奏,康熙帝着实被靳辅的“浚河深通,筑堤坚固,实心任事,劳绩昭然”所感动,觉得对靳辅的处分委实有些过重。同年三月,康熙帝回京后,即谕令吏部“复其原品”。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河道总督王新命因勒取库银为运河同知陈良谟所告发被免职。康熙帝认为:“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靳辅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数年之虑。”遂令靳辅仍为河道总督。靳辅先以体弱多病相辞,未得允许,康熙帝随即“命顺天府丞徐廷玺同往协理”。靳辅重新上任不久,适逢陕西西安、凤翔地区遭受灾害,康熙帝下令截留江北漕粮二十万石,自黄河运到蒲州。靳辅受命之后,疏陈水路只能先运至孟津,然后再通过陆路转运到蒲州,并不顾年迈羸弱之躯亲自督运,使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得到了康熙帝的嘉奖。随后,靳辅上疏万言,复陈《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并要求恢复“骤遭诋毁,革去职衔,旋即物故”的幕属陈潢的职衔和起用因讨论河工而被罢官的熊一潇等人,其惜才之情宛若柔肠,重义之举堪称侠士。七月,靳辅病情加剧,再次疏请卸任,被允。康熙帝对靳辅的病情十分关心,委派内大臣明珠前往探视,并传达谕令,想方设法进行调养治疗。十一月,靳辅终告不治,卒于任所,享年六十岁。
靳辅的溘逝,使康熙帝“深为轸怀”,并以汉大臣未有之例,“特命入都治丧”,清廷也依例给予祭葬,追谥文襄。按照清廷礼制,“诸臣谥法,‘襄’字为最隆重……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7]大概是因为亲政后的康熙以平定三藩、治理黄河和疏通漕运为三件大事,而作为治河名臣的靳辅则尽瘁于河事一十六年,襄赞圣功,成就斐然,与开疆辟土、武功卓著的能臣无异,所以对靳辅赐以“襄”字,特谥“文襄”。康熙三十五年(1696),江南民众吁请在黄河岸边为靳辅捐资建祠,时任河道总督的董安国因此入奏,下部议行。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第六次南巡之后,鉴于靳辅功劳卓著和贡献杰出,又“加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用彰朝廷追念勋臣之典,为矢忠宣力者劝”。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又因靳辅“劳绩茂著”,再追赠工部尚书,“以示朕笃念前劳至意”。雍正八年(1730),以“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衔河道总督谥文襄靳辅”之名,入祀京师贤良祠。众所周知,清代祀贤之风颇盛,靳辅除祀于上述两祠之外,江苏淮阴清江浦所建“四公祠”,将靳辅、齐苏勒、稽曾筠、高斌等四位清代治水名臣合祀;开封东南隅古吹台禹王殿供有治水八贤,其中包括靳辅;济宁至南阳的百里长堤命名为“靳公堤”,济宁州天井闸口北岸建有“靳文襄公祠”等。纵观靳辅的一生,虽然屡遭非议,饱受委屈,但死后的靳辅在朝廷和民间,均获有流芳百世的英名。
历史既顺理成章又不可思议。不管是有情抑或无意,冥冥之中似乎已经注定,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靳辅都将与浩繁的水利工程结下不解之缘。据新闻媒体报道,从2006年秋到2007年初,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北保定段文物抢救性发掘工作中,根据《满城县志》的明确记载和当地村民的传说,文物考古人员按图索骥,在满城县城西7.5公里处的东渝河村南勘探和发现了清代治河名臣靳辅的家族墓地,并进行了野外发掘。迄今为止,资料整理和深入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至于是否还会有其他新的发现不得而知。倘若靳辅九泉有知,发现从自己当年曾一度主持的浩大而繁复的治河工程,到尚处于建设中的这项惠及当代、造福子孙的南水北调工程,两者虽然间隔着遥远的时空,但竟有如此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他该会感到何等的兴奋与喜悦!
《清史稿》的编纂者对靳辅写有一句略带憾意又不失精当的赞论:“世以开中河、培高家堰为辅功,孰知辅言固未尽用也。”当然,历史更不会忘记,知人善任的康熙帝在第六次南巡回京后,在对吏部的训谕中,以“治河之得失”为切入点,对靳辅作了如下最公正、最全面的盖棺论定:“康熙十四、五年间黄、淮交敝,海口渐淤,朕乃特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自受事以后,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创开中河,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大且远。朕每莅河干,遍加咨访,沿淮居民感颂靳辅治绩,众口如一,久而不衰。”
时代的脚步渐行渐远,历史的云烟随风澹淡。今天,靳辅的《靳文襄公奏疏》《治河奏绩书》和《治河方略》等传世著作,已然成为展示这位治河名臣心路历程和大器之才的重要载体。靳辅治理河患的卓越实践及其造福苍生、泽及后代的伟大创举,也同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宝贵遗存。为此,靳辅赢得炎黄子孙的敬仰当之无愧,受到世世代代的怀念理所当然。
[1]在本文中,凡引文出自《清史稿·靳辅传》《清史列传·靳辅传》《辽阳乡土志·耆旧录》和《辽阳县志·勋旧志》者,均不一一标明,其余则分别加注。
[2]诸葛亮.前出师表.
[3]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靳文襄公奏疏(卷一).
[4]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5]清圣祖实录(卷134).
[6]康熙起居注(第3册).
[7]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