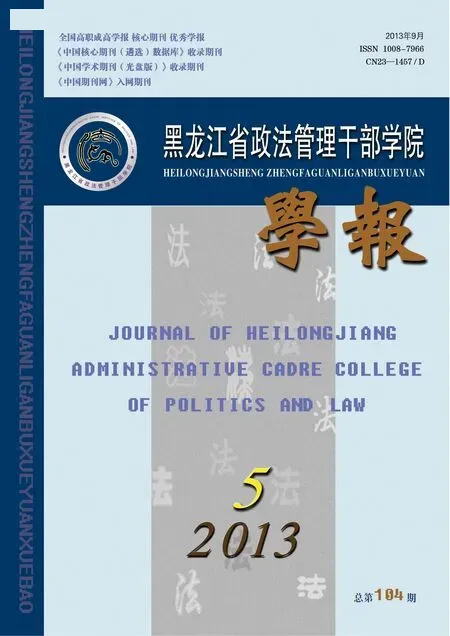商标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宏观分析
尹晓静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江苏常州213022)
商标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宏观分析
尹晓静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江苏常州213022)
商标侵权现象在现代社会呈剧增趋势,如何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对于司法实务和理论研究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故从宏观上构架起商标侵权判断的体系尤为重要。从商标权人的意思表示、商标使用的性质、侵权实质等进行分析,界定了商标侵权的内涵和外延,试图通过理论的重构来厘清和区分商标侵权行为,以准确打击侵权,维护良好商标秩序。
商标侵权;宏观分析;混淆可能性;商誉损害
“商标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不同于“商标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概念,前者决定该行为的侵权属性,而后者决定侵权行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及在多大范围内承担。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一般民事侵权具有四个要件:一是有违法行为的存在;二是损害事实发生;三是危害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四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商标权属于私权,商标侵权也应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但鉴于商标侵权行为自身的特点,商标侵权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根据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不同,二者对主观过错要求不同,我国《商标法》第52条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一)项是关于直接侵权之规定,均未要求主观过错,故商标直接侵权适用无过错原则,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二)项之规定属于间接侵权商标侵权之规定,要求“故意”,即间接商标侵权要求行为人主观过错,必须为“故意”,故在商标侵权判断中应对不同行为要求不同主观状态,准确认定。
以上是商标侵权相较于一般民事侵权的共性与特性,但仍未揭示商标侵权行为的具体构成要件,有学者认为其包含三个要件:第一,行为人行为未经商标权人同意。第二,行为人在商业上使用特定的标识。第三,行为人的标识使用行为可能导致混淆[1]。笔者认为此种概述较之普通民事侵权构成要件,更加契合商标侵权的概念,同时这些要件构成本身即结合了一些制度,将商标许可使用、合理使用等排除在商标侵权范围之外,防止了商标侵权过度扩张,但笔者认为该种论述并不是很全面,下面笔者将对之具体展开和补充论述。
(一)未经商标权人同意
商标权属于私权,商标权人有处分自己权利的自由,若“商标权人同意”他人的商标实施行为则当然不构成商标侵权行为,而是授权合法使用行为,这是当事人私法上的合意对违法的排除。在我国,商标权人同意一般表现为“授权使用契约”,即指我国商标法上的许可使用制度,指商标权人在一定期间内授权他人使用该商标,自己收取报酬,被授权人在法律或契约所订立的条件下使用该商标不构成对商标权的侵害。故“未经商标权人同意”是商标侵权的直接前提要件。
(二)行为人在商业上使用该标志
“商标”之“商”意为商业性的,“商标”意指商业性标志,商标所代表的区分作用及商誉是商标权人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竞争优势,对商标权的侵犯应为对商标权人商业竞争利益的损害,若个人仅仅于口头诋毁商标权人商标并不适用商标法之商标侵权之规定,而应适用民法一般规定寻求救济。
国外很多国家在规定商标使用时即规定了此使用行为必须为商业上的使用,如《美国商标法》第1114条第1项(a)规定“在商业中将已注册商标的任何复制品、伪造品……用于与任何物品或服务相关联的销售、销售要约、分配或广告中……”注册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2]。及(b)“……企图在商业活动中用于与任何物品或服务或相关联的销售、销售、销售要约、分配或广告中……”第1125条(B)项将商标的非商业化使用排除出民事诉讼范围。
英国《商标法》第10条对于“侵犯已注册商标权”中(1)、(2)、(3)项中的侵权行为规定中均限定了“在贸易过程中”,在(4)项对“使用”的界定中也为“该物件是被有意用来作为商业凭证配用在货物上或用来包装货物的,或是有意用来为货物或服务做广告的……”
虽然近年来商标侵权越来越严重,各国都出台了一些严厉措施加大商标权保护力度,打击商标侵权行为,但此并不能成为商标权无限扩张的理由,我国《专利法》、《著作权法》中都有对权利进行限制的条款,而我国《商标法》却鲜有规定。毫无疑问这种私权的无限扩张会侵犯公众权利,必须对商标权进行限制,一般来说对商标权的限制包括合理使用及非商业性使用。非商业性使用主要包括新闻报道及滑稽模仿,新闻媒体对事实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是宪法赋予的一种言论自由权,当然若严重失实批评不当构成新闻侵权;滑稽模仿则重在突出了模仿与模仿对象的不同[3]。若将商业性使用作为商标侵权构成要件则可将类似行为排除出侵权行为之列,从而平衡商标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
我国《商标法》中没有对商标使用是否为商业性使用作出界定,仅在《商标法实施条例》第3条规定了“使用”的含义,但也仅仅从客观表现上来说明的,这种立法与商标法理论及国际立法趋势是相悖的,故建议我国《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中应增加商标使用应为“商业性使用”之内容。
(三)行为人的标识使用行为可能导致混淆或其他商标商誉损害
混淆,指公众可能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错误认识,将冒用者的商品或服务误认为是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或认为二者存在隶属、赞助、许可关系等,混淆包括现实混淆与可能混淆[4]。防止混淆成为《商标法》保护的重点。
将混淆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重要标准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商标功能上。如前文所述,商标具有来源区分作用和表征商誉作用,商标的价值来源于商标标识与特定商品、服务的紧密联系,而如果发生混淆则割断了此种联系,干扰了有效信息的传达、破坏了商标区分来源的基本功能。另外商标表征商誉的功能作为商标的根本功能将在下文中作具体的阐释。
第二,国际趋势上。世界各国多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
(1)德国。《德国商标法》第14条规定:“使用一种标识,该标识由于其与商标的相同性或近似性并且由于商标和标识所涵盖的商品和服务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而存在引起公众混淆的危险,包括易于令人将该标识与商标加以联想的危险”视为商标侵权行为[2]195。
(2)美国。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规定只要在商业上使用任何文字、词组……或虚假错误的标记、事实陈述于商品、服务或商品容器上,“可能造成他与他人直接存在从属、联系或联合关系,或者其商品、服务或商业行为来源于他人或获得他人支持或赞助的混淆、误解或欺骗……”便可构成商标侵权。
(3)TRIPS协议第16条规定“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应有专有权来阻止所有第三方未经其同意在交易过程中对已经获得商标注册的货物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的货物或服务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标记,如果这种使用可能产生混淆,若对相同货物或服务使用了相同标记,则应推定为存在混淆的可能”。
第三,我国的司法实践。从我国司法实践看也有许多法院直接将是否导致混淆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依据。如2003年陈某诉成都某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中,陈某注册了“老坛子”图文商标后将其许可重庆某食品厂使用,被告成都某食品公司生产的方便面“统一巧面馆老坛酸菜牛肉面”内的调味料包装袋上印有原告相似的“老坛”及图商标,二审法院认为陈某商标无商业性使用及有市场影响力的证据,而被告使用该商标时间早于原告注册时间,一般消费者将成都某食品公司酸菜调味包误认为是陈某生产的或陈某许可生产的产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尚不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因此不构成对陈某的“老坛子”商标专用权的侵犯[5]。
我国《商标法》第52条以列举的形式列明了几种商标侵权行为,但都是对行为的描述,而无具体行为程度、性质、后果的规定,即无“致公众混淆可能性”之规定。《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一)项有“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虽有有关混淆之相关规定,但一方面此种条款仅规定了一种侵权行为,作为对《商标法》第52条第(五)项之补充,且“误导公众”与“导致混淆可能”在含义上确有程度确定性上的差别。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条也有“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误导公众”、“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等字样,但其不足之处亦同《商标法实施条例》之规定,且其第9、10条关于商标相同、商标近似,第11条关于类似商品、类似服务之判定均以是否导致误认或混淆作为判断要件,这实际上颠倒了行为关系,犯了目的工具倒置的毛病,有些人认为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此绝非“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是明显的逻辑混乱问题,商标侵权判断中应将商品相同、相似作为混淆的判断因素,而绝非将混淆作为商品相同类似的判断要件,因为首先“相同、相似”本身即含难以区分、难以辨认之含义,而单列的侵权行为只是列明行为并非所有此类行为都构成侵权,应对行为性质、后果进行限制,此处应加“混淆的可能性”这一限定条件。
此外在商标、商品相同相似中,“易于混淆”只可作为参考要件,关键还在于商品服务本身的商品学意义上的区别性,而在判断侵权行为构成时,“混淆可能性”则为非常重要条件甚至是关键要件了。
鉴于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近似商标不必然构成混淆,与混淆可能也不仅限于相同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二者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故建议立法应将混淆可能性作为主要的判断标准,仅以在相同、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相同近似商标作为其典型行为样态。
此外,混淆虽然是判断商标侵权的重要理论,成为判断侵权行为构成与否的关键点,但混淆仅是从商标区分来源功能着手,并未说明商标本质功能——表征商誉的受损性。即将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用于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服务上,此时由于驰名商标经营范围的限定,一般消费者也不会对此产生混淆,此即为驰名商标淡化的情形,淡化分为两种,若此种使用行为只是一般商品服务时仅冲淡了该驰名商标与商品之间的特定联系,如“海尔”商标用于水果糖、面包等会冲淡“海尔”商标与电器的关系,此为弱化;若将该驰名商标用于与驰名商标商品或服务相悖、性质相反的商品或服务上,会使得驰名商标本身形象降低,如“芭比娃娃”用于成人用品,会损害芭比娃娃作为儿童玩具本身的健康、纯洁形象,上述情况若完全按照传统的商标混淆可能性理论很难界定为商标侵权,因传统混淆理论以消费者的混淆可能作为判断标准,而上述情形并不符合,但若不将其作为商标侵权行为则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它严重损害了商标商誉。
在美国对驰名商标的淡化保护主要规定在联邦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欧盟则将反淡化规定纳入“商标法”的范围,日本则既以商标注册保护形式将驰名商标保护纳入商标法,又以不正当竞争形式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故很多学者试图从国外立法中吸取经验,试图从普通商标与驰名商标区分上入手,在我国《商标法》中建立混淆与淡化的两个侵权判断标准。
笔者并不赞同此“两重标准”的保护模式,个人认为完全可以用“致人混淆可能或其他商誉损害”来做统一规定,以“侵害商誉”作为“致人混淆可能性”的补充与概括。理由如下:
第一,商标权保护的本质是商誉,商标侵权判断本质应以商誉受损为基础。
商标是商誉的表现形式,商誉是商标的内容,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6]。商誉即企业给顾客的商业信誉,这种信誉有可能为消费者认同接受、赞许,即积极商誉,也可能为消费者反对、摒弃、厌烦,即消极商誉,故商誉应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当然侵犯商标权中商誉一般是指积极商誉。商标权保护并非对商标标识的保护,而是对企业经营、良好管理、优良品质、特殊气质等商誉的保护,对商标标识的保护只是对商誉载体的保护。
日本学术界对商标权保护本质是商誉形成一致意见,强调商业标记与商品之间的联系,强调对商业标记的保护是对于该标记所体现的商誉的保护[7]。故一切侵权判断标准都应着眼于商誉的损益性,无论商标混淆或商标淡化均为对商标商誉的一种损害。关于商标混淆对于商誉之损害前已有论述。商标淡化中弱化为侵权人不正当的利用了驰名商标的商誉,即使消费者清楚驰名商标权人不可能经营该商品,但仍可能会对该商品怀有一丝好奇心,而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关注无疑能为驰名商标侵权使用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玷污”则是指对驰名商标“商誉”赤裸裸的践踏,“香奈儿”香水代表的本是高贵、优雅、纯洁等商品及企业形象,若用于洁厕或杀虫商品上,该形象将会大打折扣,商誉也从而贬低。故商标“淡化”也仅仅是侵害商誉的另一种形式,完全可以将其纳入“侵害商誉的其他行为”中去。同时将商誉是否受损作为商标侵权的概括性判定标准也可以将形形色色的各种复杂商标侵权行为区分排除,如商标反向混淆、贴牌加工等,只需判定其是否侵犯了相应的商标商誉,避免了复杂的定性争论。
第二,引入驰名商标淡化制度不符合我国现行商标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商标法》中关于驰名商标认定、审查等很多规定还处于一片空白状态,此时若将驰名商标淡化引入则现行商标制度设计会存在较大的滞后与不足。孔祥俊教授认为我国《商标法》修改草案中引入《欧共体商标条例》中有关商标淡化的规定不足取,因反淡化保护是对商标保护范围的一次重大扩张,不仅已突破现行《商标法》保护范围,打破了既有的利益平衡,也超过了TRIPS协议的要求[8]。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一方面国内驰名商标数量泛滥,另一方面驰名商标远未达到可适用反淡化程度,即使作出该制度规定很可能不具有真正够格的驰名商标而使该制度处于闲置状态,要么将不适格商标获得超额保护力度,加剧商标权私益与社会公益的失衡[9]。
第三,仍应将混淆作为主判断依据,“商誉受损”只可作为总体补充概括性规定。
虽然“商誉受损”可概括“商标混淆可能性”与“淡化”之情形,其虽具有概括性但往往也具有难以判断性,究竟是从专家、消费者角度判断还是从法官角度判断?笔者认为不同角度可能会有偏差,不若规定其具体的判断方式方法,而因混淆仍是商标侵权的常态,不妨将之规定为实践中易于操作的标准,即从消费者与潜在消费者角度的“混淆可能性”之主观判断标准与“其他商誉损害”之补充概括标准。
第四,此判断标准可以将合理使用之情形排除在外。
商标合理使用指未经允许,基于正当目的使用权利人的商标不必支付对价的合法事实行为,该行为不构成侵权[10]。
合理使用分为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叙述性使用实质为对商标构成之词汇的叙述性使用,它是着眼于商标的第一含义的使用,不同于商标的“第二含义”,如“青岛啤酒”中“青岛”是作为第二含义使用的,而“青岛双星”等之“青岛”是一种行政区域上作为地名意义的使用,是第一含义的使用,因此种使用行为不构成混淆,故可将其排除在侵权范围之外。指示性使用指为使一般公众了解与产品有关信息而允许在善良公平条件下指示性使用他人商标,如标注“大众”汽车维修点等以“大众”来标识服务对象,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在服务商品上使用。
现代社会国际条约、各国立法也很多都将合理使用制度纳入立法中,如“TRIPS协议”第17条,《日本商标法》第26条,美国《兰哈姆法》第33条,《德国商标法》23条,《欧共体商标条例》第23条等均对此作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商标法也规定了合理使用,其23条第(一)项规定:凡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称、形状、品质、功用、产地或其他有关商标本身之说明,附记于商品之上,非作为商标使用者,不受商标专用权之效力拘束。纵观各国之规定,商标合理使用应具有的要点为:
(1)非商标意义的使用。使用他人商标标识非借用该商标本身的显著性或商誉,而是描述意义的使用。
(2)客观上不会造成混淆。使用他人商标以不贬损他人商标显著性、商誉为限,若造成混淆此种使用即为贬损了他人商标之价值。
(3)公平善意的使用。即使有些不会造成混淆之情形,若故意贬损玷污他人商标也构成商标侵权。
合理使用商标要保护的是竞争者正当的描述其产品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因其利用而遭到损害,这要求使用人必须出于对自己产品描述之必要使用,不应利用他人商标价值为自己服务,更不得玷污他人商标。
从逻辑上讲,合理使用构成要件中本身即含有不造成混淆可能性之内容,故若以“混淆可能性”作为侵权判断标准,似乎合理使用制度已无专门存在之必要,但笔者认为可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判定之原则,同时规定法定的合理使用之情形。即将原则性与列举性相结合的立法体例,使那些明显不具有“混淆可能”之法定情形排除出“混淆可能性”的复杂判断中,即使其因明显合法而免受违法判断之累。
我国《商标法》并无合理使用之规定,仅在《商标法实施条例》第49条中规定了商标叙述性使用之规定,且情形单一,对于指示性使用则只字未提,故建议我国《商标法》第三次修改细化叙述性使用的内容并增加“指示性使用”的内容。
[1]邓红光.商标法的理论基础——以商标显著性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04.
[2]卞耀武.外国商标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2003:33.
[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59.
[4]绍兴全,顾金焰.商标权的法律保护与运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冯小青.引起消费者混淆是商标侵权判断的唯一标准——陈某诉成都某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C]//商标侵权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194.
[6]刘晓军.商标淡化的侵害对象研究[J].知识产权,2000,(1).
[7]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商标法专利法修改专题[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454.
[8]邓宏光.中国商标法律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3).
[9]邓宏光.从公法到私法:我国《商标法》的应然转向[J].知识产权,2010,(3).
[10]刘瑞霓.如何界定商标的合理使用[J].中华商标,2002,(3).
[责任编辑:刘 庆]
Macro Analysis of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YINXiao-jing
In modern society, trademark infringement phenomenon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how to judge whether a behavior constitute trademark infringement have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both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uild the macro frame work system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judg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on the real meaning of trademark owner, the nature of trademark using, the essence of trademark tort, and defines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trademark infringement, tries to clarify and distinguish what is trademark infringement by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hit the infringement behavior, maintain good brand order.
trademark infringement;macro analysis;confusion possibility;goodwill impairment
DF523.3
A
1008-7966(2013)05-0077-04
2013-06-26
尹晓静(1986-),女,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
book=80,ebook=85